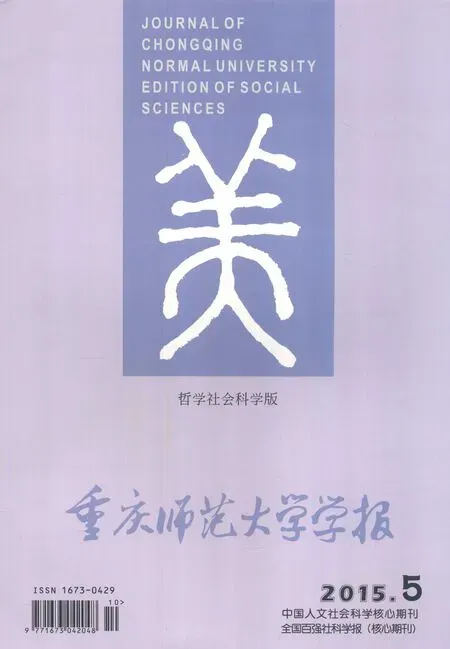更化與歸化
——略論秦王朝治域下的巴蜀
劉力 王小華
(1.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重慶400047;2.重慶市輔仁中學,重慶400066)
更化與歸化
——略論秦王朝治域下的巴蜀
劉力1王小華2
(1.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重慶400047;2.重慶市輔仁中學,重慶400066)
在戰國諸侯爭霸謀求一統天下的過程中,巴蜀因其獨特的戰略地位以及豐富的物產而為秦王朝所認知與重視。在據武力吞并巴蜀之后,秦王朝先后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諸方面對其加強治理,施行更化。此舉措不僅保障了秦在成就其帝國霸業的過程中擁有巴蜀這一大后方,而且亦推動巴蜀民眾對秦中央政權的認同與歸順。
秦王朝;巴蜀;社會治理;認同
早在先秦,巴蜀與中原商周王朝就有著不絕如縷的聯系,不僅甲骨文中有商王武丁及其夫人婦好征伐巴方之記載,[1]199而且史書亦載有巴蜀參與武王伐紂,“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2]2。且“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2]2。然終因地處偏遠,故巴蜀在其時始終屬于“外夷狄”之列,“有周之世,限以秦巴,雖封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2]27這一狀況在隨后秦統一大業推進過程中得到改變。
一、秦統一霸業視域下對巴蜀的認知
隨著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展開,西戎之秦經過商鞅變法,國力大增,逐漸呈現出統一六合之勢。在秦與楚角逐以推進其統一霸業的過程中,巴蜀因其戰略地位和富有的物產尤為秦所重視。
秦惠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巴、蜀相逐,巴遂向秦請兵伐蜀。秦惠王擬欲發兵于蜀,然又恐其“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意欲先伐韓,后伐蜀,又“恐不利”,一時間“猶豫未能決”。[3]2281遂交由張儀、司馬錯論之。立足于統一霸業的推進,在秦君臣內部引發了一場是先行“南下”巴蜀亦或“東進”伐韓擒周的戰略爭論。[4]
張儀認為,蜀不過“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故主張先行東進伐韓,認為這樣可以盡早實現“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的“王業”。[3]2282
司馬錯則認為,巴蜀不僅在物產上“其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而且就戰略地位而言,“水通于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2]29,故主張先行伐蜀。在司馬錯看來,先行南下控制巴蜀對于秦實現統一霸業更具有戰略意義,為此,他向秦惠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愿先從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3]《張儀列傳》,2283
司馬錯分析比較秦在其時“南下”占據巴蜀與“東進”伐韓擒周的利弊。認為首先南下占據巴蜀不僅有“禁暴止亂”的道義之名,而且還可以獲得“利盡西海”之實,尤其還可避免諸侯警覺,“諸侯不以為貪”。相較于“攻韓劫天子,惡名也”的東進之策,“南下”巴蜀可謂“一舉而名實兩附”。
司馬錯的主張得到秦王認可,“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3]《張儀列傳》,2284秦遂借巴人所請之機,起兵伐蜀。當年十月即定蜀,更蜀王號為侯,并派陳莊相蜀。次年,“(張)儀貪巴道之富,因取巴,執王以歸”[2]3,秦又一鼓作氣吞并巴國。
秦在據有巴蜀之后,遣張儀游說楚背齊親秦,以期破壞蘇秦所倡導的東方諸國合縱抗秦之策。在向楚懷王的進諫過程中,張儀著重闡發了已為秦所有的西南巴蜀對楚國的戰略威脅: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關,扦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3]《張儀列傳》,2290
張儀此番游說,一方面是一種認同,即認可了巴蜀對于秦實現統一霸業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則更多的是一種實力上的宣告與彰顯,是“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后,輕諸侯”[3]《張儀列傳》,2284。
其后的歷史進程果如張儀所言。在據有巴蜀之后,秦以之為后方戰略根據地,不斷向南向東出擊,逐漸侵蝕并吞楚國之屬地。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在楚國奪取黔中郡不久,秦國就一次令“司馬錯派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為黔中郡”[2]29。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3]《秦本紀》,213。公元前277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3]《秦本紀》,213。在蜀郡守張若奉命伐楚的過程中,張若僅以巴蜀的兵力就攻下了楚的巫郡、黔中之地,并設立秦的黔中郡。到秦王嬴政統治時期,巴蜀已經成為秦穩固的大后方,有力支持了秦統一霸業的實現。
巴蜀在秦統一霸業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早為人們所認知。宋人郭允蹈就在其所著《蜀鑒》一書中總結了巴蜀對于秦“一天下”的重要的戰略作用:
秦并六國,自得蜀始。……秦既取蜀漢中,又取黔中,則斷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勢孤矣。劫質懷王,操縱予奪,無不如意,于是滅六雄而一天下,豈偶然哉,由得蜀故也。[5]1秦著力于對巴蜀的爭奪,占據,近人徐中舒先生認為其乃勢所必然:
秦因與楚爭天下,所以必須奪取巴、蜀和漢中,進而奪取黔中、巫郡,占據楚的大后方,居高屋建瓴之勢,對楚國形成嚴重的后翼包抄。[6]216
隨后,更有學者從秦東進以期實現統一霸業的整體進程予以分析,認為奪取巴蜀是秦實現統一霸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戰略階段與戰略目標:
秦東進態勢大抵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以后實力增強的秦人在東向正面向以魏國為主的三晉發動進攻,旨在奪取河西地、攻占函谷關,以取得完整的對東方有利形勢;第二階段,主要是秦惠王時期,秦人由于東進乏力,而其在東方又占據了有利形勢而閉守有余,從而開始了南進爭奪巴蜀;其三則是秦昭襄王到秦王政時期,秦人由于獲得了巴蜀地緣縱深與對楚的有利態勢而迫使楚人一再東移進而全面展開對東方諸侯的吞并戰爭。[7]
上述學人的論述,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在秦統一霸業的過程中對于巴蜀的倚重,也從另一層面論證了西南巴蜀在秦統一霸業的推進以及最終實現的過程中所發揮的戰略作用。
二、秦王朝對巴蜀的治理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秦在全國的統治雖然只有15年(前221-前206),然伴隨其從僻居西隅的一個諸侯國至統一大帝國,秦在巴蜀地區的統治卻長達110年(前316-前206)之久。在此百年間的前四十年,秦對于巴蜀的統治主要是圍繞著其謀求統一霸業的軍事需要而展開的,充分依憑、鞏固巴蜀的戰略地位;其后的七十年,則更多的是圍繞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對巴蜀進行治理與更化,從而使得巴蜀最終成為秦王朝較為穩固的大后方。
首先,實行開土列郡,將巴蜀納入秦王朝“中央—地方”的行政格局之內。
秦滅巴蜀后的一段時間內,根據巴蜀不同的社會狀況對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將郡縣制實施于巴,“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置巴郡”[2]29,另一方面卻又在蜀地保留對其君長的封位,三封蜀王后裔為蜀侯以統治蜀國故地。之所以如此,有學者以為此乃其時蜀地還存在諸多大姓,他們的勢力強大,利用這一方便的權力系統比較切合實際。[8]318此后,隨著秦在蜀地統治的漸趨穩固,加之三個蜀侯先后叛秦而被誅殺,秦遂于蜀地亦設置郡縣,后“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2]30,此約為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5年)。
秦在巴蜀故地共設置了巴、漢中、蜀三郡。較之于先前邦國分封的世襲,實行郡縣制后的巴蜀郡守均由秦王直接任命,對秦王負責。與此同時,秦還在巴蜀之地仿照咸陽修筑城池,構筑營建新的政治經濟中心。在蜀郡,置有成都、郫縣等城。“儀與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休整里阓,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2]29在巴郡,筑有“江州”城,“其中心在朝天門、望龍門、千廝門,上至小什字之間”[9]。這些“與咸陽同制”城池的修筑,使之既是統治者居住、統治的中心,又是工商業薈萃的繁華鬧市,更是控制巴蜀廣大地域的軍事重鎮。郡縣制的施行,不僅加強了秦政權在巴蜀之地的統治,且隨著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發展,亦有助于巴蜀民眾對于秦政權的歸化與認同。
其次,實施“世尚秦女”“爵比不更”的政治恩寵與賦稅從輕的經濟優待之策。
在依據武力占據巴蜀之后,為了充分利用并發揮該地的戰略地位,秦在該地實行較為優厚的政治經濟政策,以示優寵。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鏃。(《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此處,秦對于“君長”的巴貴族保留了其對本族的相當支配權,并給予“世尚秦女”的恩寵。而對于巴地民眾,則是統一享有“爵比不更”的優待,“不更”為秦二十級爵中的第四級,巴民統一享有且可以以之抵罪,這較之于其他區域的民眾而言,無疑更是一種特殊的優待。
除卻“世尚秦女”“爵比不更”此類政治上的優待,秦對巴還施予經濟賦稅方面的優厚政策。對于巴人頭目,每年平均出賦二千六百一十六個“半兩”錢,而巴民戶則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鏃。依照云夢秦簡《金布律》可知,八尺為一“布”,八丈二尺為十又四分之一布,而“錢十一當一布”,共折合錢一百一十三個。而關中居民則是“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比較之下,巴人每歲要少繳納八十七個錢。此外,巴人每歲交三十鏃雞羽,也就是繳納三十支夾于箭桿尾端的野雞翎,這對于以漁獵為主的巴人并非難事。[10]109
此外,在秦人與巴人關系糾紛的處理上,更是明顯的給予巴人以偏袒,“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以鐘”[2]4。這是秦在巴地推行的羈縻政策,旨在保持該地區的穩定。
其三,加強對巴蜀之地的水利建設,注重經濟開發,縮小與中原間的差距。
除了實施政治恩寵、刑罰從輕、賦稅從輕的這些優待外,秦政權還注重對巴蜀的開發。早在秦昭王時期,任命李冰為蜀守,從而拉開了開發巴蜀的序幕。“(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簡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2]30
秦對于巴蜀的開發,不僅縮短了其與中原地區的差距,而且“隨著秦對西南邊地的開拓,巴蜀內地經濟對周圍邊地的影響空前強烈,開始孕育以成都為核心、巴蜀盆地為內圈,輻射整個西南地區的巴蜀經濟區”[11]245。而巴蜀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更加鞏固了其作為秦統一霸業戰略后方的地位,同時也緊密了巴蜀民眾與中原民眾的聯系。
其四,通過移民加強巴蜀與中原的融合,進而推動巴蜀民眾對于秦政權的認同。
秦入主巴蜀后,為加強對巴蜀的控制,同時也是政治斗爭的需要,對巴蜀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長達百余年的移民運動,將大量中原民眾、豪戶、罪犯等強行遷徙至巴蜀。
周赧王元年(前314),隨著秦先后滅蜀、巴,遂以巴蜀“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2]29。在秦吞并六國后,始皇將一大批富商大賈如趙國卓氏、山東程鄭遷到南陽、巴蜀等邊遠之地。“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杰于蜀”[2]32。“(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實之。”[2]35此外,“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3]《呂不韋列傳》2512。呂不韋因與嫪毐叛亂有牽連,秦王政賜呂不韋書曰:“其與家屬徙處蜀。”[3]《呂不韋列傳》2513呂不韋為秦相國,其門下“士至食客三千人”,“食客”“舍人”等一大批文化人,應在遷徙之列。
秦王朝實施的這些移民盡管很大程度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但是這些移民的到來,不僅開啟了秦帝國對西南巴蜀的開發序幕,同時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巴蜀民眾的構成,有助于巴蜀與中原的融合與同化,推動著巴蜀民眾對秦政權的歸化與認同。
三、巴蜀民眾對秦政權的認同
隨著秦政權對巴蜀的大力開發與治理,巴蜀得以快速發展,這不僅縮短了西南巴蜀與中原地區在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同時也推動著巴蜀民眾對以秦政權為政治象征的中原文化的認同和帝國認同。
其一,巴蜀“夷人安之”。
自秦在巴蜀分置郡縣,從而將先秦獨立的巴、蜀方國納入秦中央集權的行政序列之中。這不僅加強了巴蜀與秦中央政權的聯系,也促使巴蜀民眾對中央集權政權的歸順與認同。
前已述及,秦滅蜀、巴之初,也曾繼續三封蜀王后裔為蜀侯統治故地,然三個蜀侯均因叛秦被先后誅殺,此后秦方于設置郡縣,“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2]30。幾任蜀侯的相繼反叛說明在秦初入巴蜀之時,其地民心并非心甘情愿的臣服。此后,秦加大對巴蜀的開發以及給予“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的優惠政策,甚至是“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以鐘”的偏袒。
不僅如此,李冰在治蜀的過程中,為了加強與當地的融合,曾建有三祠——瀆山祠、江水祠(江瀆廟)、望帝祠以祭祀蜀神。李冰如此舉措,一方面是欲以之說明他與蜀神有著特殊關系,以之獲得蜀人的認同與支撐。另一方面,李冰代表著秦王朝,作為一個外來統治者,是秦國勢力統治蜀土、秦文化統治蜀文化的代表。但是其通過大祭蜀神,使蜀人意識到李冰已經接受了蜀文化,這樣,由秦國派來的統治者,就轉變成了蜀地民眾認同的首領。
秦的這些羈縻之策的確收到了預期的成效,在實施上述政策之后,史載“夷人安之”[2]4,“置守張若而定黔中,繼用李冰爾始平水患,蜀自是安寧”。“安之”,“安寧”不僅是巴蜀社會秩序的安定,更是巴蜀民眾對秦中央政權歸順與認同的寫照。
秦末戰亂,原東方六國再次烽煙四起,社會秩序大亂。而唯有原秦國腹地關中、漢中和巴蜀卻較為安定平和,既沒有爆發反秦的農民起義,更沒有出現守將郡守們的叛亂倒戈。對此,有學者指出,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在于:“百姓在心理上形成對故國的認同,不易滋生反叛意識。因為這里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沒有打亂,所以在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七年之久的動亂里成為最穩定的地方也最容易統治的地方。”[4]
其二,巴蜀“染秦化”。
秦政權在巴蜀采取的諸多措施,尤其是直接遷入大量移民,這不僅極大的促進了巴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更是促進了巴蜀文化與西戎之秦所帶來的中原文化的融合。在此進程中,以秦為政治象征的華夏語言、文字系統、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逐漸對巴蜀產生極大的影響,巴蜀民眾不僅在日常生活,甚或在文化習俗上都漸趨“染秦化”:
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杰于蜀,資我豐土,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居給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結駟連騎,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設太牢之廚膳,婦女有百兩之徒車,送葬必高墳瓦槨,祭奠而羊豚犧牲,贈襚兼加,赗賻過禮,此其所失。原其由來,染秦化故也。[2]32-33
“染秦化”的出現,更多的是一種由隱形到顯性的潛移默化的結果。這種日常習慣的改變乃至風尚的變化較之于政治上的認同,社會秩序的“安之”而言,是一種更為深層次的改變與接納。這種“染秦化”不僅增進了巴蜀民眾與中原華夏族群在心里上的親密度,而且也加劇了彼此間的趨同乃至認同。
其三,巴蜀族群身份的華夏化。
隨著“華夷之辨”的出現,春秋戰國時期,普遍把分布在中原周邊的民族或族群視為“外諸夏”的蠻夷戎狄。在這一視域下,僻處西南的巴、蜀即為西南夷。這種劃分,除了文化優劣的區分外,也包含著情感心理上的排斥。與此劃分相對應的是,被視為“外諸夏”的巴蜀有著異于中原文化的悠久而獨立的文化始源。其淵源甚至“肇于人皇,也殊未可知”[12]。在戰國晚期秦滅蜀以前,巴蜀文化雖與楚文化和秦文化乃至中原文化有密切交流,但主要依舊是具有巴蜀本土特色的獨立發展。
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對巴、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進行了大規模改造,巴和蜀成為漢文化圈的重要一員。從此才不再被視為西南夷。”[13]與文化上的演變相應,巴蜀的身份亦在發生蛻變。一方面,巴蜀的祖先變成了黃帝后裔——昌意與顓頊,從而在祖源上將巴蜀與華夏列入統一的黃帝祖源序列;另一方面,“西南夷”的范疇變為“巴、蜀西南外蠻夷”,根據“內諸夏而外蠻夷”的傳統觀點,“巴、蜀自然是相對‘外蠻夷’——西南夷的‘內諸夏’,被視為華夏文明在西南地區的代表。”[14]對“大一統”思想文化的接受及其祖源傳說的改變,使巴蜀由蠻夷蛻變為華夏,這一方面顯現了以秦帝國為政治象征的中原文化對于巴蜀的接納,另一方面也顯現了巴蜀對于中原文化的認同,對于中原文化載體的秦帝國的認同,這是較之于政治上的歸順更為深層次的情感心理認同
要之,隨著秦帝國的建立,巴蜀被納入秦專制集權體系的“中央”和“地方”的格局之內。隨著這一格局的完備與強化,處在帝國西南邊陲的巴蜀民眾,不僅“漸漸覺察到‘天高皇帝近’統治秩序的存在”,而且“與遙遠的君王及中央朝廷有了上下一體的感覺”。[15]316-317這種“上下一體”是一種歸順,也是一種認同。
[1]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冊)[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
[2][晉]常璩.華陽國志[M].濟南:齊魯書社,2012.
[3][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
[4]孟祥才.論巴蜀在秦漢統一大業中的作用[J].三峽學刊(四川三峽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94,(2-3).
[5][宋]郭允蹈.蜀鑒[M].轉引自羅開玉.秦漢三國[M].四川通史(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6]徐中舒.論巴蜀文化.古代楚蜀關系[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7]蕭映朝.戰國、秦漢之際巴蜀地區地緣意義述論[J].國學園地,總第446期.
[8]孫華.四川盆地的青銅時代[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9]琦看.古代的重慶[J].重慶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82,(1).
[10]管維良.巴族史[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6.
[11]羅開玉.秦漢三國[M].陳世松,賈大泉主編.四川通史(卷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12]李學勤.蜀文化神秘面紗的揭開[J].尋根,1997,(5).
[13]段渝.先秦漢晉西南夷內涵及其時空演變[J].思想戰線,2013,(6).
[14]張勇.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變遷——巴蜀祖源傳說的歷史人類學解讀[J].史學理論研究,2012,(1).
[15]雷戈.秦漢之際的政治思想與皇權主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Reform and Capitulation——Brief Analysis about Bashu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Qin Dynasty
Liu LiWang Xiaohua
(1.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Academic Journal,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 2.Chongqing Furen High School,Chongqing 400066,Chi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all the feudatory kings vied for hegemony and sought for unification,Bashu was acknowledged and valued by Qin dynasty due to its unique strategic superiority and abundant resources.After conquering the land Bashu by force of arms,Qin Dynasty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its politics,military,economy and society and reformed all of them successively.This act not only guaranteed its occupation of Bashu,a rear area,when building the great empire,but also made the common people who lived in Bashu identify Qin’s central power and pay allegiance to the government.
Qin Dynasty;Bashu;social governance;identity
K27
A
1673-0429(2015)05-0044-06
[責任編輯:劉力]
2015-07-08
劉力(1975—),女,重慶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歷史學博士,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王小華(1974—),女,重慶市輔仁中學,教師。
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秦漢民族文化格局下西南巴蜀的地位》(項目編號: 15SKG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