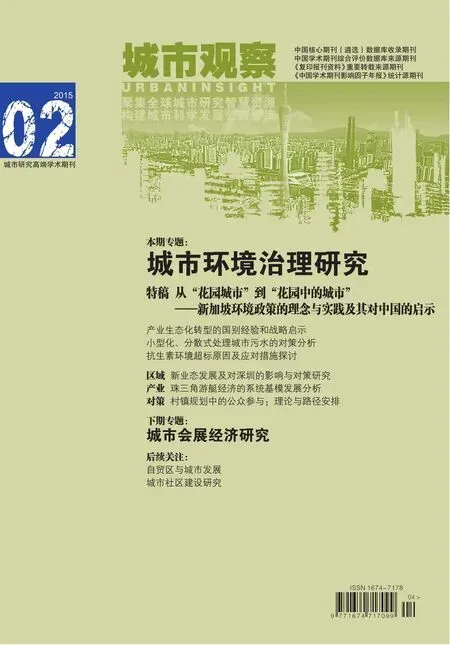后現代主義視角下廣州城市文化研究
◎ 傅蜜蜜
一、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
后現代的產生是與二十世紀中后期社會運動的對話,如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反文化運動、普普運動。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受現代西方各種思潮、流派的影響,如結構主義、存在主義、浪漫主義、虛無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批判理論等[1-2]。后現代伴隨著文化霸權的危機,經常被描述為對社會敘述的質疑,意味著解釋社會的架構,例如宗教、科學、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進步啟迪的迷思或其他的理論家企圖解釋所有生活的局面[2]。后現代主義的“后”(post),體現出的是與現代主義(modernism)時間上的先后次序,和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但是并不是指在現代已經結束之后才興起的一個思潮或文化發展的方向。而是在現代社會里面所興起的一個“文化的”后現代,尤其是文學、藝術,乃至于社會的思潮。后現代并不是現代的結束,而是現代的延續、加深,也包含某種斷裂。因此,“現代”和“后現代”之間,表現在時間、空間上的“先后持續”、“相互重疊與交錯” 、“斷裂性的間距”的三重復雜關系結構[3]。
1.從社會的文化特征方面來看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全球化帶來的多元化價值追求與判斷,以實用主義和功能主義為特點的美式文化生活也開始讓人反思。現代主義所帶來的標準化、精英化和中心化日益受到質疑或挑戰。后現代主義思潮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新形式”,比如傳統的制造業被服務業、金融業、文化產業和信息等產業所取代。這也促成了傳統的以階級為核心的政治格局向基于族裔、性別等的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的政治”轉變[4]。后現代主義精神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動,是一種反智主義思潮(antiintellectual)[5]。其興起和盛行是站在現代主義之上,對現代主義風格的挑戰并否認。
后現代主義強調多元的主觀性(而不是非黑即白,非西方即東方,非男性即女性),強調社會認同是不分性別、種族、階級、年齡的,如公民權、女性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等等。與現代主義單一的主體不同,后現代主義強調介于主體間的差異性,同時注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性[2]。由結構主義所展示的多重不確定性(indeterminancies)和虛無主義的普遍內存性(immanences)[6],主導反中心化觀點并解放了多元化的可能性。因此,不確定性和多元性成了后現代社會的文化特征。
2.從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來看
現代主義推崇的是精英主義(eliticism)和差異化/分化(differentiation),相信人文精神的不變本質、理性思維的中心觀點。后現代論述和實踐往往被視為“反現代的涉入”(antimodern interventions),表現出與過去一切斷絕關系,積極性否定并拒絕現代意識形態、風格與實踐[7]。對此,后現代主義弘揚多元主義(pluralism) 、折中主義(eclecticism) 和去差異化/去分化(dedifferentiation),以創新、多元化的價值中心思想來重新對待發生在社會中的人和事物。瓦解了精英與大眾文化間的邊界,是一種反本質、消解正統中心地位的文化,提倡多元、流動和異質性。
3.從對城市的態度來看
現代主義表現的是疏離和排拒;后現代主義展現的是雙重態度,即除了批評之外有擁抱,致力刻畫城市的多重面貌,并與前衛運動中的未來主義呼應,歌頌都市文明[8]。
二、后現代主義與城市文化
大凡要討論“后現代”,似乎總須從“文化”這個層面入手。德國哲學家施本格勒(Spengler)曾說,所有偉大的文化都誕生城市,世界的歷史就是城市人的歷史。其實“city”的拉丁字源“civitas”就是從拉丁文“civis(公民)”這個字延伸出來的。所以呼應施本格勒(Spengler)的說法,是城市中的人記錄流傳了城市的文化,這些人的思維操控了城市的文化。城市是一種文化形態,是鮮活的人類文化的載體和存在方式[9]。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時尚的符號,是民族與歷史的記憶,是城市人格價值的訴求。認識一個城市就是要認識這一城市的文化與文明。
后工業時代,文化呈現出同質化的傾向,卻又同時創造著自身特色。文化與地域風格在全球化的地球村中越來越雷同,受到交通便利、大眾媒介傳播的影響,廣州、首爾、倫敦、舊金山都有許多相似之處,如相似的快餐、商店、現代建筑、快捷的居民生活。如何在全球同質化的文化版圖上占得一個富有自身特色的、不一樣的席位,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和城市發展的新課題,基本目的皆在創造城市文化風格、增加知名度、吸引觀光人潮、并建立自身的城市品牌以增加經濟效益。存在主義有自我表現的強烈欲望,后現代主義的城市文化體現在一系列非同一般的文化符號上,各種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的碰撞現象。如滿街混搭的時裝秀、街頭擁吻的情侶,以及隨處可見的媒介和充滿活力的藝術匯展等,表現存在主義的歌劇、電影、海報、建筑也比比皆是。
三、后現代主義廣州城市文化
廣州市民文化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始終影響并主導市民的生活,這是從世俗的生活空間里生長出來的本土文化。廣州市井生活頗為精致,其中“飲茶”最具代表性。一杯清茶、幾碟點心、三五好友、幾小時的時光,便是早茶、下午茶和夜茶(俗稱“三茶”)的全部內容。長期的“飲茶”習慣導致廣州人見面便問“飲茶未”?把喝茶稱為“飲茶”,文縐縐的語言,其實是古代漢語的余韻,著一“飲”字,境界全出。
廣州是一座后現代的城市,廣州的包容性成就于百年前敞開胸懷接納西方文化,這里有現代化的小蠻腰,也有紅磚藍瓦的嶺南風格建筑;有世界各地的美食,也有按傳統工藝制作的各色小吃;無論何種節日,你都可以在廣州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度過。至今,廣州民俗中仍保持有許多古老的習俗,其中有中原漢人的古風遺韻,也有百越古族的特別稟賦,這是廣州魅力所在,畢竟國際化處處相似,只有市井文化才各不相同。從中可以看出廣州文化寬容、務實、開放,以及兼容并蓄的氣度。
城市文化涉及城市建筑、科技、教育、習俗、語言文字、生活方式、價值觀等,現針對廣州后現代主義建筑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切入探討。
1.廣州后現代城市建筑文化
大凡走進一個城市,我們會立即從它的建筑群風格與城市布局中感受到其都市文化上的追求,在其傳統或現代的城市居民生活習俗中領略民族文化的底蘊,在時尚與現代思潮的沖突中感悟時代的文化價值及其多元特性,在無孔不入的產業體系統治中體察城市文明的基礎支撐力。現代建筑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開始時對未來城市的想像,是人道的烏托邦主義者想像的產物。工業生產方式不需要古典形式和象征來說明其正當性,但創造性破壞也給現代建筑帶來危機。
后現代建筑崇尚百變之美、多元之美、新奇之美。后現代的建筑借用各種不同的風格形式,古典的、現代的、后現代的等等,追求形式的標新立異,而不強調其功能性[3]。美國建筑家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逐步總結后現代主義建筑主要表現為嘲諷的古典主義(Ironic Classicism) 、 比喻性的古典主義(Latent Classicism) 、解構主義建筑、新現代主義建筑和奇異建筑。
比喻性的古典主義,基本采用傳統風格作為構思,設計多半處于一半現代主義,一半傳統風格之間,取古典主義的比例、尺寸、某些符號作為發展構思。先鋒藝術與懷舊傳統纏繞交織,服飾時尚與街景空間驟然變換,人文理念與都市建筑在日新月異中返璞歸真,使當代人產生一種莫名而深刻的歷史感和回歸感。古老的建筑語言、封存已久的傳統精神正在被啟封而重現魅力,后現代主義建筑也體現于對歷史古典傳統的某種模仿和回復。大屋頂樓房、雕梁畫棟的牌樓在絕跡多年之后又在廣州悄然興起。廣州具有上千年歷史、古老嶺南文化的沉淀與積累,如中山四路上的廣州騎樓最具其特征,在窄窄的街道兩旁,一幢幢房子被架于半空,底層的房子往里掏空了近兩米,在馬路兩邊便形成了一條自由步行的人行走廊,在其現代性建筑中揉進了古典主義的裝飾,從而讓兩種文化精神與語言在城市的建筑上展開對話。我們可以做個對比,北京建筑是如何的?最具北京特色的建筑可以四合院為代表,氣派、布局嚴整,講究長幼有序。而廣州騎樓體現出了廣州人開放又包容的價值取向。
解構主義建筑的特點是把整體破碎化(解構)。主要想法是對外觀的處理,通過非線性或非常規幾何的設計,來形成建筑元素如樓層和墻壁,或者結構和外廓之間關系的變形與移位。廣州大劇院設計的“圓潤雙礫”,猶如兩塊被珠江水沖刷過的靈石,外形奇特,復雜多變,其獨特的幾何外形設計充滿了后現代主義的浪漫和前衛氣息。大劇場和多功能廳,二者的幾何外形呈石頭形狀,分別被稱為“大石頭”和“小石頭”,其建筑寓意是珠江水流沖來的兩塊漂亮石頭[10]。英國《每日電訊》:“扎哈解構主義筆調下勾勒的流動設計,賦予了廣州大劇院無限靈動。鑲嵌滿天星LED燈的香檳色歌劇廳,不對稱、流線型的雙手環抱看臺,大幕開啟的舞臺流動著撼動人心的樂章。”[10]
另外,廣州的摩天建筑在對高度的追求中,體現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可以通過媒體對新電視塔宣傳的自豪感中呈現出來,如廣州周大福金融中心(東塔)。廣州電視塔的靈氣與“霸氣”,顛覆了廣州建筑界為人熟悉的摩天大樓概念,它恰似中國的武俠傳奇中,各派江湖高手云集的比武較技盛會。甫一現身,便顯現出君臨天下的“霸氣”,足以讓已經盤踞在廣州珠江新城CBD的其他商業建筑臣服。廣州市民稱之為“小蠻腰”,把意義顛覆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
奇異建筑是后現代主義建筑中的一個流派,表面看來,設計師似乎把建筑當作游戲。由米蘭AM Project建筑事務所設計的“廣州圓大廈”從設計到建成都遭到廣州市民的熱議。這座珠江西岸的新地標建筑是廣東塑料交易所總部大樓,有33層高,外形設計是一個圓環,中間帶一個圓孔,樓高138米、外圓直徑146.6米、內圓直徑47米。此“大金環”由于外形酷似一枚大銅錢,因此被網友昵稱為“銅錢大廈”[11]。
2.廣州后現代生活方式
當資本主義以跨國公司的形式,移植到世界各個角落時,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模式也起了重大的變化。這種文化具有雙重性格,一個是消費社會的形成,一個是批判精神的建立。前者依附于高度的商品營銷之中,而跨國企業在背后推波助瀾;后者則是抗拒舊有的主流價值。其實,后現代社會是當一個社會的服務業生產金額超過工業生產時,就已經具有后現代的性格,也就是說金融、百貨、傳播、餐飲、運輸等這些行業的崛起,正慢慢改變著工業革命以來的生活形態。
從工作文化氛圍看,如今的廣州的社會可以發現,工人不再是落魄裝扮,老板也不再是西裝革履。為了爭取顧客的青睞,公司上下都打扮得非常光鮮亮麗。如廣州蘿崗科學城的技術工人也是驅車上班,不再是出身于空氣污染的貧民窟,身份跨界較諸過去還要活潑而更具彈性。
從話語權方面來看,當然后現代對于之前現代主義時“全球性”文明的侵略,紛紛放棄地域性特色的一切進行反思,轉而從自我的根源找尋靈感,開始重視民族、地域性的文化潮流等。2010年,廣州市政協一份關于增加電視臺普通話播音時間的提案,引發了一場關于“粵語存亡”的大爭論。如果粵語沒落,嶺南的生活方式也會隨之改變,人們擔心廣州人到時會因此而集體失憶,嶺南文化再次引發廣州市民的關注。粵語不僅是嶺南文化的載體,而且是維系華人華僑的重要紐帶,是連接廣東與港澳以及東南亞華僑的重要橋梁。隨著廣州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新移民、“新客家”大量涌入,北方文化迅速滲透和浸染,使得嶺南文化的發展空間萎縮,無形加劇了粵語圈的文化焦慮。在廣州城市景觀日新月異、文化舊貌急劇變為商業新顏的今天,粵語幾乎成為了嶺南文化的最后立身之處。
從消費文化來看,后現代反對嚴肅、理性、同時反對失控且或無厘頭,唯一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在一種類游戲的模式中,發展以“享樂”為主的生活觀。后現代的文化消費高漲,以旅游消費為生活中心的模式生存,不愿意過平凡安居樂業的生活。后現代的生活方式就是玩生活,或者說在玩中生活,在玩中尋求新的自由,在玩中不斷的創新。廣州市民對休閑娛樂的需求與重視高漲,開始充分利用消費文化會所提供的休閑娛樂,幾乎一年四季都對泡溫泉熱衷有加。流行文化符號和消費文化,深深影響后現代人的生活模式,人類的精神世界被完全抽離,然后被強行植入許多程序化和時尚的物件,人類開始追求名牌,產生夸耀的“炫耀式消費”。廣州市井文化的平民化根深蒂固,對比內地城市,奢侈品文化在廣州并不是一路順風。像是主要奢侈品牌所在的麗柏廣場和太谷匯分別于2004年和2011年開業,LV1992年已進入中國市場,卻是2004年后首次進駐廣州。由此可看出,這種“夸耀式消費文化”也開始漸漸影響廣州城市文化。
從生活文化氛圍來看,當傳統的身份、階級、名聲次第瓦解之后,藝術觀念也開始有重大的調整。我們可以看到在廣州博物館、美術館、歌劇院、演藝廳再也不只是上流社會的聚會場所,而是向所有的市民階級開放。藝術家可以在街頭、車站、地下通道公開展演,夜游珠江邊往往都會沉迷在二沙島來自各國各地藝術家表演的美妙音樂聲中。現代主義時期所立下的美學典范,慢慢被后現代主義風潮翻轉并顛覆。最近在廣州相當熱門的kinfolk, 倡導一種愛健康愛地球崇尚簡單友情的生活方式,席卷廣州。從快速且刺激的生活中逃離,享受溫暖而樸素的生活,kinfolk在英語字面是指親戚、親近的人們。Kinfolk life則指親近的人聚在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時段空間,物品、料理不需要華麗,也不復雜。強調不再追求財富物質的虛華享受,而是以更樂觀簡約的方式,透過消費和衣食住行的生活美學實踐,享受慢活的簡單生活。最簡單化使得朋友間對話的時間延長,沒有過多的裝飾,催生出一種日常的幸福感。使親友們擁有簡單、樸素的聚會,感受到那種樸素又帶著溫暖感的那些氛圍。
四、結語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雙重浪潮推動下,城市文化的價值觀念、結構和功能發生轉變,城市從現代主義工業文明的集中營轉變為后現代主義的游戲場。后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在多元城市文化的共舞對話中走向兼容共處,在差異性對話中走向普適性的價值建構和共享。廣州自古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又毗近港澳,盡管改革開放后其城市文化都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實際上卻并未真正被這些進口的西方思想與意識形態所觸及。在贏得改革開放的經濟動力之后,廣州現面臨著如何營救城市文化的沉重難題。目前,廣州的后現代化處境其實并不都是正面的,過度的物質主義仍是基于現代發展與成長的意識形態。在廣州,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成為主導的生活、文化形態。在過度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之后,廣州仍渴望快速與不斷的改變,同時也不斷質疑和顛覆著舊有的事物與思想。當代的廣州具備了后現代社會中迅速和不斷改變的特征。未來廣州對“現代多元大都市”的追求,似會面臨一個去西方化、去單一思維的一個現代世界的挑戰。
[1]Hans Bertens,〈后現代主義世界觀及其與現代主義的關系〉摘自Douwe Fokkema and Hans Bertens等著《走向后現代主義》,王寧等譯。臺北:淑馨,1992, P11-64。
[2]Sturken, M. & Cartwright, L(2001). Practice of looking:An 壹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 New York:Oxford. Chapter7,pp237─278.
[3]高宣揚,《后現代論》,臺北:五南,1999.
[4]Eagleton, T., (1996),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1st ed., London: Wiley-Blackwell.
[5]王岳川等,《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P36
[6]Hassan, I., (1987),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7]Best, S. & Kellner, D., (2001), The Postmodern Adventure Science, Technology, &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Third Millennium. Guilford Pubn.
[8]Jencks, C., (1992), “The Post-Modern Agenda”, The Post-Modern Reader, London: Academic Editions,P10-39.
[9]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0]建筑時空,《扎哈設計的廣州大劇院被評為世界十佳歌劇院》,2014-05-28,http://www.ccbuild.com/article-387273-1.html
[11]中國建筑學會,廣州銅錢大廈落成,2014-05-05,http://www.chinaasc.org/news/difangxuehuidongtai/20140505/1022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