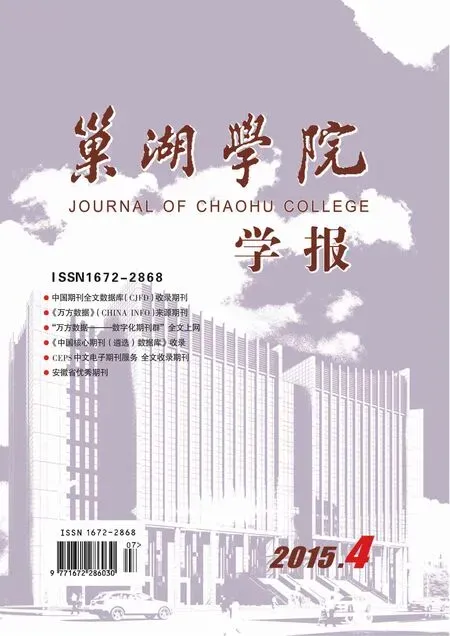新型城鎮化視域下發展小城市的契機與著力點
金 玥 夏 琦
(合肥市行政學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新型城鎮化視域下發展小城市的契機與著力點
金玥夏琦
(合肥市行政學院,安徽巢湖238000)
當前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根本內涵是“以人為本”,重要途徑是發展小城市,推進就地城鎮化,從而有效破解均衡城鎮化難題。因此形成我國小城市崛起的諸多契機和可行條件。文章立足小城市的現實困境,提出要把握好的著力點包括:調整行政區劃,構筑產業體系,推進戶籍等系列改革和謀求生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小城市
1 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演進途徑——“就地城鎮化”
1.1城鎮化演進途徑分析
城鎮化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由農業社會走向發達的工業社會必經的社會變遷過程,也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自然社會演變。其演進途徑有兩條:“就地城鎮化”和“異地城鎮化”。與多數發達國家無異,中國在城鎮化的初期,“異地城鎮化”為主導實現模式。為了擴張早期的城市規模,必然大力推進市政工程建設,在城市顯性及隱性提供大量工作崗位。由此吸引大量農民走出原住地,走向城市,實現城市的規模化集聚。此外,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經濟收入落差對異地城鎮化構成進一步強力推動。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率快速遞增,2012年達到52.57%,基本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但正如徐紹史在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報告中指出,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由此,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指導性《規劃》及時頒布,結合地區特點、多維推進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成為新一輪歷史變遷期的研究焦點。伴隨中國的“大城市病”日益凸顯,在“拉美陷阱”的警示下,大城市難以繼續承受農村人口的大量涌入,然而尚需將5億多農村人口轉移為城市人口。時代命題之下,農民離土不離鄉型的“就地城鎮化”以其內在優勢和獨特魅力,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必然選擇[1]。觀今宜鑒古,美國位列當今世界城鎮化最高水平,二戰后同樣因大城市過度膨脹,轉將郊區和小城鎮設為城鎮化中后期的發展依托,并以其實踐清晰折射出“就地城鎮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1.2新型城鎮化的落腳點與“就地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的落腳點在“以人為本”,這一科學論斷的完全明確是基于對舊型城鎮化的深刻反思。反觀中國近三十年來的城鎮化發展,雖然平均速度高居世界最前列,但粗放的“異地城鎮化”模式已經積淀出許多矛盾和問題。
農民工的非完全“城鎮化”問題。中國快速城鎮化的過程,離不開龐大的農民工人口紅利和艱辛付出。目前流動在城市的2億多農民工及其家屬,已被納入城鎮化率計算范疇,并占據城鎮人口的32.89%。然而由于實質上的戶籍歧視,他們無法均等享有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同處城市中的差異化生活狀況,無疑凸顯了城鄉差距,更易于激化社會矛盾。農民工無法融入城市,自然無法割舍鄉村,于是出現了難以化解的春運難題。
大城市“沉重的負荷”與小城鎮“無奈的衰落”。在近些年政府較少干預情形下,作為增長極的大城市,其極化效應占支配地位,加速度集聚人、財、物和政府的政策傾斜,不斷拉大與小城鎮的經濟發展差距;經濟的兩極分化加速形成人口聚集和產業聚集的兩極分化,造成環渤海、珠三角和長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國土面積,集聚了全國18%左右的人口和全國37%的GDP總量[2]。意味著這些地區以有限的自然物質基礎承載了過高的社會發展壓力,伴隨而來的是環境污染、交通擁堵和住房緊張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亟需發展的小城鎮在缺資金、缺人才、缺項目的窘況下,不斷地衰落。
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的“空心化”。作為農耕大國的中國,“三農”問題位列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決定社會穩定和國家富強。目前"三農"改革的突出“短板”是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明顯滯后于城市化,更滯后于工業化。然而在前一階段的城鎮化進程中,近半數的農村強壯勞動力,尤其農村中學習和創新能力最強的青壯年勞動力紛紛遠離農業和農村,帶來農村“空心化”問題[3]。“空心化”可謂直接導致農業現代化嚴重缺失高素質的農民,即最核心的推進主體。此外,“空心化”引發的多米諾效應直接沖擊農村的 “以人為本”社會發展。
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舊型城鎮化發展模式難以真正打造出宜居城市群和美好鄉村網。因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了對新型城鎮化的宏觀要求,即保持“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四化”同步發展的命題下,“就地城鎮化”必然躍為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推進維度。
2 “就地城鎮化”的戰略實現途徑——發展小城市
2.1發展小城市契合新時代需求
中國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村幅員遼闊、居民分散。在農業現代化剛剛起步,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有限的現狀下,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及公共服務差異仍較明顯,農民依舊會積極追逐城市夢。同時,當前中國保持經濟增長的關鍵是擴大國內需求,城市化正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因此,未來中國需進一步努力推進農民的市民化。然而,因大、中城市快速膨脹引起的資源緊張,在住房、教育等方面的生活成本急劇上升,與小城市相比甚至高達十多倍。對經濟基礎本就薄弱的廣大農民而言,落戶小城市更為現實。況且小城市基本具備城市功能,一定條件下,同樣具備聚集生產和生活的集約化效應。因此,只要能夠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保障進城農民的基本生計,小城市自然能夠成長為城鎮化進程中的重要新極點。
毫無爭議,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重點要“以人為本”,要側重城鎮的內涵性發展,就是要讓城市居民能夠在就業、生活及居住條件各方面獲得更好的綜合收益。處于初級開發階段的小城市雖然暫時的硬件條件尚待完善,但多數在環境、交通和居住等方面具有天然良好的基礎條件。人文生態方面,小城市重視親情和特色文化的傳統仍較濃郁,加上競爭壓力遠低于大城市。因此,不斷發展的小城市,以其安逸的生活、適宜的節奏等生活質量重要指數,與精英匯集、競爭激烈的大城市相比,具備特有的優越性。進而在未來分流大城市人口和吸納鄉村人口上,必然產生強大的內生吸引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2013年在四川德陽和河南舞鋼兩個地區進行的農民城鎮化意向調研發現,兩地農民在選擇城鎮化的理想地時,96.4%青睞附近的小城鎮和縣城;另據清華大學經濟社會數據中心同年進行的全國性大樣本調研證明,尚有絕對數量的生于50-70年代的外出農民工計劃返鄉就業,并定居臨近縣城[4]。
結合數據分析和知網核心期刊許鈞為作者的文獻分析,筆者又進一步從209篇中選取141篇核心期刊作為研究語料。其中翻譯活動29篇,翻譯理論、翻譯批評和翻譯方法分別為23篇、7篇和5篇,文學翻譯、《紅與黑》和《追憶似水年華》分別為12篇、11篇和10篇,翻譯學科13篇、翻譯過程8篇,翻譯家和翻譯工作者分別為8篇、5篇,通過歸納和梳理發現:許鈞近年來研究的熱點大體劃分為翻譯活動、翻譯理論、翻譯批評、文學翻譯、翻譯主體、翻譯學科等,具體結果如下:
2.2發展小城市基于可行性研究
廣大農民“就地城鎮化”的必要條件是,有大批小城市完成快速發展,從而具備更高程度的人口承載和吸納能力。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接連打造出從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到中三角及西部成都等系列經濟增長極。在增長極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交互作用下,以上區域極點的突進發展自然引發其輻射面的連帶發展,具體表現在輻射區域的小城市迅速崛起。即便發展相對遲緩的中、西部地區,近幾年在中部崛起和西部開發等國家戰略下也不斷跨越發展。因此,全國百強縣的格局被逐年刷新,從2010年至2014年,中、西部的席位從22席迅速增至31席。折射出不同的經濟地理條件下,各地小城市仍舊可以并日漸快速發展。進一步解析小城市的發展機遇,可以發現從國家的宏觀環境到小城市的微觀競爭力,合成了大批小城市即將崛起的充分條件。宏觀環境而言,東部大城市必須加大產業梯度轉移,“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又將開局,以及交通信息等技術的深刻變革和運用,為小城市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從微觀競爭力而言,眾多小城市從基礎設施、優惠政策、公共服務到產業載體都在不斷優化,不斷營造吸引企業“落地”,構筑城市產業體系的優良內在環境;不難預想,在這些充分條件下,大批小城市的紛紛崛起,鑄就了農民就地城鎮化的現實基礎。
回顧世界城市化的發展歷史,發達國家與較發達國家都紛紛經歷了小城鎮振興過程,德國最為典型。德國在城鎮化過程中,按照“小城市”配合“多中心”的發展理念,形成82個10萬人口以上的中心行政區,吸納德國總人口的30%;其余1900多座小城市,分布均勻、設施完善、經濟發達,人口規模多在2000—10000人[5]。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拉美的城鎮化陷阱,一度拉美的農村人口以爆炸性速度流入以首都為主的少數城市,形成“超火城市”的同時,也致使一系列的“混亂城市”問題。尤其是這些涵蓋經濟、社會乃至環境各方面的問題在拉美國家大城市均普遍存在卻長期難以解決[6]。
3 發展小城市的若干著力點
3.1科學調整行政區劃,集聚小城市發展能量
行政區劃是便于國家機關進行行政管理的國家結構形式,其區域劃分的主要參數包括地域經濟聯系、地理條件、民族分布、歷史傳統、風俗習慣、地區差異、人口密度等。由于行政區劃具有歷史連續性,因此歷來調整和變更不明顯。然而區劃結構終究與經濟發展緊密關聯,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地理經濟及傳統行政區劃均日漸束縛一些地方的發展。于是近年來,上海、天津、沈陽包括合肥等大、中城市都通過“撤市設區”“撤縣設區”等形式,陸續進行了大手筆行政區劃調整。在城市的發展空間和規模得到明顯提升的條件下,這些脫穎而出的大都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不斷展現更新、更強的城市競爭力,而被調整區域社會發展也進入更高層次的水平。
聯系到以縣為主體的小城市,卻發現中國的小城市呈現出多、小、散的主要特點。以縣級市為例,全國僅有45.2%的縣級市面積在2000平方千米以上,且大多分布于人煙稀少、地域廣闊的西部地區。而中、東部的小城市往往由于城區規模小,城鎮布局凌亂,輻射帶動能力弱。在小城市規模局限的狀況下,城市建設資源有限,建設水平普遍較低,不具備招商引資方面的吸引力。在僅有求發展的主觀意識,缺乏客觀條件的困境下,縣域經濟特別是二、三產業發展滯后,成為小城市發展的 “軟肋”。為了集聚小城市發展能量,推進行政區劃科學調整勢在必行。不妨借鑒成功的城市區劃調整做法,結合各個小城市實際,建議堅持全域規劃的理念,綜合考慮現有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條件,在功能和區位等多方面,構建分層次、分職能的城市空間布局。首先,分拆“小”城市。對于經濟發展相比周邊城市長期弱勢的地級市,依據地理條件和經濟聯系分拆合并至周邊城市,從而融入周邊城市的快速發展,并為其準備必要的發展空間。其次,升格 “強”鄉鎮。一方面,在缺少中心城市地區“撤鎮設市”,賦予“強鎮”更多的發展權限和空間,充分釋放“強鎮”的輻射帶動力;另一方面,將較小的中心城市鄰近的“強鎮”升格為街道,以擴張所屬城市的體量,同時提升“強鎮”的體制;再次,合并“弱”鄉鎮。可以將弱小鄉鎮合并至相鄰的中心城市,進入其城市發展統籌規劃,成為其產業集聚和人口集聚的新基地;對于鄰近無中心城市區域,可以通過合并相鄰的弱小鄉鎮,以中心鎮的標準給予統一扶持、規劃和建設,以整合區域建設資源,培育區域發展中心。
3.2積極構建產業體系,筑就小城市發展支撐
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是小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支撐,是小城市承載吸納能力的決定要素。有了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才能創造出穩定的就業機會、充裕的財政收入乃至優良的公共服務。鑒于不同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城市自身稟賦天然不同,不妨立足所屬經濟發展區域,科學定位、規劃產業布局,明確主導產業,最終形成區域內特色產業集群。因此,需要著重三個方面:
其次,優化平臺建設。小城市在發達地區產業梯級轉移的浪潮中,不僅要揚其要素豐裕之所長,更要補其承接平臺環境之所短,以實現轉移產業在小城市能壯大、能集聚和能提升。由此,一要優化各類產業園區的基礎設施等硬件保障;二要優化從公共服務、市場秩序直至行政效能等各方面的軟件保障;三要優化必要的土地、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總之,以不斷優化的成長環境,引導和支持產業轉入和快速發展。
再次,發展現代農業。小城市脫胎于農村,根基是農村,于是其轄區農村的發展水平,極大程度上決定其城鎮化總體水平。而農村發展的根本途徑在于農業現代化,并且必須從地域實情和農業發展實際出發,構筑城鄉產業或聯動、或互補的一體化機制。首先,以小城市的特色產業為基礎,不斷延伸關聯性現代化種植、養殖等產業鏈條;其次,積極引導發展與城市構成互補的休閑農業、生態農業等;再次,穩步引導“互聯網+農業”進入生產方式、組織方式的深度變革。
3.3大力推進各項改革,突破小城市發展瓶頸
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意味著小城市的城鎮化必須同時考慮人的自然聚集和物的硬件提升。因此,形成于城鄉二元結構下的傳統慣例,以及關系各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通行規則,都需要通過創新性改革,實現突破性發展。
首先,改革“戶籍制”,實行“居住證制”。傳統的“戶籍制”對流動性日益增強的城市人口來說,無法有效落實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只有結合居住證制度進行常住人口管理,并統籌提供包括“非基礎”類公共服務,才能讓身居城市的人充分享有可能的權利,提升在城市永續生存與發展的能力;而且可以穩步儲備城市發展必需的人力資源,甚至可以成為調控城市特色產業的重要方式[7]。
其次,創新土地流轉機制,發展集約經營。土地流轉讓農業由傳統向現代轉型,農民由一產走向二、三產業成為現實可能。然而,全國各地在土地這一要素的流轉實踐中,也遇到“有流轉無集約”等困境。因此,選擇并創新科學的土地流轉機制尤為關鍵。政府不僅需要為公司與農戶搭建流轉信任平臺,鼓勵農戶以土地入股折換企業收益,同時需要引導并支持公司與農戶構建市場機制和塑造產業品牌。最終實現品牌價值對土地價值和產業價值的規模提升。
再次,導入多元共建機制,啟動社會資本。不斷完善并提升基礎設施供給水平是小城市城鎮化進程中的重點任務,而無論國際經驗與國內的嘗試都證明,公共私營合作(PPP模式)可以使基礎設施的建設達到效益最大化。因此,不妨在市政供水、垃圾處理等投資較大、收益穩定、權責清晰的項目上,科學設計PPP模式,對社會資本開放。通過激發社會資本活力,合力政府財政資金,形成城市多元共建機制,從而解決城市建設的資金難題。
3.4科學規劃城市發展,謀求小城市生態城鎮化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飛躍進程中,生態與經濟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發展速度級差,甚至少數城鎮的生態環境已瀕于健康的邊緣。由此,生態城鎮化成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目標。這里的“生態”就是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城鎮化的過程中去,是要將循環經濟理念融入三次產業、居民消費乃至生活居住各方面。由此,城市發展的科學規劃、建設與管理,成為實現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所在。
首先,注重城市生態規劃。城市規劃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先導,因此建設生態型城鎮必須明確城市發展的中長期生態規劃。必須準確測定城市的資源承載能力、環境容量和生態適宜度,從而制定最佳的城市生態位,科學開發空余生態位[8]。不同的小城市還應立足各自實際,以國家環保部的要求為準則,結合生態學的原理,打造風格各異的小城市。以實現城市環境與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之間的協調共生與科學發展。
其次,加強城市生態建設。發展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都是城鎮化的必要手段,于是不僅原有的城市生態基礎顯薄弱,而且未來的城市生態需求被放大。只有構筑堅實的環保基礎設施、科學的生態建設項目和完善的環境安防體系,才能有效支撐起現代城市的生態維護。城市生態建設還要突破局部思維,加強相關城市間的生態聯動。彼此充分發揮資源和條件優勢,積極承擔環保義務和責任。
再次,強化公眾生態理念。屬于公共產品的生態環境,若想根本規避公地悲劇的發生,必須強化公眾的生態理念,才能保證生態建設成效和生態文明發展。為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各類媒體,強化生態環保主題宣傳;一方面必須加快制訂和完善地方性生態環保法規,強化環境保護的法律監督。從而,培養廣大公眾的節約意識和環保理念,引導各類企業的節能力度和減排實效。
[1]喻新安,谷建全,王玲杰.新型城鎮化引領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203.
[2]黃延信,張海陽,李偉毅,等.農村土地流轉狀況調查與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1,(5).
[3]劉田喜,方亞飛.農村城鎮化的現實選擇:就地就近城鎮化[J].農村工作通訊,2013,(17).
[4]李強.主動城鎮化與被動城鎮化[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
[5]王鵬.城鎮化建設的德國經驗[J].行政管理改革,2013,(4).
[6]孫鴻志.拉美城鎮化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財貿經濟,2007,(12).
[7]秦叢叢.山東省就地城鎮化建設的實踐及啟示[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2013,(15).
[8]趙興華,詹國輝.論新型城鎮化發展中的生態路徑選擇[J].商業經濟研究,2014,(22).
OPPORTUNITIES AND KEY POINTS OF DEVELOPING SMALL CITIES UNDER THE HORIZON OF NEW URBANIZATION
JIN Yue XIA Q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Hefei City,Chaohu Anhui 238000)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urrent China is“people-oriented”.Developing small cities and promoting local urbanization are important approaches,which can effectively crack problems of balanced urbanization and therefore can creat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and feasibl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small cities in China.Based on the realistic difficulties of small cities′,this thesis proposes grasping several key points,including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 building of a sound industrial system,the promotion of reform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seeking for ecological urbanization.
new urbanization;local urbanization;small cities
F127
A
1672-2868(2015)04-0030-05
2015-03-15
金玥(1976-),女,安徽巢湖人。合肥市行政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經濟學。
責任編輯:陳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