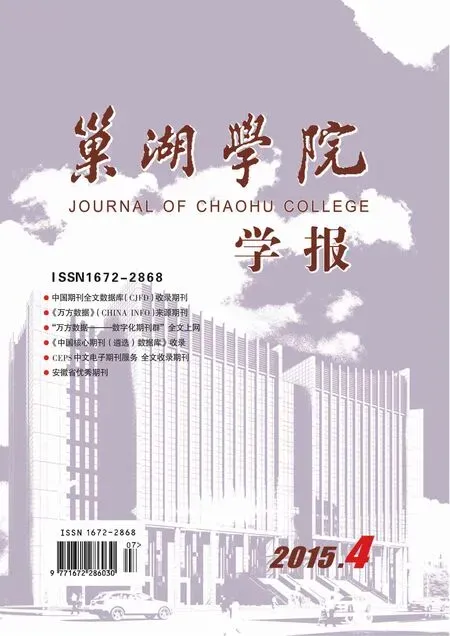金融促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依據與路徑選擇——基于中國一次能源現狀的視角
孫佳燕 金澤虎
(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我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一年多以來,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與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已成為我國建設開放經濟新體制的工作重點,2015年“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將進入實質性進展階段。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建設“一帶一路”遵循“規劃先行,金融先導”的原則。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是能源資源、跨境通道、基礎設施等。能源作為人類活動的物質基礎,掌握著一個國家經濟和政治命脈。能源貿易合作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也是我國“一帶一路”戰略建設的重點。我國的能源生產與消費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近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迅速,對能源的需求量也是與日俱增,對能源進口的依賴程度日趨嚴峻。
1 我國一次能源的基本概況和發展瓶頸
能源有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之分,像煤炭、石油、天然氣、水能等自然界天然存在的能源就是一次能源。一次能源經加工而成的電力、煤氣和石油制品等屬于二次能源。一次能源中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氣是核心能源,且是不可再生能源。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對能源的需求不斷加大,一次能源前景堪憂,亟需樹立正確的“能源憂患意識”。
1.1 我國一次能源的生產與消費狀況
我國一次能源的生產和消費結構與其儲量結構一致,以煤炭為主。從下面表一可知,2001年以來我國煤炭一直占生產總量的70%以上,占消費總量的70%左右;石油占生產和消費總量的比重逐漸下降,至2013年,石油占生產總量的比重跌破10%,占消費總量比重下跌到20%以下;水能、核能、風電和天然氣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

表1 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及構成
我國是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隨著經濟發展步伐的加快,能源生產和消費總量在快速增長。從2001年至2013年,短短十三年,能源生產總量增長約1.3倍,消費總量增長了1.5倍。結合圖1可以看出,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快于生產總量,消費與生產間的缺口不斷擴大,供需形勢嚴峻。

圖1 2001-2013年我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與消費總量圖(單位:萬噸標準煤)
1.2 我國一次能源的貿易現狀
我國是一次能源貿易大國,以出口較為豐富的煤炭,進口相對稀缺的石油為主。但是隨著對能源需求的增加,2012年一次能源進口總量上升到2005年的2.5倍,然而出口總量逐年下降,能源貿易缺口不斷擴大,從2005年到2012年幾年內擴大了2.8倍。由表3可知,2009年我國煤炭進口量大幅度增加,從此進口量居高不下,我國完成了從煤炭凈出口國向凈進口國的轉變,成為了完全的一次能源凈進口大國。石油貿易缺口隨著進口量的增加一直保持高昂的增長勢頭。

表2 我國一次能源進出口貿易總量 單位:萬噸標準煤

表3 煤炭和石油的進出口情況 單位:萬噸
我國一次能源供需失衡,貿易缺口不斷擴大,能源的對外依存度持續上升。2005年到2012年能源進口依存度由12%上升為18.41%。我國能源貿易的進口結構越來越集中于石油,石油的進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到2012年,石油的進口依存度接近70%,面臨極高的能源安全風險。

表4 2005年以來我國一次能源進口依存度

表5 2005年以來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
由上述情況可知,我國雖然是能源大國,但是以人均能源存量衡量,我國的能源存量處于稀缺狀態。然而我國卻是一次能源消費大國,面臨儲量稀缺和消費需求高的矛盾,且隨著生產和消費的缺口不斷擴大,這一矛盾在不斷惡化。究竟該如何解決我國一次能源供不應求且日趨嚴峻的矛盾,我們不凡借助國際貿易的相關經典理論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2 要素稟賦理論依據及其對“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啟示
在所有的經典理論中,要素稟賦理論對“一帶一路”中的能源合作問題具有啟發作用。要素稟賦理論又稱赫克歇爾一俄林模型 (簡稱H—O模型),由赫克歇爾和俄林共同提出,后來薩繆爾森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價格均等化理論對該理論

如圖2所示,A國的要素稟賦點用EA,通過EA點的兩條線和分別表示A國把全部生產要素用來生產X或Y產品的等產量線。B加以完善。該理論通過對相互依存的價格體系的分析,闡述了要素稟賦差異與國際貿易產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國際貿易領域中的支柱理論。
2.1 H—O 模型

要素稟賦指一國所擁有的兩種生產要素的相對比例,是一個相對概念,與絕對數量無關,通常是以人均要素存量來衡量。現以某國A和我國B為例,兩種要素分別是能源和某一其他要素,生產X和Y兩種產品。我國相對稀缺,相對豐富,某國則相對稀缺,相對豐富。X是能源密集型產品,Y是其他要素密集型產品,即X產品的生產所采用的能源與某一其他要素的投入比例,大于Y產品的生產所采用的能源與某一其他要素的投入比例,即國的要素稟賦點用EB表示,通過EB點的兩條線和分別表示B國把全部生產要素用來生產X或Y產品的等產量線。和是A國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兩個端點,用曲線連起來即可得到A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線,如圖3中曲線AA′,同樣連接和兩個端點即可得到B國的生產可能性曲線BB′。相對價格線P表示任意的相對價格水平,與曲線AA′、BB’的切點就是A、B兩國的生產均衡點,對應X和Y兩種產品的供給量。圖中A國均衡生產點對應的X與Y的比值總是大于B國,表明A國的X相對供給大于B國。A國的能源密集型產品供應能力較強,B國則其他要素密集型產品的供應能力較強。
在封閉條件下,供給差異必然導致相對價格差異,A國X產品的價格低于B國X產品的價格,而B國Y產品的價格低于A國Y產品的價格。開放以后,B國因為A國X的相對價格低于本國市場從而進口X產品,A國也會因為B國Y的價格低于本國市場而進口Y產品。A國出口X產品到B國會導致A國X產品價格上升,而B國X產品價格下降,X的相對價格差異不斷縮小,最后趨于一致即達到國際均衡價格。如果加強并不斷擴大出口豐富要素密集型產品、進口稀缺要素密集型產品這種貿易模式,顯然對雙方都有利,一國的稀缺要素密集型產品不再昂貴,可以大量進口以滿足國內需求,優勢要素的密集型產品不再廉價,可以大規模生產出口,實現規模經濟。
2.2 要素價格均等化趨勢
就我國而言,X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而Y產品的價格上升,這必然導致X生產部門的報酬低于Y生產部門,于是和從低報酬的X生產部門涌向高報酬的Y生產部門。但是X生產部門釋放的較多而較少,在生產要素重新配置的過程中,Y生產部門的供過于求,則是供不應求,從而要素市場上的價格下降,價格上升。我國原來昂貴的變的不那么昂貴了,原來廉價的變的不那么廉價了。
隨著貿易的開展,兩種產品的價格差不斷縮小,最終達到均衡。與此同時,要素的價格差異也會發生變化,豐富要素的價格上升,變得不再廉價;稀缺要素的價格下降,變得不再昂貴。兩國要素的價格差不斷縮小,最終趨于一個共同的水平。價格均等化實現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最佳配置。要素出口國充分利用便宜的優勢要素,實現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進口國稀缺要素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替代產業通過要素流動與合作——能源合作,實現能源產業生產成本的下降,從而提升競爭力。
2.3 要素稟賦理論對我國與 “一帶一路”國家能源合作的直接啟示
核心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且分布不均衡,而人類對能源的需求具有普遍性,所以能源的貿易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相對于中亞、西亞和北非等國家,我國能源稀缺,且能源和能源制成品的需求量很大,根據要素稟賦理論,我國應大量進口能源及相關產品以滿足消費需求,不僅如此,進口能源可以降低我國能源的價格,從而降低能源制成品價格,促進能源產品進口競爭產業和相關產業的發展。
在這個靠燃燒能源發展經濟的時代,能源的地位不言而喻,掌控著整個世界的經濟與政治命脈。能源主要分布在中東、中亞和俄羅斯等少數國家,包括美國、日本、中國等經濟大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依靠進口能源解決國內能源短缺問題,能源爭端問題不斷涌現。根據要素稟賦理論的分析,能源貿易和能源產業合作不可或缺,推動能源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能源產業合作是金融支持的重點,那么“一帶一路”真正意義上的能源合作究竟如何開展,這需要我們構建一個清晰的基本框架。
3 金融促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路徑選擇
3.1 能源合作:可以依托的金融渠道選擇
3.1.1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我國提出的亞投行(AIIB)目前正在積極籌備當中,預計2015年年底正式運行,亞投行的注冊資金達1000億美元,按GDP權重中國出資比例最大,總部將設在北京。籌建亞投行自提出以來,便得到了其他國家的積極響應,表示愿意加入并成為亞投行成員。目前,成員國數量已確定為57個,這些國家分布在五大洲。亞投行作為政府間的區域多邊開發合作機構,旨在投資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是其重要職責之一,其運營模式和原則與其他多邊開發銀行基本一致[1]。
3.1.2 絲路基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1月的APEC領導人會議上提出由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用于強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實現全面互聯互通[2]。絲路基金兼具政策性和開發性,習近平主席曾多次強調,絲路基金是開放的,歡迎其他資金的加入。在現行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背景下,絲路基金將按照基金要求運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聯合推動各國家能源合作,帶動“一帶一路”區域經濟發展。
3.1.3 國際其他金融機構
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作為先期啟動資金,應發揮其杠桿效用撬動萬億資金以支持 “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應加強與國際開發性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銀行、世界銀行等)以及國際知名商業銀行的合作,借助其他合作機制實現多渠道融資;此外,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應聯合各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完善銀行信貸體系以擴大資金來源,必要時通過發放銀團貸款對需要大量資金的重大能源項目可予以支持;建立政策性的能源金融機構,為能源企業能源開發和自主創新提供資金支持,同時有效解決能源安全問題[3]。
3.1.4 民間資本
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都是開放的,鼓勵民間資金參與國家戰略建設。民間資本零散量小,但是聚集起來可發揮巨大的作用,如“溫州模式”。運用優惠政策鼓勵民間資本與公共資本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民間資本可以通過 BOT、PE、PPP等方式參與公共投資,其中PPP模式是近年來西方國家流行的一種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方式,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應積極利用PPP模式推動 “一帶一路”建設。讓民間資本與公共資本協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一帶一路”能源合作[4]。
3.1.5 證券市場
擴大證券市場、資本市場融資能力。能源企業可以從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等渠道獲得融資,如發行融資債券、能源債券等,提高融資比例;鼓勵能源企業擴大上市規模,扶持企業境外上市,一方面可以通過股權融資,提高企業擴張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資本市場的監督和規范,改善企業運營模式,提高盈利水平,最終促進能源產業的發展。同時探索拓展其他融資渠道,如能源信托和投資基金等金融產品[5]。
3.2 金融促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沿線國家及其能源產業選擇
3.2.1 蒙古國及其煤炭產業
蒙古國的煤炭資源相當豐富,開發潛力巨大,已探明的煤炭儲量約有1500億噸。全國探明的煤礦床有兩百多個,正在開采的有40多個礦床。蒙古最大的三個煤礦分別是巴嘎諾爾煤礦、沙林格爾煤礦和戈壁省新烏斯煤礦。有關地質資料顯示,塔旺套勒蓋煤田可采儲量在50億噸以上,是蒙古國最大的處女煤礦[6]。
近年來我國進口的蒙古煤炭量不斷增加,蒙古國已經成為我國最主要的焦煤供應國。2012年從蒙古國進口的煤炭量是2212萬噸,預計2015年煤炭進口量會突破5000萬噸。基于地緣優勢、社會文化優勢和經貿合作優勢,蒙中兩國在能源合作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礎,兩國于2009年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蒙古國政府關于在礦產能源領域開展合作的協議》。在此基礎上,以“一帶一路”為契機,應擴大與蒙古國的能源合作空間、細化合作項目。目前蒙古國由于煤炭企業資金短缺和基礎設施落后,煤炭生產量連年下滑,面臨產業發展瓶頸。應加大對蒙古國煤炭產業的投資力度,作為金融支持的重點。
3.2.2 中亞地區的天然氣和石油
中亞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處于歐亞大陸的中心,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波斯灣與里海聯在一起,中東與中亞一起形成“石油心臟地帶”,這一地帶的油氣儲量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分別高達65%和75%。其中里海探明的油氣儲量分別為328億噸、18萬億立方米。哈薩克斯坦探明的石油儲量可能高達195億噸,天然氣儲量大概4萬億立方米。素有“中亞科威特”美譽的土庫曼斯坦,已探明的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四位,高達22.8萬億立方米。烏茲別克斯坦的油氣儲量分別約為9480萬噸、3萬億立方米[7]。
中國具有天然的地緣優勢,正好處于“石油心臟地帶”中央。此外,中亞地區的經濟現狀不景氣,期待搭“一帶一路”便車,需要國際資本的投入,這為我國與中亞取得能源合作、參與石油和天然氣投資提供了機遇。鑒于中亞各國資金和技術有限,以及對俄能源管網體系依賴性較強等問題。我國在與中亞能源合作及投資時,既要抓重點產業項目,也要開展多方位、多元化和深層次的合作,促進國際能源合作進程。
3.2.3 西亞國家及其石油和天然氣
西亞地區自古以來就被作為全球的交通要道和貿易樞紐,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西亞處于“五海三洲”的中心,在亞、非、歐三大洲的交界處。西亞作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生產、出口和運輸中心,其石油儲量也是世界最豐富的,截止2011年底,探明的石油儲量占全球的比重為48.1%,石油產量和出口量分別占全球總量的32.6%、36.2%。
2000年以來,西亞成為了中國能源資源的最主要進口來源地,中國對西亞能源的依賴性相對較強。以我國與西亞國家的產業互補性為基礎,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深化能源貿易伙伴關系,加強能源深層次合作。利用互補優勢,積極探索兩地能源合作的新模式,以多樣式的合作方式開辟更加廣闊的能源貿易市場,形成多元化、深層次的能源合作局面,共同在全球能源治理方面發揮作用[8]。
3.2.4 北非地區的石油
北非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根據BP公司2012年的數據顯示,該地區的石油探明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4.3%,產量和出口量分別占世界總量的4.1%和3.5%。北非地區包括西撒哈拉地區和其他7個國家,分別包括突尼斯、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蘇丹、南蘇丹、摩洛哥等。
近年來,北非地區動蕩不安,形勢復雜。首先是2010年突尼斯發生騷亂,此次騷亂成為導火線,動亂在整個北非地區迅速蔓延開來。突尼斯、埃及兩國領導人先后下臺,隨后阿爾及利亞等國發生示威游行,最終引發了利比亞戰爭,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被反對派軍隊捕殺[9]。北非是我國主要的石油進口來源地之一,我國與蘇丹石油合作有十年之久,該地區形勢突變必然對我國石油安全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應積極維護該地區形勢穩定,保證能源生產安全,倡導區域能源合作和投資預警機制,維護各方共同利益。
3.3 金融促進“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路徑探索
具體到鼓勵金融機構為能源合作提供融資支持,鼓勵金融機構“走出去”,加快金融機構海外布局,提高為“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服務的能力。我們可以從以下具體路徑尋求突破。
3.3.1 擴大出口信貸,拓寬出口信貸國家擔保制
出口信貸是一國政府為支持和擴大本國大型設備等產品的出口,增強國際競爭力,對出口產品給予利息補貼、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及信貸擔保,鼓勵本國的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本國的出口商或外國的進口商(或其銀行)提供利率較低的貸款,以解決本國出口商資金周轉的困難,或滿足國外進口商對本國出口商支付貨款需要的一種國際信貸方式。對本國出口商提供貸款是出口賣方信貸,對國外進口商提供貸款則是出口買方信貸。在能源合作、高效開采、利用等環節都對機械設備和高科技技術的要求越來越高情況下,出口信貸在能源貿易合作領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我國的能源相關設備、技術比較先進,有效利用出口信貸帶動大型設備、高新技術的出口,不僅促進區域能源合作,還有利于消化我國過剩產能。出口信貸國家擔保制是一國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對本國出口商和商業銀行向國外進口商或銀行提供的延期付款商業信用或銀行信貸進行擔保,當國外債務人不能按期付款時,由這個專門機構按承保金額給予補償。國家承擔出口風險,有效降低非商業風險,由政府牽頭鼓勵能源相關企業擴大能源設備和技術等出口,積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能源合作項目。有效緩解我國能源危機問題,更能發揮我國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領導作用,與能源大國合力實現全球一次能源的可持續發展。
3.3.2 充分發揮PPP模式的協同合作效應
PPP模式是近年來西方國家流行的一種政府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方式,在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應積極利用PPP模式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讓民間資本與公共資本協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公私合營模式(PPP),以其政府參與全過程經營的特點受到國內外廣泛關注。PPP模式將部分政府責任以特許經營權方式轉移給社會主體(企業),政府與社會主體建立起“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關系,政府的財政負擔減輕,社會主體的投資風險減小。充分利用PPP模式獨特的優點,可以有效支持“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基礎設施、設備、運輸通道等建設。
3.3.3 積極創新外匯儲備運用渠道
通過外匯儲備委托貸款等多種方式支持企業“走出去”。我國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其規模位居全球第一。為使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保值升值,外匯儲備委托貸款辦公室就要發揮作用,不斷創新優化外匯儲備運用方式,抓住“一帶一路”戰略機遇,與國開行和亞投行等進行更多的委托貸款,將大量的外匯儲備有效投資到“一帶一路”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合作等領域,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積極投資沿線國家,參與一次能源的開采、加工和合作等工作,切實發揮外匯儲備對“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發展的支持作用。
3.3.4 研究建立融資保險長期制度性安排,強化對能源合作的促進和保障作用。
我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能源合作領域面臨著諸多不確定風險,這些風險可能為企業開展能源貿易合作蒙上陰影,需要政策性保險保駕護航。我國跨境融資保險發展較弱,需要加強“一帶一路”能源領域的貿易保險和投資保險,特別是要發展中長期業務。鼓勵商業保險公司在沿線國家建立分支機構或者與本地保險公司開展合作,為我國能源合作項目提供財產保險、責任保險等保障。鼓勵保險公司與銀行開展合作。在銀行發揮積極作用的地區,都要安排保險公司介入,提供相應服務,改善現有海外投資保險的制度設計和運行,以充分滿足多樣化的金融需求[10]。
3.3.5 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能源貿易與投資中的使用,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人民幣跨境結算有利于降低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和個人的匯兌成本,規避匯率風險,對促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往來將發揮積極作用。[11]繼續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推動人民幣走出去。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人民幣清算和安排,同時加快建設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促進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并為區域內國家相關機構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便利[12]。鼓勵企業參與能源合作、投資和貿易等直接使用人民幣結算。
3.3.6 鼓勵金融機構向能源產業合作提供更多的投融資產品,完善銀擔合作機制。
開發適應實體經濟發展需要的避險產品和風險管理工具,幫助企業有效規避匯率風險。推動“一帶一路”區域內國家的金融機構“走出去”,為多邊金融合作提供支持。我國金融機構要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更直接的為企業參與“一帶一路”能源貿易、投資合作等提供支持,結合項目需求和東道國情況為企業提供服務。開發避險產品和風險管理工具等,幫助企業完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引導企業構建對外投資金融風險控制和防范機制。同時發展政府支持的融資擔保和再擔保機構,完善銀擔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是新興體和發展中國家,為充分幫助我國企業在參與能源合作領域克服各種風險,政府要發揮作用,推動政府機構與商業銀行業務聯動創新。深化商業銀行與信用保險公司、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業務合作,支持融資擔保和再擔保機構,發揮政策性金融擔保和再擔保作用,完善銀擔合作機制,支持商業銀行擴大“一帶一路”能源合作投放力度[13]。
綜上所述,我們的金融機構針對“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支持與促進不僅要在源頭渠道和產業投向上要有宏觀定位,更要在具體手段上敢于拓寬思路、大膽創新,才能讓“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在金融支持與促進的基礎上真正實現中外多贏和可持續發展。
[1]史可,楊為敩.亞投行金融攻略[J].新理財(政府理財),2014,(12):44-45.
[2]周立偉.“一帶一路”金融加碼[J].紡織科學研究,2014,(12):88-89.
[3]何凌云,劉傳哲.能源金融:研究進展及分析框架[J].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9,(5):88-98.
[4]繆林燕.貫徹“一帶一路”戰略 金融支持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建設[J].國際工程與勞務,2015,(3):25-28.
[5]付俊文,范從來.構建能源產業金融支持體系的戰略思考[J].軟科學,2007,(2):92-95+101.
[6]崔健.中蒙能源合作開發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0.
[7]張辛雨.中國與中亞能源開發合作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2.
[8]韓永輝,鄒建華.“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與西亞國家貿易合作現狀和前景展望[J].國際貿易,2014,(8):21-28.
[9]張春宇,唐軍.當前中東北非地區形勢與中國石油安全對策[J].國際石油經濟,2012,(10):16-20+109.
[10]趙志剛.“一帶一路”金融區域化路徑[J].中國金融,2015,(5):39-41.
[11]閆衍.“一帶一路”的金融合作[J].中國金融,2015,(5):32-33.
[12]易誠.進一步加強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金融合作[J].甘肅金融,2014,(4):10-13.
[13]程軍.構建“一帶一路”經貿往來金融大動脈[J].中國金融,2015,(5):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