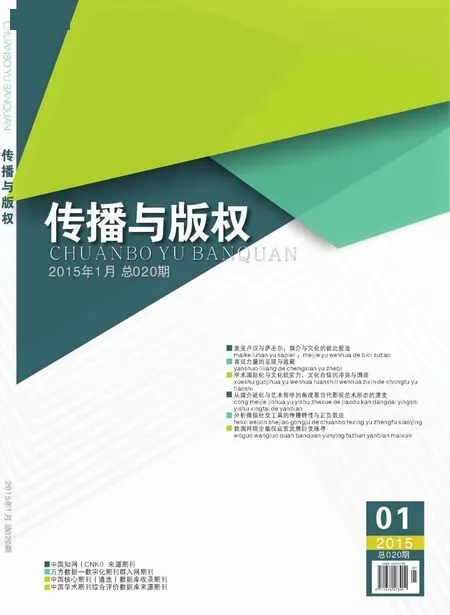突發災難時媒體應對慈善公信危機的報道策略研究——以魯甸地震中媒體“起底”郭美美為例
宋常蕊
突發災難時媒體應對慈善公信危機的報道策略研究
——以魯甸地震中媒體“起底”郭美美為例
宋常蕊
[摘 要]云南魯甸地震后,媒體呼吁民眾“忘記郭美美”,捐款捐物投身抗震救災,卻引發網民反感與斥責。本文通過分析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為今后媒體的議程設置提供科學有效的策略。
[關鍵詞]魯甸地震;郭美美;框架分析;公信危機
[作 者]宋常蕊,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
一、魯甸地震中“起底”郭美美的新聞傳播效果綜述
(一)積極的傳播效果與社會影響
1.澄清紅會丑聞,緩解公信危機。眾多涉及“郭美美事件”的新聞報道都有一個極為醒目的部分,就是澄清郭美美與紅會并無任何關系,郭美美的炫富行為和不法收入更不能佐證紅會的善款外流和監管不力。反觀近年來,紅會丑聞不斷,郭美美炫富事件更是使紅會的公信力跌到歷史最低谷。在人們紛紛對紅會投以懷疑甚至憤怒的目光時,警方深入嚴謹的調查取證確鑿證明了紅十字會在此事件中的“清白”,對于緩解公眾誤會,改善紅會公信形象具有直接而深刻的效果。
2.直面公信問題,督促慈善公開。部分媒體體察到紅會身陷的公信危機,選擇從此切入,直面指出郭美美事件過后紅會應該如何扭轉其在民眾心里形成的刻板印象,深入思考紅會公信屢遭質疑的體制原因。事實上,郭美美在公信危機的漩渦中僅僅扮演了一個助推劑的作用。“沒有多年來日積月累的失信,紅會聲譽不會一朝崩裂;沒有公眾對紅會嘖有煩言,郭美美再拉升仇恨,紅會品牌也會紋絲不動。”①蘇西:《郭美美“倒下”未必是壞事 紅會還需公眾監督》,《中國青年報》,2013年8月4日。公信力的重塑絕不能僅僅依靠郭美美事件的危機公關,如果不能建立信息公開、監督問責的長效機制,所謂的公信重建只能是空中樓閣。這些新聞報道深刻啟發了人們對于紅會公信問題的認識,也代表了督促紅會公開信息、加強制度整改和權力監督的公眾意見,更是為紅會今后的公信改革指出了方向。
3.注重價值反思,肅整社會風氣。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輿論環境中,部分網絡推手不僅不合理運用自己的接近權與言論自由權、理智發聲交換意見,反而利用此次事件,三番五次故意抹黑紅會,致使郭美美事件不斷升溫,以期通過網絡炒作和幕后交易獲取不正當利益。新聞媒體的正面報道也為這些網絡推手敲響了警鐘,一方面有利于社會風氣肅整與道德底線的重建,另一方面也促進了網絡環境的凈化與輿論秩序的和諧。
(二)消極的傳播效果與社會影響
1.過度重視“郭美美”,忽視災情報道。郭美美涉賭被抓正值昆山爆炸與魯甸地震兩大公共災難之際,部分媒體不僅沒有第一時間對于地震災情給予密切關注,卻在此時大規模報道“郭美美”。據中青輿情監測室統計,在8月4日凌晨0時至上午10時,郭美美相關網絡輿情總量及增幅超過云南魯甸地震輿情。在輿情領先的過程中,媒體對于郭美美事件的過度關注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新聞事件的重要程度與媒體報道的議程設置錯位嚴重,導致媒體環境監測功能嚴重缺位,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和人文情懷。
2.“窺私”現象有違新聞倫理。在涉及郭美美的新聞報道中,有“性交易”“開房”“過夜”“性感”等過分暴露的詞語,更有甚者,竟然將“花多少錢和我睡一覺”作為新聞標題,將王軍與郭美美發生性交易的過程描述得極為露骨。盡管郭美美在此次事件中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出現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她的隱私不受到法律的保護。有些調查采訪更是深入郭美美的家庭關系,使大眾自然而然認為郭美美的成長環境必然會導致她人性的扭曲。這樣的報道盡管可以滿足一部分人的好奇心與窺私心態,卻對郭美美及其家人的隱私權與名譽權造成了嚴重侵害,嚴重違背新聞道德和新聞倫理。
3.議程設置過于強硬,造成民眾更深誤解。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程設置”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正值魯甸地震期
間,災區物資緊缺,亟須依靠紅十字會號召民眾積極捐資捐物。主流媒體大量編發、轉發有關郭美美涉賭事件的新聞通稿,運用傳媒的力量澄清郭美美與紅會毫無關系,通過特定的議程設置重塑紅十字會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以期紅會可以重獲信任承擔起組織捐款、轉運物資、協助救援的責任。但是如此刻意且強硬的議程設置引發了民眾情緒極為強烈的反彈,造成民眾更為深刻的誤解與憤怒。
二、受眾對“郭美美”涉賭報道解讀的影響因素
(一)受眾認知的“選擇性機制”假說
卡茲和拉扎斯菲爾德認為,制約和影響大眾傳播效果的“中介因素”主要有四種,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是選擇性接觸機制——包括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三個層次。該機制的存在說明受眾對某些媒介或內容具有回避傾向,而被回避的媒介和內容是很難產生效果的。①郭慶光:《傳播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在郭美美涉賭的相關報道中,更多民眾在閱讀新聞時會有選擇性地注意到郭美美的情感經歷與淫亂生活,而不是隨著媒體議程設置的引導將注意力集中于紅會清白與否相關的議題上。受眾認知的選擇性機制,會減弱媒體報道的傳播效果和傳播影響,無法達到改善紅會公信形象、積極推動慈善募捐的官方目的。
(二)新媒體時代傳播環境的影響
1.受傳界限淡化,信息互動共享。在傳統媒體語境中,信息的傳播者和受傳者界限明確。而社會化媒體的出現,則大大改善了這一局面。普通民眾信息的傳播行為得以從被動地接受信息向主動發布信息、設置議題轉變,而民眾和傳統媒體受傳的角色界限已經淡化,逐步實現了信息的互動共享。主流媒體一面佐證紅會的“清白”,網友卻在另一面不斷爆料著紅會的“丑聞”。由此,慈善機構公信危機的議程設置主體的身份也由傳統大眾媒體擴大為任何使用社交媒體的用戶,人人皆可“揭黑”已然成為新媒體時代的普遍現象。對公共機構和政府機關的公信質疑,也不再因為傳統媒體的把關過濾而湮沒于信息海洋。②龔捷:《大數據時代突發事件的輿論引導策略研究》,重慶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在這種媒體語境下,人們更愿意輕信網絡爆料,更愿意執著地堅持自己的偏見與質疑,而不愿意接受新聞媒體轉述的“官方聲明”。
2.主流權威消解,草根意見崛起。在社會化媒體興起以前,傳統媒體在突發事件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中無疑擁有絕對的權威。傳統媒體的議程設置直接影響到民眾對新聞事件的理解、判斷和輿論的價值取向。然而,出于對媒體建構的“擬態環境”真實性的質疑,民眾越來越習慣于通過社會化媒體參與公共事務,而不是毫無條件地信任官方發出的聲明和權威媒體的新聞。由于主流媒體受制于自身的運作邏輯與管理體制,在公共機構遭遇信任危機的時刻,其本身澄清事實、引導輿論的主流權威正在受到自發形成的網絡輿情的巨大沖擊。
三、突發災難下新聞媒體化解慈善公信危機的建議
(一)優化議程設置,謹慎引導輿論
1.及時切入災難報道,暫緩慈善危機公關。在魯甸地震剛剛發生,災情規模與傷亡狀況尚未清楚時,眾多媒體并沒有及時跟進災情,而是對于郭美美涉賭事件尤為關注,其報道的密集程度以及由此引發的輿情關注度一度超越魯甸地震。這不但反映了新聞媒體對于新聞事件重要程度的誤判,更是其缺乏社會責任違背新聞倫理的具體表現。在突發災難下,新聞媒體必須扮演“社會風險的守望者和預警者、社會輿論的引導者、集體行動的溝通者、不當行為的監督者與社會心理的救治者”③郭小平:《危機認同與電視的社會動員策略》,《新聞與信息傳播研究》,2008年春季卷。的角色,利用傳播優勢實現及時可靠的信息披露,實現災區“缺食補食,缺衣補衣”,才是媒體此刻最為重要的工作任務,也是為慈善事業做出的最大貢獻。
2.內容多元、平衡基調,優化輿論引導的策略。新聞媒體需要從此次事件中得到深刻反思。以旁觀者身份介入報道,須尊重客觀實際,堅持中立的報道立場,不偏不倚,公正無私,端正報道動機,尊重受眾知情權,積極披露相關信息以促進慈善的透明,重塑紅會的公信。平衡報道的基調,不能一味重申紅會光輝的歷史,一味指責郭美美令慈善事業受損,一味批評社會跟風謾罵的炒作熱潮,而是要在回憶紅會光輝的同時正視其面臨的公信危機與監管漏洞,澄清丑聞的同時思考紅會的制度改革與發展路徑,批評跟風炒作的輿情同時肯定民意對于實現輿論監督、推進改革步伐的巨大貢獻。
(二)加強輿論監督,推進慈善制度改革
新聞媒體對于公共組織運用公共權力的監督有著極為深厚的理論基礎與現實基礎,無論是從其監督對象的廣泛性、監督方式的公開性、監督影響的及時性,還是其監督過程的持續性、監督效果的威懾性來看,都使得新聞媒體無可爭辯地獲得了社會輿論監督的主體地位。④朱穎:《新聞輿論監督與公共權力運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回應民眾對于紅會長久以來的誤會與質疑,媒體機構有責任對紅會的善款使用、資金運作的具體情況進行監督披露。對于民間流傳的有關紅會的不實謠言要運用事實和證據予以制止,引導民眾理性、冷靜地看待網絡推手的炒作與網絡謠言的傳播。在監督中發現的問題和不足之處要及時予以公開和批評,對于有關紅會的“丑聞”要迅速調查追蹤、嚴謹核實、及時報道。此外,媒體也應主動配合慈善組織,提供信息交流和公開的媒介平臺,定期
將其經費收支情況、捐助項目進度公之于眾,實現機構內部規范、公開和透明管理。
(三)融合新媒體,實現慈善報道“日常化”
新媒體時代,媒體機構應該利用主動運用新媒體技術,創建新媒體平臺,對網絡上的“微公益”和民間慈善組織進行宣傳推廣,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推動全社會慈善活動的新高潮。媒體除了在突發災難的危急時刻對民間捐款進行緊急動員以外,還應該逐步推進慈善報道的“日常化”、民間與官方慈善互動的“常態化”。媒體機構更應該憑借自己豐富的傳播資源和傳播經驗,積極投身慈善活動的組織策劃中,以“旁觀者”的角色跳轉到“參與者”甚至是“領導者”的角色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