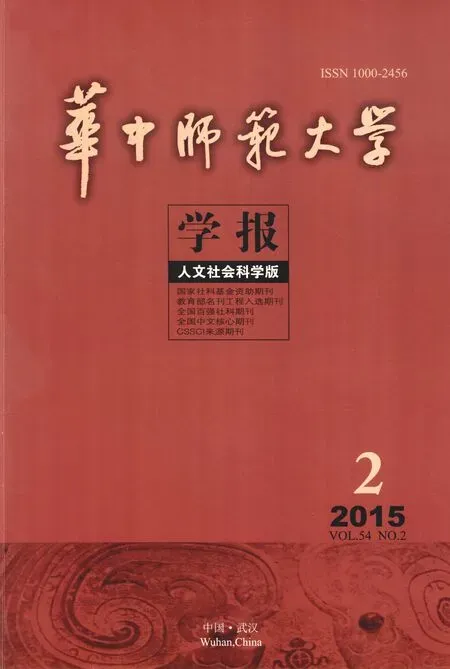國語、漢字、國語文討論的再思考
孫 郁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100872)
今人批評《新青年》的激進意識,不能容忍者殊多。其中之一是對于傳統的背叛,非儒、叛祖,以虛無的態度面對遺產。而最重者,乃對漢字的不恭,所謂廢除漢字的口號,在后來的許多學人看來,是有認知的偏差的。這些其實未必深得要領。細讀那些前輩的文章,并非無端的非理性悸動。
一
在新文化運動之前,許多學人已經開始考慮漢語書寫的改革問題。1892年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提出切音新字的思路,此后,趙元任、吳稚暉等人就思考過文字改革的路徑。拼音化、簡化漢字,已經被學人以認真的態度思考過。但那時還是書齋里的行為,影響還十分有限。讀趙元任早期的文章,關于漢語、漢字的思考都意味深長,如《吾國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國語羅馬字”的方案后來也因他的努力而出籠。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新文化運動是推動漢字改革的重要推力,因這個運動的存在,才使語言問題提到議事議程中,這個近代文化史中的熱點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不斷回味。
白話文運動的本質是語言的表達的問題,它涉及國語、漢字、國語文三個方面。①如果不系統考慮三者的關系,可能難以找到新的表達的途徑。在新文化運動初期,人們對于這樣的話題考慮不周,只是后來才漸漸清晰起來。白話文的提倡,乃尋找表達的突圍,在論及這個問題的時候,胡適提倡白話文于前,陳獨秀、錢玄同等呼應于后,系一代人精神的共振。胡適等人認為,新文化運動要解決“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而文學問題與語言問題是可以在相近的邏輯里解釋的。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卷頭言》中,胡適把文學改良和漢字簡化看成同樣重要的事情。重新認識語言與文字,考量其間的得失,恰是那代人自覺的使命。
就思想表達的奇異性而言,章太炎對錢玄同的影響不可小視。無論在文章學還是音韻學上,都有承傳之跡。章太炎當年的文章變化,與他的學術理念有關。他以古文為基礎的思想表達,隱含著一種寓意,那就是在意象、韻律與節奏方面,與當下精神拉開距離。文章之道原也有內在規律,不應馬虎而敷衍之。與章太炎一樣,他弟子們都不太看得上梁啟超一類人物,因為梁氏缺少精神的亮度,文章還在舊的路上。《新文學與今韻問題》就說:
“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舊氣未盡滌除,八股調太多,理想欠清新耳;至于新名詞,則毫無不合。我以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決非二十世紀時代所夠用;如其從根本上解決,我則謂中國文字止有送進博物館的價值。”③
連梁啟超都不太及格,那中國的文字與文章,則非有大的變革不能解之。章太炎的辦法是向后轉,走向復古之路,在晚清已取得學術上的勝利。不過因為時間的跨度過大,難以與現實對話,自身的局限也顯示出來。章門弟子們大凡擁護新文化者,后來都以為那是一條險路,與大眾的距離甚遠,故沒有誰再沿著此路而行。而面向民眾,從大眾的接受角度與思想普及的角度看,語言文字的通俗化,才是應當考慮的一種選擇。胡適認為,白話文即口語文的一種,需讓百姓喜愛。而文字方面,拼音化之前,簡化字的實行,才更為重要。關于文章之道,則一清如水的書寫,才是應當提倡的選擇。周作人、魯迅、錢玄同、朱希祖等章門弟子,對此是頗為贊佩的。
白話文之所以很快流行,與西方文化的翻譯有關。在交流增多,西學漸進的過程中,漢語表達面對許多問題,如美文不可譯的問題就出來了。如何對接西方的思想,較為準確表達對方的意識,漢語的限度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錢玄同與友人通信時就討論過這類問題。在《關于西文譯名問題》中,他寫道:“弟以為凡用中國字譯西文人名地名,萬難一一吻合。其故因字音之理,母音可單獨成音,子音不能單獨成音,必賴母音拼合,始能成音。中國文字之構造,系用六書之法,與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絕異。”他的辦法是,“竟直寫原文,不復譯音”,而“譯音務求簡短易記”。④可以看出,他們那代人希望從未有的方式里解決翻譯里的問題,是頗有道理的。在漢語里夾雜一些外文,既可保存原意,亦能激活句子,使段落有一種別樣的意味。
在公安、檢察院、法院、監獄、校園、機房等不同領域,安防管理應用有比較大的區別,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會有很多的定制需求提出來,因為涉及具體行業特征的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業務邏輯和管理模式,需要軟件平臺能夠根據行業的特征量身重塑。同時,平臺廠商需要和行業的上級主管部門開展長期合作,將個別用戶的創新需求變成可推廣示范的規范版本,推動成為行業標準,并貫徹實施。
伴隨著文學改良運動,世界語的話題在學界蔓延。蔡元培、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都提倡世界語。連吳稚暉、劉師培、章太炎也加入了問題的討論。早在1908年,吳稚暉在《新世紀》第44號上發表《新語問題之雜談》提出“棄中國野蠻之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較優良文字”。這是主張漢字改革思想的延續,也是走拼音化道路的探索。為什么如此,錢玄同在《論世界語與文學》中說:
日前孑民先生語我,謂用世界語譯撰之書,以戲曲小說之類為最多,科學書次之。是世界語非不能應用于文學也。世人說到“文學”一名詞,即存心以為必須堆砌種種陳套語、表象詞,刪去幾個虛字,倒裝賓主名動,效法“改‘龍門'為‘虬戶',易‘東西'為‘甲辛'”之故智,寫許多費解之怪事,以眩惑愚眾,學選體者濫填無謂之古典,宗桐城者頻作搖曳之丑態。⑤
世界語的理念背后,也與世界主義的思潮有關。相信未來的世界是大同的,不再被民族的封閉語系所囿,打破表達的界限,那就多了幾重夢幻之意。世界語是人造的語言,它與自然語有很大的不同。就交流的便捷而言,是很有價值的創造。但因為沒有歷史文化的背景,信息量相當單薄。就審美的精神傳達而言,自然語的功能是無法代替的。“五四”那代人是創造性強烈的一代,他們覺得人造的語言必將給世界的交流帶來曙光。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語言其實也是一種文化的記憶,倘使缺失了千百年的記憶,詩意與哲思都會有所減輕。文明是綿延性的和發展的,不是斷崖式的決裂可以解之。在后來的文化進化里,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二
主張世界語的普及,思路上受到了歐洲和日本人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與文學的國際性頗有關系。日本學者小坂狷二在《世界語反對文學》中闡述了世界語必然流行的道理。認為人類語言經歷了方言時代,民族文語時代,民族文語與國際補助語時代,世界共同語時代。他以日本語內在的問題為例,談到世界語必然形成的道理。⑥中國的文人與學者與日本人的感覺,在這一點上有共振。說“五四”學人是在世界思潮里反省自己的母語也并非不對。
在開放的語境里建立新的精神表達,改造文章與詞語書寫就有了可能性,也催促了新的文化意識的誕生。比如錢玄同不僅在思想層面討論西化的可能問題,于書寫的形式上亦多有用心。他自己是書法家,卻不滯于舊習,而有一種變革的沖動。我們看那篇《〈新青年〉改用左行橫式的提議》:“我所看見的,第一個改用橫式的是美國留學生所辦的《科學》。后來教育部出版的《現象叢報》,也是用橫式。這兩種雜志,都是講科學的,常有算式表譜嵌在文章中間,用橫式便利,自不消說得。至于別種雜志書籍,既不純粹講科學,或完全和科學不相干的(小說詩歌之類),也是用橫式比用直式來得便利。因為以后的中國文章中間,要嵌進外國字的地方很多。”⑦文章的表達都不過分,所思所想,未嘗沒有道理。后來中國報刊的“左行橫式”流行于今,他的建議都有所應驗,可謂功莫大焉。
錢玄同在自己的判斷里,作了大膽的預言,未來的中國文學,應以世界語為之。這個簡便、可用的新式表達,當在未來成為一種可能。他在《答陶履恭論Esperanto》中談及了自己的依據:“進化之文字,必有賴乎人為,而世界語言,必當漸漸統一;因玄同對于文字之觀念,以為與度量衡、紀年、貨幣等相同,符號愈統一,則愈可少勞腦筋也。”⑧錢玄同的表述流露出的是樂觀之思,簡單化的一面也流露其間。但他的更為激進的說法還在后頭。在《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里他干脆說:
“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除漢文。”⑨
他又說:
“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識,不便于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⑩
不難看出,他的表述是有內在的邏輯的。大凡懂得一點拼音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到漢字與漢語的缺點。現代學者已經意識到,在翻譯英文的時候,因為古語不能對應,遂造出新詞,而中文的單位是字,“英文沒有對等于字的文字符號”?。從這個層面可以看到漢語的一些問題。“五四”那代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影響國人的精神表達,而中國文化的落伍大概與這種載體的落后有關。
應當說,這給錢玄同等人一個錯覺,那就是把漢字假設為一種與現代性不可兼容的存在。它在邏輯的綿密與傳達的精細方面可能存在先天的弊病。胡適、蔡元培也多少抱有類似的看法,他們對于拼音方案的態度和對西方文化的態度,多少說明了彼此的心靈相通。其實漢字有技術功能,也有承載功能。人造語可以解決技術功能,但無法與自然語那樣有承載的功能。錢玄同大概更多從技術的層面討論問題,對于承載的功能思之甚少。在翻譯實踐不多、白話文不得發展,文言文一統天下的時候,他的判斷顯得急躁和脫離語言的規律。在意圖倫理支配一切的情況下,文字的表達的復雜性未得彰明。“五四”新文人那時候的精神困頓和突圍意識里的問題,都給后人留下諸多思考的難題。
三
新文化運動一個重點,是開啟民智。但因為教育普及困難,文字變成了人們審視的對象。不僅國內的學者如此,外國的思想者到中國來,也發出漢字改革的感嘆。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說:“因為中國有這種文字障礙,你們知識分子,不但與歐美的文化相隔絕,并且與你們自己的人民相隔絕。這種障礙,比古代的萬里長城更堅固,比專制君主的野蠻性還要危險。”?美國的杜威來華,也感嘆漢字的難認,“中國無論如何傾向進步,其文字殊足為前途的大障礙”?。這兩種勢力的會合,在民國知識界造成很大的影響。許多作家學者加入漢字改革與中國語文的思考者的行列。爭論也在此間出現。黎錦熙與聶紺弩的看法不同,鄭振鐸和魏建功有別。在討論語言、文字、文章的時候,聶紺弩認為:
不但我們現在的文章,還有濃厚的文言文的色彩,就是我們的語言,也馱著一副死文字的重擔子,局促在文言文的影響之下,使人們養成一種輕視語言、重視文字的觀念,無形中削弱了新的語言的創造的可能。這副擔子,無疑地是由漢字這特殊形態所規定,它將和漢字相伴始終。如果不把漢字根本推翻,決不能把我們的語言從漢字的束縛之下解救出來的。?
可以看出,從白話文的提倡,到文字改革的呼吁,有一個精神的必然過程。那就是尋找新的、適用的載體。人們對于文言文的唾棄,可能是因為其內在的肌理缺少現代性的表達途徑。文言的缺點,可以在白話文里克服,這還沒有引起論者的注意。而漢字的簡化,可能傷害語義表達的內在邏輯,也被漠視了。聶紺弩的思想,直接從錢玄同與魯迅那里來,但一面也簡化了論述的邏輯。他所佩服的魯迅文章,難道不是用這古老的文字所書寫的么?
“五四”前后的知識分子,在啟蒙的激情里的諸種思考,都有歷史的合理性。他們只是在思想的層面追問選擇的可能在何處。不過,在與強大的舊勢力抗衡的時候,主張漢字改革的人忽略了兩點事實。一是民智的開發,要靠社會改良,通過結構的變革,是可以使千百萬人成為使用漢語的主力。二是,白話文還在實踐中,它有與文言不同的功能。錢玄同、聶紺弩所說的漢語的問題,都是文言里的問題。而后來的白話文的實踐證明,外來語可以融匯在口語里,而其內在的彈性是文言所沒有的。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關于語言與文學問題的爭論,顯示了一代人的表達的焦慮。除了世界語的提出外,對民間語言資源的調查、借用也成為研究的話題。這種選擇的價值走向就是由象牙塔走進民間,由古代語走向現代漢語。他們在文學的大眾化的思考里,把文章與文字視為被動的存在,而沒有看到人的思想可以激活古老的文字,從而給新文學注入新鮮血液。思想的鮮活,定可以帶來語言的鮮活,這在魯迅后來的實踐里被證明了。魯迅在晚年延續了早期與錢玄同互動時的思想,比如對漢語不綿密的思考,對于表述的似是而非的警惕,都頗有意義。而他在翻譯過程的新奇句子的創造,不僅文言文不能有此功效,連世界語也難見佳績吧。魯迅在無意中已經以自己的實踐回答了錢玄同的疑問。
我們今天審視那些言論與思想,會感到他們是在一個特定的空間進行對話的。那時,大眾還沒有廣受教育的途徑,社會充滿了不公。他們沒有從社會改造層面意識到改變窘態的可能,而是從文字上著手,以此為突破口,自然有進入歧路的危險。另外,他們意識到人的創造性可以使靜態的文字和文章之道更合乎人類合理的生活。魯迅在《門外文談》里討論過字是誰造的,怎么來的,談到寫字就是畫畫,以及古代文與言的不一致的問題。注意,在這里,魯迅是在文盲甚多的語境里來討論問題的,在這樣的語境里,他的所思所想,也并不過激,還有著許多的道理。
從思想性來講,魯迅認為古書里有許多毒害人的因素,讀了未必讓人聰明。大眾在沒有受到古文污染的時候,以新的文字表達自己的思想,可以保留他們的純真之氣。魯迅說:
大眾并無舊文學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致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里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哪怕你銅墻鐵壁!
哪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么??
魯迅看到了舊文人的問題,也殃及古老的文言文與漢字。這里的情況復雜,人是活的,文字是死的,活的人一定比死的文字更有創造力。故舊文字與舊文章一定被新文字、新文章所代替。不過,文字有自己的內在規定性,這個規定也非死的存在。上面所引的《目連救母》的唱詞,不也是舊文字所書寫的么?我們一方面要看到生活的不斷流動帶來的新的創造性的契機,另一方面也要意識到文字系統與語言系統的超穩定性。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語言文字是有相當的彈性的存在。
其實我們細細分析可以發現,魯迅是把漢語的功能和潛質發揮到極致的人。他對此不置一詞,似乎看輕了自己的智慧。他所言者,乃漢字的局限,或者說,是文言的局限。唯其看到了局限,才有了創造的沖動。因為在寫作過程中,他攝取了日語的元素,也從德文中受到啟發,又能以口語、方言為文,于是漢語的內在的力量輻射出來,給人以奇絕之美。而他書寫過程的章法,乃民國書法的精品,其間有六朝的峻急,亦多宋元以來的疏朗、小巧,古風之中卷出詩意的漣漪,都非一般人可以比肩。恰恰是看到舊的書寫的有限性,才能不隨眾俗,在方寸間現奇氣。我們從這里讀出那代人的苦心。在面對漢字與漢文的時候,他們不是匍匐在其間,而是有超越的渴望。在試圖超越而又無法超越之間,他們的審美維度得以打開,漢語的魅力,也在其間有了自己的展示。
現代漢語與簡化字的出現,是中國人語言自覺的一個標志。在多種語言的交匯中,我們才意識到一個民族的文字、語言、文章之道的路徑如何。日本、韓國、越南、蒙古都有諸多實踐值得我們深思。他們擺脫漢字的過程,留下了語言的難題,對于古老的中國而言,這難題依然存在。不過,在差異里看到共性,也豐富了對母語的認識。語言學家周有光在對比東西方的文字時發現,二者是有對應關系的?。
幾千年來,從來沒有誰敢去懷疑自己的母語的正當性,而“五四”那代人看到了國人表達出現了問題。在新的思想與文化中,文言文失去應對的可能。尋找一種新式的表達途徑與載體,對于他們而言是一種不能回避的使命。后人對漢語的認識,恰是從那個邏輯里發展過來的。自然,其間也有修正,有顛覆,但推動了對于漢語言文字及文章學的認識是無疑的。
四
魯迅對比中外語言的發展史,看到了詞語與文字變遷的可能。他自己想寫一部《中國字體變遷史》,因為忙碌而未能如愿。從字體來看漢字的形態與表達的擴張,有很深的題旨可談。他在夏目漱石、果戈理的寫作實踐里,看到了改變舊的書寫的可能性。在翻譯中,不斷借用西洋的詞匯與句子結構,其實就是改變舊的書寫的努力。不過,魯迅在藝術層面考慮漢語的書寫時,與胡適的現代白話文的理念有別,也和后來語文的現代化要素不同。按照周有光的觀點,語文現代化的內容包括四個部分:一、語言的共同化;二、文體的口語化;三、漢字的簡便化;四、表音的字母化。?魯迅的實踐有的與此相吻合,有的不夠平易曉暢。對于他來說,漢語還有一個智性的問題。如果只是一般性處理思想與知識,難以進入形而上的層面,這是個矛盾。魯迅一方面強調大眾化,一方面又在翻譯中反大眾化,遇到了漢語表達的兩難。后者從思維的層面考慮問題,前者有啟蒙的意義。在表達上,他與胡適、錢玄同差異的根本點,就是既要照顧到百姓的接受,又要在智性上保持高度。變革的時代要兩全其美,其實非簡單的辦法可以為之。
從一個民族的發展史看,語言文字是不斷變化的系統,但也有其內在的規定性。魯迅、錢玄同那代人思考漢字與漢語的表現力,是從變化的需要提出來的。因為是探索性的討論與實踐,成就與偏差都有,一些基本的觀點成為后來學界不能不面對的話題。母語的變化與發展,是靠歷史的積淀方能實踐的。魯迅后來翻譯的實踐,留下很多遺產值得總結。他的實踐多于口號,因為知道自我耕行的重要。表面看來,他們的問題意識在今天被整體的文化理念所否定,但在未來的發展中,未必沒有自身的價值。敢于向母語挑戰的人,可能是最能豐富母語的思想者。我們看看“五四”以來的文章與藝術,那些偉大的存在,多是由善于創新的人們完成的。他們可能一時的表達存有盲點,甚或錯誤,但也是因為越軌的意識存在,才使母語有了無限的生機。經歷了新文化的沐浴與洗禮,我們對自己的文化遺產的珍貴性,定然會有著與前人不同的認識。
注釋
①周作人:《國語與漢字》,《獨立評論》第207號,1936年6月28日。
②③④⑤⑦⑧⑨⑩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頁,第60頁,第12頁,第18頁,第33頁,第99頁,第162頁,第166頁。
⑥吳朗西:《吳朗西文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第288頁。
??周有光:《語文閑談》(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284頁,第357頁。
???聶紺弩:《聶紺弩全集》(第八卷),武漢:武漢出版社,2000年,第13頁,第14頁,第179頁。
?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周有光:《語文閑談》(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