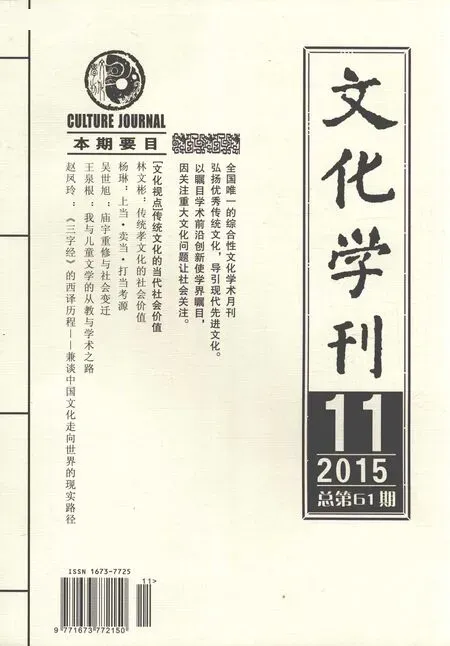廟宇重修與社會變遷
吳世旭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通過物質性的建筑和儀式性的展演,民間廟宇為信眾提供了一個存在意義上的地方,并使其社會生命的形成與延續成為可能,此乃民間廟宇重修的根本原因[1]。1980 年代以來的民間廟宇重修不過是中國歷史中近乎常態的重修廟宇之舉的特殊表現,不僅作為民間信仰復興之后果體現為國家與民間權力互動的文化表征,更重要的是因對民間廟宇之社會生命的重構反過來推動了民間信仰的復興[2],因此,當代中國的民間廟宇重修在本質意義上構成了對傳統的延續,一方面是在地方營造的層次上對存在感的重新確認,另一方面則是在社會重建的層次上對社會性的再度形塑,但是,由于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劇烈變遷的時期,圍繞著廟宇重修的地方營造和社會重建不可能是對傳統的簡單復制,而是在新的觀念形態和制度形式的影響下,具有更復雜的社會機制和過程,并呈現出不同的地方意象和社會表征。本文認為,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族主義的興盛使特定民間廟宇的重修帶有濃重的國族認同的色彩,市場經濟的擴展使其帶有強烈的經濟投資的味道,而相應的政策和行為則使其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民間的范疇,成為一個文化展示或經濟交換的地方,并疊加在傳統的地方意象和社會表征之上;更多的民間廟宇處于國家與市場之下的社會空間之中,在重構自身之社會性的同時,其社會生命也隨著國家力量的伸縮而搖擺不定,與之相伴的則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博弈。
對于1980 年代以來的民間廟宇重修,很多研究者將之歸咎于國家意識形態松懈造成的民間信仰復興的后果。但是,如果放在長時段意義上的社會變遷中來思考民間信仰之命運的話,從“天下”到“國族”的變化對民間廟宇的重修帶來的影響才是更為重要的問題,而國族主義對包括民間信仰在內的民間文化的改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有不同的表現。要而言之,在“天下”時代,傳統國家將民間信仰活動置于“正祀”與“淫祀”的二元框架之中,并給“淫祀”以特定的生存空間,但在民族國家時代,這個空間一度被嚴重壓縮,1980 年代之后又使其具有了一定程度彈性;在這個過程中,民間廟宇也隨著晚清以來的國家政策的變化而具有不同的命運。
從“天下”到“國族”的轉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國族主義是其重要的精神內核之一,并在晚清以來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傳統與現代”的話語形式在國族主義的形塑中成為進行歷史解釋最基本的框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認為:
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天下”的觀念實際上是與儒家的“道”,亦即中國自身主要傳統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的。由于某種原因,當近代中國人被迫求助于外國的“道”時,將國家置于文化亦即“天下”之上,也就成了他們的策略之一。他們說,如果文化的改變有利于國家,那它就應該被改變。[3]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民間文化被納入到傳統文化的范疇之中,成為現代國家改造的對象,以追求和強化國族認同。其間,各種運動構成了這種改造的焦點,從晚清延續至民國的“廟產興學”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破四舊”運動,無不是其集中表現。
“廟產興學”運動與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緊密相關。1898 年,康有為和張之洞同時提出“廟產興學”的建議,其中,前者主張中的“廟產”就直接指向村落淫祠。康有為在“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中提出:
我各直省及府州縣,咸有書院。……而中學小學直省無之。莫如因省府州縣鄉邑公私現有之書院義學學塾,皆改為兼習中西之學校。……并鼓勵紳民創學堂。……查中國民俗惑于鬼神,淫祠遍于天下。以臣廣東論之,鄉必有數廟,廟必有公產。若改諸廟為學堂,以公產為公費,…… 則人人知學、學堂邊地。[4]
“改諸廟為學堂”表面上看是出于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實質上則是政治層面上的新舊更迭之訴求的文化表達,其象征意味遠遠大于革新者的現實考量。其背后所隱含的社會邏輯恰是列文森所指出的變遷之道,對“新”的追求同時意味著對“舊”的改造,盡管康有為并未在國家的問題上走得更遠。
從民間廟宇到現代學堂的轉化體現的是傳統與現代的二元觀念,如果說這種觀念在晚清還有其限度的話,那么到了民國時期,便隨著各種辯論而逐漸深化,“廟產興學”運動在彼時的延續與擴展是其最好的說明,“新文化”運動更是將這種二元觀念推向極致,使其滲入到新國家建設的各個層面。但是,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在不同層面的鋪展也形成了頗為有趣的吊詭,并在知識分子階層對待民間文化的態度中得到集中的體現。一方面,科學與迷信的對立使很多民俗研究者對民間文化持批判的態度,另一方面,新文學與舊文學的對立又使其希望在民間文化中尋找替代性的文化資源,從而使整體性的民間文化處于“肢解”的狀態,甚至抽離其特定的文化要素,用以服務于國族認同的塑造。列文森認為,反傳統者為了唾棄傳統,會將傳統凝固在過去的時空,以示其不合時宜,維護傳統者為了使傳統生生不息,倒是會加以更新和修改[5]。實際上,反傳統者不只是將傳統推向歷史深處,也會在實踐的層面上起到對傳統進行有限保護的作用,而這很大程度上便有賴于對民間文化的“肢解”。“廟產興學”運動固然是反傳統的體現,但卻在客觀上保護了民間廟宇,其作為民間信仰活動場所的地方意象已經被新式教育的場所之意象所取代。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傳統與現代的二元觀念的支配下,對民間文化的“肢解”愈加明顯,并且更突出地服務于國族認同的塑造。在這個過程中,文物保護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文物保護工作對于新中國來說,不僅具有學術研究和文化保護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具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功能。這種功能圍繞著國族認同展開,并主要通過物質文化的展示得以實現。因此,民間廟宇的物質性使其具有了保存自身的可能,尤其是那些歷史悠久、建筑特色顯著的民間廟宇。從1956 年開始進行的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始,每一批次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建筑類均有民間廟宇在列。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對于民間廟宇來說不僅意味著重修資金有所保障,更重要的是獲得了重修的合法性;但是,與之相伴的則是其原有的地方意象不可避免地有所損益。錫伯家廟的重修便充分地體現出了文物保護對其地方營造帶來的深刻影響。
錫伯家廟又名太平寺,為錫伯人南遷至盛京后集資修建的一座喇嘛廟,據“太平寺碑記”記載:
康熙三十六年,荷蒙圣祖仁皇帝施以高厚仁恩,將錫伯部眾分為三批,于康熙三十六、七、八年,遷入盛京,并分置各省駐防效力。康熙四十六年眾錫伯籌集白銀六十兩,購房五間,建立太平寺。自京師虔請甘珠爾經一百零八部,每年四季,集眾喇嘛,誦經不絕,永償所愿。[6]
乾隆二十九年(1764),為了加強新疆防務,清政府從盛京及其所屬諸城調撥一千余名錫伯官兵移駐伊犁,這次大西遷的出發地便是錫伯家廟,從而使其成為錫伯西遷的重要象征。
新中國成立前夕,錫伯家廟停止了其宗教活動,隨后廟宇相繼被太平寺群眾小學、摩托車廠、縫紉機廠等占用,廟宇建筑也大部分被拆毀改建[7]。1980 年代初,隨著國家民族政策的落實和錫伯族眾與相關學者的呼吁,遭受嚴重破壞的錫伯家廟不斷得到修繕與重建,并相繼成為市級、省級和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這個過程中,錫伯家廟的地方意象始終處于調試之中,其主要變化在于,喇嘛教活動場所的意象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而作為錫伯文化尤其是錫伯西遷的重要表征則得到了凸顯。如今,錫伯家廟既是錫伯人懷念祖先、紀念西遷等活動的主要場所,也是進行錫伯文化展示的重要場所。前者的行為主體是錫伯族人,后者的行為主體則是地方文化部門。雖然活動的主體不同,但幾乎所有活動都圍繞著國族主義這一精神內核展開。
盡管文物保護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促進民間廟宇重修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民間廟宇都具有文物的價值,更多的民間廟宇仍然處于民間的范疇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種運動中風雨飄搖,其中“破四舊”運動的破壞性尤大,甚至波及到了作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民間廟宇。通常所言的民間信仰復興,主要是相對于這種“破壞”的歷史而言的。但是,對于作為“破四舊”等運動重要對象的民間廟宇來說,1980 年代以來的重修風潮并非是簡單的國家力量收縮的結果。對于作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民間廟宇而言,國家力量非但沒有收縮,反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正是這種延伸,其重修才是可能的,并且獲得了穩固的合法性,只不過其地方意象有所調適并被賦予了濃重的國族主義色彩。對于其他民間廟宇而言,所謂國家力量的收縮主要體現在政治態度上對一度被貼上“迷信”標簽的民間信仰的相對“寬容”,但是,這種“寬容”除了帶有“撥亂反正”的色彩之外,還與市場經濟的放開緊密相關。
經濟的發展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變遷最突出的表現,而市場經濟對民間廟宇重修的影響并不亞于國族認同。1980 年代以來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于民間信仰領域中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民間廟宇的重修。很多民間廟宇正是借助自身“靈驗的遺產”來發展“靈力經濟”,甚至出現了企業化、公司化的經營,并對特定地方經濟的繁榮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北鎮醫巫閭山的青巖寺,借助“歪脖老母”在東北民間的影響力,從1980 年代開始便不斷進行重修與擴建,從而成為融宗教與旅游于一體的著名風景區和北鎮經濟的重要支柱。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民間信仰基礎的支撐,也有地方政府的扶持,最重要的則是市場經濟的推動,并伴隨著不同形式的“傳統的發明”[8]。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文化本身成為手段,在客觀上導致了對特定民間廟宇之地方意象的再造。青巖寺作為“祈福圣地”便是在這種社會邏輯下,通過經濟利益和文化手段的結合而被塑造出來;同時其作為經濟交換場所的地方意象也越來越明顯,甚至危及了“祈福圣地”的地方意象,盡管二者都是疊加在青巖寺原有地方意象之上的新意象。
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中,廟宇經濟并非什么新鮮事物,比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因免稅政策而導致的寺廟地主對寺廟經濟的大肆擴張[9],商業對民間信仰的影響也不乏先例,比如宋朝高度發達的商業迫使國家允許神明可以離開原來的祭祀社區而導致跨地域神明的興起[10]。但是,當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對民間廟宇重修的影響與傳統時代有著諸多不同之處,最為明顯的是其所導致的對民間廟宇地方意象的再造或疊加。
在具有文物價值或經濟利益的民間廟宇之外,更多的民間廟宇處于國家與市場之下的社會空間之中。它們在1980 年代以來的重修,構成了特定意義上的社會重建的表征,也是對現代社會的個體化某種程度上的“補償”。但是,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認知中,這些民間廟宇的合法性是頗為模糊的,近年來國家宗教局多次召開“民間信仰工作座談會”與此直接相關。而對民間信仰“管還是不管”之所以成為問題,大概源于“國家的焦慮”[11]。面對這種焦慮,很多民間廟宇在重構自身之社會性的同時,其社會生命也將隨著國家力量的伸縮而搖擺不定。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不管何種類型的民間廟宇都不可避免地與國家力量有著或遠或近的關聯關系,它們的重修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國家力量的影響。盡管此種關系和影響在傳統社會中同樣存在,但由于觀念形態和制度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代中國的廟宇重修與傳統時代有著很大的不同,因此所帶來的問題也并無成例可循。盡管如此,但歷史提供的思想空間是不可估量的,而對于當代中國的民間信仰問題,研究者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所謂“原生態”的民間文化只不過是一個神話。
[1]吳世旭. 廟宇重修與地方營造[J]. 文化學刊,2013,(5).
[2]吳世旭.廟宇重修與民間信仰復興[J]. 文化學刊,2012,(5).
[3]列文森.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87-88.
[4]徐躍.清末廟產興學政策的緣起和演變[J]. 社會科學研究,2007,(4).
[5]程美寶.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21-22.
[6]趙展. 錫伯族源考[J]. 社會科學輯刊,1980,(3).
[7]李云霞. 錫伯家廟——太平寺的歷史變遷[J].滿族研究,2011,(1).
[8]霍布斯鮑姆,蘭格.傳統的發明[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9]簡修煒,夏毅輝.南北朝時期的寺院地主經濟初探[J].學術月刊,1984,(1).
[10]韓森.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1]王銘銘. 宗教概念的劇場——當下中國的“信仰問題”[J].西北民族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