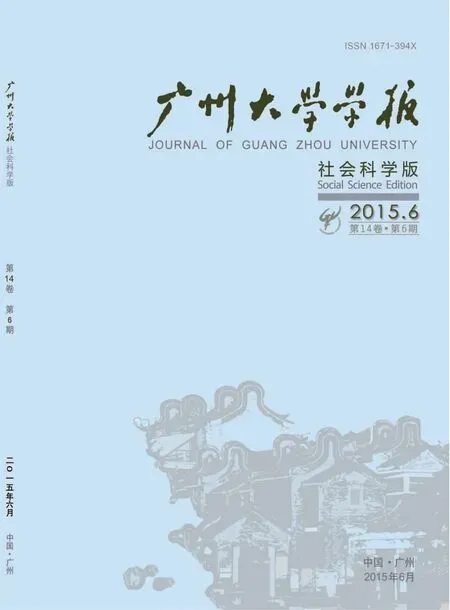印順“人間佛教”倫理觀芻議
譚苑芳
(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廣東廣州 510006)
自20世紀初太虛大師提出“人間佛教”理念以來,“人間佛教”已經逐漸為中土佛教界所廣泛接受而為公認的當代佛教發展方向。1983年,趙樸初先生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今后中國佛教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就是“人間佛教”[1]。與傳統佛教相比,“人間佛教”的意義在于其“人間”指向。亦即是說,佛教一切精神信仰都將落實于現世的、具體的、可以感知的“此岸世界”,而非飄渺且難以認識的“彼岸”。就其源而言,太虛“人間佛教”的理念之提出具有強烈的現實應對策略色彩,乃是針對中土佛教長期的窳敗和民國時期戰亂的時代需求。[2]9-20盡管它有著長遠而深厚的原始佛教教旨依據,但其實質卻是特殊時期的非常構想;這一構想的現實指向性使其天然具有倫理屬性。而“人間佛教”之所以存在并深入民心的實踐性也在于極力彰顯、貫徹其佛教倫理意味于種種信仰的行為之中。
作為太虛學生的印順法師繼承了“人生佛教”的精髓,并進一步將其完善為“人間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人間佛教”;甚至有學者認為,“而成熟的‘人間佛教’理論形態則是在釋印順那里才得到明確建立”[3]。因此,剖析印順“人間佛教”的具體內涵和實質,特別是從不同側面切入印順“人間佛教”思想,有助于在當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會語境中展開“人間佛教”建設,發揮宗教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和作用;而這恰是以往的“印順研究”或“人間佛教”研究所忽視之處。本文擬就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倫理觀做初步探析,辨析其倫理觀的主要內容,并著力從中找尋與西方倫理學思想相契合之處,以求通過比較的視野與方法,能夠更好地把握印順“人間佛教”的豐富內涵。
一、印順人間佛教的實踐理智屬性
“人間佛教”的倫理觀首先強調的是其現實精神,即在社會實踐中完成人格的超越(成佛)。這當然是“對治”的要求,但也顯現出某種精神上的指引。印順說:“人間佛教不但是適應時代的,而且還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4]125。前者可以認為是“人間佛教”的實踐品質,而后者則表現為精神、意志上的作用——人的理性選擇。佛法并非俯拾即得,而是需要主體去“求”“習”“修”才能得到的,這就為個體精神的理性參與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從這個根本意義上來講,“人間佛教”乃具有實踐理性的屬性。
倫理學意義上的“實踐理性”概念由亞里士多德提出,他的《尼各馬克倫理學》劃分了人的不同屬性:實踐理智(明智)、技巧理智和理論理智(理智),其中實踐理智屬性是人的理智運用的重要表現。它表現為人在對他者交往的事務中進行理智的思考,進而決定在其中求得正當(真)與善的方式,即“一種同人的善相關的、合乎邏各斯的、求真的實踐品質”[5]1140。而在“人間佛教”的理念框架中,既定的“佛法”即是衡定真與善的標準,也是真與善本身。《菩薩瓔珞經》云:“順第一義諦起名為善,背第一義諦起名為惡。”[6]1021這里的“第一義諦”與西方的邏各斯(Logos)也有類似之處。因此,可以認為,“人間佛教”的實踐理智乃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意識(心),將其作為“行為善惡之決定者”。“人間佛教”認為,心(理智)對實踐的意義表現為“心對根身的主宰力、心為善惡的發動,以及心能影響報體等”。[7]36-40這些方面突出了人的理性意識在實踐——包括對個體(根身)、社會行為道德(善惡)和行為效果(報體)的實踐——中的作用,是一種指向現實個人與社會的理念。
在“人間佛教”中,實踐理智主要表現為《金剛經》所言的“應住”或“降服其心”。人的主體理智可以有兩種面向,向內則是應對個體的內心煩惱,向外則是以對待種種事物,即實踐。后者既是前者產生的原因,也是其所處的語境,還是檢驗主體“發心”善惡的試金石。換言之,乃是外向的社會實踐使得人的煩惱被理智感知;外向的社會實踐所產生的倫理判斷(善惡、正當與否等)促成或阻礙了主體的社會行為。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實踐理智與道德德性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緊密關系,其直言:“明智是一種德性”[4]1140。實踐理性的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道德制約,而是內在于實踐之中的,具體說是作用于人心的。實踐理智所追求的“善”并不具有強制性,而是實踐本身所要求的,也是主體的倫理意識所要求的。通俗地說,“人間佛教”的實踐理智即是印順所言:“要老老實實地覺得自己有種種煩惱,發心依佛法去調御它,降服它。”[4]127可以說,主體所抱持的“老老實實”的態度和行為就是印順“人間佛教”實踐理智屬性的典型表現。
這并不意味著,作為宗教形態的“人間佛教”之實踐品質與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之間可以畫等號。二者仍是出于不同時代需求和不同思想傳統所提出的哲學—社會命題,它們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佛法”本身兼具外在于人與內在于心的雙重屬性。事實上,這也是西方哲學邏各斯與“佛法”的根本區別所在。佛教經典強調“佛法”必須“求”“習”“修”,即主體必須依照佛教教義而行事、運思,這是“佛法”外在于人的表現,“人間佛教”也不例外。印順指出,“佛法,只可說發見,不像世間學術的能有所發明。因為佛已圓滿證得一切諸法的實相,唯佛是創覺的唯一大師;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溫故知新而已”[4]125。這與西方倫理學重視個體精神與自主力量的傳統是迥異的。同時,印順的“人間佛教”特別強調個體依品次第進修的重要[7]75-76,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輕視了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更為重要的是,“人間佛教”理念成立的根本前提還在于,承認“佛性本人人自有”的命題,主張成佛乃是一種生命的超越性體驗。這顯然與西方先驗的邏各斯中心是大相徑庭的。
另外,值得說明的是,亞里士多德所區分的實踐理智、技巧理智和理論理智,后兩者在大乘佛教的教義中并未付諸闕如,只是“人間佛教”,尤其是印順的“人間佛教”在教旨上不是那么強調人的主觀意識、邏輯判斷中對“技巧”和“理論”的把握。傳統大乘佛教中,“五明學”乃是“慧”的主要內容。《瑜伽論》言:“菩薩求法,當于五明處求”[8]227,其中“聲明”“因明”“內明”當屬理論理智;“醫方明”“工巧明”等實用的社會知識則可歸于技巧理智。然而,“人間佛教”其意之所指卻并不在于“技巧”或“理論”。印順的遠見在于,他已經意識到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技巧”或“理論”早已不是缺乏而是遠遠溢出了人們固有的需求,不斷通過媒介技術而膨脹,甚至成為統治人的工具,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所認為的人之“異化”正在于此。“人間佛教”理念于此有著巨大的精神超拔作用。
總而言之,印順“人間佛教”理念的實踐理智是綜合了技巧理智與理論理智的一種居間形態。所謂“佛化的道德在般若”[9]212,它并非純粹實踐的,也非純粹沉思的,而是在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引導主體尋找正當與善的意義。它同時作用于人的理性與感情,形成了完整的宗教信仰。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三分法具有明顯的遞進色彩,即理論理智最高,實踐理智次之,技巧理智最次;而印順“人間佛教”倫理觀則以“實踐理智”為居中,調和了“理論理智”與“技巧理智”,絕不偏廢,顯示了后發佛教理論的圓融。因此,印順“人間佛教”的倫理色彩顯然更具說服力。
二、印順人間佛教的交往倫理學意涵
倫理學是研究社會交往事務的學問,而“人間佛教”正是發自社會交往的一種宗教訴求。佛教立意之初,即是為了應對人生之苦。印順說:“世間無處不充滿憂苦,就人類來說,最嚴重的莫過于人與人之間的殘酷斗爭了。”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印順將人間關系之苦歸為“個人”“家”“國”和“全世界”四類,[9]114分別予以評析。這一思路的出發點是原始佛教的基本觀念,《中阿含·苦陰經》即云:“以欲為本故,母共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親族展轉共諍……以欲為本故,王王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因共相諍故,以種種器仗轉向加害。”[10]585印順認為,這一狀況“千古如此,于今尤烈”,現代社會在通過“世間一切學術——醫藥、教育、競技、工巧、政治、法律,以及科學的聲光電化”來“解除苦厄”之外,“又有新的憂苦”。[9]116-117因此,應對社會問題的根本方式不在于科技的“解厄”,這一點早已為西方哲學為現代性“祛魅”之說所證實。“人間佛教”提出的應對方式,仍是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具體而言,印順提出,欲諍、見諍、慢和癡四種因素構成了人際交往的主要障礙和危機產生根源。[9]118-126顯然,盡管這四種因素是由人心之興發感動而生成的,但其作用對象都是指向外在的他者,是主體在與他者交往的過程之中才發生作用的。
這一點與晚近以來興起的交往倫理學間有著頗為相似之處。隨著多元文化的出現,對話與跨文化交流成為共識,倫理學的研究也逐漸走向了對交往理性的探討。其中,哈貝馬斯的觀點尤其值得注意。哈貝馬斯認為,交往必須以相互可理解的環境因素為背景;交往的目的在于尋求協調與合作;交往行為也尋求建立共同的理解。[11]99-100這與印順“人間佛教”所倡導建立的“佛化人間”(或稱“在家的佛教”),即以和敬為目的的人類群體生活是相一致的。但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卻并不是單純的“日常交往”,而是帶有哲學意義的反思性交往。這在操作層面上就排除了從事諸如以經濟、政治等為目的的交往活動進入其所關注的范疇,從而阻斷了社會倫理在交往倫理中發揮根本性/指導性的作用。
印順的“人間佛教”之交往倫理意味,著眼點在于“法味同嘗”。以家庭為例,“一個在家的正信弟子,如果對佛法有正知見,有真信仰……家庭的每一分子都能信受佛教,領受佛法的利益。”這就要求在家的佛教徒與其家人有相互可理解的環境,并其目的都在于推動家庭的幸福;通過在家佛教徒的解說與引導,一個家庭建立了共同理解的基礎,在此之上而尋求現實的突破:“一位在家弟子,皈依三寶以后……對自己的父母、兒女、兄弟、夫婦,更體貼、更親愛,更能盡著在家庭中應盡的責任。這樣,家庭因此而更和諧,更有倫常的幸福,大家會從他的身心凈化中,直覺到佛法的好處,而自然地同情,向信佛者看齊,同到三寶的光明中來。”[12]28-29如是建立一種“交往的循環”,不斷由社會實踐的行為(不僅是哈貝馬斯所謂反思性的哲學交往,而是包括重復性的日常交往)推動社會認知的基礎,再由對社會認知的意識來促進社會實踐的“佛化”,最終都指向佛法之所認同的“善”與“正當”,由家庭而及國家,由國家而及國際,這樣,“人間佛教”才有得以全面實現的可能。這當然是一種日常的、重復的,并在重復中不斷深化的倫理作用。因此,可以說,印順“人間佛教”的基本構思都是立基于社會交往的倫理意義基礎上的。需作說明的是,“人間佛教”所強調的家庭倫理,同樣是以情感為基礎的,是一種“正當”的情感。[13]135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也試圖溝通所謂“三個世界”,即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他說交往的參與者乃是“對三個世界中行為語境的不同因素進行歸整”[11]100。這說明哈貝馬斯并不僅關注人的主觀反思,他的理論也兼具有生產性的“技巧理智”,又具有哲學性的“理論理智”,前者以外在的目的性為特征,后者則重視內在的目的性,二者都關注社會行為的內在善惡問題。但是,哈貝馬斯卻將其局限于反思性而非重復性的哲學交往之中,這就決定了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難以對全社會產生普遍而深遠的影響,難免最終淪為精英哲人的沉思與獨白,或知識分子為社會開出的一廂情愿的藥方。與之不同的是印順“人間佛教”理論中切實的倫理指向。印順說:“在水中救人,是不能離水上岸的。要學會浮水,也非在水中學習不可。菩薩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14]94菩薩行的關鍵是慈悲,即是善的利他行;“人間佛教”作為大乘佛教的教義就在于它要從現實的利他行中去成就自我。印順說:“大乘道,發愿以后,就應該見于實行。”[14]95這種“實行”就是自利與利他的統一,是一種建立在交往基礎之上的善行。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哈貝馬斯“交往”理論的單方面沉思,而是由深厚的佛法積淀來完成“沉思”或“反思”的功能,個體只需要按照既定的“善法”經行即可成就。
更為重要的是,“人間佛教”將交往不僅看成是人類群體(如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礎,而且是一種成就自我的修行方式。這一點是非宗教的交往倫理學所無法兼容的。換言之,在善與正當之上,“人間佛教”的交往倫理還具有超越性的指向,它由“人間”指向“天國”,由“此岸”指向“彼岸”,具有很強的形而上色彩。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人間佛教”理念就會被庸俗化為社會慈善精神或志愿品質,從而成為僅具有倫理意義的一般社會理論。
三、印順人間佛教倫理的形而上指向
就倫理學的目標而言,其規范性的論述之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個體的道德覺解。[15]217可以說,一切哲學思辨的目的,都是在于使主體精神能夠“覺悟”或“理解”。倫理學如此,宗教更不例外。印順“人間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人間凈土”,但其路徑也是通過作用于個體的心性,來實現從“有漏”到“無漏”的轉變。因此,就修行方法上來講,強調交往、強調他者和群體的倫理最終要回歸到個體的心性倫理上來。亦即是說,“人間佛教”倫理的實現與否,乃是維系于個人的道德覺解。個體的問題,是“人間佛教”超越性指向的核心;個體的善惡觀,是“人間佛教”倫理所要涵化的主要內容。
一般認為,個體的道德覺解要經過由對規則的覺解到對正當性的覺解,進而才是到德性的覺解。[15]221這三者之間是一種逐層遞進的關系。但如果仔細分析這一“三段論”可以發現,此種倫理論斷的標準是由外而內的,其所建立的基礎并不是主體自我,而是社會交往的基本實踐規則。這與印順“人間佛教”的倫理觀很不一樣。印順說,佛教道德的“三增上”,首先是建立在自我基礎上的。“時常喚起自尊心……尊重自己,擴展自心的德行,負起自救救他的重任。尊重自己,不甘下流,便是促進道德的主要力量。”[9]211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接受“法增上”與“世間增上”,由外在環境的力量對個體的道德選擇形成某種規范。這意味著,“人間佛教”將人視為可以通過先驗的精神加以調教的個體,不斷強調“學佛即是道德實踐”,以充分的戒律來保證煩惱的斷除,消滅“散亂、失念、不正知”[9]215;《華嚴經》所云的“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懺悔”[16]847,乃是諸多大乘經典所共同奉持的金律。而西方倫理學則認為,許多道德品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在某個年齡段里“自然地獲得的”[5]1143。從此可見,西方倫理學重視的個體經驗、強調個人主義,但在具有超越性指向的一面中,西方哲學家卻是斷然拒絕從個體入手實現轉變的倫理規劃的。他們或寄希望于從制度、體制等客觀方面對社會進行的種種改造,或對科技未來抱持著倫理上的樂觀主義。
印順“人間佛教”對這種倫理思想是有極大的不滿的。“人間佛教”認為,學佛或修持佛法的起點和關鍵都在于“發愿”“發心”,即是率先由自我入手,從“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17]750的真慈悲入手,破除自我,掃蕩執見。之所以要從內在的心而非外在的物入手,印順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解釋,他說:
一切文化施設,對于人類憂苦或福樂的關系,異常密切。佛法并沒有輕視這些的重要性,而是說:老、病、死引起的憂苦,雖僅是個人的,卻是最基本的(也可說最原始的);一切問題、一切苦痛即使解除了,而每個人的老、病、死苦還是存在的。佛法是說:物產的增加、政治的革新等,對人生苦厄的解除、幸福的增進雖極為重要,而最根本的,還是每個人理性的智慧與道德的提高。消除種種不良的心理因素,凈化自己的身心。重視個人——根本的革新與完善,才能徹底解除苦厄,實現個人、家庭、國家、國際的真正幸福……以佛法的觀點來看,一切憂苦,一切問題,是依人類自己而存在的。唯有從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改善,自己的解決中,才是根本而徹底的辦法。[9]117
可見,“人間佛教”的倫理指向并非是一種普遍性的立法,不是康德所言“同時認為也能成為普遍規律的準則”[18]38-39,而是極其重視個體經驗的、從個體出發而抵達群體的關懷。這一點,是“人間佛教”的基本特征。印順也認為,“直覺有我,這種‘我癡’,為‘我慢’、‘我見’、‘我愛’的根源,為‘見諍’與‘欲諍’的根源。我們自己就是這樣,依自己存在而有的一切存在”[9]126。佛教的基本倫理觀是建立在一個悖論的基礎之上的:它看似承認“自我”的存在,并以此為信仰的立足點,要個體從“心”發愿;同時,它又要求打破“自我”,摒棄“我執”。因此,佛教的倫理指向始終在“自利”與“利他”之間搖擺,大小乘、菩薩與擔板漢的區別就此而生。而印順的“人間佛教”則大不相同,他“以最高之人格安立佛格,讓佛陀永遠留駐人間”[3],“佛在人間”就意味著人的即身成佛,就意味著成佛的進階途徑是通過利他而實現自利。這是一種在次第間將自利與利他合一的倫理指向。因此,學者周貴華所認為的,印順的“佛在人間”說乃是對大乘佛教的直接否定,這一觀點仍值得商榷[3]。至少在形而上的倫理意義上,“人間佛教”與“大乘佛教”是相融洽的。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說:“趣求諸欲人,常起于希望;所欲若不遂,惱壞如箭中。”[19]176這形象地說明了,自救是救他的前提,而自救的方式乃是去欲,也就是印順所言的“祛除私我”。此為“人間佛教”倫理的形而上指向之路徑。印順說:“不知者以為佛法的修持與世間與人類無關,這是重大的誤解。要化除我、我見,要依戒、定、慧——三學去修習。”[9]214所謂“戒定慧”三學其實包含了技巧理智、實踐理智與理論理智三種類型的倫理觀,通過修持把握三學就可以穩健地控制自己的德性,運用佛陀所設立的“法”來作為一種內化的尺度。這有類于亞里士多德所言的明智給具體的實踐設立“靶子”,人的德性會在明智的引導下“自然地”瞄準,并爭取能夠“命中”。[5]1138其所不同的是,印順“人間佛教”為明智設立了不同的境界與層次,要求修持者依品次進行。最終做到“私我凈盡,般若現前”。這是“人間佛教”倫理的最高指向,即依靠“般若智慧”來保證善與正當的實踐,因此,印順說:“佛教所說的一般道德,與其他相通;唯有從般若而流出的無漏德行,才是佛化的不共道德。”[9]214而這一切都是要在自家心田里下功夫才能實現的。由上可見,印順“人間佛教”的形而上指向的主要意涵在于個體心性的調整,以般若智慧為倫理的目標,二者相輔相成地實現“即身成佛”的目標。
印順“人間佛教”的倫理關懷,既有與世間倫理相似之處,也有其鮮明而獨到的特征。這些特征甚至與太虛的“人間佛教”也有所不同。或者說,印順與太虛在為佛教規劃應對時代的挑戰時,都具有昂然屹立的佛教人格,將錚錚鐵骨響徹于圓融博大的佛性慈悲之中。繼承“人間佛教”的傳統,印順豐富而深刻的精神遺產尚有待多方面的耙梳與辨析。
[1] 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J].法音,1983(6):13-21.
[2] 羅同兵.太虛對中國佛教現代化道路的抉擇[M].成都:巴蜀書社,2003.
[3] 周貴華.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之特質評析[J].哲學研究,2006(11):47-52.
[4] 釋印順.人間佛教論集[M].北京:中華書局,2010.
[5]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克倫理學[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6]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2[M]∥大正藏:冊24.
[7] 釋印順.學佛三要[M].北京:中華書局,2010.
[8]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3[M]∥大正藏:冊39.
[9] 釋印順.佛在人間[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0] 中阿含經:卷25[M]∥大正藏:冊1.
[11]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 釋印順.為居士說居士法[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3] 布勞德.五種倫理學理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4] 釋印順.菩薩心行要略[M].北京:中華書局,2010.
[15] 廖申白.倫理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0[M]∥大正藏:冊10.
[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M]∥大正藏冊8.
[1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9]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34[M]∥大正藏: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