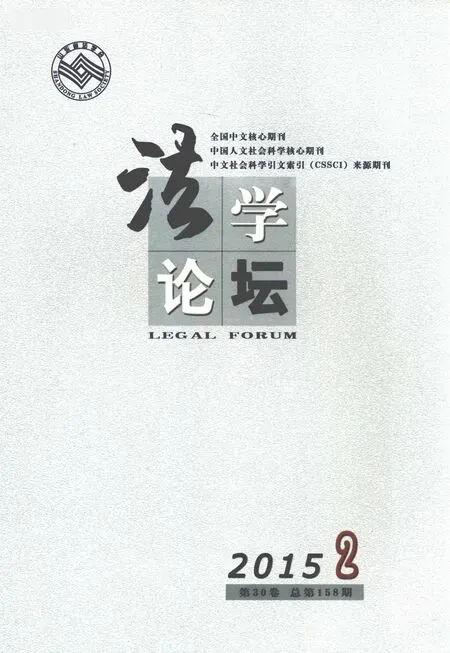關于民法典總則立法的幾點思考
房紹坤
(煙臺大學 法學院,山東煙臺 264005)
【名家主持·民法典總則立法難點研究】
關于民法典總則立法的幾點思考
房紹坤
(煙臺大學 法學院,山東煙臺 264005)
我國民法典的編纂應當采取分步走的方式,首先進行民法典總則立法。民法典總則立法不能采取修改補充《民法通則》的方式進行,應當重新立法,也不能以制定民法典通則代替民法典總則。民法典總則的體例設計應當采取總則加實質序編的“大總則”模式,不能以序編代替總則,其邏輯構造應當以權利為主線。
民法典;民法通則;總則;序編;權利主線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的重大改革任務。為此,編纂民法典已經成為當前重大的立法工作。筆者認為,由于編纂民法典是一項浩大工程,很難一步到位,因此,宜采取分步走的方法。目前,首要任務是制定民法典總則。為此,本文擬就民法典總則立法中的三個宏觀問題談點看法。
一、民法典總則的立法路徑
1986年4月,我國頒布了《民法通則》并一直適用至今。應當說,《民法通則》在新中國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于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歷史功績不容否定。因此,在民法典總則立法時,如何對待《民法通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這直接涉及到民法典總則的立法路徑選擇。對此,理論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修改補充《民法通則》,將其改造為民法典總則。*參見王利明:《法律體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載《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崔建遠:《編纂民法典必須擺正幾對關系》,載《清華法學》2014年第6期;楊立新:《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頁。其主要理由在于:《民法通則》雖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頒布的,但其基本涵蓋了所有民法典總則的內容,并且其大部分內容仍然可以適用于我國的現實情況。因此,在制定民法典時,不宜徹底拋棄《民法通則》,而應剝離其中的民法共性規范,作為民法典總則的藍本。*參見王利明:《法律體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載《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另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以現行《民法通則》為基礎在民法典中設置開放性的民法通則,而不是相對封閉的民法總則,統合人格權、財產權總則、商事總則,以增強民法典通則部分與分編之間的融通與互動關系,使之更具包容性。具體建議是:(1)擴張“自然人”和“民事權利”兩章,將人格權法主要部分納入其中;(2)擴張“法人”和“法律行為和代理”兩章,將“商法通則”主要部分納入其中;(3)擴張并重述“民事權利”和“民事責任”兩章,將涉及“債之關系總則”、“財產法通則”(或“財產權總則”)主要部分納入其中。*參見易繼明:《歷史視域中私法統一與民法典的未來》,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筆者認為,在民法典總則的立法路徑選擇上,應當采取以下兩種態度:
態度一:民法典總則立法不能通過修改《民法通則》的方式進行,而應當采取重新立法的方式。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從修改法律的基本規則看,某一法律的修改應當是對法律內容的修改,而不應當涉及法律的名稱。如果改變了法律名稱,就不再是法律修改的問題了,而應屬于重新制定法律。因此,將《民法通則》修改為民法典總則,與修改法律的基本規則不符。第二,《民法通則》貫通了民法典總則與分則的內容,實際上是一個微縮的民法典,而不是民法總則。*參見孫憲忠:《防止立法碎片化、盡快出臺民法典》,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因此,不能將《民法通則》與民法典總則相提并論。如果將《民法通則》修改為民法典總則,則是降低了《民法通則》的法律地位,從法律階位上說是不合適的。第三,從《民法通則》的內容來看,其大都失去了適用價值。隨著我國民事立法的發展,立法機關制定了許多民事單行法,從而使得《民法通則》的許多規定實際上已經成為具文。例如,有關分則的內容基本上被《物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所取代,幾無適用價值;而有關總則的一些內容如個人合伙、法人、民事法律行為、代理等因有相應的《合伙企業法》、《公司法》、《合同法》等的規定,其適用價值也已不大。同時,有的內容如法人聯營因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已經喪失了存在的基礎。綜上,通過修改補充《民法通則》的方法進行民法典總則立法是不可行的,其立法成本一點也不低于重新制定一部新法。當然,民法典總則立法不能采取修改補充《民法通則》的方式進行,并不意味著在民法典總則立法時完全拋棄《民法通則》。從法學發展來看,法律具有傳承性,立法也應當如此。《民法通則》雖然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制定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局限性,但其確定的調整對象、基本原則、法律行為、民事權利、民事責任等基本制度仍具有合理性。因此,在民法典總則立法時,應當將《民法通則》所體現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作為重要參考。
態度二:不宜以民法典通則代替民法典總則。其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在民法典中設置通則而不是總則不符合民法典編纂技術的要求。從民法典編纂技術來看,世界上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法學階梯模式,民法典基本上由人法和物法兩大部分組成;二是以德國民法典為代表的潘德克頓模式,民法典由總則與分則組成。在我國學者中,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和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采取了潘德克頓模式,設置了總則與分則。*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梁慧星(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徐國棟教授主持起草的《綠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法學階梯模式,設置了序編、人身關系法、財產關系法、國際私法。*參見除國棟主編:《綠色民法典草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無論何種民法典的編纂模式,其都遵循著由一般到特殊、由抽象到具體的立法規則。這種立法規則,體現的就是將一般性規則前置的技術。*參見黃立:《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頁。在民法典中,一般性規則的前置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將適用于民法各部分的共同規則進行歸納,設置為總則編;二是將民法各部分的共同事項進行歸納,設置為該部分的通則或一般規定,如《法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在諸多編章中都設有通則或一般規定。*參見《法國民法典》第一卷第一編(二)、第二編、第七編、第十一編,第二卷第二編、第三編、第五編、第二十編等;《日本民法典》第一編五、七章,第二編第一章、第八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一節、第十章第一節,第三編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節,第四編第一章、第四章第一節,第五編第一章、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一節。按照上述第二種觀點,民法典除設置民法通則外,還應設置婚姻家庭法、繼承法、物權法、知識產權法、合同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參見易繼明:《歷史視域中私法統一與民法典的未來》,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這種設計基本上也是潘德克頓模式,但其將民法典通則與分編之間加以貫通,在民法典通則部分又規定債之關系總則、財產法通則(財產權總則)的內容。這種立法設想,一方面割裂了民法各部分的內在聯系,使債之關系的總則與分則、財產權的總則與分則處于民法典的不同部分,這就會破壞民法典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第二,即使在民法典通則中就債之關系總則、財產法通則(財產權總則)的內容作出規定,其意義也更多的是原則性的、宣示性的,其應用價值不大。這是因為,物權法、合同法屬于典型的財產法,繼承法、知識產權法也具有財產法的屬性,而這些法律的性質存在很大差異,因而可以統一適用的基本規則也不多。第三,民法典總則在比較民法立法史上并非僅指民法的總則,而系為一般私法體系之總則。*參見朱柏松:《民法總則的使命及其應規范之內涵——以中國民法總則草案為探討中心》,載《北方法學》2013年第6期。因此,民法典總則對于商法也是適用的。上述第二種觀點主張將商法通則規定于民法典通則之中,雖符合民商合一的精神,但并不符合民法典的體系化要求。因為民法典不可能規定特別商法的內容,這就會使商法通則的內容被架空,從而無法發揮其作用。筆者認為,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典總則應當設立適用于民法和傳統商法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則。*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按照這一要求,民法典總則中并無必要特別規定商法通則,只須在民法典總則的相關部分如民事主體、法律行為、代理等就統一適用于民法和商法的內容作出規定即可。
二、民法典總則的體例設計
從各國民法典的體例設計來看,民法典是否設有總則與民法典的編纂模式直接相關,基本上可以分為總則模式、序編模式和混合模式。總則模式和混合模式主要為潘德克頓模式的民法典所采用,而序編模式主要為法學階梯模式的民法典所采用。總則模式是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將民事法律制度共同適用的規則抽象出來編排于總則編,以避免相關規定在分編一再重復出現,從而形成民法典的“總則—分則”結構,如《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序編模式是將不涉及民事法律制度但與民法適用有關的最一般性原理原則加以規定并設計為序編(序言、序題),如《法國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荷蘭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西班牙民法典》、《奧地利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智利民法典》、《菲律賓民法典》、《美國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等。混合模式即總則+序編模式,即民法典采取“總則—分則”結構,但在總則的開篇以“基本規定”、“一般規定”、“通則”、“法例”、“法律、法律之解釋與適用”等形式規定序編的內容,如《俄羅斯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韓國民法典》、《巴西民法典》、《蒙古國民法典》、我國澳門民法典和臺灣地區“民法”等。我國有學者將混合模式中的序編稱為實質序編,而將序編模式中的序編稱為形式序編。*參見陳小君:《我國民法典:序編還是總則》,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在我國,民法典總則的體例如何設計,學者間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民法典應當設置總則編。例如,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設計了總則和分則,總則的內容包括一般規定、自然人、法人、合伙、民事權利客體、法律行為、代理、訴訟時效、期間與期日、民事權利的行使和保護;*參見王利明(項目主持人):《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總則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梁慧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亦設計了總則和分則,總則的內容包括一般規定、自然人、法人與非法人團體、權利客體、法律行為、代理、訴訟時效。*參見梁慧星(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總則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種觀點認為,民法典應當設置序編。例如,徐國棟教授主持起草的《綠色民法典草案》設計了序編,其內容包括:預備性規定、人、客體、法律事實和法律行為、代理、民法世界中的時間、基本術語的定義。*參見除國棟:《綠色民法典草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三種觀點認為,民法典應當設置序編性質的總則編。陳小君教授指出:“民法典的首編選擇何種形式,不但關乎首編自身成敗,且影響到整個民法典體系的協調和諧。但這并不意味著非設總則不可,同時亦不能非此即彼地認為簡單地冠之以序編就萬事大吉。民法典應設總則自不待言,但這一總則,是集序編和總則之成、格二者之非的總則。名同而實異,因此稱之為‘小總則’或許更為妥帖。”這個“小總則”編應就民法的淵源、民法的解釋及適用、基本原則、權利的行使、期日和期間等問題設立總則性的規定。*參見陳小君:《我國民法典:序編還是總則》,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從上述觀點來看,民法典的體例如何設計,實際上反映的是應設置“大總則”還是“小總則”的區別上。第一種觀點所指的“總則”屬于“大總則”,屬于混合模式中的“總則”;第二種觀點所指的“序編”不同于序編模式中的“序編”,而與總則模式和混合模式中的“總則”相當。但因其剔除了自然人和法人的相關內容,可以將這種“序編”稱為“小總則”;第三種觀點所指的“總則”既不同于總則模式中的“總則”,也不同于混合模式中的“總則”,其內容更接近于序編模式中的“序編”。因其將總則模式和混合模式中的民事主體、客體、法律行為、代理、訴訟時效等內容排除在外,其內容較之第二種觀點所指的“總則”還要少,可以稱之為“小小總則”。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總則應當采取混合模式,設置“大總則”,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序編與總則具有不同的功能,兩者不能相互替代。從各國民法典的規定來看,無論是形式序編還是實質序編,其內容主要包括法律的一般效力、法源、法律適用、法律解釋等。這些內容是法律適用的通例,是全部民法的法則。就實質序編而言,其可以看成是總則中的總則,是民法適用上最基本的原理原則。*參見鄭冠宇:《民法總則》,2012年臺北自版,第38頁。因此,序編的內容處于抽象的最高位階,并不是法律規范的具體構成要素*參見韓松:《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結構》,載《當代法學》2012年第4期。,一般不具有直接適用性,對于民事法律制度不具有統率作用;而總則是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從民事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來的共同規則,具有直接適用性,對分則具有統率作用。因此,序編與總則不能相互替代。上述第二種觀點所稱的“序編”在內容上大都屬于總則的內容,對“人身關系法”和“財產關系法”大都具有統率作用,實為混合模式中的“總則”。因此,這種“序編”稱為“總則”更為合適。第三種觀點主張我國民法典應以“總則—分則”作為構造模式,建構一個“小總則—人法—親屬法—繼承法—財產法”的五編制體系。*參見陳小君:《我國民法典:序編還是總則》,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但這種“小小總則”與序編模式中的“序編”更為接近,基本上不具有總則的功能,稱之為“序編”更為合適。可見,無論是將“總則”說成是“序編”,還是將“序編”說成是“總則”,均存在名不符實的弊端,也混淆了兩者的功能,實不可取。
第二,民法典總則的共同規則與分則的具體規則并非嚴格的對應關系。民法典總則的優點是將私法上的共同事項加以歸納,具有合理化的作用,可以避免重復或大量采準用性規定。但這種抽象規定也存在缺點,就是必須創設例外,正所謂“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頁。就民法典總則的設置而言,要么制定一些非常一般的規則,這樣,一般規則的數量勢必就很少,總則為分則減少負擔的效果難以發揮出來;要么承認在一般規則之外,還存在個別的例外。*參見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1頁。基于民事法律制度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民法典總則只能選擇后一種方式,不可能做到與分則的規定完全對應。如果這樣要求,就是犯了絕對主義的錯誤。筆者認為,只要能夠從民事法律制度中抽象概括出共性的東西,并能夠適用于分則規定的某些具體制度,都可以設計為總則的內容。例如,第三種觀點將總則模式和混合模式中屬于總則的民事主體、客體、法律行為、代理、訴訟時效等內容排除在總則之外,認為法律行為、權利客體、訴訟時效等只適用于財產法,故應在財產法編設置總則加以規定。*參見陳小君:《我國民法典:序編還是總則》,載《法學研究》2004年第6期。筆者認為,法律行為、權利客體、訴訟時效是否只適用于財產法是值得討論的。其實,在親屬法、繼承法中,法律行為、權利客體、訴訟時效也都有適用的余地。例如,親屬法上的夫妻財產約定和收養協議、繼承法上的遺贈扶養協議和繼承協議,在本質上都是一種法律行為,有關法律行為的基本原理對其也是適用的。再如,繼承法上也有訴訟時效的適用問題,而遺產本身就是權利客體。可見,將法律行為、權利客體、訴訟時效規定于財產法編,將會影響親屬法、繼承法對法律行為、權利客體、訴訟時效的適用。
第三,民事立法不能忽視我國的法律傳統。在我國歷史上,民法法典化開始于清末法制變革。1911年,清政府編纂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采取“總則—分則”結構,總則內容包括法例、人、法人、物、法律行為、期間及期日、時效、權利之行使及擔保。1925年,北洋政府修訂法律館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修訂完成了《民國民律草案》(第二次民法草案),總則的內容設計為人、物、法律行為、期限之計算、消滅時效。*《大清民律草案》、《民國民律草案》的有關內容,參見楊立新主編:《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頁。1928年12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在《民國民律草案》的基礎上分編完成了《中華民國民法》 編纂工作,亦采取“總則—分則”結構,總則內容包括法例、人、物、法律行為、期間及期日、消滅時效、權利之行使。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亦進行了多次民法典起草工作。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民法起草,至1956年形成了《民法草案》,設置了總則,內容包括基本原則、民事權利主體、民事權利的客體、民事行為、訴訟時效。196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起草完成了《民法草案(試擬稿)》,其總則的內容包括民法的任務、基本原則、參與經濟關系的單位和個人、制裁和時效、適用范圍。1982年,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起草完成了《民法草案(第四稿)》,雖沒有采取“總則—分則”結構,但民法的任務和基本原則、民事主體兩編屬于總則的內容。*1956年《民法草案》、1964年《民法草案(試擬稿)》、1982年《民法草案(第四稿)》的有關內容,參見梁慧星(課題負責人):《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序言第4—5頁;何勤華等:《新中國民法典草案總覽》(上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5頁;何勤華等:《新中國民法典草案總覽》(下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37頁、560—624頁。1986年,我國頒布了《民法通則》,設基本原則、公民(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民事權利、民事責任、訴訟時效、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適用、附則。其中,基本原則、公民(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訴訟時效屬于總則的內容。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起草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其總則的內容包括一般規定、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為、代理、民事權利、民事責任、時效、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有關內容,參見楊立新主編:《中國百年民法典匯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620頁。從上述民法起草及法律文本來看,新中國成立前的《大清民律草案》、《民國民律草案》、《中華民國民法》均采取了潘德克頓模式,設有總則,且內容基本相同,屬于“大總則”。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法草案》、《民法草案(試擬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均設有總則,內容大同小異,也屬于“大總則”。《民法草案(第四稿)》和《民法通則》雖然都沒有設置總則,但都規定了總則的相關內容。綜上可見,在民法典中設置總則且為“大總則”是我國的法律傳統。這種傳統已經根植于我國立法實踐,應當繼承和發揚,而不能放棄。
三、民法典總則的邏輯構造
如前所述,民法典總則是通過“提取公因式”方法從分則中抽象出來的共同規則,那么,分則中的“公因式”是通過何種途徑被抽象出來的,這些“公因式”之間又存在何種邏輯關系,這些問題直接涉及到民法典總則的邏輯構造。換言之,民法典總則的設計應當確定一條貫穿始終的邏輯主線,并圍繞這條主線設計總則的章節結構。從潘德克頓模式的民法典總則來看,其大都以法律關系為主線,形成了“主體—客體—行為”三位一體的邏輯結構,規定了人、物、法律行為及相關內容,而具體權利則規定于分則。例如,德國、俄羅斯、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等民法典總則規定了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物(客體)、法律行為及相關內容,巴西民法典總則規定了人、財產、法律事實,而葡萄牙及我國澳門的民法典總則更是明確地將“法律關系”作為總則的第二編,具體規定了人、物、法律事實、權利之行使及保護四個分編。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潘德克頓模式的民法典總則的邏輯主線是法律行為,是對法律行為經抽象而形成的共同規則。例如,梅迪庫斯曾指出:民法典設置總則編的優點,主要反映在有關法律行為的規定方面。將這些規定提取概括,可以取得唯理化效應。這樣,立法者就無需為每一項法律行為都重新規定其生效的要件。*參見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30頁。我國有學者指出,德國、日本、俄羅斯等民法典總則是以法律行為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人和物分別是法律行為的主體和客體;如果沒有法律行為,總則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同時,總則中有關期間、期日、時效的規定,都可以看成是對法律行為的技術性規定,而德國民法典總則中有關“提供擔保”的規定是保障法律行為履行的技術性規定。*參見謝鴻飛:《法律行為的民法構造:民法科學和技術問題的闡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年度博士學位論文,第136、144頁。轉引自彭誠信、戴孟勇:《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的結構設計》,載《煙臺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王澤鑒教授也指出,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總則是建立在兩個基本核心概念之上,一為權利,一為法律行為。基于權利而組成權利體系,有權利主體、權利客體、權利行使等;法律行為乃是權利變動的法律事實,而以意思表示為要素。但在總則體系構成中,法律行為是私法學的最高成就,區分債權行為、物權行為及身份行為,而以意思表示為核心概念,經由多層次的抽象化過程而建造其體系。*參見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頁。
在我國,關于民法典總則的邏輯主線,理論上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以法律關系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因為法律關系是整個民法邏輯體系展開與構建的基礎,總則中應當根據法律關系的要素確立主體、行為、客體制度,然后在分則中確立法律關系的內容,即民事權利。*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175頁。第二種觀點認為,應當以權利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因為以權利為主線符合權利關系的邏輯結構和發展順序,使總則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體系性,也符合民法作為權利法的屬性。*參見彭誠信、戴孟勇:《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的結構設計》,載《煙臺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第三種觀點認為,應當以民事活動(法律行為)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因為民事活動是民法的基本范疇,是民法典總則的核心,總則的內容應當圍繞民事活動這個中心予以設計和展開。*參見李建華:《論民事活動——兼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結構的設計》,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第2期。第四種觀點認為,應當以法律關系、法律行為、權利三者的結合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因為這三者之間具有相互補足的作用且無相互沖撞之處,可以有效避免某一內容按照某一條主線應當放進總則而依據其他主線則否的矛盾狀態。*參見朱格鋒:《論民法典總則的技術構造》,載《研究生法學》2009年第5期。筆者認為,上述第三種觀點并不可取。該觀點認為,民事活動是指民事主體實施的、旨在實現其民事利益的、受到民法調整和評價并產生相應民事法律后果的法律活動。*參見李建華:《論民事活動——兼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結構的設計》,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第2期。且不說民事活動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用語,單就其內容表述而言,其與法律行為并無本質區別。而若將民事活動等同于法律行為,并以法律行為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則因法律行為僅是法律關系或權利的變動要素之一,除此之外還存在非法律行為的權利變動要素。因此,若以法律行為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則將非法律行為納入總則就不符合邏輯。第四種觀點主張的是三條主線,即按照法律關系主線,應當將主體(自然人、法人)、客體(物)、法律事實(法律行為、代理、期日、期間、訴訟時效)放入總則;按照法律行為主線,應當將實施法律行為的自然人、法人,實施法律行為對象的物,實施法律行為的特別方式和期限的代理、期日、期間、訴訟時效歸于總則;按照權利主線,應當將權利主體的自然人、法人,權利客體的物,權利行使方式的法律行為、代理,權利行使期限的期日、期間、訴訟時效,平等、公序良俗、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概括進去。*參見朱格鋒:《論民法典總則的技術構造》,載《研究生法學》2009年第5期。可見,無論是哪種主線,基本上都是按照主體、客體、法律事實展開的,而這與法律關系主線或權利主線已經沒有什么區別。因此,這種觀點不足取。而且如果堅持三條主線,必定會造成總則邏輯構造的混亂,不利于與分則的協調。可見,民法典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只能從法律關系或權利這兩者之中選擇。通過比較發現,上述第一、二種觀點其實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第二種觀點主張按照“權利主體(人)—權利客體(物)—權利內容(各種具體的權利)—權利變動的意定原因(法律行為)—權利變動的法定原因(時效)—權利的行使”這一權利主線來編排總則的內容*參見彭誠信、戴孟勇:《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的結構設計》,載《煙臺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而這里所述的權利主體、權利客體、權利內容、權利變動等完全可以用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內容、變動等來表述。但通過比較法律關系和權利這兩條主線,筆者更傾向于權利主線。
第一,從民法的屬性上看,應當將權利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德國著名法學家v.Tuhr曾指出:“權利系私法的中心概念,且為多樣性法律生活的最終抽象。”*轉引自王澤鑒:《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頁。近代民法的思考方式是“把所有的法律關系用‘權利’來表示”,而民法就是“作為權利的體系而被構建起來的”。*[日]大村敦志:《民法總論》,江溯、張立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頁。因此,民法是權利法,權利是民法的核心理念,無論是法律關系還是法律行為均應圍繞這一核心理念展開。民法典總則以權利作為邏輯構造的主線,完全符合民法作為權利法的屬性,這也有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權利,增加人們的權利意識。*參見彭誠信、戴孟勇:《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的結構設計》,載《煙臺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退一步講,即使民法典總則以法律關系作為邏輯構造的主線,其實也可以從權利角度加以理解,其落腳點也在于權利。例如,法律關系的主體和客體可以理解為權利的主體和客體,作為法律關系變動原因的法律行為也可以理解為權利變動的原因。
第二,從民法典“總則—分則”的結構上看,應當將權利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潘德克頓模式的民法典采取了“總則—分則”的結構模式。民法典總則是從諸多問題中抽出共通的事項而設置的一般規定,而整個民法共通的、最基本的事項,正是權利。*[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第三版),解亙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頁。任何一項權利都包括主體、客體、內容、變動、行使、保護等要素,而這些要素均應當在民法典中有所體現。如果總則的邏輯構造以權利為主線,則根據總則的功能,涉及權利的共同規則就應當在總則中加以規定,而特別事項則應當在分則中加以規定。權利的主體、客體、變動、行使、保護等均存在共同規則,這些規則在總則中加以規定當無問題。但權利的內容難以一般化,缺乏共同規則。即使試圖就權利的內容抽出共通的東西,也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不過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因此,物權、債權、繼承權等權利的內容被規定于分則。*[日]山本敬三:《民法講義Ⅰ:總則》(第三版),解亙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頁,注1。這樣,民法典就確保了總則與分則的明確分工,保證了民法典的體系性。如果此論成立,則人格權在民法中的地位就不再成為問題。因為人格權屬于特別事項,為自然人所獨有,其顯然不具有納入總則的屬性,只能在分則中以單獨成編的模式加以規定。
第三,從法律關系的要素上看,應當將權利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法律關系包括哪些要素,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認識。三要素說認為,法律關系的要素包括主體、客體、內容;*參見王利明:《民法總則研究》(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頁。四要素說認為,法律關系的要素包括主體、客體、內容、責任*參見董學立:《民事責任應為民事法律關系的要素》,載《山東法學》1997年第4期;郭明瑞:《民法總則規定民事責任的正當性》,載《煙臺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也有主張四要素為主體、客體、法律事實、保障;*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民法總論》(中譯本),澳門翻譯公司等譯,澳門法務局、澳門大學法學院2011年版,第95-96頁。五要素說認為,法律關系的要素包括主體、客體、內容、變動及變動原因。*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頁。在上述各種觀點中,只有“主體、客體、法律事實、保障”四要素說得到了葡萄牙及我國澳門民法典總則的明確認可。這兩部民法典將“法律關系”作為總則的第二編,并嚴格按照法律關系的要素設人、物、法律事實、權利之行使及保護四個分編。在其他國家民法典總則中,法律關系主線通常是學者根據總則的內容概括出來的,與法律關系的要素并無嚴格的對應關系。筆者認為,法律關系要素的認識分歧會影響到民法典總則的邏輯構造,而且也會因為分別規定法律關系的各要素而使得民法典總則的邏輯構造不夠嚴謹。而如果以權利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則上述問題即可避免。例如,關于民事責任應否在總則中規定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民事責任是法律關系的要素,而以法律關系為主線,總則就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則。*參見郭明瑞:《民法總則規定民事責任的正當性》,載《煙臺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而有的學者認為,只有法律關系的要素才能獨立成為民法典總則的內容,而民事責任并非法律關系的要素,因此,總則中不應當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則。*參見尹田:《論中國民法典總則的內容結構》,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均以法律關系作為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但結論卻截然相反,其主要原因就是對法律關系要素的認識不同。如果總則的邏輯構造以權利為主線,則這個問題即可以得到解決。權利不僅包括主體、客體的問題,還包括變動、行使、保護等問題。而民事責任是權利保護的重要措施,因此,在民法典總則中就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則作出規定,就完全符合民法典設置總則的邏輯要求。
筆者認為,以權利作為民法典總則邏輯構造的主線,總則的基本結構應當包括以下內容:(1)一般規定。一般規定是實質序編,應置于民法典總則的首章,就民法典的調整范圍、基本原則、法源、法律適用等一般性事項作出規定。(2)權利主體。關于權利主體,有的國家采取自然人、法人兩分法,如德國、日本等;有的國家采取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三分法,如葡萄牙、我國澳門等。筆者認為,我國現行法已經采取了三分法,這種作法應當堅持。同時,應當取消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的規定,代之以商自然人;取消企業法人與非企業法人的分類,代之以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規定公法人,以取代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3)權利客體。關于權利客體,主要就物的種類及其具體規則作出規定。同時,應當擴充物的范圍,將無體物納入其中,并就動物作出特殊規定。(4)權利變動。關于權利變動,主要規定權利變動的原因,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等。應當指出的是,總則中不應當規定取得時效,因為取得時效并不是民法的共同規則,其僅適用于財產法,不符合歸入總則的要求。(5)權利行使。關于權利行使,主要規定權利行使的一般規則,如權利行使的限制、禁止權利濫用、權利失效等。(6)權利保護。關于權利保護,主要規定民事責任的一般規則,如歸責原則、承擔方式、一般免責事由等。
[責任編輯:吳 巖]
Subject: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Author & unit:FANG Shaokun(Law School,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
The compilation of civil code of China should take step by step way, first carry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Code. The legislation cannot take the way only to modify and renew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but should formulate a new legislation, and should not us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to replace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 The system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 should adapt the model that includes a substantial preface, which may be called “A Big General”. The main logic line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vil code should be “the right”, but not the others.
Civil Cod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law; general provisions; substantial preface; rights
主持人:房紹坤
2015-02-06
房紹坤(1962-),男,遼寧康平人,法學博士,煙臺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
D913
A
1009-8003(2015)02-0005-08
主持人語:《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為此,要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這表明,在新的歷史時期,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舉措,我國民法典的編纂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民法學界的共識認為,我國未來民法典應借鑒德國潘德克頓法學的法典編纂體例,設總則編,就民法典其余各編中具有“公因式”特質的共性條款予以集中規定,以便更好地構造民法典的科學體系和節約集約法律條文。但就民法典總則編立法中的諸多問題,我國民法學界尚未達成共識。為此,《法學論壇》編輯部特邀了幾位學者以“民法典總則編立法”為題,就民法典總則編立法的一般性問題和民法的調整對象、訴訟時效、權利失效等具體問題展開探討,以期拋磚引玉地參與和激發學術爭鳴,共襄民法典制定的學術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