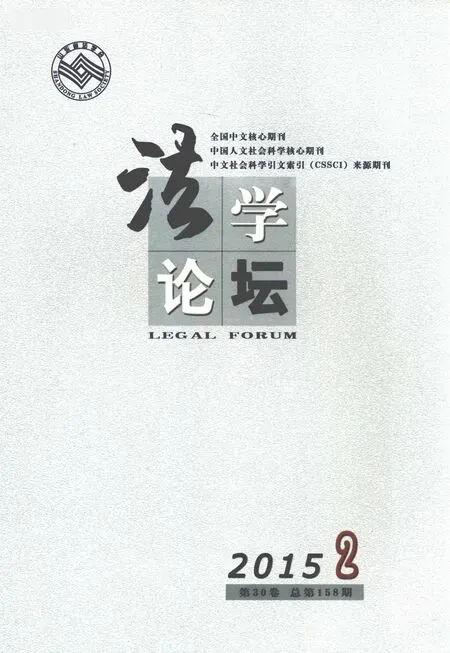先行調解制度重述:時間限定與適用擴張
李德恩
(九江學院 政法學院,江西九江 332000)
先行調解制度重述:時間限定與適用擴張
李德恩
(九江學院 政法學院,江西九江 332000)
法學界對于新《民事訴訟法》第122條先行調解規定的理解及實施還存在較大爭議。調解之“先行”必須與特定的時間節點相比較才有意義。從體系解釋及術語使用規范的角度解讀,先行調解是當事人將糾紛起訴至法院之后,在立案之前進行的調解。先行調解的適用條件“適宜調解”強調的是不能違法調解或不應在案情復雜、當事人對抗激烈之類的糾紛上徒勞消耗資源,是否“適宜調解”宜采取個案判斷的方法。人民法院既可以通過立案庭或專門機構實施先行調解,也可以將糾紛委派人民調解組織、行政機構,在先行調解中實現三調聯動。調解協議只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但通過訴調對接,即當事人自愿選擇立案簽發調解書和啟動司法確認程序兩種方式,能夠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
先行調解;訴訟調解;訴調對接
新《民事訴訟法》第122條(以下簡稱“第122條”)規定了先行調解制度,“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糾紛,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但當事人拒絕調解的除外。”雖然該法實施已逾一年,但法學界對先行調解的理解和相關研究依然存在爭議和誤區,存在自說自話、與司法實踐脫節的現象。本文認為先行調解之“先行”二字是強調進行調解的時間先于某個節點,即先予立案,其立法之首要目的在于將法院調解擴展至訴前,然后在此界定的基礎上針對先行調解的適用范圍、實施主體以及最終效力展開研究,希望能夠在澄清誤區、凝聚共識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一、先行調解之時間限定
(一)先行調解進行時間的誤讀
在法學界,認為先行調解既可以在立案前也可以在立案后進行的學者為數不少。有法院系統的研究人員認為,“對于先行調解的適用時間并未有所限制,只要是當事人起訴到人民法院即可,至于是收到當事人起訴狀或者口頭起訴后、尚未立案之前,還是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后、移送業務庭審理之前,抑或是開庭審理前或者開庭審理后均在所不問。”*奚曉明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頁。立法機關的研究者存在類似的觀點,“先行調解的適用范圍,主要指向法院立案前或者立案后不久的調解”,“案件受理之后尚未開庭審理前,人民法院仍然可以進行調解。”*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頁。理論界的李浩教授也將第122條的先行調解分為兩種性質的調解:立案前的調解和立案后的調解。*參見李浩:《先行調解制度研究》,載《江海學刊》2013年第3期。
以上針對第122條所規定的先行調解發生時間的理解過于寬泛。作為符號的法律術語只有在特定的時空情景下才有其特定的含義。*參見程樂、沙麗金、鄭英龍:《法律術語的符號學詮釋》,載《修辭學習》2009年第2期。對于先行調解這類使用時間意蘊限制詞語的術語而言更是如此,因為“先行”之意為先實行、先進行,即先于某個特定時間或程序運行而進行。上述針對第122條的理解都沒有明確一個與調解相比的特定時間或特定程序,因而不符合法律的文義解釋的基本要求。
(二)基于體系解釋及術語使用規范的解讀
誠然,《民事訴訟法》沒有明示先行調解進行的時間,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該規定所處位置、從法院各種調解形式彼此的關系推導而出。考察第122條在新《民事訴訟法》中所處位置,我們可以發現,先行調解處于第二編“審判程序”、第十二章“第一審普通程序”的第一節“起訴后受理”中,而在立案期間要求的條款之前。在邏輯關系上,先行調解之“先”應該是與立案相比較,先行調解也就是在當事人起訴之后人民法院先于立案針對糾紛組織調解的意思。從調解制度的立法體系上看,第122條的先行調解與第133條的審前調解、第142條的判前調解等關于訴訟調解的規定是并列關系,互不包括,共同體現了新《民事訴訟法》對于延伸適用調解的追求。
在將122條的先行調解界定為立案前調解,也就是訴前調解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主張,122條對先行調解這一術語的使用應該具有排他性。新中國的其他立法文件中早已多次出現“先行調解”的字眼,由于語境不同,與調解進行相比較的時間也各不相同,先行調解的詞義明顯有別于122條的規定。法學界有學者對此進行總結之后認為,先行調解作為一種程序上的安排,包括三種含義,即作為訴訟調解意義上的先行調解、作為非訴訟調解意義上的先行調解、作為訴訟調解與非訴訟調解相交錯意義上的先行調解。如此解讀相關法律規范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不同語境下先行調解的詞義。但是,在新《民事訴訟法》出臺之后,先行調解已經逐漸被法學界作為術語加以使用。術語的使用必須滿足單義性和穩定性的要求,達不到這種要求就會造成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的混亂。這就意味著,作為術語使用的先行調解必須存在一個且只允許一個與調解相比較的特定時間,這個特定的時間就是第122條界定的當事人將糾紛起訴至人民法院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如此認定的原因有三:其一,從立法頒布的時間而言,后法優于前法;其二,從立法的層級而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優于行政規章、司法解釋;其三,先行調解的表述在我國立法中雖然早已出現,但被學術界作為術語廣泛使用卻是在新《民事訴訟法》出臺之后。
概而言之,從文義解釋的角度而言,先行調解必須與特定時間相比較,其詞義隨比較時間的不同而變化;而從術語使用規范的角度出發,先行調解應該專指當事人將糾紛起訴至法院之后,法院在立案之前進行的調解。筆者認為,在新《民事訴訟法》出臺之后,即使以前立法對于立案之后的調解規定出現了先行調解的字眼,也不宜冠以先行調解的稱謂。先于開庭審理、先于法院判決而進行調解的規定可以稱之為庭前調解、判前調解,與立案調解、庭審調解一樣都屬于訴訟調解,它們與先行調解不在同一層級。與先行調解處于同一層級的應該是訴訟調解和執行調解,三種調解方式分別代表人民法院將調解全程延伸至訴前、訴中和判后的努力。
將先行調解界定為立案之前的調解,即訴前調解,并與訴訟調解、執行調解并列,這種分類對于學術研究以及司法實踐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三種調解性質上的不同直接導致了調解協議效力上的差異。先行調解發生于立案之前,訴訟程序還沒有啟動,因此在本質上應該屬于訴訟外調解,調解協議自身缺乏強制執行力,但可通過后續程序而獲得;訴訟調解發生于立案之后判決之前,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后可以通過調解書結案,調解書具有與判決相同的強制執行力;執行調解發生于當事人依法啟動執行程序之后,執行調解的成功往往以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協議而呈現,本身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也沒有必要獲得強制執行力,原因在于和解協議之外還存在原生效的法律文書,可以為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之時提供強制執行的保障。這體現在新《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款的規定之中,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
二、適用先行調解案件范圍之解釋
(一)關于“適宜調解”解讀的評析
第122條并沒有明確規定先行調解的案件范圍,只是設立了“適宜調解”這一條件。對此應如何解讀呢?李浩教授采取的方法是將糾紛劃分為三類,“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不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以及“可以先行調解的糾紛”。*李浩:《先行調解制度研究》,載《江海學刊》2013年第3期。其中“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指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確定的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的六類民事案件:(1)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2)勞務合同糾紛;(3)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4)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5)合伙協議糾紛;(6)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這種觀點得到了部分學者的支持,有學者進一步建議將先行調解的案件類型規定為:涉及相鄰關系的糾紛;涉及親屬間的糾紛;事實清楚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涉及共有物的使用和分割的糾紛;符合小額訴訟案件的糾紛等為宜,待司法實踐經驗豐富之后再進行擴大或限縮。*參見田海鑫:《論〈新民事訴訟法〉視野下的先行調解》,載《西部法學評論》2013年第6期。
采用以上方法界定先行調解的范圍是存在疑問的。首先,李浩教授對糾紛的這種分類是建立在第122條規定的先行調解的范圍既涵蓋立案前的調解也包含立案后的調解這種認定的基礎上,立案后先行調解的案件范圍當然也就適用于立案前的先行調解。但如前所述,這種認定本身就不正確。其次,這種分類的標準本身也不科學。李浩教授界定“可以先行調解的糾紛”的用意還是盡量擴大先行調解的覆蓋范圍。但是,“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和“不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已經是對于糾紛的一種完全分類,不應存在一種既不屬于“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也不屬于“不適合先行調解的糾紛”的糾紛,在這兩種糾紛之外再出現“可以先行調解的糾紛”在邏輯上就難于證成。再次,筆者對根據糾紛類型來界定糾紛是否適用先行調解的做法也持反對意見。總體而言,熟人之間的糾紛比陌生人之間的糾紛、小額的糾紛比大額的糾紛適用調解固然更有必要也更易成功。但這并非絕對,也不能成為除此之外的案件就不能適用調解的理由。起訴到法院的糾紛是否適合調解應該采用個案判斷而不是類型劃分的方法,這樣才不致于遺漏“適宜調解”的糾紛。最后,《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規定的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的案件與122條規定的先行調解存在太多不同之處,將兩者混為一談是對立法的誤讀:前者是先于開庭審理而進行的調解,而后者是先于立案而進行的調解;前者僅在簡易程序中使用,也就是案件必須符合以簡易程序進行審理的條件,而后者則是針對所有適合調解的案件均可啟動;前者是典型的訴訟調解,而后者本質上應該屬于訴訟外調解;前者之前的應當二字隱含不必經當事人同意就可啟動調解程序之意,只是根據案件的性質和當事人的實際情況不能調解或者顯然沒有調解必要的除外,而后者則明示當事人拒絕調解就不能啟動調解程序。
其實,如果使用術語來概括《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的六類案件,強制調解比先行調解更加接近立法者的真實意圖。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六類案件要求“應當先行調解”,其詞義自然包括了調解先于開庭審理進行之意,但更核心的內涵卻是通過“應當”二字得以展現,即這些案件在簡易程序中,基于修復當事人之間合作關系的目的或糾紛解決費用相當性原理的考量,可以不經當事人同意而直接由法院依職權啟動調解程序。如果將強制啟動調解程序的嚴格的案件適用限制機械套用于新《民事訴訟法》第122條的先行調解,實際上是大大壓縮了先行調解適用的可能性。
(二)“適宜調解”之再認識
如果我們認可先行調解的初衷是將法院調解的觸角從訴中向訴前延伸的話,也就應該同意,凡是法院可以調解的案件就不應該在先行調解中受到限制,單獨限定先行調解案件范圍的做法就明顯與立法目的相悖而不可取。因此筆者認為,“適宜調解的,先行調解”并非限制先行調解的范圍,而是強調不能違法調解或不應在案情復雜、當事人對抗激烈之類的糾紛上徒勞進行調解。“適宜調解”包含兩方面的意思:其一,案件爭議的民事權利屬于當事人處分權的覆蓋范圍,涉及公益的人身糾紛以及非訟案件則不得適用調解。其二,糾紛當事人有調解的意愿,存在調解成功的可能性。這就是說,對于當事人處分權覆蓋范圍內的糾紛,是否“適宜調解”最好由法官進行個案判斷。在對第122條進行解釋時,我們應該始終牢記,立法規定先行調解的初衷是對法院調解時間的延伸和擴展。
三、先行調解實施主體之擴張
(一)委托調解與委派調解之區分
當事人將糾紛起訴至人民法院,即可視為當事人已經表達由人民法院處理糾紛的意愿,人民法院成為先行調解的實施主體也就順理成章。先行調解可以由立案庭負責實施,也可以另行設立負責訴前調解的機構。例如,常州市新北區法院于2006年3月首創設立訴訟服務中心,此后常州中院、江蘇高院先后對這一做法進行完善推廣。*參見張寬明:《江蘇訴訟服務中心“遍地開花”》,載《人民法院報》2009年11月10日。江蘇省的各級法院已經全部設立了訴訟服務中心,80%以上的人民法庭和部分地區的鄉鎮社區設立了“訴訟服務站”。訴訟服務中心承擔的職能除了訴訟服務之外,還包括糾紛化解和糾紛分流,先行調解當然可以成為其工作任務之一。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先行調解可否由人民法院轉介負有調解職能的組織加以實施。對于訴前調解的法院轉介調解,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中給予了肯定。其中第14條規定了立案之前的委派調解: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訴狀或者口頭起訴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職權或者經當事人申請后,委派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或者其他具有調解職能的組織進行調解。第15條規定了立案之后的委托調解:經雙方當事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認為確有必要的,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后將民事案件委托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調解組織或者其他具有調解職能的組織協助進行調解。當事人可以協商選定有關機關或者組織,也可商請人民法院確定。
由于委托調解和委派調解在《民事訴訟法》中都缺乏明確規定,再加之兩者最終都表現為法院之外的調解組織參與調解,混用委派調解和委托調解、將委派調解納入委托調解的現象在法學界非常普遍。其實兩者在性質和效力上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14條對于立案之前使用的詞語是委派調解以區別于15條的委托調解,顯然是因為“委托”意味著將自己的事務托付他人管理,只有在立案之后,人民法院才取得對糾紛的專屬管轄權,可以行使審判權解決糾紛。人民法院同當事人作為訴訟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受到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調整和約束。人民法院也才因此具備將糾紛委托調解的資格。在委托法律關系中,受托人應以委托人的名義處理事務,因此委托調解成功之后可以由法院直接簽發調解書;而委派調解的結果卻應以調解協議的形式呈現,想要獲得調解書則還須通過法院立案,將訴前委派調解轉化為訴訟調解才能實現。鑒于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在學術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嚴格區分委派調解和委托調解實屬必要。
(二)先行調解中委派調解之適用
法學界對于訴前先行調解能否由法院外的調解組織調解也存在爭議。李浩教授認為受理前的調解可“委托”給附設于法院的人民調解室。而趙鋼教授的觀點則相反,對于第122 條規定的“先行調解”,人民法院并無權力通過“委托調解”或“委派調解”的方式作出處理。其理由在于,“先行調解”時人民法院并沒有立案受理,并沒有最終取得或者說實現對這個特定案件(其實應稱為“民事糾紛”)的管轄權;既然法院自己都尚未立案受理,它又憑什么“依職權”將糾紛委托或委派給其他主體去處理呢?*參見趙鋼:《關于“先行調解”的幾個問題》,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3期。
“依職權”委派或委托調解意味著當事人不能拒絕。在正式立案之前,糾紛還沒有處于訴訟系屬之下,人民法院確實不能“依職權”將糾紛委托或委派其他主體處理。但筆者認為,人民法院不能依職權將先行調解的案件委托或委派處理并不意味著先行調解不能由法院之外的調解組織實施。調解與審判在本質上的區別在于調解屬于自治的糾紛解決方式。審判程序的啟動必須以法院正式立案為標志,但調解程序能否啟動的關鍵因素是考察當事人自愿的條件是否得到滿足,而非法院立案與否。質而言之,是否立案能夠決定調解的性質和效力,卻不會對調解能否啟動產生實質影響。人民法院訴前不能依職權將糾紛委派調解與人民法院經當事人同意之后采取這種做法并不矛盾。按照第122條的規定,當事人明確拒絕的情況下是不能啟動先行調解程序的,這樣已經足以保證委派調解的啟動不會違背當事人意志。
在司法實踐中,全國各地法院均存在將訴前調解委派人民調解機構或其他負有解決糾紛職能的機構的做法,訴前調解大量采用委派調解的方式已經是普遍現象。開展學術研究不能對這一事實視而不見。陜西丹鳳縣法院通過糾紛訴前審查對案件進行合理分流,以調委會為主體,以法官為指導進行訴前調解,調動各方力量包括派出所、司法所、土管所、林業站、綜治辦、婦聯等部門共同調解。*參見李政:《關于新修訂民事訴訟法“先行調解”的若干探討——以陜西丹鳳縣法院“訴調對接”為例》,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2012年,揚州市基層法院民商事案件進入訴前調解程序的有16328件,調解成功8270件,訴前調解成功率為50.6%;訴前調解案件成功數占同期新收一審民事案件總數比為28.34%。按訴前調解的方式分,法院附設的調解工作室調解結案4860件,占訴前調解結案數的29.8%;法院對外委托調解案件585件,占訴前調解結案數的3.5%;由法院法官自行調解案件10883件,占訴前調解結案數的66.7%。*參見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訴前調解運行現狀及其對先行調解制度實施的啟示》,載《人民司法》2013第19期。可見,將社會力量引入訴前調解的司法實踐早已如火如荼,并且運行情況良好。第122條一直被視為立法對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廣泛采用的訴前調解的肯定而不是否定。即使從立法者的意圖進行解釋,先行調解可以適用委派調解也無疑義。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而言,先行調解過程中適用委派調解可以更好貫徹各級黨委政府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的工作體系的倡議。出于應對日趨復雜的社會矛盾和糾紛的需要,“三調聯動”機制在2006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報告以及2013年溫家寶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等重要文件中一再得到強調。“三調聯動”已經被視為接納群眾訴求、維護群眾合法權益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期黨和政府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舉措。*參見李德恩:《社會管理創新視野下的“三調聯動”》,載《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1期。人民法院在其主導的調解中引入社會力量、行政力量的參與,是積極融入三調聯動工作體系的具體表現。
四、先行調解與訴訟程序之銜接
(一)立案程序之跟進
第122條規定的先行調解制度使得法院調解向訴前延伸具有了法律依據,必然成為人民法院構建的訴調對接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訴調對接是訴訟和調解的雙向度對接,向度之一是調解進入人民法院主導的糾紛解決的整個過程,向度之二是訴訟程序對調解支持和銜接。訴調對接后一向度對于先行調解而言有兩方面的意義:調解失敗后訴訟程序的快速跟進與調解成功后通過法定的司法程序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
這就意味著,在經過先行調解不能達成協議時,人民法院應該及時立案,啟動訴訟程序解決糾紛。調解進行與訴權保障并行不悖。新《民事訴訟法》第123條規定,對于當事人的起訴,人民法院認為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立案,并通知當事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作出裁定書,不予受理。趙鋼教授發出疑問,第122條的先行調解是否應遵守七日時限的規定呢?他的回答是應該遵守,不過同時認為如果原告同意,可以在七日時限屆滿之后繼續先行調解。*參見趙鋼:《關于“先行調解”的幾個問題》,載《法學評論》2013年第3期。趙鋼教授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將先行調解的時間計入七日期限,不過將原告同意繼續調解作為例外,可以突破該時限。
如果將先行調解的時間也納入到七日的立案時限,立案庭將難于從容組織和開展先行調解工作。在原告起訴之后如果實施先行調解,除了調解進行需要時間保證以外,還存在通知被告和調解機構(委派調解)、與被告協商調解時間等問題。與其讓時限被突破的例外規定在實踐中成為常態,導致七日時限規定有名無實,還不如允許先行調解的時間在法定范圍內不計入時限。在司法實踐中,各地法院普遍規定了先行調解進行的時間。規定先行調解的時間并不意味著不遵守七日立案時限,而只是進行先行調解的時間在法定期限內不計入立案時限,超出法定期限的時間則應計入其中。這樣,先行調解的進行在時間上就有了保障,而且不會以侵犯當事人訴權行使為代價。
(二)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之賦予
對于先行調解的效力,有學者主張,由于先行調解是在法院認為案情適宜且當事人并不拒絕調解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旦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主動認可其效力,無須當事人申請。*參見胡曉濤:《關于先行調解若干問題的思考》,載《江蘇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人民法院主動認可調解協議效力表面上方便了當事人,但同時也剝奪了當事人的選擇權。將司法為民的真諦“為民服務”演繹為“為民做主”并非處理民事糾紛的正確做法。當事人同意先行調解并不意味著當事人同意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更何況由法院認可先行調解的效力,不論是立案后以調解書結案還是通過司法確認程序加以進行,都是需要收取一定費用的,人民法院主動認可先行調解效力無異于強制消費。
筆者認為,由于先行調解在性質上屬于訴前調解,也可以說是訴訟外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只應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在達成解決糾紛的合意之后,應允許當事人在撤回起訴書和要求人民法院認可其效力之間做出選擇。如果當事人選擇后者,人民法院應遵循便民原則,依先行調解實施主體的不同而分別對待。由法院立案庭或其他專門機構組織實施的先行調解,糾紛一直在法院的掌控之下,達成調解協議之后可以直接立案并依法制作調解書結案。由人民法院委派人民調解委員或承擔調解職能的行政機構等調解成功的案件,鑒于當事人之間已經不存在實體爭議,啟動非訟程序更加符合立法原理。新《民事訴訟法》在第15章“特別程序”第6節中專門增加了“確認調解協議案件”,當事人可以據此向委派調解機構所在地的基層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程序。為避免或減少當事人在不同法院之間來回奔波之累,應該規定法院訴前只能委派本院所在地的負有調解職能的組織進行調解,這樣就能保證受訴法院和司法確認程序的法院是同一基層法院或同一地域的上下級法院,為當事人可能選擇的后續的調解協議司法確認程序提供很大方便。不論是以立案后以調解書結案還是通過司法程序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都不能認為是先行調解本身具有的效力,而應當理解為是訴調對接的結果,即通過訴訟程序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通過這種方式,先行調解解決糾紛的實效性將得到很大提高。
[責任編輯:王德福]
Subject:The Restatement about Mediation First System:Time Limit and Application Expansion
Author & unit:LI Dee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0,China)
There is much controversial in the jurisprudential circle about the rule of mediation first in Article 122 of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The word “first” can show its meaning by compared with a specific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sing rule of the terms, mediation first is such kind of mediation which is carried on after the parties file the lawsuit and before the case is registered.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 “suitable for mediation” stresses to prohibit illegal mediation or the consumption of mediation resources in vain. We can make the judgment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people's courts can implement the mediation first either by the case acceptance tribunal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delegated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he conciliation agreement has the effectiveness just the same as the common civil contract, but the parties can voluntarily entrust the mediation agreement with enforceable effectiveness by making a mediation record or initiating a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mediation first;lawsuit mediation;the mechanism of litigation and mediation connection
2014-11-05
李德恩(1969-),男,四川隆昌人,法學博士,九江學院政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事訴訟法學、調解制度。
D915.2
A
1009-8003(2015)02-0047-06
基金薦: 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2013年)規劃項目《“調解優先”司法政策研究——以新〈民事訴訟法〉實施為視角》(13FX1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