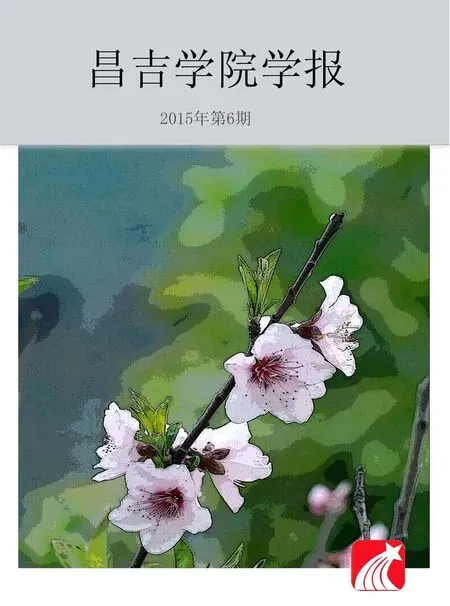論星漢七言絕句的“趣”
劉坎龍
(新疆教育學院人文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43)
“詩趣”,是創作主體的一種審美思想與情趣在詩歌文本中的反映。其突出特征是在韻味雋永之外,以純真的情懷或洞徹的智慧,創造出妙趣橫生的詩境,在展示作者的情感與人生智慧的同時,給人一種生機勃發、無拘無束而又活潑幽默的愉悅感。在新疆當代詩詞創作中,星漢的一些七言絕句就具有這樣的特點。其作品中既有純真放任的情趣,也有洞徹人生的理趣,甚至嬉笑戲謔的諧趣。而詩歌意境往往生動活潑、妙趣橫生,在韻味雋永中彰顯著“詩趣”之美。分別論述如下。
一、純真放任的情趣
抒情是詩歌的本質特征,也是詩歌動人的魅力所在,但由于詩人的性情不同,詩歌抒情也就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星漢是一位多情而富于靈性的詩人,他的一些七言絕句在抒情時,往往把“情”和“趣”巧妙相融,從而使詩歌畫面生機活潑,在表達純真情思的同時,彰顯著靈性飛動的趣味,讀之令人解頤。比如描寫親情的《劍歌被選為少先隊中隊長》一詩,便是通過鮮活情境的描摹,在幽默風趣中表達對女兒成長的欣慰。詩云:
大紅等號臂間懸,近日雙眸斜左邊。
只怕針穿額頭破,白牌才未掛眉前。
詩寫女兒被選為少先隊中隊長時的家長心態,但卻蕩漾著盎然的情趣。所謂“大紅等號”,指的是少先隊中隊長的徽章標識,一般用白底方形塑料制成,中有兩道紅杠,佩帶時用別針別于左臂衣袖上。被選為中隊干部,是小學生品學兼優的表現,故而學生與家長都比較看重。但這里家長的自豪,卻是通過孩童的情態來表現。“近日雙眸斜左邊”一語,采取白描手法,聚焦于瞬間的動作,勾勒出鮮活的人物形象,將孩子當選后的自豪、欣喜、美滋滋的神態,表現得活靈活現。而“只怕針穿額頭破,白牌才未掛眉前”兩句,可謂異想天開、妙趣橫生。作者以詼諧的語調在夸飾中對孩子的得意神態加以議論,于貌似嘲諷、戲謔的背后,深藏的是對女兒進步的關愛與欣喜。此詩濃郁的“趣”,完全出自于孩童情思的天真、父親愛女的深切,以及在真情中生出的異想天開的夸張。這種純真而放任的情思,以風趣的筆調表達,便使詩歌境界蕩漾著濃郁的喜劇氛圍,令人在捧腹之后感悟詩中所蘊含的父女摯情。
鮮活生動是“詩趣”的突出特征,但詩的情趣之美,更在于情感的絕假純真、畫面的自然天成。星漢的一些七絕,往往在活潑的生命境界中,體現出一種情真景真的審美趣味。如《回家初見劍歌》:
片時呆立似含疑,俄爾高呼報母知。
恐我今天還復去,抱頭雙手不稍離。
詩歌描寫離別多日后與女兒初見的情景。由于作者抓住剎那間靈動的情境,惟妙惟肖地描繪出孩子初見父親時的“憨貌傻態”,便使詩歌彰顯著濃郁的趣味。這里不論是“片時”的“呆立”,還是“俄爾”的“高呼”,都把女兒初而乍疑、進而驚喜的情境,刻畫得栩栩如生。而“抱頭雙手不稍離”的動作情態,進一步表現了女兒恐怕父親再度離開的依戀之情和憨癡之貌。畫面的鮮活生動,使詩歌充滿著濃郁的情趣之美。
其他如《回鄉偶書五首》其一“墮地當年帶土腥,霜絲難掩舊神情。離鄉縱使鄉音改,翁媼猶能喚乳名”。作者以質樸的語言,形象地寫出回到闊別三十七年的故鄉見到鄉親父老的情景。“墮地當年帶土腥”“霜絲難掩舊神情”,雖覺離奇,但卻在看似矛盾的敘述中,突出了“翁媼猶能喚乳名”的驚訝情趣。這種情趣,不僅把與父老鄉親乍見時的驚喜場景與人物神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而且使隱藏于形象背后的情感溢于言表,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象空間。可以說在藝術上與賀知章《回鄉偶書》中“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情趣,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再如其《入天山遇微雨口占》:“雨點一車云一溪,雨停又得半天霓。時髦我欲學商賈,運向家中售與妻。”一、二句寫雨中、雨后天山云霓景色,已覺新奇;三四句又忽生奇想,欲將山中美景“運向家中售與妻”,這種奇思妙想與純真、放任的情思相交融,便使詩歌染上了動人的情趣。
至于一些描寫新疆風物、少數民族人物的七絕,也往往趣味十足,在出神入化中令人解頤。請看《草原日出》:
日輪拔地帶風聲,千里新紅壓草青。
堪笑牛羊夢醒后,卻尋昨夜滿天星。
詩歌描寫草原日出,既雄渾有力,又新奇無比。詩中的“日輪”可以“拔地”而起,可以“帶”動“風聲”,可以“壓”低千里青草。尤其是“牛羊”還能“夢醒”,還能尋找“昨夜滿天星”。這種天機靈性的發動,使得全詩寫景狀物,奇妙有趣而又富于生機,一幅生動活潑、色彩鮮明、趣味濃郁的草原日出風景圖躍然紙上。再如描寫維吾爾族孩童的《開都河農家小坐書所見》,也充滿著情趣。詩云:
白楊影里面河居,鴿弄晴空落照虛。
坦腹巴郎游泳后,拖泥帶水笑騎驢。
詩歌一、二句寫農家居處的優美,清新自然。而“面河居”一語,則為下文聚焦于坦腹巴郎的游泳做了鋪墊。三、四句重點寫維吾爾族兒童的頑皮可愛,“拖泥帶水笑騎驢”的畫面,生動活潑,調皮的頑童形象栩栩如生,情趣盎然。其《天山見哈薩克打草者,戲贈》,以輕松的筆調描寫哈薩克牧民打草,也是妙趣橫生。詩云:
扇鐮揮起落青云,長嘯一聲山外聞。
多少人間剃頭匠,盡施手段不如君。
“扇鐮”,是新疆牧民秋季打草的工具,這種鐮刀手柄很長,比人還高,其割草不用彎腰,而是站著掄動大鐮,所以首句才有“揮起落青云”的描寫。一、二句具體描寫哈薩克牧民打草的畫面,“揮起”“長嘯”的動作、情態,可謂形神兼備。后兩句在觸景生情的感慨中,贊嘆牧民打草技巧的嫻熟。“多少人間剃頭匠,盡施手段不如君”的比擬,既新奇又反常,從而使詩歌洋溢著輕松活潑的情趣。
袁枚曾說:“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詩。”[1]星漢這些富于情趣的七絕,首先是有著“不可解之情”,不論是對女兒的至愛,還是對少數民族人物的描摹,都是情真意切,從肺腑流出。而其對這種情懷的表達,則又純真放任、無拘無束,故而鮮活生動,情趣盎然。
二、洞徹人生的理趣
詩歌中的情趣如果與某種意理相結合,便生成了作品的理趣。與“情趣”相比,這種“理趣”除了通過感性情懷來體驗之外,更需要悟性的參與。所以嚴羽在提出“詩有別趣”的同時,一再強調“詩之道惟在妙悟”。[2]星漢是詩人,也是學者型的大學教授,職業的特性,使其思慮精深。所以在游覽山水、登高臨遠、觸景生情之際,往往對物沉思。那些瞬間的感悟、理性的思考,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表達出來,便使作品帶上了濃郁的理趣色彩。如《泛舟布倫托海》:
上下晴光共雪山,鷹銜云影逐輕船。
人間顛倒尋常事,彼在清波我在天。
詩歌描寫布倫托湖泛舟之景:晴空萬里,天高日晶,水面清澈,湖平如鏡。雪山冰峰倒立水中,天上的雄鷹銜著云朵在湖中追逐著游船,而乘船游覽的詩人卻像在天上一般。這種湖光天色相映相融的奇妙境界,本身就有著獨立的耐人尋味的審美情趣。但由“彼在清波我在天”一句,引發的“人間顛倒尋常事”的瞬間感悟,卻又包含著發人深省的哲理,給人許多社會層面的聯想和思考,詩歌也就有了“弦外音”。而詩中的“趣”,則來源于詩人對鮮活詩境的營造,以及聰穎睿智的靈性對社會人生的穿透與感悟。“彼在清波我在天”的形象描繪,既打破了常情常理,又符合特定情境的真實。正是這種“熟悉的陌生化”,使詩歌理趣相容,渾然天成,引起讀者極大的興趣。
再如《游路南石林》:
處處無門處處門,通幽曲徑費精神。
平生不會彎彎繞,自是前程碰壁人。
詩歌描寫游覽石林的感受。前兩句狀物抓住具體特點,可謂栩栩如生,曲盡其妙。但詩歌并未停留在景物的表象,而是深入一層,描寫自己身臨其境的感悟。“平生不會彎彎繞,自是前程碰壁人”兩句,表面看來是自嘲,實際上寄寓的是作者光明磊落、不會見風使舵的耿直性情。在隱深婉曲的聯想中,給人以為人處世的啟迪。由于詩人營造出富于詩情畫意的詩境,抒寫的又是自己的直觀感悟,完全出自天然,不見造作痕跡,故而顯得事理渾成,意趣盎然。
星漢的一些七絕,有時并未營造絢麗的意境或意象,而是憑借作者的妙悟與睿智,在敘述議論中凸顯作品的“理趣”。比如《吐魯番過火焰山戲作》:
妖猴借扇枉相傳,未必死灰無復燃。
因在人間最低處,便將窩火怒沖天。
詩歌名為“戲作”,實則有著深刻的寓意。一、二句在觸景生情的感悟中直接議論,否定了孫悟空借扇撲滅火焰山大火的故事,為下文說理作鋪墊。三、四句是作者自己對“火焰山”形成原因的重新解釋:“因在人間最低處,便將窩火怒沖天。”其妙處在于將對自然現象的感悟,上升為社會人生的哲理。處于最低處,往往心有不甘,積郁過久,必將怒火沖天。表明人的生命激情,不會在壓力下屈服,而積蓄的越久,爆發得也越猛烈。由于火焰山處于全國海拔最低的吐魯番地區,所以這里由具體形象而引發的人生哲理,并不枯燥乏味。其《乘索道上三清山感賦》也有同樣的特點:
果然一步可登天,我為高升彼為錢。
從此懸空難自主,由人操縱暗中牽。
此詩描寫的是登山坐索道的感悟,顯然也是有意說理。但由于是通過對具體事件的議論來表現,故而不乏神韻。“我為高升彼為錢”中的“我”和“彼”,并非限于游客乘索道一事,而是在眾多“一步登天”的事例中,有著普遍意義。至于“懸空難自主”的描摹,也會讓人想到許多社會現象,都給人們留下多重思考的余地。從而使有著不同閱歷的人,產生不同的聯想和感悟,獲得不同的哲理意趣。
袁中道曾說:“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瓏而多態,水之漣漪而多姿,花之生動而多致,此皆天地間一種慧黠之氣所成,故倍為人所珍玩。”[3]但自然中的趣,還需要詩人的靈機妙悟,才能在作品中得以呈現。正因為星漢有著聰慧的靈機,以及穿透表象的感悟能力,所以不管是面對玲瓏多姿的自然景觀,還是世人皆見的平常現象,多能參透其中的奧秘,悟出其中的新意與深意,使作品彰顯出生機靈動的理趣,也令讀者在欣賞作品的同時,獲得一種人生的啟迪。
三、嬉笑戲謔的諧趣
情趣向著機巧、戲謔的方向發展,便生成了作品的諧謔之趣。星漢一些抒發日常生活中自我懷抱的七言絕句,往往寫得風趣幽默,甚或滑稽戲謔,從而彰顯出一種“諧趣”。但這種諧趣,并不是低俗的噱頭、笑料,而是包含著深刻的社會內容。是將悲劇情懷以喜劇的筆觸來展示,可謂“戚而能諧”。如《買書后作》:
不沾煙酒只因貧,說與他人未信真。
月月薄薪書店了,索錢每每惹夫人。
學者型知識分子的一大“嗜好”,就是買書,這是人之常情,本無可厚非。但在經濟拮據的年代,自然要擠壓家庭的生活費用,也會引起家庭主婦的不滿。但一般的男人為顧及“戶主”的面子,絕不會對外人說。而星漢不但說了,而且還寫入詩中要流傳下去,其胸襟之曠達可想而知。“索錢每每惹夫人”一句,將執著敬業而又生活拮據所引起的“家庭矛盾”以及生活的酸楚,用諧謔的筆調來表達,便生成了異樣的審美效果。有類似經歷的人都會依據自己的切身體會,去想象那具體的畫面。
面對工作的辛苦、待遇的不公等現實問題,作者也往往巧妙地運用修辭手法,以輕松、逗趣的筆調表現出來,使作品彰顯著幽默詼諧的情趣。如《論文完成后口占》:
千古文章幾夜熬,書生待遇往高調。
按勞分配非空話,贏得金星滿眼飄。
詩中有教師撰寫學術論文的辛苦,有對行業之間分配不公的牢騷,還有對“空話”的尖刻嘲諷,以及作者萬般無奈的自嘲。其中“按勞分配非空話,贏得金星滿眼飄”兩句,以雙關的手法,將寫論文熬夜時贏得滿眼飄的“金星”的“金”,與金銀、金錢的“金”相關聯,讓人在笑聲中,感悟到作者內心的憤慨。詩歌所述本為辛酸之事,但卻寫得風趣、詼諧,正見出作者那種擺脫俗套的感悟能力和性靈獨抒的才氣。
其《葡萄溝食葡萄》也帶有同樣的特點。詩云:
周身染綠入冰壺,一飽已貪無再圖。
萬貫賈兒休傲我,而今滿腹是珍珠。
于吐魯番葡萄溝吃葡萄,新疆人可謂司空見慣,但星漢卻寫出了新意。一、二句在比喻中描寫飽餐葡萄的自得神態,極其自然。但接下來“萬貫賈兒休傲我,而今滿腹是珍珠”兩句的陡然急轉,卻令人驚悚不已。作者奇思妙想的比喻,使得清貧知識分子的狂傲、郁勃之氣,躍然紙上。然而細讀,又不禁啞然失笑,因為你這“珍珠”,不是那“珍珠”啊!其實作者又何嘗不知如此,他不過是借助比喻與雙關,來營造詼諧的氛圍,在自嘲中抒發知識分子的清貧與牢騷。這種內心的不平,以幽默詼諧的語言出之,便使作品充滿了滑稽可笑的諧謔之趣,令人釋卷解頤。再如《打鼾自嘲》:
豪氣儲胸力萬鈞,南柯夢里顯精神。
平生功業君休笑,也是驚天動地人。
睡覺打鼾本是生活中的常事,星漢以諧謔化的筆調寫來,便形象地再現出詩人豁達、超逸而又帶著幾分牢騷的個性情懷。這不僅得力于“南柯夢”典故的點染,更得力于“驚天動地人”這一雙關手法的運用,使得作品在逗人發噱的同時,也傳導出作者的諧謔性情,可謂風貌獨具。
前人論詩趣常常強調一個“奇”字,而這種“奇”又應符合日常的人情物理。比如蘇軾就說:“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曰趣。”[4]星漢的一些絕句帶著諧趣,正在于其描寫人情物理時,以“反常”凸顯新意,但細細玩味,卻又深契事理,余韻無窮。如其《初戴老花鏡自嘲》:
于無有處有還無,明鏡高懸慰小儒。
世事豈能渾到此,用真眼看便糊涂?
人老眼花自是常理,眼花配鏡更是常情,在這老年人必須經歷的小事中,詩人卻悟出了社會中的一番道理:“用真眼看便糊涂”。作者將日常生活中互相矛盾、反常錯亂的細節,加以提煉、點染,在近乎開玩笑的幽默口吻中,對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加以嘲諷,含蓄深刻而又詼諧別致。因其“反常”,詩歌就有了新穎性,因其“合道”而又以輕松、俏皮的語言說出,便在睿智中彰顯出靈心穿透事象的諧趣。
再如《過干溝遇修路,走便道》也飽含著奇妙的諧趣:
車走黃塵彌兩間,萬山如鬼路盤盤。
出溝也讓鐘馗怕,我是媧皇上古摶。
詩以夸張的手法,寫自己旅途中因干溝修路而走便道,以至于灰頭土臉、令鐘馗也怕的情景。而“我是媧皇上古摶”一句,不僅想象新奇,更是靈心慧口、灑脫風趣。南宋楊萬里曾說:“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5]星漢正是以其特有的性靈與才氣,把日常生活中的感悟,以灑脫詼諧的方式道出,在新奇中給人以“趣”的享受。
幽默詼諧之趣,作為詩歌中的一種風格,自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其實古人論詩,也有強調諧趣的。如宋人黃庭堅就曾說:“作詩正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6]所謂“出場”,就是在終篇之時,要讓讀者有意外的收獲。雖然諧趣不一定非限于收結不可,但黃庭堅對這種風格的肯定,足以說明詩歌的諧謔之趣是早已有之的客觀存在,也彰顯著詩歌風格的多姿多彩。當然,風趣也好,諧趣也罷,雖然強調的是“趣”,但這種“趣”要有豐厚的內蘊,而不是淺俗的噱頭。星漢的一些絕句,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在引人深思的同時,展現著妙趣橫生的“娛人”效果。
四、“詩趣”生成的原因
陳伯海先生在談到詩趣時曾說:“‘趣’多起自人的感受,立足于人的詩性生命結構中的感性與悟性的機能,再由人的審美創造與欣賞活動將這一機能傳遞并落實于作品之中,構成作品的審美質性。”[7]可見,詩歌之趣源自于詩人之趣。星漢的一些七言絕句,所以能展現出生動活潑的詩趣,與其性情、學養以及嫻熟的詩歌創作技巧密切相關。
第一,星漢性情曠達灑脫、自由自在,接人待物無拘無束而時帶幽默,有著詩人的睿智與靈氣。故而登高臨遠、觸景觀物之際絕不膠著,而是在思緒飛揚中,生出洞徹事理的靈機妙悟,其作品也就染上了靈機飛動的詩趣。正所謂“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所以我們說,詩歌之“趣”,是詩人主體之“趣”的投影。在創作過程中沒有詩人性情與感悟的共振,詩趣是難以呈現的。
第二,作者的學養背景熏染著詩趣的生成。星漢作為大學教授,在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培養中,主講宋元文學。宋代在詩學批評史上,是以“趣”論詩的昌盛時期,諸如“風趣”“理趣”“禪趣”“諧趣”等,都在宋人的詩歌評論中頻頻出現。宋人在創作實踐中也追求著“趣”,蘇軾、黃庭堅、楊萬里都是典型的代表。而元代抒情文學的主體是散曲,其在審美風貌上與詩詞的主要區別正在于詼諧風趣。至于元雜劇中的插科打諢,也是戲曲娛人的重要手段。星漢長年累月沉浸于這些內容之中,自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詩歌創作時創作主體的心理機能,從而使其詩歌呈現出濃郁的“趣”味色彩。
第三,作者在感悟到詩歌意象趣味的同時,還應該善于表達。所以詩人純熟的創作技巧,是詩歌趣味得以充分呈現的重要條件。星漢精通詩律,在觸景沉思之際,往往能以嫻熟的技巧表達奇思妙想,得心應手地創造出鮮活生動、自然天成而又妙趣橫生的藝術境界,從而使作品飽含著豐富雋永、極具娛樂感的動人情趣。
總之,星漢的七言絕句洋溢著濃郁的詩趣。這種自然天成、生機勃發、妙趣橫生的藝術境界,來自于詩人深切的感性體驗,穿透事物表象的睿智與悟性,以及自得自娛而又無拘無束的瀟灑曠達情趣。
[1]袁枚.隨園詩話(卷五·答蕺園論詩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2]嚴羽.滄浪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
[3]袁中道.珂雪齋集(卷一·劉玄度集句詩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惠洪.冷端夜話[A].中國歷代詩話選[C].長沙:岳麓書社,1985:367.
[5]袁枚.隨園詩話(卷一)[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2.
[6]王直方詩話[A].宋詩話輯佚[C].北京:中華書局,1980:14.
[7]陳伯海.“味”與“趣”——試論詩性生命的審美質性[J].東方論壇,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