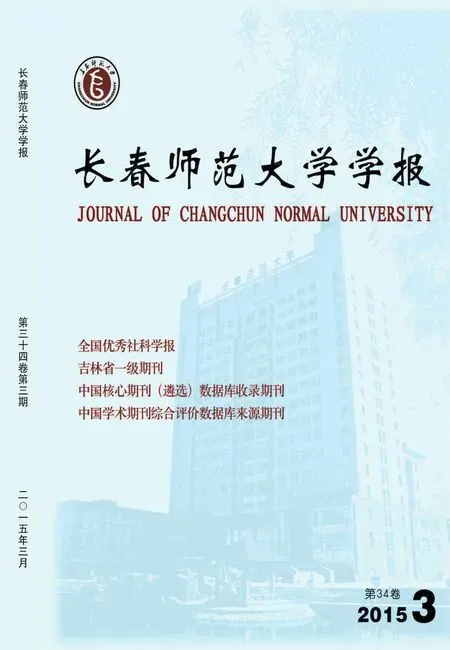法國遣使會司鐸馮烈鴻的溫州生涯
黃 漢
(溫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溫州325035)
溫州素有“東方的耶路撒冷”之稱,關于溫州當地基督教的研究已然成為學術熱點。對傳教士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歷史文獻的基礎上,才更有說服力。透過有關傳教士群體的文獻,充分理解他們如何影響溫州的近代化,進而如何豐富溫州當地的宗教文化,可以得到比較公正客觀的認識。鑒于此,筆者以晚清民國時期法國天主教神父馮烈鴻的游記手稿為基礎,結合其差會——遣使會的歷史背景,對馮烈鴻的著作文本進行解讀,旨在還原歷史信息,豐富當前溫州基督教的研究成果。
馮烈鴻神父來自法國天主教遣使會。該差會成立于1625年,最早于1699年入華,屬于中國天主教四大差會之一。就規模而言,遣使會的影響力不及耶穌會和方濟會,這或許與遣使會主要把關注重點放在貧困的農村有關。耿升指出,“遣使會的宗旨是向鄉間貧苦民眾們派遣布道使者、在貧窮和偏僻地區創建修院以培養原住民中的青年神職人員、積極從事慈善事件。”[1]531耶穌會自16世紀入華以來,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這種初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利瑪竇等人的文化適應策略,但最終還是避免不了“禮儀之爭”的爆發,促使其他教派向教廷告狀。教廷傳信部接到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命令:北京傳教區由遣使會全權取代。遣使會傳教士自教廷解散耶穌會的1773年起大舉進入中國。至此,遣使會獲得大幅度的發展。據在華遣使會士助理主教方立中(P.-J.van Den Brant,1903-1908年在華)的《入華遣使會士列傳》(1936年北平版)統計,1697-1935年間在華遣使會會士共有946人。他們之中絕大部分來自法國,部分來自荷蘭、波蘭、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國。他們主要活動在北京、直隸、浙江、江西、上海、內蒙古、四川等地區,在京、津、滬和寧波地區力量最強、最為活躍。
一、馮烈鴻溫州生平
馮烈鴻(1876-1949)的法文原名為Cyprien Aroud,在法國羅納省(Rhone)里昂市出生,于17歲被接收進修院。[1]6391899年,被派遣來到溫州接任教務,負責溫州、處州兩地的教堂工作。
語言交流問題常常成為布道的嚴重障礙,溫州的方言令馮烈鴻感到頭疼,使他備感學習溫州方言的重要性。為此,他特意每天跑到廚房,聽廚師的插科打諢,終于能會意別人的講話內容。馮烈鴻專門聘請一位中文老師,教授他中文。馮烈鴻每次布道之前都要先用法文將布道稿寫出來,再翻譯成中文,經由中文老師的指導再用拉丁拼法轉換成溫州話,經過多重校對修改、反復背誦,讓每一位慕道友能基本聽懂。這樣,馮烈鴻很快掌握了語言技能,開始了他的旅游布道。馮烈鴻經常往返于溫州、處州兩地,為信徒施洗,與教友保持密切的交流,并在各處建立分堂。
教區建設方面,馮烈鴻依托其他教會組織的資助,籌集大量的募捐資金,又額外獲得溫州董若望醫院院長的協助和支持,拓展教區,建立大大小小的教堂和禮拜點,給當地的信徒提供每日禮拜的活動場所。教區網點幾乎遍布溫州地區,就連周邊的縣城也成立了一些中心點,例如平陽的西坑天主堂、瑞安的城關天主堂、龍灣的滄頭天主堂等等。
在培育信徒方面,馮烈鴻秉公辦理教內外事務。他將教務發展委托給有能力的人,對教內的不法分子嚴懲不貸。
在教育醫療方面,馮烈鴻對教堂內部進行了整改,使其預留出一部分場地以便學童學習念誦經文,在墻體四周建立書架并購置大量藏書,供信徒研習天主教教理。馮烈鴻還致力于帶動地方醫教文衛事業的發展,分別成立了董若望醫院、平陽善導堂、增爵中學、平陽西坑一泉小學等。
馮烈鴻曾在法國巴黎出版《遣使會年鑒》,并在寧波《小消息報》上發表不少報導文章,后在法國出版《傳教生涯》一書。他的家書甚多,曾在法國油印成冊,已知的達11冊之多,累計100萬字以上。馮烈鴻于1928年因眼疾返回法國。
二、馮烈鴻與《傳教生涯》
《傳教生涯》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馮烈鴻第一次布道的場景、探訪信徒的熱忱、抗臺賑災的舉措;第二部分主要講述他對當地社會的認識,記錄有關溫州家庭、行政司法、教育宗教、社會陋習等方面的內容;第三部分則記錄他的一些隨感沉思,包括對海神、婚姻、烈士、中醫、葬禮等的看法。
馮烈鴻以一個人類學家的視角真實地記錄溫州當時的人口狀況。他在《傳教生涯》中寫道,“總體上來講,在平陽,瑞安,樂清等地區,無論是平原還是山谷,部落氏族的形態似乎早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竟是人口雜居和混居,集群與合作成為一種主流。”[2]107然而,這種合作有時候卻具有一定的破壞力。例如,“在大沙村(Dasa),頭哈村(Toha),繆氏咖(Mousika),塔子村(T’azi),卡老村(Kalao),渭石村(Vouzi),大后村(Daho)等地的平原上都有一塊廣袤的田園,在那里人們只種一種植物,那就是罌粟,萬惡的毒品來源。”[2]80
馮烈鴻指出:“自從1907年以來,皇帝為了制止毒品的種植就已經積極地采取嚴厲的措施:鞭刑,監獄,罰金,沒收財產。然而種植罌粟的土地比原本應該用于播種小麥或者油菜高出九倍;有一個農民似乎對禁毒政策充耳不聞,他僅有少量的財產,更沒有什么資本,卻要養活人數眾多的家庭,于是這個可憐的男人只能依靠種罌粟來維持生計,從而逃避厄運。他目前耕種的那幾個鴉片場地,都是向地主租借的,那個地主還允許借款。如果鴉片被強行掠奪,那么農民一家人就只有等著餓死了。”[2]81社會的階級差異日益分化,使老百姓寧可種鴉片也不種糧食,可見當時的社會稅賦的沉重。
馮烈鴻在該書的第二部分第二章節專門論述當時的官場制度,在本章開頭描繪了典型的官場特征,“我們溫州接連換了四個區長,其中三個調到后來更加富庶的地方上任,他們變本加厲地使用陰險狡詐的手段斂財,巧立收繳鴉片之名目,鎮壓民眾,盤剝農民。”[2]111馮烈鴻詳細描寫了現任“道尹大人”的形象,“劉先生是我們的行政官員,他手握實權,年紀很輕,才25歲,同時也是一個軍事分子,血氣方剛,好用武力”[2]111。這位行政官員劉先生突發奇想,以收繳鴉片為名,到處抓捕鴉片吸食者,以禁煙之名向百姓敲詐勒索。
馮烈鴻一方面融入當地文化,促進溫州基督教精神塑造,另一方面撰寫大量書信、游記,向海外傳播溫州形象。他以一位外國旅居者的身份記錄著發生在異國他鄉的每一件事,行文中飽含著他對當時社會的關注和同情,這一點或許與其差會背景有一定的關聯。
三、總結
馮烈鴻不僅身體力行地通過興辦醫療教育促進當地的社會發展和進步,還通過撰寫回憶錄《傳教生涯》幫助更多的人認識和了解中國。將傳教士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可以更好地反觀自我。我們研究近代溫州傳教士的意義還在于關注當下,了解歷史上溫州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以便為我們當下的海外傳播服務。
[1]榮振華,等.16-20世紀入華天主教傳教士列傳[M].耿升,譯.桂林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2]Cyprien Around.La Vie en Mission[M].Vichy:En vente Maison du Missionaire,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