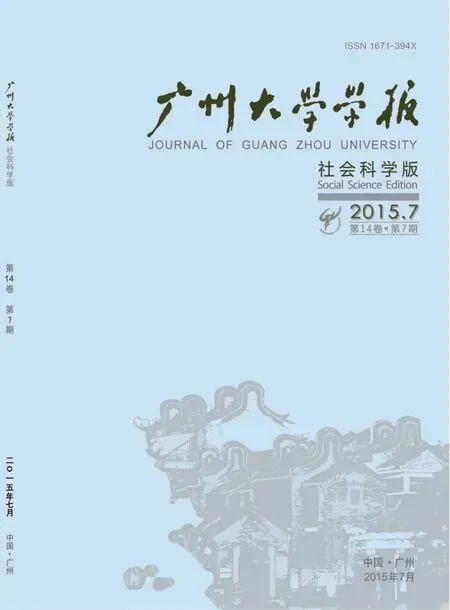胡塞爾視域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
夏 宏
(廣州大學 政治與公民教育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引 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批判理論第二代思想家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診斷,其意是:以權力為媒介的政治子系統與以貨幣為媒介的經濟子系統在整個社會中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取代了以語言為媒介的生活世界,使得本應該為這些子系統提供意義和價值的生活世界處于“殖民地”狀態。這一不正常現象是導致晚期資本主義各種社會危機的源泉。值得指出的是,“生活世界”這一概念最初源于現象學家胡塞爾。在胡塞爾那兒,生活世界還只是一個科學批判的概念,而不是社會哲學的概念。[1]28但是,透過胡塞爾對科學,特別是現代實證的自然科學及其思維方式的批判,我們可以發現另一種意義,即現象學意義上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生活世界被另一個世界——科學世界所支配,也正是在這種“鳩占鵲巢”的局面,歐洲科學,進而歐洲人性才出現了危機。
一、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
一般來說,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相對應,它以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為研究對象。從事自然科學研究是人類非常重要的實踐活動之一,迄今為止,人們已在這一研究領域獲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界和人本身因這些巨大成就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于任何一位科學家或一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來說,一旦他們把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確立為基本目標和追求,并按照相關的方法(通常稱之為“科學方法”)和他們自己的工作興趣而行動,那么,圍繞著這些工作就形成了一個特定的職業性領域——科學領域。同時,也正是在這個領域中,既存在著真實的知識,也潛在地存在著“未被認識的、隱蔽的、但是借助合理的方法能夠認識”的問題[2]548-549。這種領域,與科學家們特有的興趣、信念以及與這些信念相關的基本理論、觀點、假設和和方法,構成了自然科學的世界。用胡塞爾的話來說,科學世界就是科學家的世界,它僅僅是由科學真理構成的合目的的領域,具有“科學上真的存在”[2]564。由于自然科學是以客觀的、普遍的理解為取向,自然科學的世界也就是“客觀科學的世界”[2]549或“科學世界”。人類的活動多種多樣,科學及科學研究是人類各種實踐活動中的其中之一,因此,科學世界如同我們平時所說的各種具體研究領域,如文學世界、宗教世界、動物世界、植物世界等一樣,也只不過是人類活動所涉足的多種領域中的其中一種而已。
生活世界這個術語已在1912年齊美爾的生命哲學領域中曾得到過使用,胡塞爾大約在1917年開始使用“生活世界”這一術語[3]182,胡塞爾有時也將其稱為“周圍世界”“日常經驗世界”等。直到1936《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中,這一術語才具有其現象學意義。由于它是在他最后的著作中得到關注,這個術語的含義是相當的模糊。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生活世界是“唯一現實的世界,現實地由感性給予的世界,總是被體驗到的和可以體驗到的世界”,也是所有理論生活和實踐生活的原初基礎[2]64;同時,它是“經常有效的基礎”“不言而喻性的源泉”[2]148。因此,作為基礎和源泉的生活世界應該先于科學世界,出現在客觀科學的方法論、理論和成就之前,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前科學”或“先于科學”的世界。換言之,生活世界在邏輯上優先于科學世界。這種邏輯上的優先的原因在于一個簡單的事實:人從母體出生后,首先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與動物相類似的基本需要,如吃、喝、性之外,還有與其他動物不同的活動,如人際交往、科學研究等等。這些活動都可籠統稱之為“生活”,都是世界生活(Weltleben)[2]151,它們都是發生在生活世界之中。但“個人的生活一般來說并不是理論上的生活”[2]347,理論研究或科學研究當然也是一種生活,但它的成果、意義、價值等原則上也只有在生活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
基于生活這一優先地位,胡塞爾認為人們一定要區分兩種領域:一是先于所有目的的“領域”,即生活世界,它是持續地并且自明地在先被給予的(pre-given),并總是為我們而有效地存在著。但與人類活動的各種潛在取向的多樣性相比,它并沒有因為某種特定的目的或目標而獲得它的有效性;二是目標領域,它是與每個人的特定興趣相關的領域,它是“在其自身的普遍性之中,已有意地得到的領域和有待得到的領域;作為被喚醒了或早或晚所想象到的確定性視域,以及為科學而特殊被喚醒的領域”[4]381)。科學家所關注的科學世界就是目的領域。從這兩種領域的區別可以看出,科學世界是由某些目標或興趣的取向所確定的,有關這個世界的真理問題是根據最終的目的而在與這個目標的關系所決定的。在先給定的、前科學的生活世界則存在于所有目標、興趣之前,這些目標或興趣也只有在這樣的領域里才可能得到實現或成為所追求的東西。每個目標和興趣都預設了作為已存在的和有效的生活世界。就此而言,生活世界為所有其他活動提供了基礎。
與科學世界的區別還在于,生活世界從根本上是可以從經驗上體驗到,是“直接經驗上確定性”的世界[2]107。在胡塞爾看來,生活世界中的對象總是在經驗上與活生生的對象相關的,并根據自明性的直覺被人們從經驗中感知。它存在于人的直覺之中,并以相對于主體的方式而存在,因此生活世界是主觀的、相對的。科學世界則是由特定的觀念、系統的理論命題構成的大廈,一般只有在科學家的視域中才很容易被理解。并非每個人都是科學家,因而并非所有人都一定會理解和經驗到科學世界。但是,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提供各種經驗(其中有些是共同的經驗)的生活世界中,因而我們能理解生活世界。例如,在沒有現代物理學以前,或一個從未學過物理學的人,他很可能是模糊地理解他經驗中所遇到的聲音、熱、顏色。那些善于表達的人也可能解釋得很清楚,但在了解物理學的人或自然科學家面前,他的解釋就可能顯得特別的不準確。因為在物理學那里,聲音被理解為空氣的振動、熱是分子的運動、顏色是光波的變化等。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們經驗不到空氣是如何振動的,分子是如何運動的,光波又是如何變化的。空氣的振動、分子的運動、光波的變化都是發生在生活世界之中的事情,但卻是在科學世界里很容易被描述的事情。
如今人們對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解釋頂禮膜拜,也越來越關注科學世界,而包括科學活動在內的所有“目的和行動以及所有其他東西注入其中的領域”[2]564的生活世界則完全被忽略。在這種對科學及科學世界的關注中,生活世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以至于被遺忘。進而,科學對世界的解釋往往被認為唯一合理的解釋。科學指導的生活被視為真正的生活,科學世界也被當作真正的世界。在胡塞爾看來,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的數學化”。
二、自然的數學化
數學是各門自然科學之母,以至于人們常常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5]191但是,作為數學博士出身的現象學家胡塞爾卻指出,從數學上來理解自然,并不完全是人類長期實踐經驗積累的結果,它與“普遍哲學的理念和任務所發生的根本變化”相關。[2]31
現今作為數學分支之一的幾何學起源于古希臘人測量和土地勘查過程之中,這些都是發生在生活世界中的基本活動。在這樣的活動中,他們產生了“完美性的理想”:使直線更直,使平面更平,等等,進而產生了純粹幾何學概念,正是這些概念使人們獲得了關于日常測量活動中所必須涉及到那些點、線、面等精確的、普遍的和客觀的確定性。其次,他們還認識到“理想”的對象(理想的形狀)可以用普遍規律來描述。這些理想形狀與人們在經驗中遇到的物質形狀不同,也與人們測量的形狀不同,有關它們的真理獨立于特定的人類境遇,并且具有普遍性。當人們開始把幾何學概念運用于自然本身時,自然就開始被作為一種理念的數學流形(manifold,Mannigfaltigkeit)而得到理解,即自然被當作以數學方式(如數學符號、公式、定理等)來理解的。人們借助于純粹幾何學概念,借助于“理念”“理想對象”來指導他們的測量活動時,可以達到在經驗的實踐中所達不到的東西,即“精確性”。其結果是,測量技術的提高而產生的效果反過來使當時的古希臘人有理由相信:有關人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世界的真相問題,完全可以借助于數學、物理學等概念科學地表達出來,而且,這種科學表達出來的東西能夠獲得客觀、普遍的認可。因而在伽利略等自然科學家們看來,正是這種對“精確性”的追求使得人們更愿意用純粹客觀的、數學性的規律或定理來描述自然。由于純粹幾何學指導測量技術日臻完美、精確,世界的真實存在問題也逐步被納入數學的視野,并與數學的流形逐漸混為一談。當自然被當作數學的流形來理解時,一個與自然相類似的普遍的、客觀的世界就逐漸形成了。胡塞爾認為,盡管希臘人有著對“精確性”的追求,但卻并沒有“在遠離直觀的符號領域中活動”[2]34,而伽利略等科學家們不加批判地繼承源于希臘人的純粹幾何學,直接影響了后來人對科學活動及其意義的理解。
眾所周知,按英國經驗論者洛克的理解,物體的第一性的質,如形狀、質量等與物體不能分離,而第二性的質,是能借其第一性的質在我們心中產生各種感覺的那些能力,如顏色、聲音、滋味等等則在主體之間存在著差異,即具有相對性。盡管如此,人們仍相信一個真實世界的存在,只不過是以不同形式顯現而已。當測量的目的在于獲得更準確、更客觀的結果時,這就勢必要求超越主觀性和相對性,進而達到那種客觀可靠性和互主體的可證實性,這種要求必然涉及到抽象,并系統地排除第二性的質的主觀相對性。按康德的理解,幾何學之所以可能,在于它的對象是形式性的空間:它構建人類感官接觸到的外在現象。或者換成康德的話來說,正是這種形式性的空間才使得幾何學作為先天綜合判斷具有科學性,也使得物體的形狀、質量等第一性的質在空間中具有客觀性。但是,第二性的質則不顯現在空間,它與內在時間相關。因而當我們“沒有兩種,只有一種幾何學”,即形態幾何學時[2]49,第二性的質的客觀性問題仍然存在。因此,數學這門科學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克服經驗的主觀—相對性,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法也需要訴諸于抽象化的數學,即對物體的特殊感性性質(即內容充實)進行數學化。胡塞爾將這種過程稱之為“間接的數學化”。它的出發點是,這些特殊感性性質或內容充實在本質上與屬于它的形態是以一種完全特殊的方式,按一定規定緊密聯系著的。按照伽利略等人的理解,自然界中的物體包含著先驗地存在著的空間、時間形式,這些形式必定是與其內容相結合的,此外,抽象地可分的具體物各部分之間也存在普遍的因果性。以這些前提作為出發點,加上實用測量技術的發展,進而就有可能在“被限定的領域內”將具體因果的物體世界“客觀化”。例如,在前科學生活中體驗到的物體的第二性的質,如聲音、熱,在“物理學上”被理解為可以測量到的聲波振動、熱波的振動。這樣一來,“整個無限的自然,作為受因果性支配的具體的宇宙……變成了一種特殊的應用數學”[2]50。通過對源初地呈現出來的世界進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解釋,這種間接的數學化使在經驗中遇到的物體也展示出數的特征,如顏色的深淺、溫度的高低等都可以用數量來表示,從而克服了日常經驗的模糊性和相對性。
胡塞爾關于現代科學對自然的數學化的分析表明:數學上理解為“自然”的東西,其最初動機源于對自然界中的物體、形狀的精確測量,因而數學化的自然實際上是人類按照特定方法論所建構出來的東西,是理念化的、模擬的抽象世界,“精密科學的自然并不屬于這樣的周圍世界,而只屬于那些是精密自然科學家的人(或那些理解自然科學的人)的周圍世界”[2]365,這些人也是“在方法方面最有創造性的技術家”[2]73。當然,這種抽象是人類思維活動的成就,卻與自然的經驗世界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是,在對自然進行數學化的過程之中,作為數學的以及奠基在數學之上的自然科學所理解的世界成為了一種在邏輯上和數學上可以理念化的結構,而且這種結構可以在主體之間獲得客觀普遍性。這樣一來,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標準就成為了對包括自然在內的整個世界的解釋標準。客觀性世界逐漸替代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作為某種確定的和在前給定的東西而消失了。這就是自然的數學化的結果。
三、科學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替代
在胡塞爾看來,自然的數學化實際上就是“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學的直觀的自然”[2]65。盡管如此,但這些被數學化的自然也好、自然界中的對象也好,仍是與主體、具有一定主觀性的人相關的自然或對象。換言之,客觀—科學的世界,作為腦力的成果,在整體上屬于生活世界領域。客觀科學本身也屬于生活世界的一個因素。正如胡塞爾所揭示出來的那樣,科學是人的成就,是自身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于一般經驗世界之中的人類成就。[2]143沒有離開人的純粹客觀的世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被抽象地理解的,自為的,被確定為與人分隔開來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6]116用數學、物理學方式所理解的客觀世界實際上是作為活動著的人類的成就,也同樣屬于生活世界。
如同所有其他實踐一樣,科學也是許多實踐形式中的一種,科學活動本身也必須不斷地在預先給定的生活世界中移動。科學家的問題都是與直觀地在先給定的生活世界相關的問題。科學家在追詢真理時,必須最終訴諸可經驗到的生活世界的互主體自明性之上;當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時,總是需要有已預設的生活世界作為其奠基支撐。這樣一來,在先給定的生活世界就起到了前提的作用,科學家正是把它們的客觀結構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之上。同樣,科學活動的目的也要以生活世界作為視域,“一切前科學的和科學的生活都已經將它作為前提,它們將這種普遍成就的精神獲得物當作永久的基礎,而所有它們自己的獲得物都能夠匯入到這個基礎之中”[2]137-138。
可是,在伽利略和以后的科學家那里,真正客觀的、真實的自然卻被理解為用數學、物理學等概念和符號來理解的自然,并認為這樣理解的自然才是在純粹主觀顯現中顯示出來的那個自然。這種理念化的自然首先在自然科學家已被互主體性地得到認可,并為他們所接受。此外,數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逐漸通過教育、教學、研究或學習等途徑而進入到從事科學活動的人思維之中,他們“按照嚴格的方法論與現成的概念和命題打交道”,“通過畫出的圖形將概念變成感性直觀的,以此代替原初理念東西的實際產生”[2]444。由于數學在實踐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們進而還相信,這些奠基在數學之上的自然科學方法本身就具有最終效力和典范性特征,能夠被普遍地得到運用,借助于數學、物理學等方法來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也獲得了普遍性意義。這樣一來,自然被暗中取代的結果是,自然對象就成為了可用數、量進行測度的物體,并成為可以理解的東西,不可理解的只是那些不能被數學化的東西。整個自然界也成為了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再也沒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于是,整個世界完全在科學的操控之下,“整個世界被從自然科學方面進行思考”[2]344。因此,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人實際上酷似于上帝。正如胡塞爾指出的那樣,“正如數學談論無限遠的點,直線等等一樣,在一種類似的意義上人們在這里可以用比喻的說法說:上帝是‘無限遙遠的人’”[2]84。
科學活動也開始遠離生活世界了。古希臘人孜孜以求的“真理”現在也開始由自然科學來界定。不僅如此,現代科學還創造了“客觀真理”這種觀念,并使之成為所有知識的規范。現代自然科學用自身所建構出來的程序和方法還能把不完善的、前科學的知識轉換為客觀的、普遍的真理,轉換為完善的知識。其結果是,人們開始習慣地以科學作為取向,從而逐漸對前科學的生活感到陌生,并且開始“將只不過是方法的東西認作是真正的存在”[2]67。他們“以用數學方式奠定的理念東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現實的世界,現實地由感性給予的世界,總是被體驗到的和可以體驗到的世界——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2]64。在這樣的科學態度中,人們就不會有理由去考察主觀—相對性領域——生活世界。而且,這種暗中替代隨即傳給了后繼者,即以后各個世紀的物理學家。
四、現象學視域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
“殖民”本意是指,強勢國家用武力等非法手段占領本不屬于它的領土之后,繼續向所占領土移民,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進行全面的支配和統治。在這一過程中,殖民者為了使自己的侵略行徑合理化,還往往借口自己本國文明的先進性,從而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在被征服者們面前。這是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掠奪海外資源的基本方式。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上絕大多數殖民地國家獲得了獨立。殖民主義時代雖然過去,但“殖民(colonization)”一詞所具有的特殊含義卻在文化層面上得到了廣泛運用,例如,西方學術界的“后殖民主義”就是一例,哈貝馬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亦屬此列。胡塞爾依照現象學的方法對生活世界與科學世界進行區分以及“自然的數學化”過程進行了分析,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科學世界“暗中代替”生活世界的過程。這種暗中取代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過程。與哈貝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不同之處在于,它是被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及科學世界殖民化了。這種殖民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以數學為基礎的現代自然科學以“客觀性”真理名義去克服了生活世界本身所固有的“相對性”,排斥了它的“相對性”。按照胡塞爾的理解,在生活世界中,經驗上顯現給人類的對象,具有無限多的可能性,人們經驗它們時具有主觀性,也具有相對性,但它們都屬于生活世界本身。自然科學力圖以“幾何學化”、理念化為基礎,并“借助于理念性的概念,自在存在的概念,和作為自在真理的理念的真理的概念”[2]352,對這些無限多的可能性作出理想性的概括,這就是“客觀性”形成過程。以數學為基礎的現代科學的目標在于客觀性真理本身,因此,這類科學超越了實踐性的、境遇性的視域。這種以客觀性真理為己任的科學實際上構建了一種“知識”,它僅僅把科學所認識的世界作為“真實的世界”使其有效;而前科學的日常知識則被當作“被輕視的意見”,因為它只能“模糊地”認識到“數學構成的世界的物自身”。[3]183在科學的“客觀性”面前,生活世界被當作僅僅是主觀—相對的意識世界而貶值,更確切地說,它被當作感覺的感官世界,也被當作人類行動的世界以及個人生活的世界。鑒于生活世界的奠基性,胡塞爾毫不客氣地指出,“自然科學那種樣式的客觀性,簡直是荒謬的”[2]319-320。
其次,源于生活世界的人生意義和人性問題被擱置一邊。胡塞爾對科學(尤其是實證科學)進行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科學或敵視科學,也不是對科學的內在價值和有效性進行質疑,而是要提醒人們注意到它們本身的意義的來源,即“科學,科學一般,對于人的生存過去意味著以及現可能意味著的東西”[2]15。但是現代科學在相當程度上是“只問效果,不求意義”。科學所產生的“嚴格的科學性要求”將與生活世界相關的“一切評價的態度,一切有關作為主題的人性的,以及人的文化構成物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問題全都排除掉”。與此相聯系的是,特殊的人性問題被排除在科學領域之外,因為“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唯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種唯一性意味著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2]16。由于科學也不思考人性問題,與此相關的是,科學的真正意義從一開始就被模糊了。科學家憑著自己的興趣,借助于理想化的概念、公式、符號等創造了他所追求的目標領域——科學世界。雖然科學的概念、公式、符號等能很好地解釋生活中的現象,揭示自然現象之間的因果關聯,但它并不能替代生活世界本身。科學的意義和價值難道可以與人生無關,甚至與人性無關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科學這一實踐活動以及科學世界也只有奠基在生活世界之中才能得到理解。科學與科學世界源于生活世界,也只有從生活世界中才能得到理解。
再次,與生活世界相關的形而上學問題被丟棄了。在胡塞爾看來,形而上學是有關最高和終極問題的學問,是諸種學問的王后,只有形而上學的精神才賦予一切認識、一切其它學問以終極意義[2]19-20,作為諸多文化之一的科學的意義也應從形而上學中汲取意義。眾所周知,形而上學討論的是作為目的論源泉的上帝、世界“意義”、“絕對”理性、自由、不朽等帶有根本性的哲學問題。與專注于客觀事實的問題相比,它們與“作為原則上可直觀東西之全域的生活世界”[2]154聯系在一起,因而都超出了作為由純粹事實構成的大全的世界,是比事實問題更重要的問題。但是,在對自然進行數學化之后,科學和形而上學之間就變得勢不兩立了,數學家、自然科學家不僅不去思考形而上學問題,甚至,只要是來自數學家、自然科學家圈子以外任何一種引導他們進行這種思考的嘗試,都被當作“形而上學”加以拒斥。[2]73因為“在數學家、自然科學家那里,作為數學的自然,這個自然總體超越了前科學的感性的自然,但是在它本身后面不再有形而上學的自在,即只是所謂照亮它這個作為純粹現象的感性自然的自在”[2]501。這也就是為什么自近代以來實證科學的理論和實踐取得了越來越巨大的輝煌成就,而形而上學不斷走向失敗的根本原因。這種鮮明對比使得,“即使在充滿哲學精神因此主要對最高的形而上學問題感興趣的研究者那里,也出現一種越來越緊迫的失敗感”[2]21。
隨著科學世界對生活世界的“暗中取代”而出現的殖民化,意義的領域從主觀的生活世界轉向客觀的科學世界,生活世界也便消失在這個理念化的世界之中。其結果是,人類對于世界由以獲得其意義的“絕對的”理性的信念,對于歷史的意義的信念,對于人性的意義的信念,即對于人為他個人的生存和一般的人的生存獲得合理意義的能力的信念,都崩潰了[2]23。這就是生活世界被暗中取代,即“生活世界殖民化”之后的現代困境。
[1]胡塞爾.生活世界現象學[M].倪梁康,張廷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
[2]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M].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3]HANS-HELMUTH GANDER (Hrsg).Husserl Lexikon[M].Darmstadt:Wissenschafteliche Buchgesellschaft,2010.
[4]EDMUND 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translated by David Car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0.
[5]中央編譯局.回憶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