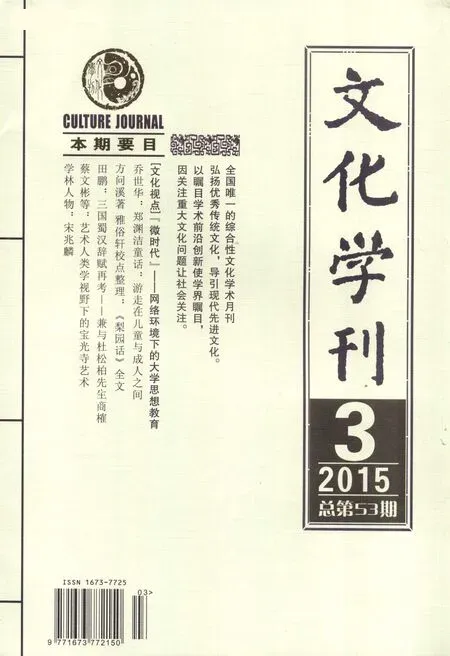論《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
黎蕾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北碚 400700)
論《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
黎蕾
(西南大學文學院,重慶 北碚 400700)
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20世紀20年代的經典文學作品,然而它在中國卻經歷了一個短暫卻曲折的譯介與接受史。本文試圖以本土化的視角,審視中國對這部作品的譯介與接受歷程,透析其中所折射出的各時期兩國文化交融與碰撞的姿態。
《了不起的蓋茨比》;美國文學;中國;譯介;接受
美國著名的現實主義小說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蓋茨比》在2013年可謂炙手可熱,不僅有最新譯本上市,好萊塢公司也上映了最新的改編電影。盡管觀眾對電影褒貶不一,絕大多數人都已基本認可了這部經典原著,然而,這部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文學經典在中國卻經歷了一個時間短暫但道路曲折的接受史。由于《了不起的蓋茨比》帶著美國文學的標簽,它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必然涉及到中國對美國的本土化視角的問題,翻譯自身即涉及兩種文化的碰撞,所以,這部小說被中國所譯介和接受,不僅關乎一部小說本身,也帶著兩國文化交融和碰撞的色彩,需要我們置之于大的文化語境之中去觀察與審視。
蓋茨比的故事在美國可謂家喻戶曉,對于當今許多中國讀者也不再陌生,故事講述了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美國,一個出生于西部貧寒之家的青年蓋茨比為了實現夢想而努力拼搏卻最終失敗的故事。故事情節并不復雜,卻深刻地反映了一戰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冷漠和人的自私以及美國社會物欲橫流、道德淪落的景況,具有發人深省的現實意義。雖然我國從上世紀80年代才基本開始對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等作品投入關注的目光,但學界對這部小說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從探討作品的美國夢等主題思想,到評析其藝術成就(象征、視角、敘事、語言等),近年來的研究文章和著述越來越多,反映出中國對這部小說重視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譯介和接受時間短,受國外研究經驗的影響過深,國內對這部作品的解讀與研究仍有許多欠缺,這就是我們需要再深入思考的地方。關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介和語境方面確實也有一些有成效的研究文章,但總體來說多是概述性的總結,少有細致的體察。本文希圖就各個時期的代表譯本為本,以文獻資料為輔,站在本土化的立場上審視中國對這部美國經典文學作品的譯介與接受,同時考察中國對美國文化和文學看法的轉變歷程。
菲茨杰拉德作為美國“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成就在西方早已獲得認可,經歷了40年代的“菲茨杰拉德復興”,菲茨杰拉德的文學聲譽不僅已得到了恢復,而且上升到了他生前從未企及過的高度。”[1]他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發表于1925年,艾略特稱之為“美國小說自從亨利·詹姆斯以來第一部代表作”[2],然而這位在美國極富盛名的現代小說家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道路卻并非一帆風順,其原因有很多,具體可從三個階段來考察:
一、70年代末以前:微有曙光
上世紀70年代末以前,我國讀者對菲茨杰拉德等美國作家還比較陌生,中國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多選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題材也傾向于選擇革命文學,對美國文學的翻譯也“大體局限于左翼的現實主義和無產階級文學”[3]。整個社會文化系統都是根據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翻譯淪為了意識形態、政治系統的附庸。《了不起的蓋茨比》描寫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享樂,以販賣私酒的資本家作為主人公并冠以“了不起的”字眼,在當時封閉而同一化的政治氣候中,其境遇自然可想而知,因此,“及至70年代末期,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我國大陸仍無中文譯本出版……受前幾十年極‘左’觀點的束縛,學術界對這位文學家依然持批判、否定的態度”[4]。著名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者巫寧坤就曾因從國外帶回一本英文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而被檢舉批判,其經歷之辛酸可以從其自傳《一滴淚》里窺見。
雖然在中國大陸受到冷遇,但這一時期在港臺地區卻出現了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最早的有黃淑慎譯的《永恒之戀》(臺灣正中書局)。此外還有幾部譯本,其中美國學者喬志高譯的《大亨小傳》(今日世界出版社)頗有代表性,當時在港臺地區頗為流傳。喬志高是生于美國的華人學者,在菲茨杰拉德已聲名顯赫的這一歷史背景下,他對這部作品的譯介無疑帶著一份激動與熱情,在這本書的封底上他印著這是“想了解美國人民和精神歷史的人的重要文獻”。雖然對這樣一本小說的歷史地位未免看得過重,但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譯者對推廣美國經典文學到中國的用心良苦和熱忱。此外,在林以亮(原名宋淇)撰寫的序言中,我們也能覺察出一些有意味的東西。
在《大亨小傳》序言中,菲茨杰拉德一直被視作“浪漫主義派作家”,而非現在公認的“現實主義作家”,可見隨著時代的轉變,對“浪漫主義”的定位也不同。上世紀70年代,譯者們之所以認為菲茨杰拉德是“浪漫主義”作家,應該是考慮到他那種抒情、華麗并帶著哀傷筆調的語言風格,他們并不想把菲氏的寫實手法作為他的作家標簽。結合上世紀60年代臺灣的文學思潮不難發現,這種對浪漫主義的推崇并非毫無緣由。上世紀60年代以來,臺灣出現了民主思潮和現代主義文學風靡的現象,從對浪漫主義的厭棄和驅逐轉變為浪漫主義的回歸,而《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帶有浪漫色彩的英雄悲劇故事自然能夠得到譯介和承認,現實主義面對現代主義的滾滾大潮顯得無能為力,譯者也更愿意給這部小說貼上浪漫派的標簽。
二、70年代末——90年代:承上啟下的探索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國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認可與接受度呈現一種逐步上升的態勢,中國大陸對這部作品的譯介和了解也不斷加深,這體現在譯本和研究文章的從無到有,這是由于在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環境的改善和中美交流的發展為中國對美國現當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譯介與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條件”[5]。經歷了文革極“左”路線對文學的摧殘,知識分子普遍呼喚新文學和新思想來洗滌單一陳舊的文學界。類似于晚清時期,他們認為“翻譯是建立社會系統的重要力量,因此他們愿意把翻譯放在主要的位置”[6]。而讀者也渴望重新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領略自五十年代被禁的西方作品風貌。所以這一時期來自西方國家的原著占了主流地位,菲茨杰拉德這位重要的美國作家也被推介進來。
20世紀中國文學翻譯的第二個高潮出現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80年代初已出現了巫寧坤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譯本(同中國其他譯者翻譯菲茨杰拉德的8篇優秀小說一同出版,名為《菲茨杰拉德小說選》,1983年出版),這是這部小說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譯本,在序言中不乏譯者對菲氏的肯定,但態度相比喬志高譯本的高度贊揚顯得非常謹慎和朦朧,他小心地借用艾略特、海明威等名家對這部作品的贊詞,不著主觀評判,把鑒賞的權利交給了讀者。這種謹慎謙虛的態度不僅源于譯者在文革經歷的陰影,更是因為當時并未完全開化的政治氣候。此外還有1982年出版的周敦仁的中文注釋本《燈綠夢渺》等譯著,為中國大陸讀者了解菲茨杰拉德的這部作品打開了一扇窗。撰著有董衡巽、李文俊等學者編撰的《美國文學簡史》等,這部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第一次向中國讀者系統地介紹了美國文學的概況,影響很大……較全面地概括了菲茨杰拉德的生平、歷史地位、作品特色,以及他的創作思想和藝術風格,使我國讀者對這位作家開始有了正確的認識和了解。此后,我國學者對這位作家的研究便開始得以逐漸展開”[7]。從這諸多努力中都可以看出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希望擺脫文革時期思想和文學的單一傾向、解除政治權力的絕對控制、呼喚人文學術的獨立性的渴求。但這一時期我國對《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作品的接受和研讀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對其主題思想和藝術成就的評價僅僅是一種模糊籠統的觀點,并帶有照搬美國研究成果的印記。
與此對照,這一時期文壇更為流行的美國作家還有海明威和福克納以及美國“黑色幽默”派作家如馮內古特、納博科夫、品欽等,影響頗大的美國文學作品有“塞林格的《麥田的守望者》和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8]。這些作家或作品因其“后現代性”而受到追捧。雖然福克納的意識流小說對新時期的中國讀者來說還很陌生和難于理解,但這些新文學正是當時的中國所迫切需要而為人文學者所積極倡導和譯介的。
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作并不是很多,但也能顯示出這一時期中對該作品譯介的特點。1996年由王晉華翻譯、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前言中注重對文本的解讀,也注重思考文本細節所蘊含的意義,體現出了譯者自己的思考。此外1997年的“世界名家名著名譯——大眾叢書”中也出版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譯者是吳然。該叢書本著為社會大眾著想的原則,為讀者推介了一些世界優秀的篇幅較短或中短篇小說,但對小說的解讀卻是不夠深入的,如前言中把毀滅人的田園式生活、使傳統道德觀念淪喪、欲望極端膨脹等現象均歸結為戰爭,就顯得比較草率和空淺。此外,譯文中也有翻譯地不夠準確的地方。如第一章譯者就將一個重要的語詞譯錯。原文是:“‘When ever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he told me,‘just remember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that you’ve had”[9].該譯本的翻譯是:“‘無論你想要責難什么人的時候,’他對我說,‘都要切記,這世上沒有哪個人具備你所擁有的優點’”[10]。他把“advantages”譯成了“優點”,但其實譯作“優越條件”(如姚乃強和巫寧坤譯本)應該是更準確的。從譯介情況可以看出,90年代中國對這部美國文學作品的譯介還不夠重視,對作品的解讀主要基于文本本身,缺乏細致的研讀和博大的文化視野,更沒有形成中國的本土化視角,同時研究還有很多有待拓展和深入挖掘的地方。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仍是80年代譯介和研究的繼續探索期,并未形成一個時期新的特點。
三、2000年至今:本土化視角初探
在21世紀全球化的語境下,菲茨杰拉德的這部作品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和關注,各種譯著層出不窮,研究文獻涉及的范圍也更加廣泛,這部美國經典之作也成為許多中國讀者心中的經典。究其繁榮局面出現的原因,大致有兩點:一是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中美交往愈加頻繁,國內對美國和美國文學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國人不只消除了對美國的偏見,甚至由于抱有對美國這個先進的超級大國的向往而樂于接觸美國的文學與文化,這給了《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被“視為全面展示了美國發展史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的社會、文化形態諸多特征的重要的史學著作”[11]一個良好的譯介與接受語境;二是就這部作品本身的題材來說,它生動再現的20世紀20年代紙醉金迷、道德敗壞的美國社會萬象與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當今的中國社會未嘗不形成一種對照,這使讀者能在閱讀這部小說時找到共鳴。
姚乃強在其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這樣說:“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僅《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便足以確立他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將他與同時代的美國作家德萊塞、凱瑟、海明威等人齊名而毫不遜色”[12]。在該書序言中,除了和以往譯本相似的對思想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外,還著重揭示了美國東部和西部的差距和沖突,具體分析了其東部和西部的含義,指出這種矛盾即是“傳統”與“現代”的矛盾。此外還說明了這部小說近年來受到讀者歡迎的原因,除了小說本身杰出的藝術魅力這點外,還和“我國目前處于轉型時期,社會上出現的某些現象和美國上世紀二十年代有類似的地方”[13]有關,并指出這部被稱為“金錢浪漫史”的小說對于當今的國人也有警醒作用。從序言的變化可以看到2000年之后中國譯者對這部小說從本土化視角下進行解讀的意識有了明顯提高。
在2013年,中國對這部小說的譯介和接受又達到了一個高潮,既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繼宏譯本,又有美國華納兄弟影片公司制作的同名電影上映,《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知名度持續升溫。此外,面對小說中道德淪喪的社會和持有誠實與良知的蓋茨比的對比,譯者頗具知識分子責任感地倡導我們要從中得到借鑒,面對當下道德淪喪的社會景況要注重道德的自省,這一點也表明了譯者欲借外國文學名著來淘洗和拯救中國當代人心靈和社會現實的初衷。
綜合2000年以后這兩部代表性譯本來看,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等美國文學解讀的本土化意識已經有了顯著的增強。此外,從其他研究和評論文章中也可以看到,我國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研究也更深入。在2002年出版的吳建國《菲茨杰拉德研究》中,作者給蓋茨比這個小說主人公給予了高度評價,說蓋茨比是“一個完全憑借個人努力從社會的最低層苦斗上來的人。他堅忍不拔,勇敢頑強,憑著自己的奮力拼搏終于獲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步入了社會的上層”。[14]與湯姆相比,“他崇尚的是‘奉獻’,而不是‘索取’。他的力量不在有形的外表,而在其崇高的精神內涵上”[15]。在這里,意識形態和階級劃分已經不作為全部的考慮因素。由于當時是一個更加自由包容、推崇個人奮斗的時代,蓋茨比不但不會因為其階級地位受到批判,反而因為其具有高尚的傳統品質而受到褒揚,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造成其悲劇的社會。有了這些繁多的著述和譯本,我國的讀者對這部作品就更為熟知,心中也有了更為客觀和多元的看法。
視覺文化在當今社會逐漸占有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如果一部文藝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的話,會極大地促進它形成范圍更大的社會影響和讀者效應。菲茨杰拉德這位曾經為美國好萊塢創作劇本的作家,從1920年至今,他已有十幾部作品被數次改編為電影、電視劇或者戲劇。電影的上映使菲茨杰拉德的著作在書市上更加火爆,進一步為大眾所熟知。2013年,《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上映勢必也會增加這部小說在中國的知名度。對這部獲得多個電影獎項提名的電影,網友褒貶不一。不喜歡這部電影的觀者多認為該電影有許多不符合原著的地方,如導演用現代流行的hip-hop音樂代替原來的爵士樂,有網友認為這是胡編亂造。反對者認為,這是導演用心良苦,其套用當代音樂,意在借古喻今,有人甚至讀出了“美國的過去就是現在的中國”的意味。小說的價值在于成功的人物塑造和豐富華麗的修辭”。從眾多影評中不難看出,中國的影迷里已有很多看過小說原著,它不只是美國人心中的經典,也成為了很多中國人心中的經典之作,即使對改編電影有一些微詞,但對這部小說大家基本還是持肯定甚至贊揚態度的。
結語
《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譯介和接受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短暫而曲折的歷程,然而在中國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蹉跎,由于中國譯者和研究學者的共同努力,小說本身的思想和藝術價值逐漸為大眾所知。譯本數量不斷增多,質量不斷提高,研究也越來越注重從本土化視角的解讀,雖然這種力度還不夠,解讀和研究仍有很多問題,但畢竟已經走上正軌。隨著各界的不斷努力,這部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和接受將呈現更加繁榮和多元化的局面,折射出中美兩國文化交融與碰撞的絢麗姿態。
[1][4][7][14][15]吳建國.菲茨杰拉德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32.324.145.79.256.
[2][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大亨小傳[M].喬志高譯.北京:今日世界社,1974.169.
[3]楊義.二十世紀中國翻譯文學史(新時期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9.133.
[4]劉士川.《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J].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漢文綜合版),2008.28.
[5][12][13][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姚乃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67.119.73.
[6]王宏志.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55.
[7][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小說選[M].巫寧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49.
[8][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王晉華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96.198.
[9][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吳然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70.
[10][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李繼宏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27.
[11][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彭萍.北京:中國宇航出版社,2011.49.
【責任編輯:周 丹】
I712
A
1673-7725(2015)03-0130-05
2015-02-01
黎蕾(1991-),女,四川資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外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