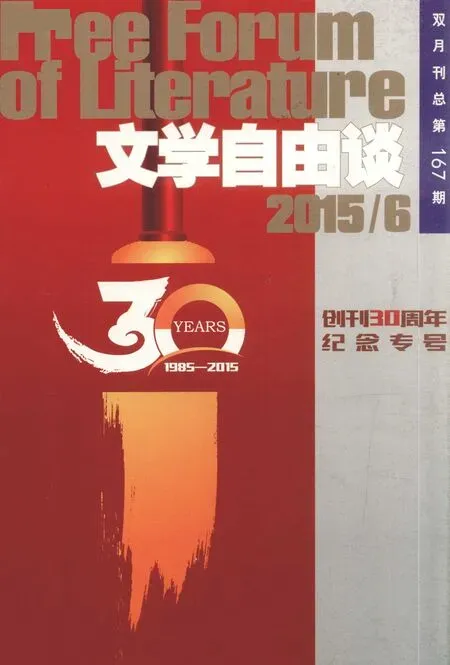文學可不可以自由談
陳 沖
我是《文學自由談》的作者之一,《文學自由談》是我投稿的刊物之一,無論是從我看《文學自由談》,還是從《文學自由談》看我,肯定都會以偏概全。話說回來,偏著看也是一種看法。你正面看,也只能看到正面,看不到背面,還是看不全,所以無妨就偏著看一回,看都能看到些什么。
我第一次給《文學自由談》投稿,并承蒙刊登在當年第4期上,是1986年,距今只差一年不到30年,應該算是刊物的忠誠老作者了。但它上次獎勵作者時沒有我,并不是它的錯,實是因為我投稿很少:在它創刊以后的前14年里,我總共投過三次稿,基本上平均五年投稿一次,用“大數據”時代的眼光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有一個事實卻不能忽略,就是這個刊物我每年都訂,每期都看。那時候我按期收到的刊物不算少,有花錢訂的,有贈閱的,并不是每個刊物期期都看,而《文學自由談》雖然不是篇篇都看,但每期總會看幾篇。為什么會看呢?很簡單,因為好看。那又為什么不經常投稿呢?也很簡單,因為我知道自己寫的文章不好看。
按我當時的定位,《文學自由談》是一本文學批評刊物,但又不是一本很“正經”的文學批評刊物。那時的我,算是個剛入行的作家。按我弟弟的說法,我之所以一生碌碌無為,皆因為從一開始就入錯了行,如果去搞理論物理或數學,情況應該會好一些。然而即便將錯就錯,既然已經入了行,我還是想當一名正經的作家。一開始主要是寫小說,寫的是一種正經的小說,以至當時有位后來發了大財的著名作家說:陳沖根本就不會寫小說。在我的一個中篇小說研討會上,一位當時的新銳批評家說:這哪兒是小說?就是一篇報告文學嘛!這些話,我當時并不認同,但很受觸動,認真地思考了與此有關的種種問題,也檢討了自己的創作。我這人自幼驕傲,從剛滿14歲就交了第一份入團申請,到21歲當右派分子的前一年,總共交過四次申請,每次都因為驕傲未獲批準。但我不自滿。我的內省力還是不錯的。檢討的結果是,即使寫不成好小說,還是得寫正經的小說。看來我弟弟說得對,我天生一顆正經的腦袋,比如搞數學,你是根本不可能靠不正經的運算成為數學家的。作為這種思維的正常延續,后來兼寫一點理論評論文章時,寫的也是正經的理論評論。我在《文學自由談》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題目就叫《試談文學的內部結構》。一點辦法都沒有,有這種思維,就有這種文字,這種題目。《論現代主義的摩登化》(發表在 《文論報》),《關于現實主義的一些思考》(發表在《文學評論》),如此等等。最出格的,也就是寫了一篇《鉆一鉆牛角尖》。今天回頭看,這一篇確實是一個苗頭,反映出我對文學批評現狀的某種不滿。為什么要鉆牛角尖?就是覺得有些批評文字太信口開河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整個1990年代我總體上寫得比較少。借用一位美女作家的說法,是因為1980年代提前一年結束了,弄得我有點發懵,有點找不著北。為了完成一個專業作家每年六萬字的任務量,我就寫一些不那么正經的文字,包括報紙副刊上的豆腐塊之類,再就是侃球。您別說,還真侃出一點小名堂來。有回被電臺請去做節目,主持人一上來就介紹說,下面請著名作家、著名體育評論家陳沖先生如何如何,弄得我更加找不著北了。
轉折發端于1999年。那年的第6期《文學自由談》上,發表了我寫的《聲援何滿子先生》。所為何事?為何滿子先生批評金庸吶喊助威。我把這種批評稱之為對通俗小說的人文批評。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確實好看,拿他自己的話說,用來自娛,亦復娛人,蠻好的。但是那里面的歷史觀、價值觀、文化觀,有些是有問題的,所以就需要人文批評,讓讀者在娛樂之余,不要受這些東西的消極影響。以一般的正經理論看,這或多或少有點多余,只因當時有些大學教授正在努力把金庸捧為文學大師乃至文化大師,這種批評就有了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稍后,2001年第5期,發表了我寫的《金庸神話隨想錄》。再稍后,2002年第4期,發表了我寫的《答冷成金》。冷先生就是那些想把金庸捧為文化大師的教授之一,認為“其文化底蘊與我們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深度的契合,甚至是暗合了我們重塑民族文化本體的百年祈盼”。這種只有教授會說的話,我根本看不懂,只能虛心請教:什么叫“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什么叫“民族文化本體”?“文化”怎么能夠成為“本體”?不知道“本體”是一個有嚴格定義的哲學概念?“本體”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自足性,而一個自足的體系,怎么還會有毀壞的時候,以至于需要“重塑”,而且一百年都未能“重塑”出來?這一百年從何說起?也不必一百年,就說五四運動以來吧,那么多的仁人志士赴湯蹈火前仆后繼,“祈盼”的就是金庸小說這樣的東西?
今天回頭看,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向學院派批評挑釁了。
真正的轉折肇始于2004年。從這一年開始,我經常向《文學自由談》投稿了。作為這個轉折的標志性文字,是我發表在當年第3期上的《“賣野人頭”一解》。這表明,我所使用的“學院派批評”這一概念,指的是一種文體,與批評家是否供職于大學院校無關。這篇文章的批評對象是李敬澤。李先生現在是我們大家的領導了,領導同志寫文章,自然會有另一種模樣,但他當時是一位編輯家,寫的是編輯家批評。醞釀寫這篇文章時,我是猶豫過的。李先生的文章通常都寫得極富編輯相,體現著一種敏銳而獨到的識文的眼光,唯獨這一段,不知為什么會寫得如此學院派。我以此來寫一篇文章,對李先生確實不太公平,但終于還是把它寫了,完全是因為實在舍不得這個樣本。它把學院派批評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當時那些供職于院校的教授們,還沒人能把這種特點寫到具有如此之高的辨識度——后來有人達到了,超過了,但那是后來。
這個學院派批評的特點是什么呢?就是“賣野人頭”。
“賣野人頭”是一句上海方言,屬于那種很精妙的方言,有一種不可譯性,在書面語、普通話和其他方言里,都找不到能完全替代它的詞,甚至用若干句話都無法把它的意思完全說清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此之謂也。上海方言不是當地土話,要聽當地土話,得到上海周邊縣的鄉下去聽。據說上海話是在夜總會里誕生的,有一定的精英性。至于據說現在在浦東說上海話會被人看不起,那是現在。上海話再好,終有地方局限性,其他地方的人,就很難意會它的精妙之處,還是得找個普遍都懂的詞來代替它。想來想去,也只有一個詞差強人意——唬人。大概其就是這個意思吧,但肯定折損了不少精準和傳神。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里,《文學自由談》顯示出了它與眾不同的特點,獲得了一種卓然而立超群脫俗的氣概。這種差別,即使對文學完全外行,也能直接從它的版面上辨認出來。如此之高的辨識度,僅僅來源于一個不起眼的細節:它刊登的每一篇文章,完了就完了,不像有些別的文學批評刊物,文章完了,還要注上一個作者的工作單位,然后跟著一大串注1注2注3直至注N,來闡明諸多引文的出處。
我對教育、科研、學術的體制問題沒有研究,研究了也整不明白。我只關心它給文學批評造成的后果。全國每年都有無數的中青年教師等著晉升職稱,更有無數的N次方的研究生等著畢業。這個“無數”,并不是真的沒有數兒,而是沒見到官方逐年公布的權威數據,若瞎猜亂估計,有被視為謠言的危險,姑且稱之為“無數”,以猶言其多也。其實不僅這個具體的數值不重要,就連這個多究竟是“很多”還是“相當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年得發表那么多篇的論文,才能使那么多的老師晉升職稱,才能使更加多的研究生得以畢業。那么這些如此之多的論文都“論”什么呢?別的專業就不說了,單說與文學有關的,亦即被稱為中文系、漢語言文學系那些。它們的研究對象,是作家、作品、文學理論、文學現象、文學流派等等。一開始,當這些研究還處在不那么野蠻的階段時,研究對象只限于古代和現代,當代文學是被除外的,老教授們認為“搞”當代文學不屬于做學問,時文當不得學術。所以那時候對當代的傷害還比較輕。后來就不行了。其實現在已經很容易看出來,即使把當代也算上,每年得生產出那么多篇論文,原材料不夠啊,沒有那么多可“論”的東西啊。原材料是個恒定值;要用有限的原材料,生產出“無數”的論文,只能在加工方法上動腦筋。而實際上辦法也只有兩個,一個是東拉西扯,這就勢必造成邏輯錯亂;一個是空話連篇,這就勢必造成話語空轉。中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們必須寫這樣的論文,導師們當然就要教他們寫這樣的論文,教得多了,自己也寫開了這樣的論文。如果老師比學生寫得更好,更“學院”,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2010年,《文學自由談》第2期發表了我寫的 《現象學發凡》。一位北大教授,為我們提供了辨識度更高的“學院”標本,而且更清晰地刻畫出如何由“邏輯錯亂”、“話語空轉”來實現“賣野人頭”的軌跡。這位教授論證了我國文學創作的形勢一派大好,空前大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表現為“漢語小說有能力”達到四種境界。哪四種?首先,“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這是典型的邏輯錯亂。這種能力不僅漢語小說有,英語小說、俄語小說、法語小說、西班牙語小說……也都有。但這不等于每一位用漢語寫作的作家都具備了這個能力,更不等于每一部用漢語寫成的小說都達到了這個境界。其次,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您別笑!這個幽默確實太黑色了,但如其不然,又怎么叫“話語空轉”呢?然后,第三,漢語小說有能力“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這就開始賣野人頭了。您在菜市場遇見過賣野人頭的小販嗎?如果有個小販過來兜攬生意,勸您買下他手里那顆野人頭,您怎么判斷那個圓乎乎的東西真是一顆野人頭?對了,您先得見過野人頭,起碼得知道野人頭啥模樣。那么您知不知道“現實”、“文化”、“堅硬的(柔軟的不算)現代(古典的不算)美學”這三種東西,被穿透之前是什么樣子的?干干凈凈的?被穿透之后又是什么樣子的?血淋淋的?如果不知道,您又怎樣判斷它們是不是真的被穿透了?就因為只要是漢語小說,就必定能把它們穿透?現在好小說不多,胡編亂造粗制濫造的小說可不缺。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賈平凹的《老生》吧,它以大量的篇幅,寫了一支共產黨建立的、專門在抗日戰爭時期用來打國民黨的游擊隊——這就把 “堅硬的現代美學”穿透了?恐怕不對吧。被它穿透的,恰恰是普通人的常識性的歷史良知!對了,這就叫賣野人頭。賣完了野人頭,這位北大教授兜了一圈回到原處。您猜他又說了什么?他說,漢語小說有能力“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您明白了吧?漢語小說就是用漢語寫的小說,發展到今天,它終于有能力用漢語來寫小說了。
有趣的是,這種學院派批評,還有個小跟班的。這種角色,很像舊戲班里那種跟包的,手里拎著個包兒,里面放著行頭道具,但并不是他們自己要登臺,包里那些東西是替“角兒”拎著的。跟班們的動機不在于評職稱或畢業,他們孜孜以求的,是重建那些已經倒塌了的殿堂,比如為“樣板戲”恢復名譽。這本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手里又沒有稱手的瓦刀灰鏟,情急之下,就從拎著的那個包里把別人的家伙什亮出來了。為了證明“樣板戲”橫看成嶺側成峰,怎么看怎么好,就發明了一個詞兒叫“藝術本體”。不錯,幾個“樣板戲”的舞臺呈現都相當講究,尤其是唱腔,既好聽又有新意,這些本是有目共睹。若要客觀,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也很應該,可是光憑這兩樣好,最多也就是把那已經倒塌了的殿堂,作為遺址來展覽,讓后人看看那廢墟里也還有點好東西,原是藝術家們的心血結晶,卻被政治陰謀家們糟踏了。但是這遠不能為整個“樣板戲”翻案呀。所以就弄出個“藝術本體”來了。舞臺呈現和唱腔都是藝術,藝術才是“樣板戲”的“本體”,這樣一來,“樣板戲”就不再是那些陰謀家篡黨奪權活動的一部分了,那些“階級斗爭”和“三突出”也可以忽略不計了,至少是成了附著在這個藝術本體上的零碎裝飾了。您瞧見沒有?冷教授要捧金庸,就弄出一個“文化本體”來;這位要給“樣板戲”翻案,就弄出一個“藝術本體”來。如果您想把小孩兒尿尿和泥捧為經典,弄一個“泥本體”就行了,別管是用尿還是用水和的,和成泥了就是好泥!可是您圣明,自然界存在的唯一一個能稱為本體的自足體系,就是宇宙本身,即“宇宙本體論”,而且直到今天,這個自足體系是不是完全封閉的,仍在討論中。
在一個隨便什么都能成為“本體”的世界里,“正經”還能找到立錐之地嗎?
在人們紛紛宣布用一些不正經的運算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時,數學還是數學嗎?
在漢語小說已經有能力把堅硬的現代美學“穿透”之后,美學還是美學嗎?小說還是小說嗎?文學還是文學嗎?
同理,陳沖也寫不成正經的理論評論了。
相比于《試談文學的內部結構》,這些文字顯然早已不是正經的理論批評了。諸如《現象學發凡》這樣的標題,其實也帶上了一點賣野人頭的味道。我究竟是怎樣從立志、堅守要寫正經的小說和正經的理論批評,一步步“淪落”到專寫這種不正經的文字,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就是寫出了這種文字之后,最有希望得到發表的刊物就是《文學自由談》。這個刊物好像很喜歡這樣的文字,所以它的編輯后來竟直接要求我必須每期寫一篇。這些年里,除了2010年,因為我太太患病、去世,經特別恩準空缺了兩期,基本每期都有。2013年末,因為一個技術上的差錯,又空了一期,編者佯怒,嚴責我立即補上,結果2014年第1期上就有了兩篇。——這樣的默契,讓我感動,讓我感激,更是對我的激勵。我保證今后好好干活兒,并加倍保證努力把活兒干好。現在確實有一種普遍現象,就是大家都再三保證好好干活兒,只是那活兒總是干得不怎么好。我保證不做這種光說不練的天橋把式。
你看學院派批評又有了新發展。靠邏輯錯亂、話語空轉再加上賣野人頭,仍然生產不出來那么多的無數篇論文,現在又有了新招數,就是提出一些偽問題。您還別說,這一招挺管用,好不容易有一個問題提出來了,別管是真問題還是偽問題,立刻就有一幫人一擁而上“論”將起來,接著便有很多篇論文生產出來,煞是鬧猛得緊——“鬧猛”也是上海方言,一看字面,就能感覺出它比“熱鬧”更有氣勢,更有動感。
不過,一切都是有代價的。當學院派批評占據了理論高地之后,其他批評自然就被擠到邊緣去了。在中國作家協會的官網上,有一個“精彩評論”欄目,有人稱之為“評論選刊”。雖然它選的文章很難說篇篇精彩,但確實篇篇正經。而這樣一來,我發表在《文學自由談》上的文章就沒有機會入選了。您圣明,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而且是個真問題,不是偽問題:文學只可以一本正經地去論,就不可以“自由”地去談嗎?即使它不能作為合乎“學術規范”的論文用來評職稱,它對文學也是毫無意義的嗎?
是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文學可不可以自由談?
我繞了這么大一圈,才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就是因為這個問題一提出來,答案就已經擺在那兒了,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也已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