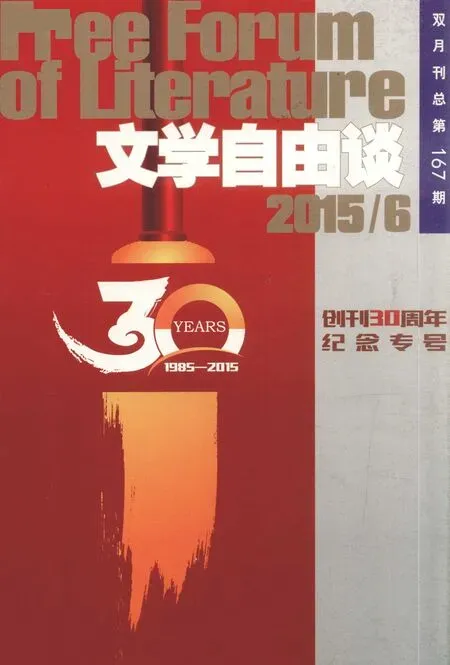履職雜說
董兆林
履職雜說
董兆林
有一天,單位的高編輯在收發室發了脾氣,原來當期他訂閱的一本刊物不見了。別人的都陸陸續續收到,唯獨自己的不見蹤影,這不免讓他有些氣急敗壞,情急之下臉紅脖子粗地向收發興師問罪。收發也是一臉的無辜和委屈,刊物訂閱郵寄一直很正常啊。當然沒過多久,那本刊物就找到了,高編輯有些羞赧地又笑瞇瞇向收發道歉。都知道高編輯愛書如命,可誰也沒有料到,為了一本雜志他會這么較真。這本讓高編輯牽腸掛肚、幾乎大發雷霆的刊物,就是《文學自由談》。
當初,參加工作沒幾年我就發現,在出版社喜歡看這本小開本雜志的人還真不少。每當新的一期出刊后,總能引起一陣子議論,刊物中的某些文章很快成為焦點,文中犀利、睿智或有幾分俏皮的精彩文字,成為周圍同事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讀至妙處,常令眾人忍俊不禁,撫掌稱道。漸漸地我也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開始享受這種閱讀的樂趣。那時在《小說月報》編輯部任職,接觸到的文學刊物可謂不少,每天閱讀小說成為工作的常態,而閱讀《文學自由談》便有些像進入一個另類的文學世界。作為一個文學批評類雜志,它和那些四平八穩的評論刊物太不一樣了。對文學的鑒賞,對作品的評價,乃至對作家的品頭論足,《文學自由談》皆以直言相對,其文多是開門見山直抒胸臆單刀直入,絕無虛頭巴腦虛以委蛇正襟危坐之類的官樣文章。這種率真的刊物性格,在當代文壇、期刊界不說絕無僅有,也是出類拔萃了。特立獨行,對文壇、作家、作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不顧忌關系情面,且能以較高的藝術水準,在文壇發出真實的聲音,這讓人不由得對這本刊物刮目相看。實事求是地講,對這一行業任何一個辦刊者來說,《文學自由談》都是大有裨益、具有較高參照系數的平臺。
不知不覺,幾年下來手邊積攢了一摞《文學自由談》,兩次搬家也沒舍得扔掉。熟料,在今年夏末時節,一個機緣,敝人竟登堂入室,加盟到了這個團隊,成為《文學自由談》編輯部的一員。過刊不舍也許就是冥冥中的一種召喚。一時間不免令人欣喜,身心俱爽,余夏的溽熱也覺得消散了不少。
到《文學自由談》后感到既熟悉又有幾分陌生。所謂熟悉是因為過去的閱讀,對這本在文壇有著相當影響力的刊物存在著一些感性的閱讀認知,這份以犀利的批評文風為主的刊物,喚起我以往曾經擁有的閱讀體驗;而陌生則是一種必然。從《小說月報》的鑒賞、遴選優秀作品,到《文學自由談》熱衷于搜尋優秀作家、作品的瑕疵,雖然說對文學目標的追求一致,但取舍的眼光卻有了極大的差異。言之有物,曉暢明理的文學批評方式,決定著刊物的生存與發展;保持以往銳氣,敢于直面文壇現狀,將繼續贏得作者的尊重和讀者的青睞。《文學自由談》走過三十年歷程,仍煥發著勃勃生機,被讀者所喜愛,難能可貴,也多少有了一些傳奇色彩,需要自己認真探究這背后的奧秘,爭取以較短的時間適應新的工作。
和一位移居國外十多年的作家朋友微信聊天,告訴他我工作上的變化,他十分興奮:“你去那里好啊!這么多年過去,依然能保持銳氣的刊物,對我們的人生也會是一種難得的修煉。”我相信這是他發自內心的贊嘆,也幫助我增添了繼續持守刊物風格的信心。
《文學自由談》編輯部的辦公樓一墻之隔便是居民區,真是熱鬧。窗外,市井之聲相聞,人間煙火撲面。間或,有小販的叫賣聲、鄰里之間的談笑吵鬧聲傳來。臨近中午,住戶廚房里散發出的佳肴美味刺激著人的味蕾。市井生活的庸常劇,從編輯部的窗口望出去,幾乎每天都在循環演出,鳴奏出一幕幕生動的音符。
和那位朋友聊到這些情形后,他發過來兩行字:唔,我知道國內現在流行一個詞,叫接地氣,大概就是你們這個樣子吧。
我知道他在開玩笑,但細細品味,此話未嘗不是說出了從事我們這一行業所應遵循的某種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