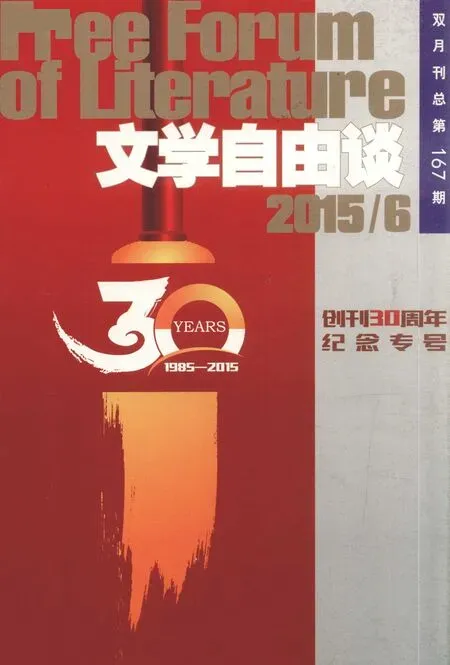我們的“大師和馬格麗特”
趙月斌
我們的“大師和馬格麗特”
趙月斌
嗨,《文學自由談》,你好哇!你創刊三十年,比我的“創齡”大一歲——從我發表第一首詩起,至今也快三十年了。如此說來,我們可算平輩,足可以套套近乎稱兄道弟。所以在我心目中,如果你有性別,也當為男性,不會是那個想來有點怪怪的“她”,因此就大大咧咧地稱你“《談》兄”吧。
這么多年,我接觸過不少文學報刊,但常常是有緣偶遇,無緣重逢,多數是一稿之交,文章發過便相忘于江湖。只有《談》兄你是個例外。回頭看看,我多次發過稿子的刊物真沒幾家,常年聯系的更少,而我和你卻有了十年的兄弟情誼。我有幾篇自鳴得意的文章,大都出自于你。我很是招搖地上了一回封面,也是因你之名。你的開本雖小,格局卻不小,總能不吝版面,任我縱筆騁懷,放言撒野。《文學自由談》之于我,自然就像自家兄弟一般,值得信賴,值得親近,甚至值得甩開膀子打一架。當然我寫這篇文章不是來“約架”的,反而是想借機肉麻一下——你正三十華誕,理當祝之賀之。可惜我既無官員字畫,也無戰國古錢,沒啥拿得出手的豪禮,只好不揣淺陋,在這里叨叨一番,權當寫給《談》兄的生日獻辭。
《談》兄出身于文學評論,然而自你一行世,便是文壇的孤劍,評論界的異端。你不立門派,不趕潮頭,自顧彈鋏而歌,不平則鳴,三十年不改初衷,在喜歡你和不喜歡你的人眼里,你,都是頗具風格的獨行俠。大概這也是我追從《談》兄的一個原因吧。假如你也像某些評論刊物那樣,權威得像衙門,大牌得像花魁,高端得像僵尸,驕貴得像百元大鈔,恐怕你也不會認同我的那種野路子,更不可能任由我不講套數地耍刀弄槍,不知深淺地和名家老手過招,跟龐然大物比劃,你在乎的不是輸贏成敗,只是一種無絆無羈的姿態。現在經常會在不同的場合,聽到有人抱怨當前學術體制,抱怨千篇一律的論文體例,“學院派”一統天下,英雄們盡入彀中,大家不得不像廣場舞大媽一樣,操練千人一面的“學報體”。這樣的抱怨聽得多了,越聽越像得了便宜賣乖:得了肥胖癥反過來怨飯難吃,怎么就不怪自己的嘴巴不爭氣呢?難道那體制和體例里,就裝不下一個騰挪跌宕的靈魂?或者,再把目光轉向廣場之外,難道他看不到,除了那種堪與國際接軌的“大媽體”,還有一種可以輕身簡行隨意走心的“自由體”?所以每每聽到英雄(大媽)們抱怨,他們是身在枷中,慘如行貨,我除了有點兒不以為然(你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好不好),還有種未入彀中的幸運感——還好,我沒被大媽收編,我離廣場很遠,但離《談》兄很近。
我等不材之木,南鄙之人,攀不上廟堂之高,只能偏于窮村陋巷,而《談》兄的所在,則如荒野中的客棧,可令許多無地彷徨的小散客有所寄靠,并可讓大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共傳一把薪火。所以在我看來,《文學自由談》既是一個看人下菜碟的小酒館,也是一個兼容并包、天高海闊的大碼頭。在這里,有竊竊私語的安靜角落,也有熱熱鬧鬧意興湍飛的大堂。因此所謂“自由體”才有其鋪排施展之地,我們才能看到,有人淺斟低唱,有人橫槊賦詩,有人皺著眉頭發牢騷,也有人撕破臉皮罵他娘。這情景有點兒像古人的壁上留言。崔灝到黃鶴樓,詩興大發,就往墻上寫詩;李白來黃鶴樓,也想在墻上題詩,可一看姓崔的寫得那么好,只好甘拜下風,便在墻上留了兩句批語:“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灝題詩在上頭。”這是著名的文壇佳話。宋江在潯陽樓喝多了酒,見酒店白墻上多有先人題詠,自己也詩興大發,接連往墻上寫了兩首反詩,還沒忘署了自己名字——結果竟犯了死罪;這是胡亂涂鴉惹來的禍端。可見古時的大白墻便是遷客騷人的文學論壇,只要心有所動,情有可抒,便明明白白寫到墻上。這樣的墻壁并無規劃設計,定是雜亂參差,眾聲喧嘩,也可能錯落呼應,互有交鋒,題壁者率意命筆,卻能讓眾看官讀出許多興味,找出許多妙處來。《談》兄給人的感覺正是這樣,你不單提供了一個來去自便的客棧,而且造出了一面任人置喙的大墻,讓來此落腳的人都能上得廳堂,登上高座,只要你的勇氣夠大,筆力夠強,完全可以擠到崔灝和李白的前頭。所以又不妨把“自由體”理解成一種“客棧體”,到這個客棧你可以高聲亮一嗓子,可以站到桌子上講一番大話,當然也可以找一塊空白的墻壁,縱筆寫出你的萬丈豪情。
客棧里的文學顯然有別于廣場或廟堂里的文學。《談》兄當也清楚:如今廟堂香火極盛,該有多少得道高人忙活著“在文學上成仙”;廣場上人多嘴雜,又有多少大內高手兼做了“維持治安”的文學大媽。眾仙家高居云端,上感天恩,下安民意;眾大媽火眼金睛,橫掃六合,絕地無敵。吾等道行既淺,視力也差,故與廟堂廣場無緣,只好一路荒腔走板,投向《談》兄的客棧。我的許多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話,我的一肚子的不合時宜,我的嬉笑怒罵,在別處可能直接啞火,或直接被卡死,唯在《談》兄這里,能夠一吐為快。這樣的刊物不在大小,只要它能留下一個說話的小口,就能通往深遠的未知之地,一份小刊物也能保持強大的生命力。盡管你也不得不修枝剪葉,掐尖去刺,但你多多少少保住了自由生長的可能。我曾在《文學自由談》發表過一篇《看哪,這個爪哇土著人》,是寫王小波的,談他的“寧靜的童心”、“人文事業”,談那只“特立獨行的豬”、“知識分子精神”,以及生來勇敢,不畏戰爭,且十分注重清潔的“爪哇土著人”。就是這樣一篇純屬向王小波致敬的文章,卻也能讓某大媽鼻孔上翻,好像嗅到了爪哇人可怕的氣息。好在《談》兄你的鼻子沒這么尖,否則我寫王小波的文章也只能呆在爪哇國了。還有一次,我寫了篇綜述文章,竟也有大媽告誡我,這樣的文章未經領導允許,不能隨便寫的。我可是真的不明白了,文學評論什么時候成了官方文書?難道都要統一口徑,要像衙門告示一樣先由領導批閱?但現在確是如此,文學評論有“學報體”,還有“公文告示體”,這種官樣文章寫得四平八穩,滴水不漏,每個字都準確到位,每個標點都不可增刪,真像是由領導層層把關研究出來的。這種“公文體”的評論總是通篇高屋建瓴,雖句句都是廢話,但又總能皆大歡喜——這樣的文學評論似乎越來越能體現出長官意志、集體智慧。所以每每想到這兒,我又為《談》兄捏把汗,誰知你的客棧會不會被大媽接管?
實際上,客棧體的精神底蘊當是“民間”,自由體評論也可視作“民間體”。《談》兄早已從文風文體上打開了“接地氣”的通道,所以,你本身也體現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民間立場、民間精神。說到“民間”二字,似乎很簡單,即便身在高位的官家老爺,也可以深入民間嘛,何況我等本來就很“民間”的平頭百姓?然而作為文學從業者的一些作家、批評家,卻往往很難具備一種自在自然的民間氣息,要么是學究氣太盛,要么是官僚氣太濃,要么就是勢利眼、軟骨頭,總之缺少那種鮮活生動的生命力,也缺少一種不失本心的真性情。有人一邊抱怨學術體制、官僚體制對文學的強奸,一邊快快活活地與其媾和,由此產下的不僅是學報體、公文體之類的怪胎,更壞的后果則是人文精神的潰敗。人們習慣了一種程式化的生存,當然也就有了程式化的思維和程式化的文體,所以某些貌似壯觀駭人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不過是浮腫且滑稽的文字僵尸。美國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有段經典臺詞:“監獄里的高墻實在是很有趣。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墻;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是體制化。”這是老牌囚犯瑞德的經驗之談。牢獄之災當然只是一種極端狀態,但誰又能說某種程式化的東西不比牢獄更可怕呢?有時候,我們強烈反對的,恰是自己最為習慣的。要打破某種教條和程式,莫如先拿自己的惰性和慣性開刀。
就拿作家莫言來說吧——“他扯下程式化的宣傳畫,使個人從茫茫無名大眾中凸顯出來。”斯德哥爾摩的幾個老頭大概沒看錯,管謨業之所以成為莫言,就因為他早就意識到,世上并非只有“歌德派”作家,還有一種作家“躲在黑屋子里,偷偷寫他們的《大師和瑪格麗特》”。莫言推崇的作家便是斯大林時期的布爾加科夫(1891—1940)。因遭到殘酷的政治迫害,這位作家生不如死,甚至請蘇聯政府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盡快“處置”他。然而就是在那種惡劣環境中,他卻傾盡最后的生命寫出了一部明知不可能出版的作品——長篇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直到他去世十七年后,這部偉大的作品才在國外出版;又過了十三年,他的祖國才有了第一個完全版本。究竟是什么信念,讓身處絕境的布爾加科夫不僅沒有放棄寫作,而且沒有變成“歌德派”?假如布爾加科夫沒有對人類的信念,沒有對個人的信念,他能否把全部生命投入到一本完全無望的書中?
還是《肖申克的救贖》中的一句臺詞:“有些鳥注定是不會被關在籠子里的,因為它們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耀著自由的光輝。”電影主人公安迪和瑞德是幸運的,他們最終逃出了籠子,獲得了自由。但人們要面對的問題往往與此相反:假如你只能關在籠子里,誰會在乎你羽毛上的光輝?假如你只能是斯大林時代的布爾加科夫,你會怎樣做?我們的作家也曾經歷過殘酷的極左時期,他們要么被迫害致死致殘,要么停筆不寫,還在寫的,則是與政治相茍且的作品;像布爾加科夫那樣醒著并寫著的,好像只有顧準、張中曉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可他們都不是作家。前兩年,有位老作家拿出了一部寫于“文革”時期的長篇——據說“窖藏”四十年——其蒙塵之久比《大師與瑪格麗特》更甚。這樣一部出土文物,是不是具有橫空出世的穿透力,是不是像《大師和瑪格麗特》那樣超越它所處的時代,具有一種先知般的省覺?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并未出土一位自己的布爾加科夫,那個作家拿出的仍只是那個時代的長篇。所以,籠子里的鳥,即便閃耀著籠子外的光輝,也難擁有一顆在籠子外面跳動的心。
再回到莫言——他不必躲在黑屋子里,便光明正大地寫出了《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等一大批作品,而且不必“窖藏”,包括《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蛙》之類大尺度的批判性作品,全都順利公開出版。莫言比他的俄羅斯同行幸運多了,也可見我們的籠子寬容多了,或者也說明我們的藝術空間并非如想象得那么狹隘。然而問題又來了:即便有作家寫出了他的《大師和瑪格麗特》,或者換一個說法,即便有作家寫出了他的《巴登夏日》,有作家寫出了他的《浮生六記》,但我們是否具有蘇珊·桑塔格和楊引傳那樣的膽識,能夠從地攤上揀出一部蒙塵的巨著?所以,還是回到前面的話題——我們如何才能打破自身的籠子?如何才能扯下程式化的假面,把個人從自身的體制中拯救出來?每個人都在種種形式的體制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黑屋子”,只是有的人把體制變成了自己的黑屋子,有的人把黑屋子變成了生命的暗室。因此也可以說,每個人都該有自己的“民間”,每個人都有自己“接地氣”的方式。就像《文學自由談》,誰把你當成籠子,誰就是你的籠中鳥;誰以你為客棧,誰就可以來去自由;誰把你視作兄弟,誰就能夠像我這樣任性,把一篇賀辭寫成不合時宜的意見書。
哦,《談》兄,請原諒我醉話連篇,辭不達意。當我談起你的客棧,談起莫言的黑屋子,其實我最想談的,卻是我們的“大師和瑪格麗特”——假如真的有這樣一部書,那么誰是其中的瑪格麗特呢?假如大師要焚燒掉他的手稿,又有誰會站出來阻止他呢?更為困難的是,假如這部手稿就在我們面前,誰能看到它的價值?又有誰敢高聲告訴大家?很多時候,我們閉著眼,什么都不想看到。很多時候,我們睜著眼,什么也沒看到。正是:
文學自由談談談,
談天談地三十年。
瑪格麗特誰曾見,
卻見荒村學莫言。
壯哉文學自由談,
文壇論劍三十年。
輸贏勿論有底線,
文學自由高于天。
——謹以此紀念《文學自由談》創刊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