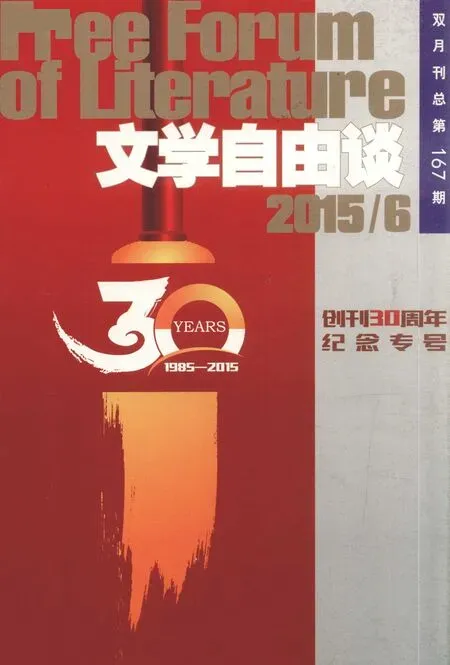相伴從混沌到透明
李美皆
相伴從混沌到透明
李美皆
《文學自由談》不折不扣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當我最初作為一個自由投稿者把稿子寄給《文學自由談》時,完全沒想到那么快會發表出來。后來我知道,稿子寄給編輯部就等于寄給任芙康老師,每篇稿子他都會閱看的,二十多年樂此不疲。
我相信幸運不會老是光顧誰,而且,無心插柳才有驚喜,有心栽花反而失望,所以,必須自覺抵制為小戰告捷而誤導,生孩子去才是正經。孩子生完,他自己長著,我干嘛呢?好像也沒做出什么來。
暑假過完,開學了。天也涼快了,心里有了落定的感覺,我就開始考慮寫東西。在完全懵懂的狀態下,憑著一點本能的直覺,很快寫出關于余秋雨的文章,寄給任老師。心里真的很忐忑很忐忑,比寄給一個陌生的編輯還要忐忑。心里是一團不安的霧氣:我這是寫的什么玩意兒?這叫文章嗎?這樣寫,成嗎?因為在此之前,我從來不知道評論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不確定使自己煞是氣餒,甚至有點后悔把稿子寄出去。
就當石沉大海,算了吧!我對自己說。但是居然,任老師打來了電話。他說,文章甚好,此期就用。他并告訴我這一期用我一張封面照片。我說,您真的認為這樣寫可以嗎?他說,怎么不可以?這就是你異于他人的路數。他的肯定,讓我安心于這種表達方式,不再狐疑。
既然這樣寫就叫“好”,我還可以寫更多呀。于是我又將一篇關于蘇童的稿子寄給任老師。他說,這一期一起用。這樣,2004年第6期《文學自由談》發了我兩篇長稿,登了我一張封面照片。當時我還沒有數碼相機,照片是臨時請單位電教中心的攝像師拍的,拍的時候我還籠罩在半信半疑惶惑不安之中,很是放不開。
一切如在夢中。然后,人生漸漸透明。
盤點一下,我與《文學自由談》結緣已有十余年了。這十余年,是我人生變化最大的時段,這變化很大一部分是它帶給我的,想想真是感慨。我對《文學自由談》的感激,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任老師的感激。在成為《文學自由談》的“經常作者”之前,我對于自己的人生從來沒有過寫文學評論的規劃,直到遇見任老師——這樣直截了當地贊美一個人,真的有點發窘,但是,對一本適逢三十華齡的刊物,感懷是必須的;對一位把最好的年華獻給了這本刊物,與刊物相伴占據職場生涯大半光陰的編輯兼主編,我自覺有義務把他寫開心了,寫感動了。《文學自由談》的三十年紀念之后,他一定會跟刊物漸行漸遠了。在這樣的時候,我理應不再保留我的贊美,而是淋漓盡致地獻給他。
整個2005年,我都在為《文學自由談》寫稿,一期不落。那時候真是混沌和無知者無畏,幾乎不查資料,也不知文壇水深水淺,就是在自己的天地里盡情地寫。多數時候寫得快意,有時也很辛苦,因為已經背負期待,擔不起他人的失望,也擔不起自己的失望。記得寫某一篇稿子時,已經做好了前期準備,任老師也等著發排了,可我就是抵觸正式寫作的開始,心累到不行不行的。當時住在郊區,生活很單調,舉目四望,沒什么可調劑的。終于,有人陪我進城去玄武湖公園逛了一個下午,吃了一頓飯,然后回到家一頭扎進去就寫,一口氣寫完才敢浮出水面,中間一直悶在水里保持一種節奏,連抬頭換口氣都不敢,居然也很順。可見,不逼不成。
現在想想,那種傻傻的混沌的狀態再也不會有了,就像亞當和夏娃再也回不去伊甸園。
那時候與任老師的電話互動真是令人興奮,我一說他就懂,他一點我就通。寫作的過程我毫無顧慮,因為總歸他會把關的,有一道安全屏障在那兒呢。有他托底,我且撒歡。從他那兒,我學到怎樣把犀利的意思表達出來而又不觸礁,怎樣把邊球擦得毫無懸念游刃有余。當然,他為人“固執”,也有過“恨鐵不成鋼”而摔電話的時候。有一期,《文學自由談》發了我批評一位詩人的文章,下一期又發出針對我文章的批評。我有些想法,又不愿電話里說,便給任老師發去短信:你發我的稿子,是為了你的刊物;你發批評我的稿子,是為了同詩人的友情。當天接到他的電話,一通訓斥:只想批評別人快意,不能承受他人的反敲打,如此狀態,怎么能在批評界混呢?事后想想,他的道理比我的道理更有道理,人應該“皮實”,于是也就釋然。這類事都不會成為芥蒂。
漸漸地,超越主編和作者關系,他似乎成為了我的“牧師”。他給我的指導,介乎出世與入世之間,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在我生活中有大事發生時,要跟他叨叨過之后才會心定,以他的智慧和閱歷,正適合做我的定海神針。他的建議不見得我會全盤接受,但他總能給我一個有益的維度。在我沮喪壓抑時,他會以掀翻世界的豪言,讓我一下子長了威風,讓我頓時看到什么都是浮云,該渾不吝時就得渾不吝。當我文藝情懷發作時,他會讓我注意地上,別騰云駕霧卻踩了虛腳。他的肯定,他的批評,總而言之,他的關切對我的一生不可或缺,我從他身上學到許多。他對我的心態、為人處世的方式以及整個人生態度都有不小的改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影響了我的“三觀”。他的存在給我一種莫可名狀的安全感,如果說我的心理到今天還算比較健康的話,應該得益于他。
再熱愛舞蹈的人,也會有厭倦穿著紅舞鞋不停地跳的時候。我喜歡改變,不喜歡長時間呆在一種狀態里。多次有看過我文章的人初次見面表示驚訝:你是這樣子的?我想象你的身高至少應該再高些。我明白別人的意思,透過我兇悍的文章,別人看見的是一個女版李逵或孫二娘。對此我也抵觸。我熱愛自己作為女人的一切。
一篇必須完成的關于丁玲晚年的博士論文也要求我改變。于是,我在《文學自由談》不再那么經常地出現,偶爾出現,也未必頭角崢嶸。于是,與兇悍相反的指責又出現了,比如,你武功廢了——我從來不是“武婦”,何來武功?又何來武功之廢?當我被正面烤了又反面烤,兩面都烤過之后,對于別人說什么已經不那么在乎了,但要說自己沒有一點焦慮,也是不誠實的。在這一時期這一狀況中,對我期望最大也最有資格給我壓力,卻唯獨不給我壓力的,就是任老師。在我自己都快不理解自己的時候,他好像還能理解我。有時他問有稿子嗎,我說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他都說,那就悠著勁兒寫吧。他當然在以極大的耐心,等著我完成博士論文回來。而且,他從來沒有因我寫不出他期待的稿子就鄙薄我的博士論文,這點對我也很重要。他讓我能夠穩住,不失信心。如果對一個作者沒有把握和包容,是很難成為好主編的。
任老師還處在前電子前網絡時代,不會用電腦不會上網不會發短信,他的看稿編稿,幾乎還是用漿糊剪刀的原始方式。這樣的方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僵化落后古板之類的詞,但《文學自由談》事實上卻辦得熱熱鬧鬧生動活潑,讀者、作者都能夠在這里感覺到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可以說,他是用前現代的方式在辦著現代或后現代的刊物。任老師敬業到好玩的程度,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主編每期逐個打電話告訴作者:你的稿子采用了,請把電子稿發到電子郵箱。這個郵箱還要從一位叫馬麗的人那兒獲取,因為他怕傳錯了字母。而在《文學自由談》創刊三十年紀念活動中,他把排版制作刊物的馬麗等人也請來了,表達多年合作的謝忱,也讓作者們認識一下這個聯系多年卻從未謀面的端莊女孩兒。這在各種紀念活動中是罕見的,可見他貌似粗放,實際卻是一個多么周全的人。
一本刊物的風格,就是一個主編的風格。任老師不是一個追求鐵肩道義之類的編輯家,而是一個有個性有張力有魅力的主編;他不是梗著脖子鐵青著臉辦刊,而是嬉笑怒罵舉重若輕,通過稿件之間的一些起承轉合的呼應,讓好玩的更好玩,有意思的更有意思。這也是《文學自由談》能夠生機勃勃的原因。
希望在后任芙康時代,《文學自由談》繼續做好文壇的輕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