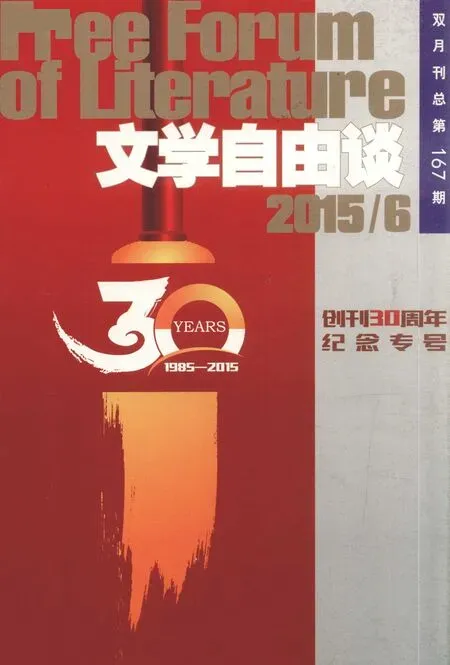我與《文學自由談》的二三事
何 英
說起我和《文學自由談》的淵源,才想起,到今年,已整整十年了——也算是老作者啦。
2005年那期魯院高研班,跟桂元同學。這個班,稱為第五屆中青年理論評論家班,時間短,就兩個月。我記得在班上,幾乎跟桂元就沒說過幾句話。結業以后,他忽然跟我約稿,好像是為魯院的一本內刊寫一篇紀念性質的文章;之后,他又跟我約了《文學自由談》的稿子。那時,《文學自由談》在我心里是很神秘的,一神秘就高大上了。在此之前,我跟當時經常一起玩的同學說,我也要上那本刊物;雖是說著玩的,但桂元大概聽到了我的呼喚。只是第一篇稿子讓他頗為失望;現在想起來,大概是他以為我會寫四五千字,沒想到我只寫了兩千多字。那篇文章叫什么,我已經忘了。那時還沒有QQ、微信,無法翻查記錄;上網搜了好久,也沒搜到;而U盤用久了會丟,電腦更是兩三年一換——我們到底還能記住什么呢?像魯迅時代那樣寫日記、存手稿,也許還靠得住一些。借紀念《文學自由談》創刊三十周年之機,我也順便回憶一下自己作為一個作者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免得六十周年的時候,死活想不起都發過啥了。
其后不久,我就認識了任芙康老師。他先是來新疆,去了喀納斯(用他的川味加津味普通話,叫“嘎拉斯”)。他在烏魯木齊停留時,我請了兩個朋友,陪他在二道橋的米拉吉民族飯店吃飯,聽他那笑點頻出的聊天。那天我得到的一個訓示是,作為一個搞評論的,永遠不要做一個只會跟風講好話、拍馬屁的庸人(我理解的大意是這樣)。直到今天,我還能清晰地在自己的文字生涯中看到這句話的影響。后來,我去天津學習,任老師請飯(為嘛我記得的都是吃呢),席間頻頻勸菜,讓我覺得他也是一個重視吃飯的人。
2013年,在上海《文學報》年度批評獎頒獎活動上,我又遇到任老師;跟桂元卻再沒照過面。但我并沒放過他:一次是我出了一本小書,本地報紙熱情宣傳,要一篇書評,我請桂元捉筆,他寫了《何英:穿越邊地,抵達“中心”》(其實,我至今也沒有“穿越”);后來,燕玲老師在《南方文壇》做批評家小輯,我又請桂元寫了《職業閱讀、邊地想象與批評氣場——何英文學批評的一種觀感》(看來,這“邊地”的身份或想象還真有點有眾不同呢)——我仗著是他的同學,又是《文學自由談》的作者,也就不管他是否不勝其煩了。
我和《文學自由談》并肩戰斗過、榮辱與共過、惺惺相惜過。如今,翻看著我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的文章,那些折射透露著我當時的狀態、見識、心情、思想的文字,還是讓我有些小激動;它們堪稱我月度或年度的紀事。很少有作者甘愿承認某個刊物培養了自己,我也一樣。我的文章風格多變,不愿受約束。但《文學自由談》似乎更強勢,在潛意識里塑造著我們,改變著我們。我還遭遇過退稿,稿子也經常被改。比如《當代文學的十個詞組》,就被改成了《當代文學的六個詞組》。后來“待遇”上去了,不怎么改了,可能是編輯發現我這個人腦子終于拎清了,或者培養成功了。我后來貼在QQ空間里的文章,都是經編輯改過的。
為什么作者自己喜歡的文章,通常跟讀者或刊物的趣味不一樣呢?比如,桂元和陳歆耕老師都會提到我的《對〈秦腔〉評論的評論》,而任老師比較欣賞《王安憶與阿加莎·克里斯蒂》(這篇文章還使我榮登《文學自由談》封面,一時間還在我們那個“邊地”引起各種小轟動)歆耕老師在《美人如玉劍如虹》中寫道:“我看到何英發在某期《文學自由談》上批評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的文章,正是《新批評》所需要的‘靶標精準’而又文字犀利的稿件,于是就聯系何英,請她做一些修改后再發給本刊。”(由于這篇文章,我跟《文學報·新批評》結緣。)有些讀者喜歡我寫張愛玲的《千古恨事由此鋪開》,而評論嚴歌苓《陸犯焉識》的《總是失敗的諸神》,甚至引起后續三篇文章提到對我的批評和反批評。其實,我自己則更愿意《當代文學的六個詞組》(六個也罷)《無情的文學》《敘事如何與信息共舞》《才女何須福薄》《閣樓上的瘋女人》這樣一些文章被關注。當代某個具體的作家或作品,跟我有何情仇,關我何事,認都不認識,不過是想把自己的真實見解分享出去,做一個說真話的唐·吉訶德——在別人看來不管有多可笑可憎,對不起,有些人就是干這個的。
到后來的《好萊塢的東方想象》,是評嚴歌苓《媽閣是座城》的,緣由是《文學報》編輯跟我約稿,后來編輯也說:我知道你寫她寫的太多了,寫得都……說到這里,我覺得還是挺幸福的。《文學自由談》也好,《文學報》也好,對我都還是較為寬容的,我的幾篇稿子,兩家差不多都是同時發。我在羞愧害臊之余,也為自己找到一點說辭:如今看評論的人少了,評論刊物有影響的,就那么幾家,辛辛苦苦地寫出來,讓更多點人看到,不也挺好嗎?但我知道,肯定很多人不這么想,所以,如今我也寫得少了,不敢寫了。
最近的《“強勢”表演的背后》,也是一篇頗為吃力的文章。其實,我寫每篇文章都很吃力,所以一直羨慕那些出手快、產量高的作者。還是積累不行,不夠眼明心快,力氣也小。搞評論是個力氣活兒,精力不旺盛、沒有說話欲的人,就不要搞了。這篇文章本來的題目是《閻連科:批判對抗姿態的后面?》,發表時的題目就更生猛了。這是刊物的需要,其實更是讀者的需要。世上的事,就是這樣,有得有失。好像寫當代作家的評論,好處是后來人可以藉此了解當時的各種狀態、背景、心理機制,可以復原鮮活的即時信息;不好之處是,誰也沒長前后眼。文學上的事兒,還有一些另外的決定力量。就像巴爾扎克,當時并不被一些法國批評家看好,嫌他文字粗糙,所寫內容也不像一個有教養的作家應該呈現的,可是現在誰能否認他的價值呢?
對那些把控不了的因素,不用去想了,做好自己能做的就好了。這句話是明理人都遵循的行事規矩。我不知道是不是還有一些文章,在《文學自由談》上發過。桂元隔段時間會來約稿,偵探一下我這個不勤快的作者。這使我又想起自己做雜志編輯時,好像從來就沒有去主動約過稿。如此對比起來,《文學自由談》更像是一個敬業的鷹巢,放飛了大大小小的鷹,但只是在那里守望著、接納著。它的眼睛盯著鷹們,也盯著讀者。封底上“自詡”的“一本……的刊物”那幾行字,他們確實做到了。這背后,誰能知曉他們的堅持和付出的努力,種種繁難和是非,是非之后的承擔,為人作嫁的甘苦和冷暖?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它在讀者心里幾十年如一日般穩定如山的品質。它向全國撒開了一張網,把我們聯結在一起并肩戰斗——原來自己并不孤單,一個遠在新疆的作者,也被緊密地粘結在這張網里,孤懸塞外與繁華津門,就這樣開始了面向廣闊天地的對話之旅。
作為奇葩的水瓶座,內心縱然翻江倒海,外面也是冰山一座,甚至會做出相反的動作來。寫到這里才發現,自己是不是太冷靜了。也許別人早都熱淚盈眶,說出一些暖心話來。好吧,衷心祝愿這本傾注了任老師、桂元及許多編輯、作者情感的刊物,生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