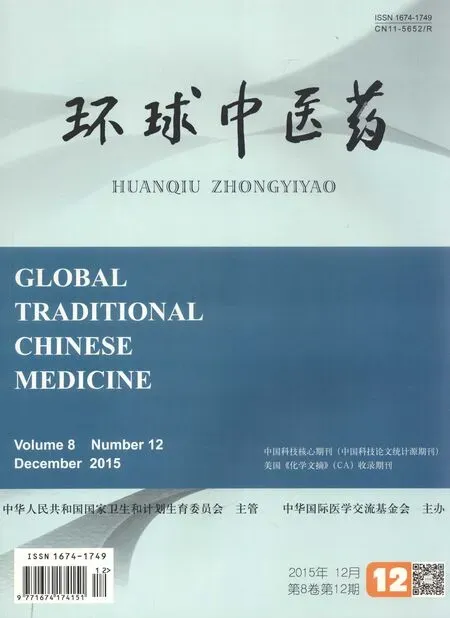從“脾損為本,濕濁為標”的角度論消渴病
趙潤栓 劉歡
“消渴”一病,今人多對應“糖尿病”來論治,或1型,或2型。自清代醫家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提出“三消一證,雖有上、中、下之分,其實不越陰虧陽亢,津涸熱淫而已”之病機以來,有后代醫家遵此古訓,認為消渴病總屬“陰虛為本,燥熱為標”,每見消渴病,動輒投以麥冬、當歸、生地黃、天花粉之屬,及至療效欠佳,復歸咎于患者飲食未加節制,或運動方式不合理云云。果真如此嗎?筆者不惴愚鈍,從“脾損為本,濕濁為標”的角度對消渴病談談個人見解,愿與同行探討。
1 對“消渴”病“陰虛為本,燥熱為標”的思考
從《臨證指南醫案》提出消渴病“陰虛熱淫”之病機以來,后人對消渴病的治療思路大多圍繞陰虛與燥熱展開,或兼氣虛,或顧血瘀。對此,筆者有些不同觀點。
中醫學在認識疾病的時候,大多數情況下是樸素的、唯物的、直觀的,尤其在定義病名上,往往患者主要表現為什么,便診斷為什么病。例如“泄瀉”“癃閉”“鼓脹”“水腫”“眩暈”,都是將主要表現定義為病名,然后再圍繞該病名進一步闡述各種證型和病機。即使對藥物功效的論述上,也是非常樸素且直白的,例如萊菔子可以“寬中除滿”治療中焦脹滿;紫蘇子可以“降逆止咳平喘”治療肺氣上逆咳嗽氣喘;小薊可以“涼血止血”治療血熱迫血妄行之尿血;白頭翁可以“涼血止痢”治療熱毒血痢等。這種樸素的認識疾病與藥物功效的思想貫穿了中醫學認識疾病與治療疾病的全過程,中醫學的理、法、方、藥和方劑中的君、臣、佐、使,以及藥物之間相須、相使、相畏、相殺等關系,也無不體現了這種思想。這便是中醫學,樸素、原始卻又圓滿、獨立。也正因為中醫是這樣一種生活化了的科學,才能在幾千年來為人們容易理解,并欣然接受,廣泛扎根于民間,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此可以推論,中醫前賢著書論述“消渴”一病,則該病必然以口渴多飲為主要表現。博觀古籍記載之“消渴”,大多也真正具備了“消渴”一詞字面含義所代表的癥狀,即患者真正表現為口渴多飲。如《證治準繩》記載:“渴而多飲為上消(經謂膈消);消谷善饑為中消(經謂消中);渴而便數有膏為下消(經謂腎消)。”《千金要方·消渴》篇說:“飲噉無度,咀嚼鲊醬,不擇酸咸,積年長夜,酣興不懈,遂使三焦猛熱,五臟干燥,木石猶且干枯,在人何能不渴?”《丹溪心法·消渴》篇也說:“酒面無節,酷嗜炙煿 ……于是炎火上薰,腑臟生熱,燥熱熾盛,津液干焦,渴飲水漿而不能自禁。”可見,前賢論述“消渴”,則該病必然以口渴多飲為主要表現。
現代醫學之“糖尿病”中,真正具備多飲、多食、多尿、消瘦癥狀的,絕大多數是1型糖尿病,而2型糖尿病中,具備典型“三多一少”癥狀者,為數不多。而且,糖尿病在今天這種生活方式下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而在古代,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一定要比今天低得多。而且,表現為典型的“三多一少”的2型糖尿病可謂更少。可以假設,古人見到的“消渴病”,應是以1型糖尿病者居多,對少數以口渴多飲為主要表現的2型糖尿病,也統統歸屬于“消渴”病來論治,畢竟中醫是不區分1型還是2型糖尿病的,也沒有必要區分,凡表現為口渴多飲者,就是“消渴病”,不管是糖尿病引起的消渴,還是非糖尿病引起的消渴。中醫的核心思想和精髓是辨“證”論治,有是證而用是藥,可以異病同治,也可以同病異治,關鍵是“證”與“治”的吻合,而非“病”與“治”的對應。對于真正的“消渴”,滋陰清熱自然如理如法,但對于現今社會常見且高發的2型糖尿病,筆者認為,治療時不可以墨守“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之陳規,有時滋陰清熱反而適得其反。關于這一點,稍后筆者會結合病例來談。
2 對“消渴”病“脾損為本,濕濁為標”的闡釋
現代醫學認為,2型糖尿病是一種具有遺傳傾向的多種綜合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謝性疾病。多數由于個體長期攝取過多高蛋白、高糖分、高脂肪、高熱量飲食,而體力活動卻不足,導致體內脂肪儲存增加所致。這與《黃帝內經》所闡述的機理是一致的。《素問·奇病論篇》說:“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可謂將糖尿病的病因、病機、患者的形體特征、臨床表現做了精辟的論述。
脂肪、蛋白質、糖,這是滿足生命活動的主要能量來源,為了保持生命,人們必須進食。但正如臨床所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沒有好好管理自己的飲食,包括食物結構、食物量、食物種類。往往恣情縱欲,貪圖美酒佳肴,膏粱厚味。畢竟香甜可口的食物對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但這種生活方式同時也埋下了健康隱患。
中醫認為,飲食不節,必然傷脾。脾失健運,后果有二:一者,中焦氣機失暢,轉輸不利,氣血生成乏源,此為虛證;二者,水液不能正常運化輸布,變為痰飲濕濁,此為實證。由此二者,可以演變出許多虛虛實實、虛實夾雜的疾病與證型。現代醫學之肥胖癥、高血脂癥、糖尿病、脂肪肝、代謝綜合征、高尿酸血癥等,莫不與此有關。甚至冠心病、腦卒中、動脈斑塊形成、厭食癥、潰瘍病、結腸炎、癲癇病、抑郁癥等,也與脾失健運、濕濁內生的病機不無關聯。蓋脾胃乃后天之本,根本受損,則百恙生焉。
據《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15年)》研究結果顯示,全國18歲及以上成年人中糖尿病的患病率為9.7%。另一項研究稱,中國糖尿病總體人群中1型糖尿病的比例大約占5%,而2型糖尿病占95%左右[1]。糖尿病患病率是如此之高,試想,如果個體出現陰虛燥熱的種種表現,他是不會感覺不到身體的異樣的,但臨床上2型糖尿病患者因口渴多飲而被確診者比例很少,多數都是通過健康體檢才被發現的,很多患者甚至疑惑自己怎么可能患糖尿病?很多患者不僅沒有“三多一少”癥狀,反而表現為不欲飲水,食欲不佳,體重增加,喜靜懶動等癥狀。這些癥狀用“陰虛為本,燥熱為標”的病機是無法解釋的,因為當今社會的糖尿病病機,筆者認為,“脾損為本,濕濁為標”應占主導地位。
飲食不節,脾失健運,故見納呆食少;水濕內生,停而為痰,留而為飲,聚而為濁,阻遏氣機,清陽不升,濁氣不降,故見大腹便便,困頓乏力,好逸惡勞,舌苔厚膩,大便黏滯;濕為陰邪,重濁黏滯,雖不傷津液,卻也非津非液,故見口黏口膩,口不渴,或飲不解渴;又因濕郁化熱,或濕滯瘀成,而生種種變證,如濕熱互結,濕瘀交困,氣滯血瘀,氣陰兩虛,陰虛濕困等等。筆者認為,這是當今糖尿病最主要的病機。圍繞此機,臨證當健脾胃,化濕濁、行瘀郁、利氣機,使中焦轉輸復職,三焦水道復利,清陽得升,濁氣得降,氣血化生有源,津液敷布正常。如此,才是恢復陰陽平衡,臟腑和諧之樞機所在。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45歲,2015年5月請筆者診治。患者因工作關系,日常應酬頻繁。兩年前單位體檢發現空腹血糖8.2 mmol/L,餐后2小時血糖15.5 mmol/L。后多次監測,血糖值均居高不下。當地醫院診斷為“2型糖尿病”,給予“瑞格列奈片”治療,每次1 mg,三餐前半小時服用,并囑控制飲食,適量運動。服用藥物后,患者自訴空腹血糖控制在6.9~7.6 mmol/L之間,餐后 2小時血糖控制在 12.1~13.6 mmol/L之間。因擔心藥物不良反應,患者未加大服用劑量。今年2月份開始,配合中草藥治療過40余日,自訴血糖控制終不理想,4月初測糖化血紅蛋白為7.4%。為求良好控制血糖,請筆者調治。
筆者參閱患者先前服用藥方,大多為益氣、養陰、清熱、潤燥之屬。諸方中生地黃、葛根、天花粉、麥冬,黃連,黃精等品幾未中斷。觀患者形體豐盛,面部油膩,舌苔厚膩略黃。自訴應酬較多,但也會考慮到病情而自覺控制食量,有空閑時間也會有意增加活動量,但常感困頓乏力,運動后也未覺輕松。自感食欲并不旺盛,有時甚或不吃亦可。大便常黏滯不爽,口干但不欲飲水。睡眠好,倒頭即可入眠,但多夢,醒后未覺神清氣爽,脈象沉濡。筆者認為,證屬脾虛濕盛,處以藿樸夏苓湯加減,廣藿香20 g、佩蘭20 g、姜半夏15 g、陳皮15 g、茯苓 30 g、黨參 15 g、蒼術 15 g、薏苡仁 30 g、白扁豆20 g、冬瓜皮 30 g、枳實 12 g、厚樸 12 g、遠志 20 g、石菖蒲30 g、紅花15 g、甘草9 g。7劑,水煎服,每天1劑,早晚空腹溫服。
一周后復診,自訴食欲較前轉佳,口內黏膩感減輕,想喝水,困頓乏力感好轉,運動后不似先前感覺疲累,尿量好像較前增加,大便黏滯現象減輕。并訴因口渴、多尿、食欲好轉,自恐血糖較前升高,近日監測反有下降。欣喜之余,不可思議,找余復診。觀其舌苔已不似先前那般厚膩,脈象也有伸揚之象,前方去茯苓、冬瓜皮,加升麻12 g、葛根12 g,7劑。
后患者又來復診三次,每次都有自行監測血糖數據,均平穩好轉。6月中旬測糖化血紅蛋白為6.4%。余每次立法遣方均著眼于健脾運、化濕濁、升陽氣,兼顧行氣活血,并告知患者血糖生成指數、食物平衡寶塔、糖尿病有氧運動注意事項等生活方式調理常識,患者降糖藥物始終未增量,但血糖控制良好,最后基本掌握了飲食、運動、藥物三者協調,幫助平穩控制血糖的最佳個體方案。隨訪至今,效果滿意。
按 但見乏力,口干,大便不爽,便認為屬于氣陰兩虛,處以益氣、滋陰、清熱、潤腸之品。殊不知,乏力乃因濕性重濁,清陽難升,令人困頓而感疲倦;口干則是濕邪困阻,氣血津液不能正常敷布所致,并非真正陰傷津虧,因而自覺口干但并不欲飲,因飲后脾為濕困,不能蒸騰氣化,反加重濕濁;大便不爽,屬濕邪牽制,并非陰虛腸道失潤;睡眠好,亦并非真正質量好,乃是濕困清陽,清竅蒙蔽,沉沉欲寐罷了,所以即使入眠也夢幻紛紛,醒后難覺神清;應酬頻繁,佳肴瓊漿,膏粱厚味,必然脾傷;形體豐盛,面部油光,舌苔厚膩,皆是痰濕壅盛之象。因而,筆者從健脾助運、化痰祛濕的角度立法組方,取得良效。后期不用茯苓、冬瓜皮者,蓋脾既損傷,津液乏源,不欲過度利濕傷正也。加升麻、葛根是為升舉陽氣;用菖蒲、遠志,意在豁痰寧神;佐枳實、紅花,功圖行氣活血。藥量偏大,是因患者形體壯實,量小恐力薄難勝重任。組方思路清晰,加上患者態度端正,積極配合生活方式干預,因此收到良效。余所遇糖尿病,“脾損為本,濕濁為標”者較“陰虛為本,燥熱為標”者為多,每次從健脾運,化濕濁角度立法治療,皆能取得良效。
4 中醫體質學研究結論對糖尿病“脾損為本,濕濁為標”的佐證
中醫學認為,體質是由先天遺傳和后天獲得所形成的,是個體在形體結構和功能活動方面所固有的、相對穩定的特征。個體體質的不同,表現為生理狀態下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性和適應性的某些差異,以及發病過程中對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疾病發展的傾向性[2]。關于糖尿病的中醫體質研究結果,各家說法不一,考慮與地域、年齡、樣本量、評價標準等因素有關。但痰濕質(或濕熱質)、氣虛質在糖尿病的中醫體質研究中,均具有不容忽視的比例。孫冉冉等[3]的研究結果認為,2型糖尿病前期中醫體質類型以氣虛質、痰濕質為主,發病期以痰濕質為主。鄭勇強等[4]的研究結果認為,氣虛、陰虛、痰濕體質為2型糖尿病人主要的體質類型;并且針對具有2型糖尿病遺傳危險因素的非糖尿病人群進行中醫體質辨識結果顯示,平均轉化分最高的4種體質類型分別為氣虛、濕熱、痰濕、陰虛體質[5]。
痰濕質,是一種以形體肥胖、腹部松弛肥滿,面部皮膚油脂較多,多汗且黏,困倦多痰,大便黏滯不爽等為主要臨床表現的體質類型。這種體質類型與個體長期攝入過盛能量,而體力活動卻不足,致體內脂肪儲存增加有關。中醫學也有“胖人多痰濕”之說。糖尿病患者多痰濕質,這與該人群普遍存在的飲食不節現象是吻合的,亦即《素問·奇病論篇》“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所言之理。
綜上筆者認為,在當今2型糖尿病高發的狀況下,醫者臨證時,要考慮到該病高發的現實背景,不可墨守“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之陳規,動輒處以滋陰清熱之治法,當適時轉變思路,從“脾損為本,濕濁為標”的角度考慮該病的病機與治法,往往可以取得良效,愿與同行探討。
[1] 梁夢璐,胡永華.1型糖尿病病因流行病學研究進展[J].中華疾病控制雜志,2013,17(4):349-350.
[2] 王琦.中醫體質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2.
[3] 孫冉冉,鄭燕飛,李玲孺,等.從中醫體質角度探討2型糖尿病的防治[J].環球中醫藥,2014,7(5):375.
[4] 鄭勇強,楊曉瓊,陳桂鳳,等.2型糖尿病患者的體質分布分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4,20(3):329.
[5] 鄭勇強,楊曉瓊,蘇茹.2型糖尿病遺傳危險因素人群的中醫體質分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4,20(6):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