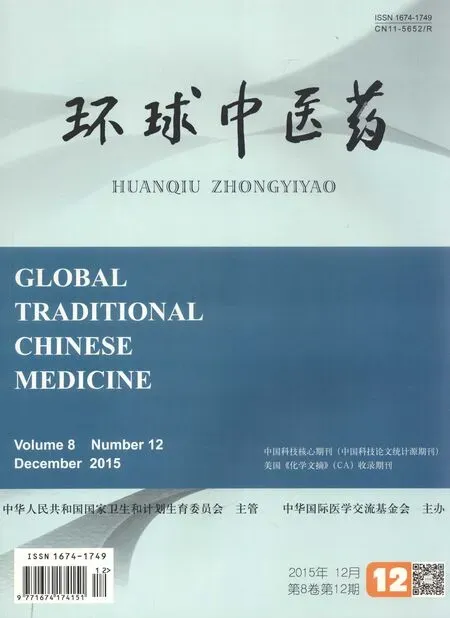李書(shū)義辨識(shí)“真中”與“類(lèi)中”探討
孟繁東
李書(shū)義,北京市著名中醫(yī)專(zhuān)家,北京市首批中醫(yī)藥薪火傳承“3+3”工程“李書(shū)義基層老中醫(yī)傳承工作室”指導(dǎo)老師,北京市第四批老中醫(yī)藥專(zhuān)家學(xué)術(shù)經(jīng)驗(yàn)繼承工作指導(dǎo)老師。李書(shū)義老師幼承庭訓(xùn),后拜傷寒派大師陳慎吾為師,得其親傳,根基深厚。對(duì)于腦血管疾病的治療,針?biāo)幉⒂茫岣吡睡熜А9P者有幸跟隨李老侍診多年,受益匪淺。茲將李老對(duì)“真中”及“類(lèi)中”的辨識(shí)進(jìn)行探討。
1 “真中”與“類(lèi)中”的歷史沿革及各家不同認(rèn)識(shí)
目前認(rèn)為,中風(fēng)病是指在氣血內(nèi)虛的基礎(chǔ)上,因勞倦內(nèi)傷、憂思惱怒、飲食不節(jié)等誘因,引起臟腑陰陽(yáng)失調(diào),氣血逆亂,直沖犯腦,導(dǎo)致腦脈痹阻或血溢腦脈之外;臨床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斜,言語(yǔ)謇澀或不語(yǔ),偏身麻木為主證;具有起病急,變化快的特點(diǎn);多發(fā)于中老年人。相當(dāng)于西醫(yī)的急性腦血管病,又稱(chēng)腦卒中,是一組以急性起病,局灶性或彌漫性腦功能缺失為共同特征的腦血管疾病。從病理上分為缺血性中風(fēng)和出血性中風(fēng)兩種[1-2]。唐宋以前醫(yī)家,對(duì)中風(fēng)病因多從“外風(fēng)”立論,如王永炎指出:“中風(fēng)的病因?qū)W說(shuō)在漢唐時(shí)代,論證皆為外因,金元以后辨證乃識(shí)內(nèi)因。這是中風(fēng)病因?qū)W說(shuō)發(fā)展過(guò)程的一大轉(zhuǎn)折。”[3]元末明初醫(yī)家王履則首次提出了“真中”與“類(lèi)中”的概念,《醫(yī)經(jīng)溯回集·中風(fēng)辨》指出:“殊不知因于風(fēng)者,真中風(fēng)也;因于火,因于氣,因于濕者,類(lèi)中風(fēng)而非中風(fēng)也。”[4]此后,對(duì)中風(fēng)病“真中”與“類(lèi)中”各有側(cè)重,強(qiáng)調(diào)“真中”之醫(yī)家如清代蔣寶素曰:“真中風(fēng)者,真為風(fēng)邪所中。卒然擊仆偏枯,神昏不語(yǔ)等證,與陰虧火盛,陽(yáng)虛暴脫之擊仆偏枯,神昏不語(yǔ)等證相類(lèi),而真?zhèn)坞y分,卻真有風(fēng)形可據(jù)之證也。”[5]強(qiáng)調(diào)“類(lèi)中”之醫(yī)家如金元四大醫(yī)家的劉河間指出:“凡人風(fēng)病,多因熱甚,……俗云風(fēng)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fēng)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fēng)實(shí)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于風(fēng)爾。由乎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yáng)實(shí),而熱氣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wú)所知也。卒中者,由五志過(guò)極,皆為熱甚故也。”[6]明代醫(yī)家張景岳的《景岳全書(shū)·非風(fēng)》指出:“非風(fēng)一證,即時(shí)人所謂中風(fēng)證也。此證多見(jiàn)卒倒,卒倒多由昏憒,本皆內(nèi)傷積損頹敗而然,原非外感風(fēng)寒所致,而古今相傳,咸以中風(fēng)名之,其誤甚矣。余以‘非風(fēng)’名之,庶乎使人易曉,而知其本非風(fēng)證矣。”[7]強(qiáng)調(diào)類(lèi)中之另一代表醫(yī)家為張伯龍:“類(lèi)中一病,猝倒無(wú)知,牙關(guān)緊閉,危在頃刻。此癥腎水虛而內(nèi)風(fēng)動(dòng)者多,真中風(fēng)則甚少。此癥原非外感風(fēng)邪,總由內(nèi)傷氣血,腎水焦枯而然。”[8]現(xiàn)在認(rèn)為,“真中風(fēng)為風(fēng)從外來(lái),自表入里,由皮毛至經(jīng)絡(luò)到臟腑,常先有寒熱、頭身疼痛、肢體拘急等外感表證,隨之出現(xiàn)口眼?斜、半身不遂、僵仆不語(yǔ)等癥;類(lèi)中風(fēng)為風(fēng)自內(nèi)發(fā),無(wú)外感表現(xiàn),常先有中風(fēng)先兆癥狀,如眩暈、耳鳴、頭痛、肢麻、手顫、舌強(qiáng)等,隨之出現(xiàn)?僻不遂或突然昏仆、不省人事等癥”[9]。
2 李書(shū)義對(duì)“真中”與“類(lèi)中”的辨識(shí)
2.1 古之“類(lèi)中”非今之“類(lèi)中”
在多年中風(fēng)病的診治過(guò)程中,李老發(fā)現(xiàn)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真中”、“類(lèi)中”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尤其是“類(lèi)中風(fēng)”的內(nèi)涵及外延與前賢已大不相同,對(duì)于中風(fēng)病是外因還是內(nèi)因致病的認(rèn)識(shí)亦有所不同,必須加以辨別。李老指出,王履首先提出了“真中風(fēng)”及“類(lèi)中風(fēng)”的概念,對(duì)中風(fēng)病因?qū)W說(shuō)是一大創(chuàng)舉,但隨之也出現(xiàn)了一些概念上的混淆,比如,王履所說(shuō)的“類(lèi)中風(fēng)”是指今之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斜,言語(yǔ)謇澀或不語(yǔ),偏身麻木五大主癥為特征的“中風(fēng)病”,而今之所謂“類(lèi)中風(fēng)”,是指“臨床中將一些不以中風(fēng)病五大主癥為主要臨床表現(xiàn)的腦卒中”,即“椎-基底動(dòng)脈系統(tǒng)及部分頸內(nèi)動(dòng)脈系統(tǒng)的腦血管病”,臨床以“突發(fā)眩暈,或視一為二,或言語(yǔ)不清,或不識(shí)事物或親人,或步履維艱,或偏身疼痛,或肢體抖動(dòng)不止等為主要表現(xiàn),而不伴有半身不遂等五大主癥,稱(chēng)為類(lèi)中風(fēng),仍屬中風(fēng)病范疇”。“雖然中風(fēng)病相當(dāng)于西醫(yī)的急性腦血管疾病,但以五大主癥為主的中風(fēng)病,多數(shù)相當(dāng)于頸內(nèi)動(dòng)脈系統(tǒng)病變的腦卒中,而椎-基底動(dòng)脈系統(tǒng)的腦卒中常表現(xiàn)為五大主癥以外的癥狀體征,不符合經(jīng)典的中風(fēng)病概念,稱(chēng)之為類(lèi)中風(fēng)。”[2]148由此可以看出,王履所說(shuō)的“類(lèi)中風(fēng)”是指今天所說(shuō)的“中風(fēng)病”(急性腦血管病),而今天所說(shuō)的“類(lèi)中風(fēng)”并不是王履所說(shuō)的“類(lèi)中風(fēng)”,而是另有所指,二者名同而實(shí)異,學(xué)者當(dāng)加注意。另外,李老認(rèn)為由于王履所說(shuō)的“真中風(fēng)”是指具有外感六經(jīng)形癥的中風(fēng),即“真正中于風(fēng)邪”,似包括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面神經(jīng)炎”(即中醫(yī)之“口僻”)在內(nèi),此點(diǎn)尚待商榷。
2.2 “真中”極少,“類(lèi)中”居多,應(yīng)辨識(shí)用藥
正是由于王履首先提出了“真中風(fēng)”與“類(lèi)中風(fēng)”的概念并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必須對(duì)此加以甄別,從而更好地指導(dǎo)臨床治療及處方用藥。此為正確立法及處方用藥的前提。誠(chéng)如張錫純所言:“審證不確即兇危立見(jiàn),此不可不慎也。”[11]李老指出,漢唐以前醫(yī)家認(rèn)為中風(fēng)病必有外感六經(jīng)之形癥,故治療皆從外風(fēng)論治,所用藥物均不離發(fā)散外風(fēng)之品,尤其是“小續(xù)命湯”,因方名“續(xù)命”,又經(jīng)孫思邈加減推廣應(yīng)用,故混淆多年,影響頗深,不可不察。李老認(rèn)為只有分清真中與類(lèi)中,才能針對(duì)病因,正確指導(dǎo)臨床治療及處方用藥。否則,若真中、類(lèi)中不分,外風(fēng)、內(nèi)風(fēng)不辨,麻桂姜附,一味升散,本為內(nèi)風(fēng)卻濫用風(fēng)藥,不但于病無(wú)補(bǔ),甚至?xí)?dǎo)致嚴(yán)重后果。如王永炎指出,“中風(fēng)的治療,……驗(yàn)之今日臨床,內(nèi)風(fēng)動(dòng)越之證必不以外風(fēng)治,故續(xù)命諸方已用之極少”。目前認(rèn)為,中風(fēng)病發(fā)病的基礎(chǔ)是“臟腑功能失調(diào),氣血虧虛”,而“勞倦內(nèi)傷、憂思惱怒、飲食不節(jié)、用力過(guò)度、或氣候驟變等為發(fā)病誘因”,“在此基礎(chǔ)上痰濁、瘀血內(nèi)生,或陽(yáng)化風(fēng)動(dòng),血隨氣逆,導(dǎo)致腦脈痹阻或血溢腦脈之外,腦髓神機(jī)受損從而導(dǎo)致中風(fēng)病的發(fā)生”[2]138。因此,李老根據(jù)多年的臨床實(shí)踐認(rèn)為臨床上真中極少,類(lèi)中居多。目前學(xué)術(shù)界亦持此觀點(diǎn),如郭淑云“臨床類(lèi)中較為常見(jiàn),真中則較少見(jiàn)”[9]。“隨著對(duì)中風(fēng)研究的不斷深入,對(duì)內(nèi)風(fēng)是根本原因,外因只是一個(gè)誘因已經(jīng)取得共識(shí)。”[11]
3 案例析評(píng)
患者,男,53歲。因“左側(cè)半身不遂,語(yǔ)言謇澀近40天”于2009年12月22日就診。患者于40天前晨起時(shí)自覺(jué)左側(cè)肢體沉重?zé)o力,不能持物,漸至左側(cè)肢體活動(dòng)不遂,語(yǔ)言謇澀,口角?斜,被家人送至某醫(yī)院,經(jīng)頭顱磁共振成像檢查后診為“腦梗塞”,住院治療,經(jīng)治病情有所好轉(zhuǎn),但遺留有左側(cè)偏癱,語(yǔ)言謇澀,口角?斜,走路跛行等后遺癥,出院后慕名求診于中醫(yī)。診見(jiàn)左側(cè)肢體活動(dòng)不遂,語(yǔ)言謇澀,口角流涎并向右?斜,伴失眠,急躁易怒,腰膝酸軟無(wú)力,小便色黃,大便秘結(jié),舌紅,苔黃膩,脈弦細(xì),尺脈弱。李老診察過(guò)病人后,認(rèn)為患者屬“中風(fēng)病,類(lèi)中風(fēng)”,證屬“肝腎不足,痰瘀阻絡(luò)”,治以“滋補(bǔ)肝腎,活血化瘀,除痰通絡(luò)”為法,處方:桃仁10 g、姜黃6 g、僵蠶10 g、生薏苡仁30 g、橘紅15 g、橘核12 g、杜仲炭15 g、懷牛膝 15 g、白芍 10 g、山茱萸 15 g、首烏藤30 g、枸杞子15 g、覆盆子12 g、雞血藤12 g、炙黃精 15 g。7劑,水煎服,日一劑。李老指出,既是類(lèi)中,故加覆盆子、山茱萸、枸杞子、杜仲補(bǔ)益肝腎,重用牛膝引血下行。不加熟地黃者,乃因舌苔黃膩,恐有滋膩之弊。二診時(shí)(12月31日),癥狀明顯改善,已能自己行走,但仍覺(jué)左側(cè)腰膝酸軟,雙下肢無(wú)力,語(yǔ)言仍顯謇澀,口角稍?斜。舌質(zhì)紅,苔薄黃微膩,脈弦細(xì),辨證為“肝腎不足,瘀血阻絡(luò)”,治以“滋補(bǔ)肝腎,活血祛風(fēng)通絡(luò)”為法。三診(2010年3月11日)時(shí),患者已能獨(dú)立行走,不需攙扶,前方稍作調(diào)整續(xù)服7劑痊愈。
[1] 王永炎,高穎.中風(fēng)病[M]//中華中醫(yī)藥學(xué)會(huì)發(fā)布.中醫(yī)內(nèi)科常見(jiàn)病診療指南·中醫(yī)病證部分.北京:中國(guó)中醫(yī)藥出版社,2008:56.
[2] 王永炎,張伯禮.中醫(yī)腦病學(xué)[M].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7:137,138,148.
[3] 王永炎中醫(yī)心腦病證講稿[M].郭蓉娟,張?jiān)蕩X,整理.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2:74.
[4] 元·王履.醫(yī)經(jīng)溯回集[M].邢玉瑞,閻詠梅,朱岳耕,注釋?zhuān)虾?上海中醫(yī)藥大學(xué)出版社,2011:37.
[5] 清·蔣寶素.醫(yī)略十三篇[M]//裘慶元輯.珍本醫(yī)書(shū)集成(第二冊(cè)).2版.北京:中國(guó)中醫(yī)藥出版社,2012:148.
[6] 劉河間.素問(wèn)玄機(jī)原病式[M]//金元四大家醫(yī)學(xué)全書(shū).太原:山西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2:20.
[7]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shū)·上冊(cè)[M].李繼明,整理.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7:231.
[8] 清·張伯龍.類(lèi)中秘旨[M]//裘慶元輯.國(guó)醫(yī)百家·雪雅堂醫(yī)案.太原:山西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0:407-413.
[9] 郭淑云.中風(fēng)病[M]//周仲瑛,蔡淦.高等中醫(yī)藥院校教學(xué)參考叢書(shū)·中醫(yī)內(nèi)科學(xué).2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8:486.
[10] 張錫純.重訂醫(yī)學(xué)衷中參西錄.上冊(cè)[M].柳西河,重訂.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06:460.
[11] 鄒憶懷,曹克剛.中風(fēng)病[M]//晁恩祥,孫塑倫,魯兆麟.今日中醫(yī)內(nèi)科·上卷.2版.北京:人民衛(wèi)生出版社,20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