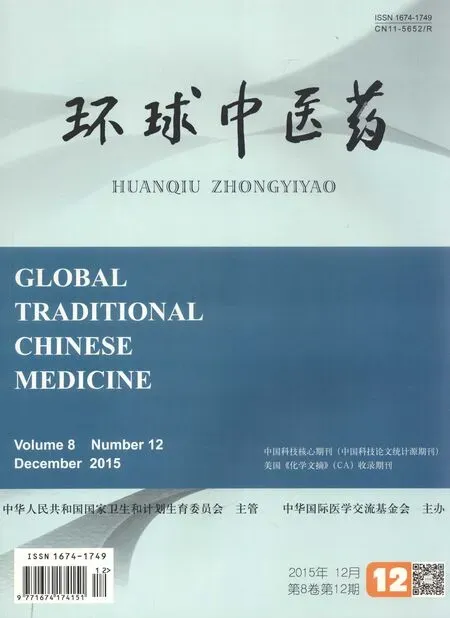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中醫(yī)證型研究進(jìn)展
扶偉 徐立然 馬秀霞 孟鵬飛 宋夕元 李亮平 李正 丁雪 邱荃 楊超華
艾滋病病毒進(jìn)入人體后通過不斷破壞免疫系統(tǒng),造成免疫系統(tǒng)功能相對(duì)低下,繼而并發(fā)各類機(jī)會(huì)性感染。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是機(jī)會(huì)性感染中較為常見的疾患,約占機(jī)會(huì)性感染的50% ~69.6%[1-3],成為艾滋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4],應(yīng)當(dāng)引起足夠的重視。肺部感染的治療過程中因其病因復(fù)雜,臨床癥狀多樣,辨證分型及臨床療效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不統(tǒng)一,有礙于中醫(yī)藥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推廣應(yīng)用。到目前為止,對(duì)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研究甚少,規(guī)范化程度不高,無法滿足臨床的需求。
開展肺部感染領(lǐng)域的證型研究體現(xiàn)了中醫(yī)辨證論治的思想,可以豐富艾滋病中醫(yī)藥防治理論,指導(dǎo)肺部感染的臨床辨證用藥。前期研究結(jié)果表明[5]中醫(yī)藥辨證治療可以較好地控制病情進(jìn)展,提高患者生存質(zhì)量,延長(zhǎng)生命,降低機(jī)會(huì)性感染發(fā)病率和患者死亡率。開展系統(tǒng)規(guī)范研究為進(jìn)一步提升對(duì)艾滋病肺部感染的病因病機(jī)、證型認(rèn)識(shí),提供理論基礎(chǔ),為中醫(yī)藥防治艾滋病提供新的臨床途徑和理論依據(jù),探求病證治療的規(guī)律。
1 證型相關(guān)研究
1.1 辨證分型
近些年所開展的肺部感染證型臨床研究主要根據(jù)《十一省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項(xiàng)目臨床技術(shù)方案(試行)》,該技術(shù)方案按照艾滋病不同分期所出現(xiàn)的癥狀進(jìn)行辨證分型,與肺部感染相關(guān)的證型分為:急性感染期風(fēng)熱型、風(fēng)寒型;發(fā)病期,此期以主癥、次癥所出現(xiàn)的頻次分為熱毒內(nèi)蘊(yùn)、痰熱壅肺證,氣陰兩虛、肺腎不足證。該方案對(duì)于復(fù)雜的肺部感染癥狀及證候表現(xiàn)作了統(tǒng)一的證型概括,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為客觀評(píng)價(jià)中醫(yī)藥臨床療效提供了辨證依據(jù)并指導(dǎo)了臨床和科研用藥,一些研究者圍繞該證型也開展了相關(guān)臨床療效觀察。其局限在于辨證分型較少無法滿足肺部感染臨床多樣化需求。河南省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專家組根據(jù)多年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編寫了《河南省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常見病癥辨證治療要點(diǎn)(2010年版)》[6],把其中關(guān)于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所出現(xiàn)的咳喘病癥分為:風(fēng)邪襲肺證、風(fēng)寒襲肺證、痰熱壅肺證、外寒內(nèi)飲證、衛(wèi)氣虧虛兼風(fēng)寒襲肺證、上實(shí)下虛證、腎氣虧虛證。該辨證認(rèn)為脾肺氣虛為基礎(chǔ),感受外邪而引起虛證、實(shí)證、虛實(shí)相兼證,該要點(diǎn)根據(jù)臨床經(jīng)驗(yàn)而總結(jié),且臨床使用時(shí)簡(jiǎn)明扼要,便于掌握應(yīng)用,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
由于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復(fù)雜病理因素,在臨床辨證過程中需要綜合考慮臟腑、氣血、陰陽等辨證方法,并且需要與中醫(yī)關(guān)于艾滋病的分期辨證相結(jié)合,體現(xiàn)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特殊病因病機(jī)。如趙曉梅[7]提出艾滋病無癥狀期從肺氣陰虛證入手選用四君子湯,艾滋病相關(guān)綜合征期多屬肺脾氣虛證或肺腎氣陰兩虛證,選用補(bǔ)肺湯等補(bǔ)脾益肺,納氣定喘之方進(jìn)行臨床辨證用藥。該辨證突出了艾滋病肺部感染患者以虛為主的病癥特征和肺脾腎三臟在病癥變化中的相兼關(guān)系,在臨床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隨著艾滋病肺部感染的研究不斷深入,王東旭等[8]總結(jié)近年臨床經(jīng)驗(yàn)提出了以“痰”“虛”為主的虛實(shí)夾雜病理因素,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六大基本證型(痰熱壅肺證、痰濕阻肺證、肺腎兩虧證、肺脾氣虛證、肺陰不足證、痰瘀阻肺證)及治療原則和方藥,該證型分類揭示了肺部感染患者基本病理因素,在治療過程中并提出祛邪與扶正兩者不可偏廢,對(duì)于久治不愈患者,根據(jù)母病及子理論,導(dǎo)致腎虛精氣耗損,最終為肺腎兩虧證。該分型體現(xiàn)了病情發(fā)展與辨證相結(jié)合的臨床實(shí)際,為臨床和科研提供了較為客觀的辨證分型。
1.2 證型聚類分析
雖然中醫(yī)藥在治療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的臨床療效明確,但研究模式僅限于臨床療效觀察,其中醫(yī)證候分類及分布規(guī)律與現(xiàn)代化研究方法結(jié)合甚少。王東旭等[9]采用聚類分析的研究方法,結(jié)合癥狀、舌象、脈象的頻數(shù)分布及專家的專業(yè)知識(shí)與臨床實(shí)際,將196例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聚為三類:風(fēng)熱外襲、痰熱壅肺證(31.1%),肺脾兩虛、痰濕阻肺證(32.7%),肺腎兩虧、陰虛內(nèi)熱證(36.2%)。該統(tǒng)計(jì)顯示了相兼證型之間的聯(lián)系,病位涉及肺、脾、腎三臟,病邪涉及風(fēng)、熱、痰、虛。并且通過聚類分析揭示了病情程度、病變性質(zhì)與臨床證型分布之間的相關(guān)性:痰熱壅肺證與肺腎兩虧證所占比率隨病情的加重呈現(xiàn)增加趨勢(shì)。通過聚類分析的方法能夠?yàn)檎J(rèn)識(shí)病情與正邪及病變性質(zhì)提供可能,早期多為正盛邪實(shí),故以痰熱壅肺證多見,隨著疫毒侵犯脾胃,可見痰濕蘊(yùn)肺證;末期多臟器受損,多見肺腎兩虧證。
1.3 臨床辨證療效研究
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臨床治療相關(guān)醫(yī)案較少,并且大部分存在樣本量不多的問題,與臨床發(fā)病率較高的實(shí)際不盡一致,中醫(yī)藥應(yīng)用于免疫低下肺部感染患者具有明確的臨床療效[10],但需要進(jìn)行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觀察和進(jìn)一步的分析總結(jié)確定辨證治療的證型、治則、方藥。岑玉文[11]、周桂琴[12]等,采用隨機(jī)、多中心、平行對(duì)照的試驗(yàn)方法對(duì)164例患者進(jìn)行研究,分別運(yùn)用清金化痰湯治療痰熱壅肺證,補(bǔ)肺湯合七味都?xì)馔柚委煼文I兩虧證,小青龍湯合二陳湯加減治療痰濕阻肺證,研究結(jié)果顯示:中醫(yī)辨證結(jié)合西醫(yī)基礎(chǔ)療法在改善患者臨床癥狀,縮短治療時(shí)間方面優(yōu)于單純西醫(yī)治療,對(duì)于發(fā)熱、頭痛癥狀改善較為明顯。馬秀霞等[13]應(yīng)用清肺培元微丸加西醫(yī)基礎(chǔ)治療方法,觀察痰熱壅肺證141例,表明清肺培元微丸可以改善患者癥狀體征,提高生存質(zhì)量,療效明顯優(yōu)于對(duì)照組,該研究明確了中成藥在臨床治療過程中的療效,為痰熱壅肺證的治療研制中成藥提供了可能,能夠極大方便患者用藥。李發(fā)枝教授認(rèn)為治療艾滋病,辨證為前提,中醫(yī)在古代無艾滋病病名亦無治療經(jīng)驗(yàn),在治療過程中辨證尤為重要,無論西醫(yī)診斷何病,中醫(yī)全憑乎證,對(duì)“證”治療,每收良效。如李發(fā)枝教授在治療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蟲肺炎醫(yī)案中,根據(jù)患者服藥后出現(xiàn)的癥狀變化,打破“效不更方”古訓(xùn),分別從痰濕阻肺證、痰熱壅肺證辨證論治,三易其方,收到良好的臨床療效[14]。
2 證型病因病機(jī)
2.1 證型病因病機(jī)分析
目前,中醫(yī)學(xué)將艾滋病多歸屬于“疫病”“伏氣溫病”等范疇,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則可歸屬于中醫(yī)“咳”“痰”“喘”范疇,因此有醫(yī)家提出在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早期,“疫毒”侵入人體后導(dǎo)致正氣不足,衛(wèi)外功能減退,復(fù)感外邪,則肺失宣肅,肺氣上逆出現(xiàn)發(fā)熱、咳嗽、咯痰等風(fēng)寒束肺證、風(fēng)熱襲肺證,又因艾滋病患者本質(zhì)為虛,故可見乏力、氣短等風(fēng)寒襲肺、肺脾氣虛等虛實(shí)相兼之證。
艾滋病“疫毒”首先損傷脾臟[15],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臟受損運(yùn)化功能失常。一方面水谷精微不能吸收輸布,氣血化生無源,漸而導(dǎo)致心、肝、肺、腎受損,“脾為孤臟,中央土以灌四旁”,終至五臟氣血陰陽俱損,此階段則可出現(xiàn)肺腎虧虛、肺脾氣虛等相兼臟腑疾患。另一方面,脾運(yùn)化水濕功能失常,導(dǎo)致水濕、痰飲內(nèi)生,上行胸中,痹阻于肺,肺失宣肅而出現(xiàn)咳、痰、喘。“痰”“虛”相互影響,導(dǎo)致氣血運(yùn)行不暢,亦可為瘀[16]。復(fù)感外邪,兼痰、濕、瘀、濁于內(nèi),可出現(xiàn)本虛標(biāo)實(shí)之證。因此肺部感染病位在肺,不外乎“痰”“虛”兩大基本病理因素[17]。治療應(yīng)當(dāng)分清本虛標(biāo)實(shí),辨?zhèn)未嬲妫稣c祛邪二者不可偏廢。
2.2 病因病機(jī)與癥狀相關(guān)性研究
綜合近年的肺部感染臨床癥狀相關(guān)研究結(jié)果,為以上病因病機(jī)的分析提供了可供參考的依據(jù)。張鐘等[18]通過分析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所出現(xiàn)頻率較高的癥狀進(jìn)行了病機(jī)探析指出,喘促、自汗為肺虛不主氣,乏力、食后腹脹、納差是“疫毒”侵脾,腰膝酸軟、氣喘則是病久及腎,腎不納氣,腎虛腰府失養(yǎng)。舌體胖大因脾腎陽虛,舌質(zhì)淡多為氣血兩虛、陽虛,咯黃或稀白痰,舌質(zhì)黯、舌苔黃膩或白膩等癥狀則提示痰、濕、熱、瘀蘊(yùn)于體內(nèi)。并且在治療中應(yīng)用健脾益肺,納氣定喘之法,病情得到較快緩解,進(jìn)一步證實(shí)了肺、脾、腎臟腑虧虛的病機(jī)特點(diǎn),而僅用扶正固本之藥或化痰祛瘀藥物用量較少時(shí),則癥狀改善較慢或無變化。劉占國[19]采用活血化瘀方加丹參注射液治療以喘悶、紫紺、舌質(zhì)暗為主要臨床表現(xiàn)的血瘀證收到良好的效果。證明濕、熱、痰、瘀貫穿疾病的重要方面[18]。屈冰等[20]通過分析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中醫(yī)癥狀、證型與非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人群進(jìn)行對(duì)比發(fā)現(xiàn),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痰濕阻肺證、肺腎兩虧證明顯高于非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人群,其出現(xiàn)的氣短、悶、喘、身體困重、食欲不振等癥狀較非艾滋病人群顯著,體現(xiàn)了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肺、脾、腎多臟腑及氣血虧虛的特點(diǎn),痰、虛、濕為其重要的病理因素。
3 證型分布相關(guān)因素探討
對(duì)于常見的證型進(jìn)行規(guī)律性的探討研究有助于豐富艾滋病肺部感染的中醫(yī)機(jī)理,為臨床和科研指明方向。隨著近年對(duì)艾滋病的研究不斷深入,初步證明了中醫(yī)證型與病情程度、年齡等方面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而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證型領(lǐng)域也進(jìn)行了相關(guān)研究,為其提供了更為客觀的理論依據(jù)。
總體來說,在臨床方面以痰熱壅肺證、痰濕阻肺證、肺腎兩虧證為主,肺脾兩虛證、風(fēng)熱襲肺證較少[21]。該特點(diǎn)反映出在肺部感染早期主要為肺脾氣虛的基礎(chǔ)上而感受外邪,表現(xiàn)為以實(shí)為主的癥狀特點(diǎn),此期發(fā)病率較低,故風(fēng)熱襲肺證、肺脾兩虛證在臨床較少見。在肺部感染發(fā)病早期,正盛邪實(shí),多見痰熱壅肺證,隨著臟腑氣血功能的虛弱,而見痰濕阻肺證,后期臟腑受累多見肺腎兩虧證[21];在病情程度方面,痰熱壅肺證多為中度和輕度,其所占比率隨著病情的加重而減少,肺腎兩虧證所占比率隨著病情的加重而增大,痰濕阻肺證隨著病情的加重而減少[9];年齡方面,肺部感染多發(fā)生于40歲以上人群,并且以痰熱壅肺證為主,肺腎兩虧證、痰濕阻肺證隨著年齡增長(zhǎng)而增多[21]。一方面可能由于研究所選艾滋病患者年齡構(gòu)成有關(guān),該年齡段患者多為感染時(shí)間較長(zhǎng)患者,且已經(jīng)進(jìn)入發(fā)病期;另一方面也反應(yīng)了艾滋病患者體虛為主的病機(jī)發(fā)展變化,在老年免疫低下患者中多發(fā)的趨勢(shì);隨著治療效果的出現(xiàn),一些癥狀消失后,證型隨之發(fā)生變化。具體為:痰熱壅肺證、痰濕阻肺證減少,肺腎兩虧證和無證可辨型增加[21]。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以免疫低下患者多見,發(fā)病急,前期診斷較為困難,多發(fā)生于感冒之后,正氣不足,外邪襲肺,而出現(xiàn)痰熱壅肺證,此期患者可因免疫低下,造成病情纏綿,隨疾病進(jìn)展多表現(xiàn)為痰濕蘊(yùn)肺證,一旦發(fā)病病情進(jìn)展較快,后期患者因元?dú)獯髠瑒t多表現(xiàn)為肺腎兩虧證。
郭會(huì)軍等[22]在對(duì)比廣東省與河南省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出現(xiàn)咳嗽癥狀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河南以痰濕或痰熱證常見,廣東多屬燥熱或陰虛而咳嗽,二者證型分布的差異一方面與地域有關(guān),嶺南地區(qū)土薄陽氣易泄,人居其地,腠理汗出長(zhǎng)期則耗氣傷陰[23],與岑玉文等[24]對(duì)廣東地區(qū)艾滋病患者證型研究表述相一致;另一方面或與患者的感染途徑有關(guān),河南以有償獻(xiàn)血為主,患者免疫低下且兼證較多病情反復(fù),多虛多痰。
除此之外,相關(guān)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證型的分布還受到性別、感染途徑等因素的影響,在合并肺部感染后在此方面也應(yīng)當(dāng)開展相關(guān)研究,指導(dǎo)臨床實(shí)踐提高療效。
4 證型與免疫生化的相關(guān)研究
近來研究初步顯示了各證型分布與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的相關(guān)聯(lián)系,痰濕阻肺證、肺腎兩虧證所占比率隨著CD4+的下降而增長(zhǎng),痰熱壅肺證在CD4+為 200~500個(gè)/μL時(shí),所占比率較大,但CD4+<200 個(gè)/μL 時(shí)其所占比率有所下降[10]。痰熱蘊(yùn)肺證、肺腎兩虧證患者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水平較低其中位數(shù)<50個(gè)/μL,明顯低于其他證型;按照虛實(shí)分析發(fā)現(xiàn),熱證患者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水平較高>150個(gè)/μL,虛實(shí)夾雜證的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水平較低,在50個(gè)/μL左右[24]。根據(jù)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與中醫(yī)證型的相關(guān)研究發(fā)現(xiàn),兩者在病情由實(shí)到虛的病情發(fā)展中關(guān)系緊密,王曉忠等[25]認(rèn)為可根據(jù)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間接判斷中醫(yī)證型的虛實(shí),能夠?yàn)榕R床辨證提供參考。根據(jù)中醫(yī)理論分析,身體正氣的強(qiáng)弱能夠較好的揭示疾病的發(fā)展轉(zhuǎn)歸,而近年開展的相關(guān)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研究結(jié)果顯示CD4+T淋巴細(xì)胞能夠較好地反應(yīng)身體免疫的變化,兩者能夠相互印證,并統(tǒng)一于臨床實(shí)際,為客觀的中醫(yī)藥評(píng)價(jià)提供了新思路和研究方向。
查閱近年文獻(xiàn),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所開展的研究多以臨床用藥療效觀察為主,而國內(nèi)關(guān)于艾滋病患者證型與免疫相關(guān)研究已經(jīng)進(jìn)行了深層次的研究和探討,相比于肺部感染僅限于證型分布與CD4+T淋巴細(xì)胞計(jì)數(shù)的研究,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進(jìn)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揭示艾滋病肺部感染與T淋巴細(xì)胞亞群、T細(xì)胞活化指標(biāo)、基因表達(dá)等方面的客觀聯(lián)系。
5 結(jié)語
由于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免疫功能較低,臨床常見于多種病原體的多重感染,由于機(jī)體免疫無力抵抗而出現(xiàn)較為嚴(yán)重的一系列復(fù)雜癥狀,病情反復(fù),不易控制,造成了較高的死亡率。經(jīng)過近些年通過對(duì)證型與病因病機(jī)的臨床研究,逐步確立了“虛”“痰”為主的病理因素,在辨證治療時(shí)提出虛實(shí)夾雜與臟腑辨證相結(jié)合的臨床辨證。在臟腑辨證中提出了與肺、脾、腎三臟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且揭示了證型分布與病情程度和臟腑等方面之間的聯(lián)系。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探討了證型與患者生化免疫指標(biāo)間的關(guān)系,為方便臨床辨證治療提供了客觀的依據(jù),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
西藥治療價(jià)格昂貴并面臨耐藥的風(fēng)險(xiǎn),長(zhǎng)期應(yīng)用不利于業(yè)已受損的免疫系統(tǒng),中藥以其獨(dú)特的辨證理論和療效在臨床得到了應(yīng)用,但仍面臨缺乏機(jī)理及藥物作用機(jī)制的研究和臨床療效評(píng)價(jià),因此有必要加強(qiáng)對(duì)肺部感染相關(guān)課題的更深層次研究,進(jìn)行臨床病例免疫及炎癥相關(guān)指標(biāo)的檢測(cè),明確中藥在患者體內(nèi)抗炎作用和對(duì)免疫功能的影響,探究肺部感染證型機(jī)理,發(fā)揮中醫(yī)辨證論治和治未病理念;進(jìn)行多中心的用藥前后證候、體征、安全性指標(biāo)等分析,以期完成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肺部感染的臨床路徑和療效評(píng)價(jià),對(duì)于降低肺部感染機(jī)率,提高中醫(yī)藥的臨床應(yīng)用途徑有著重要影響。開展中醫(yī)證型與肺部感染免疫、生化指標(biāo)更深層次的研究,探索其相互聯(lián)系,不斷開拓中醫(yī)辨證與現(xiàn)代醫(yī)學(xué)之間較為統(tǒng)一的領(lǐng)域,可以為中醫(yī)藥國際化提供支撐。
[1] 蔡柏薔,李龍蕓.協(xié)和呼吸病學(xué)[M].北京:中國協(xié)和醫(yī)科大學(xué)出版社,2005:703-711.
[2] 汪習(xí)成,黃曉婕,張彤,等.HIV/AIDS患者機(jī)會(huì)性感染特點(diǎn)分析[J].中醫(yī)內(nèi)科雜志,2007,46(5):379-382.
[3] 劉澤明,李芹,鄒永勝.艾滋病46例分析[J].寄生蟲病與感染性疾病,2007,5(2):67-68.
[4] 寶福凱.艾滋病發(fā)病機(jī)理研究中的十大熱點(diǎn)問題[J].生命科學(xué),1994,6(5):20-24.
[5] 徐立然,楊小平,郭會(huì)軍,等.中醫(yī)藥辨證施治對(duì)HIV感染者生存質(zhì)量影響的初步探討[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5):2480-2483.
[6] 李發(fā)枝,徐立然,何英.河南省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常見病癥辨證治療要點(diǎn)(2010 版)[J].中醫(yī)學(xué)報(bào),2010,25(1):1-5.
[7] 趙曉梅.中醫(yī)藥治療艾滋病咳嗽的方法與體會(huì)[J].中國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1998,4(11):40-42.
[8] 徐立然,王東旭,屈冰.艾滋病肺部感染中醫(yī)臨床證治探討[J].遼寧中醫(yī)雜志,2012,39(1):182-184.
[9] 馬秀霞,徐立然,王東旭,等.艾滋病肺部感染聚類分析及證型分布特點(diǎn)初步研究[J].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雜志,2013,33(11):1481-1484.
[10] 馬秀霞,徐立然.中醫(yī)藥治療免疫功能低下致肺部感染的研究進(jìn)展[J].中醫(yī)學(xué)報(bào),2010,25(6):1075-1077.
[11] 岑玉文,譚行華,張堅(jiān)生,等.中西醫(yī)結(jié)合療法改善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醫(yī)證候的隨機(jī)對(duì)照研究[J].中國中藥雜志,2013,38(15):2448-2452.
[12] 周桂琴,屈冰,曾玲玲,等.清金化痰、補(bǔ)肺益腎、溫肺化飲方治療艾滋病肺部感染164例療效研究[J].北京中醫(yī)藥,2011,30(9):646-648.
[13] 馬秀霞,徐立然,鄭志攀,等.清肺培元微丸對(duì)艾滋病肺部感染痰熱壅肺證患者的影響[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4,29(6):2068-2070.
[14] 張明利,韓莉.李發(fā)枝教授治療艾滋病肺系病證驗(yàn)案探析[J].新中醫(yī),2011,43(1):163-164.
[15] 李發(fā)枝,徐立然,李柏齡.中醫(yī)學(xué)對(duì)艾滋病病因病機(jī)的認(rèn)識(shí)[J].中醫(yī)雜志,2006,47(5):395-396.
[16] 徐立然,陳關(guān)征,李歡.艾滋病中醫(yī)“脾為樞機(jī)”探討[J].中醫(yī)研究,2010,23(2):1-3.
[17] 宋夕元,徐立然,鄭志攀,等.從“怪病多痰”論艾滋病肺部感染的病因病機(jī)[J].中醫(yī)學(xué)報(bào),2013,28(10):1435-1437.
[18] 張鐘,徐立然,吳景碩.艾滋病肺部感染癥狀觀察與病機(jī)探討[J].中醫(yī)學(xué)報(bào),2011,26(1):7-9.
[19] 劉占國.丹參注射液在艾滋病肺部感染中的應(yīng)用[J].河南中醫(yī)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23(5):4-5
[20] 屈冰,徐立然,王東旭,等.艾滋病肺部感染中醫(yī)癥狀及證型特征分析[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3,28(10):3128-3130.
[21] 徐立然,王東旭,屈冰,等.艾滋病并肺部感染中醫(yī)證型分布規(guī)律探討[J].環(huán)球中醫(yī)藥,2012,5(2):91-95.
[22] 郭會(huì)軍,李鵬宇.75例艾滋病咳嗽患者中醫(yī)臨床證候特點(diǎn)研究[J].中華中醫(yī)藥雜志,2011,26(1):186-189.
[23] 王偉彪,鄭洪.嶺南人體質(zhì)特點(diǎn)與何夢(mèng)瑤火熱論[J].廣東醫(yī)學(xué),1998,19(1):68-69.
[24] 岑玉文,符林春,譚行華,等.廣東地區(qū)HIV/AIDS患者中醫(yī)證型分布規(guī)律的初步研究[J].中華中醫(yī)藥學(xué)刊,2008,26(5):958-961.
[25] 王曉忠,郭峰,馬建萍,等.56例HIV/AIDS患者中醫(yī)證候與CD4+的研究[J].陜西中醫(yī),2011,32(9):1149-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