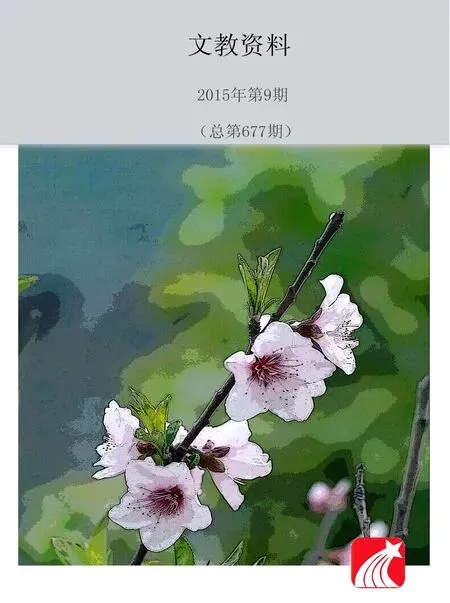《周 易》兩 漢 傳 承 蠡 測
高思莉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450001)
《周 易》兩 漢 傳 承 蠡 測
高思莉
(鄭州大學 文學院,河南 鄭州450001)
兩漢是經學傳承的重要時期,也是《周易》流傳發展承上啟下的階段。從《史記》、《漢書》對兩漢《周易》之發展脈絡進行分析,并結合新的出土文獻,對《周易》在兩漢的發展源流進行梳理,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兩漢時期《周易》的流傳情況。
《周易》 流傳 兩漢
兩漢是我國經學傳承的重要時期。《易》、《書》、《詩》、《禮》、《樂》、《春秋》等一大批儒家典籍從一家之言騰躍成為“天下之經”,從民間私學躋身于廟堂至尊,被奉為經典。它們的流傳具有深刻的學術價值和廣泛的社會意義。
春秋時期,《周易》在社會上層的流傳已經相當廣泛。至秦代“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1]P3592,“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1]P3597。《周易》逃脫了被焚的厄運,并被相對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是它相對于其他被焚典籍在漢代能夠代代相傳而不息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一、從《史記》、《漢書》梳理《周易》在兩漢的傳承情況
《史記》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紀傳體通史。關于《周易》的傳承譜系在《史記》之前的史書中并沒有系統記載,直至《史記·儒林列傳》才對孔子之后的易學傳承情況做了簡單介紹。《漢書》繼而承其緒,對《史記》所載之后至西漢末期的《周易》大致的承傳脈絡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梳理,《儒林傳》和《藝文志》中記載了《周易》流傳主線。
《周易》在兩漢的傳授可以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個體系。
(一)今文經的傳承
關于西漢《周易》最早的傳承,《史記·儒林列傳》記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2]P3127。
《漢書·儒林傳》中有著相似的描述:
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太中大夫[1]P3597。
漢初,最先傳《周易》的關鍵人物是田何。楊何于元光元年被征為太中大夫。武帝建元五年初立《五經》博士時,楊何是第一個《周易》博士。他的弟子有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自此之后,田何傳《易》逐漸開枝散葉,發展為一個龐大的傳承譜系。
《史記·太史公自序》曾云“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2]P3288。也就是說司馬談曾受《易》于楊何。
武帝時期尊崇儒學,立五經為官學,使《周易》的傳授具有更為廣闊的途徑,《易》學得到了較好的發展。通過學習《易》走上仕途、獲得官位的士子們見于記載。
《史記·儒林列傳》載有“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2]P3127。
《漢書·儒林傳》說:“齊即墨城,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1]P3597
這是說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都憑借《易》成為當時的大官。這里“本于楊何”還是“本之田何”?《史記》和《漢書》的記載不同。對此學術界有不同猜測,筆者認為《史記》所記的是楊何這一支的傳承譜系,從田何至楊何都是以每代單傳形式進行記載的;《漢書》所記乃是從田何一支生發出的多支體系,又著重強調楊何這一支的傳承。《史記》之所以如此記載,除了劉大鈞先生所說的“《史記》所云諸資料當為楊何或楊何一派提供”[3]P120和劉彬先生所說司馬遷所記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楊何的傳《易》譜系是他自己承習于的楊何傳《易》流派這些理由外,也有可能是司馬遷寫《史記》時,丁寬這一支的《易》學并未發展壯大起來。同時,丁寬在吳楚七國之亂時曾作為梁孝王的賓客,這或許是丁寬一支易學在武帝一朝彌而不彰的原因之一。《史記》著重強調“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從而未載田何的另外兩個學生周王孫與服生。直到班固寫《漢書》時,整個易學在西漢的發展脈絡才更清晰可觀,而且丁寬一支易學的發展更壯大,所以,班固寫《漢書》時才將《史記》的這句話向前推為“要言《易》者本于田何”。
武帝之后昭帝、宣帝一直到西漢末期,是今文經大力發展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周易》的傳承主要有施、孟、梁丘和京房四大家。傳習情況相對比較復雜,呈現出多支雜糅交叉、學術進一步分化的特點。
根據《漢書·儒林列傳》所說,丁寬最初從梁項生受《易》,后“才過項生,遂事何”[1]P3597。梁人丁寬曾做過梁孝王的賓客,吳楚之亂時“為梁孝王距吳楚,號丁將軍”。武帝立《五經》博士之后,丁寬本人及其門人在武帝一朝并沒有成為《易經》博士或以《易》至大官者,直到昭宣二帝時期,他的弟子才被尊為博士。
丁寬東歸之后,傳《易》給田王孫,田王孫傳給施讎、孟喜、梁丘賀三人。于是《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這三人是田何之后傳承《周易》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他們根據社會發展變化需要,凸顯和引申了先秦《易》學中的象數觀念,開創了漢代新的易學體系,至宣帝末時,《施》、《孟》、《梁丘易》皆已立于學官。
施讎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宣帝時,在梁丘賀的極力推薦下,“詔拜讎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1]P3598。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因詐言從其師處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而失去做博士的機會。梁丘賀字長翁,瑯邪諸人也亦得宣帝親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年老終官”[1]P3600。
三人中,施讎從童子時即從田王孫受《易》,他應該是三人中受《易》最早、學《易》時間最長的人,而且是了解丁寬、田王孫一系易學內容最多者。史書記載,施讎授《易》給張禹、魯伯和梁丘賀的兒子梁丘臨。張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魯伯則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邪邴丹曼容,所以施家有張、彭之學。《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劉昆在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此后傳給他的兒子劉軼。
孟喜是一個“好自稱譽”的人,他曾“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1]P3599。有蜀人趙賓嘗說跟隨孟喜學過 《周易》,大概由于孟喜“好自稱譽”,人們并不相信這一說法。除去趙賓之外,孟喜授《易》給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所以有翟、孟、白之學。《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傳《孟氏易》的有南陽育陽人洼丹、中山觟陽鴻、廣漢綿竹人任安。
梁丘賀曾經跟隨太中大夫京房受《易》,而京房是楊何的弟子。后來京房出為齊郡太守后,改投丁寬的弟子田王孫學習,年老終官后,傳子臨。這里就出現了王同這一易學與丁寬這一支易學相交叉傳承的現象。
《漢書》載“(施讎)與孟喜、梁丘賀并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乃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于是賀薦讎:“結發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1]P3598。盡管梁丘臨曾學習過施家《易》,但是他“專行京房法”,“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瑯邪王吉“聞臨說,善之”[1]P3601,就讓他的兒子王駿從臨受《易》。五鹿充宗君孟曾跟隨梁丘賀學習,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由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梁丘易學產生時期正是西漢經學急劇分化之時,從梁丘臨“專行京房法”來看,這時的京房《易》已經自成一體。與其師楊何所傳的《周易》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體系,并且被同樣自成體系的梁丘氏所承繼。加之梁丘賀父子后來亦師從田王孫、施雌師徒受《易》,所以梁丘之易學可能是雜糅了京房易的易學。
《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鏘鏘楊子行。”教授數百人[4]P2551。
傳又載“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4]P2554,這兩處記載稍微不同,范升所傳到底是孟氏易還是梁丘易,《經典釋文》載“后漢范升,傳《梁丘易》,以授京兆楊政”[5]P32。這一時期,傳授梁丘之學的還有潁川鄢陵人張興,后來他的兒子張魴繼承了他的學業。
此外,進一步發揮“卦氣”說并對今文《易》學產生更大影響的是焦延壽與京房。
梁人焦延壽以好學得幸于梁王,為郡吏。他曾從孟喜問《易》,而傳《易》于京房。京房授《易》于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由是《易》有京氏之學。《漢書·儒林傳》又說京房是楊何的弟子,而焦延壽從孟喜問《易》傳于京房,學界一般將楊何的弟子京房稱為前京房,而焦延壽的弟子則稱為后京房。
京房的易說內容龐雜而自成體系,他大量吸收社會流行的天人之學與陰陽五行觀念,建構了一個包括 “納甲”、“納支”、“八宮”、“卦氣”、“五行”等各種說解的復雜系統,把此前卦氣說、陰陽災變說推向極致,標志著西漢今文象數《易》學體系最終建立與完善。《京氏易》于元帝時立于學官,從西漢后期以至東漢,京房一派在今文諸派系中遂后來居上。
關于焦延壽所授《易》學到底是否屬于孟氏學,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都進行了否認。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相與同”[1]P3601。
之后傳承《京氏易》的有汝南平輿人戴憑字次仲,他習《京氏易》。后征試博士,被拜為郎中。時南陽魏滿牙、濟陰成武人孫期亦習《京氏易》。
(二)古文經的傳承
兩漢古文《易》的流傳相對今文經來說十分簡單。
《漢書·藝文志》稱漢初別有流行于民間“費、高二家之說”,其中費直所治“號古文《易》”。這應該是屬于別行于田何一系之外的古文《易》派。
《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
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瑯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4]P2548。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為郎,至單父令。他長于卦筮,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邪王璜傳習費氏之學。對于費氏易的傳承,《后漢書·儒林列傳》有清晰的表述:“建武中……而陳元、鄭眾皆傳費氏易,其后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4]P2554
費直治《易》大約是在王莽前后,在西漢末期“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1]P1723的學術背景下,隨著今文經學的盛極而衰和古文經學的逐漸興起,費氏易的出現是時勢使然。盡管西漢末期劉歆等極力推崇古文經,而《費氏易》的真正興起則在東漢中期之后。
與他同時治《易》的是沛人高相,他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也就是丁寬。高相授子高康及蘭陵毋將永。
關于丁寬授古文《易》的情況,《漢書·儒林傳》記載:
(丁寬)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1]P3597。
丁寬本是梁孝王的賓客梁人,在梁孝王死后,他招延的四方豪杰各自歸去,如枚乘就在梁孝王薨后返回老家淮陰,那么可以猜測大學者丁寬很有可能歸教于家。他的學生不可能只有田王孫一人,田王孫只是因為成為博士而揚名的弟子之一。“《易》以東矣”正說明,高相可能是東歸后的弟子。丁寬從田何處學成后又至洛陽,跟從他的同門師兄周王孫受古義,所以丁寬授徒時傳授一些古義內容就能說通了。
這里的“古義”是否指古文《易》呢?《漢書》和《后漢書》中都明確指出費直所傳乃古文易,而對高氏易是否屬于古文并沒有給予過多解釋。學者劉大鈞在《〈周易〉古義考》中認為:
漢初,易學的傳承已有了“今義”與“古義”之分。此所言“今”、“古”,不同于今、古文經學中的“今”與“古”,非謂田何所傳的今文易學與費直所傳的古文易學。《易》之“今義”凸顯的是一種德性優先的濃郁人文關懷,而《易》之“古義”,則更多地關涉明陰陽、和四時、順五行、辨災祥等卜筮之旨。田何的今文《易》中,既有傳世的“今義”,又有我們要考索的“古義”。費直的古文《易》中,既有“長于卦筮”的“古義”,又有“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故古文《易》其文字雖古,但用這些古文字作解的卻是《彖》、《象》、《系辭》等孔子及孔門弟子撰述闡發的《易》之“今義”。“古義”與西漢孟、京《易》中用以占筮的象數內容雖密不可分,但與興盛于東漢的象數之學并不相同[6]P142。
因此,不能因為與費氏古文易并行于民間,也不能因為二者在今文經鼎盛之時都沒有被立于學官,而斷言高氏易也是古文經。
二、出土《周易》的發現
王國維提出:“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7]P2
學術史上,將出土文獻的定點與傳世文獻的輪廓結合起來,對于文獻新證的意義深遠。《易》經亦然。
關于《周易》的出土文獻主要有:上博簡所藏戰國楚竹書《周易》文本、馬王堆帛書《周易》文本和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文本。
上博簡戰國楚竹書《周易》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周易》文本,時間屬于戰國晚期,不在本文的討論兩漢范圍之內。
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文本是《周易》的實用化和民俗化產物,只有《周易》經文,在每卦的卦爻辭之后都有俗化的、可套用的卜筮之辭,學者認為它屬于實用性筮書。《漢書·藝文志》在《六藝略》和《數術略》兩處分別記載了《周易》。這兩處載入大概和先秦易書的傳承相對應。一方面,《周易》作為卜筮之書,被賦予史官和儒家的哲學化內涵,成為義理易學,并被奉為儒家經典載入《六藝略》。另一方面,經由先秦陰陽家、方術家演化的《周易》反映了《周易》在民間流傳期間的發展情況,成為強調數術的卜筮書,被著錄進《數術略》。阜陽簡《周易》大概就是這一文本。
1973年出土于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馬王堆帛書《周易》是漢文帝前期的抄本。它的出土發現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為易學研究的熱點話題。
帛書《周易》經傳與今本《周易》經傳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帛書《易》經不分上下。六十四卦次序與今本《周易》的卦序完全不同,以八卦相重方式成卦,共分八組,每組八卦。屬另一系統的卦序”[8]P4。
邢文先生認為:“帛書《周易》經傳主要的文獻來源,應該是與今本《周易》經傳內容非常接近的一個《周易》傳本,這個本子可能與今本《周易》并傳,也可能就是今本《周易》的祖本,但一定不是今本《周易》經傳。帛書《周易》的另一來源,是作為地域學術的帛書易學的學術思想甚或某些已佚的文獻。”[9]P225劉大鈞先生經過考證認為帛書《周易》極有可能是當時流傳于楚地的一個《周易》經傳版本,不可能是直接來自田何《易》之傳本。
李學勤先生認為,上述三種文本“都是《周易》一書傳流過程中的鏈環,但它們并沒有直接承襲的關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簡本、帛書本和今傳本沒有根本上的差異”[10]P8。
但是這幾種出土文本尤其是馬王堆帛書 《周易》的發現,明確了兩漢時期除了田何系統之外另一不同傳承體系的可能存在,掀起了易學研究的高潮。
三、運用二重證據法對《周易》源流的蠡測
《漢書·藝文志》曾記載孔子沒后,《春秋》、《詩》、《易》等的傳承情況: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1]P1701。
這說明在七十子那里,《易》學的傳承已分為數家,不應該只有商瞿——田何這一系統,可能還存在別的系統。從文獻記載來看,七十子中有傳易事跡者有子夏、子貢、商瞿等人。《孔子家語·六本》、《說苑·敬慎》載有子夏向孔子請教《損》、《益》之道的事跡。
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這一猜想,馬帛書《要》篇記載子贛(即子貢)在孔子晚年,與孔子討論《易》之卜筮的問題。此外,學者發現馬王堆帛書《周易》雖與今本《周易》十分接近,但帛書《周易》體現的傳承系統是一個不同于《史記》記載的田何傳承的易學一系,而是一個在楚地傳承的文本系統。這進一步證明了人們的猜想:在兩漢時期除商瞿——田何《周易》體系之外,還有別的流傳體系存在。
進一步看《漢書·儒林傳》的記載: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于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1]P3613。
《詩》有齊、魯、韓三家,韓嬰傳《詩》眾所周知,但是他所傳《易》卻鮮為人知。原因在于“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宣帝時他的后人韓生接受了他的傳習,并有蓋寬饒跟隨他學習。《儒林傳》沒有把他這一支易學歸屬于田何一支,說明韓嬰這一支易學非田何易學之系統。這里所說的韓嬰所傳易具體屬于哪一家,原文中沒有詳說。
學者劉彬認為韓嬰所傳的《周易》當屬子夏易學這一支。他多方考證尤其通過劉向、劉歆“《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漢興,韓嬰傳”的記載猜測韓嬰易學很可能屬于子夏這一系。
子夏(公元前507—前420年),是孔子的學生之一,在四科十哲中以精于文學即文獻著稱。孔子死后,子夏傳經,功勞很大。子夏傳《易》,在《史記》、《漢書》、《后漢書》中記載的先秦到兩漢的傳承體系中均未提及,但在隋唐以后的典籍中有所記載。
《隋書·經籍志》云: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系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11]P912。
同時《隋書·經籍志》還著錄了子夏所作的《易傳》“《周易》二卷”并注:“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11]P909。唐人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子夏易傳》三卷”,陸注:“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5]P37
但是為什么在《史記》、《漢書》中只有商瞿——田何這一支而沒有別的支系的相關記錄呢?
劉彬認為司馬遷的易學是承其家學,即太史公司馬談的易學,而司馬談承于楊何,楊何承于王同,王同承于田何,因此司馬遷所記的自商瞿至田何至楊何的傳《易》譜系,正是他承習的始于商瞿的一個傳《易》流派。這同時是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既述當時數家《易》皆自田何的現狀:“乃今上即位,言《易》自菑川田生。”又推崇楊何易學,強調“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的重要原因。商瞿《易》一系被載于《史記》、《漢書》,而其他人所傳《易》不見載,正是推重家學的時代產物。因此,《史記》、《漢書》沒有記載子夏傳《易》,并不能證明子夏沒有傳《易》。
除了劉彬先生的上述觀點和劉大鈞先生所說“《史記》所云諸資料當為楊何或楊何一派提供”的原因以外,筆者認為《史記》、《漢書》之所以只記載了田何這一支,是因為本于田何的易學十分興旺發達,而其他支易學之傳承或者斷流,或者至后來彌而不彰。并且其他易學傳人沒有以《周易》揚名或成為大官,其傳人隨時間銷聲匿跡,更不見于史書記載,所以《史記》、《漢書》都只記載了這一主線的傳承情況。
[1]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
[5]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8.
[6]劉大鈞.《周易》古義考[J].中國社會科學,2002(5).
[7]王國維.古史新證[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8]陳仁仁.從楚地出長文獻看《周易》文本早期形態[J].周易研究,2007(3).
[9]邢文.帛書周易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李學勤.出土文物與周易研究[J].齊魯學刊,2005(2).
[11]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