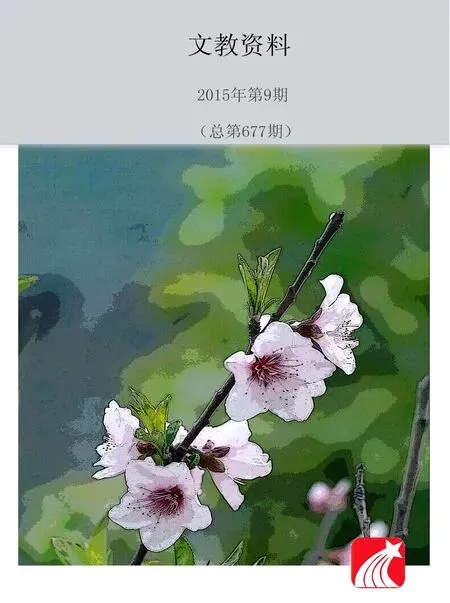李清照、張玉娘作品中的愁情比較研究
陸立玉
(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初等教育學院,江蘇 連云港222000)
李清照、張玉娘作品中的愁情比較研究
陸立玉
(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初等教育學院,江蘇 連云港222000)
李清照和張玉娘是宋代杰出的女詞人。相同的時代背景使她們的大部分作品呈現出共同的特點:作品中都包含帶有悲傷色彩的情感意蘊,尤其專注于一個“愁”字。但是由于家庭出身、婚姻狀況、個人經歷等不同,二人作品中的愁情在情感內涵、表達方式等方面存在明顯異同。
愁情 情感內涵 情感呈現
在中國古代文化最繁榮、最發達的宋代,涌現出了一大批女作家,李清照、張玉娘就是其中兩顆璀璨的明珠。譚正璧先生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一文中稱她們與朱淑真、吳淑姬為宋代“四大女詞家”。李清照和張玉娘生活的趙宋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朝代,國難深重,封建禮教盛行,婚姻和家庭不能給她們庇護,加之理學思想的束縛及宋詞以悲傷為美的審美風尚的影響,使得她們的大部分作品呈現出共同的特點:作品中都包含帶有悲傷色彩的情感意蘊,尤其專注于一個“愁”字。她們通過這些愁情描寫,反映出那個時代女性的生活狀況、社會地位和思想情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婚姻狀況、個人經歷等不同,二人作品中的愁情在情感內涵、表達方式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異同。
一、同樣的仕宦家庭出生,不同的情感經歷
李清照生于名門嫁與相府,父親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母親王氏為狀元王拱辰之孫女,丈夫趙明誠乃金石考據家,公公趙挺之曾官至宰相。早年李清照生活優裕,但由于對生活的特有敏感,造成了李清照多愁善感的性格;婚后,清照與丈夫情投意合、如膠似漆,“夫如擅朋友之勝”,然而好景不長,朝中新舊黨爭愈演愈烈,一對鴛鴦被活活拆散,趙李隔河相望,飽嘗相思之苦;靖康之變后,她與趙明誠避亂江南,喪失了珍藏的大部分文物、藏書,后來趙明誠病死他鄉,她獨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華一帶,在凄苦孤寂中度過了晚年。
張玉娘也出生于宦官之家,天生麗質、聰慧絕倫,“是一位優秀的文壇閨秀”,“時以班大家比之”。張玉娘與表兄沈佺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自幼即有婚約。但因沈家家道中落,張玉娘的父母又有悔婚之意,沈佺被迫隨父赴京趕考,高中榜眼卻感染傷寒,客死他鄉。玉娘矢志不嫁,終因積郁成疾,守情五年后隨佺而去。
二、同樣的愁情似海,不一樣的情感內涵
不同的婚姻狀況、不同的人生經歷,使得同樣的愁情在她們的作品中呈現出不一樣的情感內涵。優越的家庭出身,使李清照早期作品中充滿優裕生活中的富貴閑愁:“綠肥紅瘦”的嘆惋、“紅稀香少”的憂慮、“梨花欲謝”的無奈、“海燕未來人斗草,江梅已過柳生綿”的惺惺相惜……正是“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屢”。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感傷情緒,都源于女詞人對生活的敏感、對內心美的珍惜。除了展示優裕生活中的富貴閑愁外,李清照還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反映婚后夫妻兩地分居的別情離愁:《鳳凰臺上憶吹簫》的種種別苦離懷、《一剪梅》里的望眼欲穿、《醉花陰》中的孤獨寂寞……靖康之難,使她從家庭走向社會,作品從情愁轉向抒寫家破人亡、江山淪陷的家仇國恨:這里有訴說夫妻死別的悲愴之歌 (《南歌子》),有物是人非的孀居之苦、亡國之痛(《聲聲慢》、《武陵春》)……正如梁啟超所言:“那種煢獨凄愴的景況,非本人不能領略。”縱觀其一生,可以說李清照的作品和愁字分不開,從情愁到家愁再到國愁,這紛繁愁緒使她一步步邁進文學圣殿。誠如高宅旸《味蓼軒詩鈔》所言:“狂名近代無人識,愁絕千秋李易安。”本是有情人,卻終難成眷屬。于是,與沈佺之間不幸的愛情,構成了張玉娘作品悲傷意蘊的主要內容。這里有對情郎難消難解的思念之愁:“薊燕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到黃昏,敗荷疏雨,幾度銷魂”(《玉蝴蝶·離情》)的望穿秋水、“關山一夜愁多少,照影令人添慘凄”(《明月引》)的滿腹愁思、“深院深深人不到,憑闌。盡日花枝獨自看……愁繞春叢淚未干”(《南鄉子·清晝》)的柔腸千結……相思之苦困擾著她、折磨著她,但無限愁思并未迎來與沈生的相聚。于是,思君不見的寂寞之愁就構成了其作品中的又一個主要內容:“獨坐看花枝,無言雙淚垂”(《閑坐口謠》)、“獨坐憐團扇,羅衣吹暗風”(《秋思》)、“玉膚冰骨獨英英,繡向珊瑚照睡屏”(《梅花枕》)……一系列“獨”字展現出了一個孤獨、寂寞、無助、傷感的女子形象,她愁云密布,又無處排遣、無人可訴,只有獨自承擔如此孤獨與寂寞,以至于“瘦癯羞對鏡,怨容光”(《小重山秋思》)。沒想到與沈生的一別竟成永訣,生死兩隔的刻骨離愁成了她后期作品的主要內容:“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水調歌頭·次韻東坡》)、“中途成永別,翠袖染涕紅。悵恨生死別,夢魂再相逢”(《哭沈生》)、“行天雁向寒煙沒,倚檻人將清淚流”(《晚樓凝思》)、“細數目前花落盡,傷心都付不言時”(《秋千》)、“燕子樓空,鳳簫人遠,憂恨悲黃鸝”(《念奴嬌·中秋月次姚孝寧韻》)……生死相隔的相思之苦、痛失愛侶的刻骨之痛、渺茫不見的深沉悲哀溢于言表。終于在繁花落盡之時,她也走完了27年的生命旅程。正如孟稱舜所言:“蘭雪有辭君莫唱,夕陽煙樹不勝愁。”她的作品盡管題材狹窄,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格調過于悲傷纖弱,但它寫出了張玉娘及那個時代女性固有的悲劇命運。
總的來說,李清照親見了北宋的滅亡,并因之被迫走出閨閣,加入了自北而南的流亡隊伍,國家的變亂、政治的黑暗,使其作品中的愁性大增,尤其充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精神,正如劉大杰先生說的:“她抒的情、寫的恨,表面看是個人的,實際上具有一定的時代色彩和社會基礎。”即“國難民愁”。張玉娘從未走出深閨半步,因此,她的作品不可能像李清照一樣有著更深刻的人生感悟,從她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她對愛情的至情至真。相比之下,與沈生的愛情遭遇,使她的作品更多了一份對拆散他們的禮教的不滿,充滿了對封建禮教的叛逆:在封建專制社會中,一位大家閨秀敢于直抒胸臆,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對愛情生活的向往、哀怨和獨處深閨的煩悶寫成詩句,將自己的感情生活毫無遮掩地暴露給公眾,這是對當時日益森嚴的禮教制度的挑戰。
三、同樣的柔腸千結,不一樣的情感呈現
多舛的命運、坎坷的人生使李清照、張玉娘作品中充滿了綿綿的愁思,但她們在對這種情感的表達上卻呈現出明顯不同。
首先,在意象選取上,張玉娘更喜借月抒懷。一部《蘭雪集》中,各種月意象使用頻率高達近50次:朗照的明月,殘缺的新月、眉月,寂寞的山月、流月,清冷的霜月、涼月、蒼月、秋月,還有玉蟾、涼蟾、寒蟾、玉兔、霜兔、冰輪、團扇、銀鉤等,在她的筆下比比皆是。作為一種文化意象,自古以來,月亮就是孤獨與失意的象征,反映女性的悲傷憂郁之情。同樣,這些月意象中也滲透了詩人濃重的悲愁:明月朗照中對團聚的期待,冷月清輝中的凄婉惆悵,殘月映照下的孤獨與哀愁……而李清照更戀花與酒。李清照性情純凈,熱愛大自然,尤其愛好花類,所以,花就成了她筆下一個非常重要的抒情憑借。她的詞作中提及的近三十種物象中,其中關涉花的詞就有四十余首。梅花、梨花、海棠、荷花、牡丹、桂花、菊花、杏花、丁香都成了其信手拈來卻寓深情于其中的物象[1]。在《漱玉詞》中寫到“酒”的作品更是不少于其詞總數的一半[2]。曾有人做過統計,李清照詞中直接或間接涉及酒的有24首之多,約占其全部存世作品的五分之三,其中直接出現“酒”字15次,出現“醉”字9次,另外像“琥珀”、“綠蟻”、“玉酎”等酒的代稱或別名,“尊”、“玉尊”、“金尊”、“杯”、“盞”等酒器的名稱也在其作品中頻頻出現[3]。或對花落淚,或借酒澆愁,花和酒就成了作者抒寫愁腸的重要工具。
其次,在語言運用上,張玉娘的作品更多的是“以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明白如話、詞淺意深,完全不受“溫柔敦厚”詩教規范的束縛。當然,這也與作者充滿不幸的愛情有關:一生癡愛沈生,又不能如愿,于是愁怨橫生,不在乎斟酌詞句,肺腑之言一呼而就。相比較而言,李清照至少曾經擁有過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因此個性中柔婉的一面更突出,語言含蓄蘊藉,充滿了典雅、凝重的閨秀風度。
當然,作為宋代文壇上歷盡感情磨難的兩位女作家,她們在愁情表達上有不少相同的地方,如都善于借助客觀景物抒寫自己的一腔愁情;均喜用疊聲字深化意境、渲染氛圍、突出主題等,不僅增強詩歌的音樂感、節奏感,還在回環往復中帶給人悠揚婉約的韻味。
[1]李清照.李清照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
[2]張玉娘.蘭雪集.http://blog.sina.com.cn/s/blog_86f7241 30100zp2t.html.
[3]汪涵.李清照詞與酒淺析[J].社會縱橫,2002,04:62-63.
[4]唐圭章,編.詞話叢編·金粟詞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6.
[5]朱德華.寒煙疏雨愁多少[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