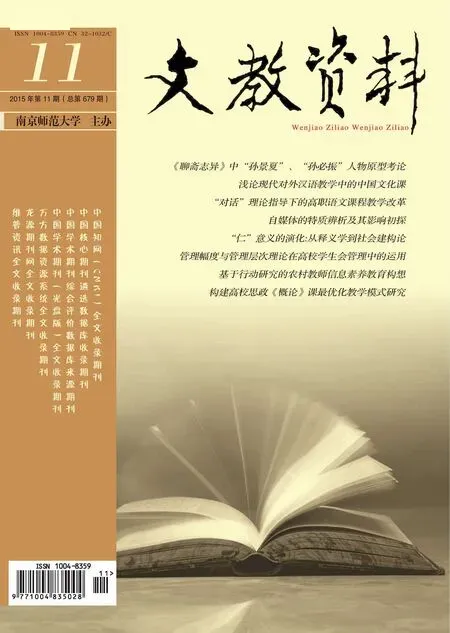翻譯與跨文化闡釋視角下的《論語》英譯
——以辜鴻銘和理雅各為例
郭麗斌 徐 曼
(湖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0)
翻譯與跨文化闡釋視角下的《論語》英譯
——以辜鴻銘和理雅各為例
郭麗斌 徐 曼
(湖北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0)
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翻譯以傳播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經典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翻譯與跨文化闡釋視角,以辜鴻銘和理雅各的《論語》英譯為例,探討翻譯儒家經典和文學著作策略。翻譯工作者應認真嚴謹,胸懷博大,思維開闊,熱愛原著;采用跨文化闡釋式翻譯,合理把握直譯與意譯、歸化與異化、翻譯與闡釋的度,再現源語作品精神內涵和文化風格,體現其文學藝術美、思想哲理美,傳播人類優秀文明成果。
《論語》 辜鴻銘 理雅各 翻譯與跨文化闡釋 哲學思想
一、引言
隨著國際交流日益增多,中華文化應時代需要走向世界。在此進程中,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翻譯是重中之重。本文從跨文化闡釋與翻譯視角,以兩位杰出翻譯家辜鴻銘和理雅各的《論語》英譯為例,探討翻譯儒家經典策略,促進中國文學和哲學經典翻譯傳播。
二、翻譯背景和動機
辜鴻銘(1857-1928)是首位英譯《論語》的中國人,其學貫中西,精通歐洲哲學、宗教文史,繼承歐洲學術敢于質疑傳統的觀念,鉆研中國儒家經典,中文功底深厚。鴉片戰爭后,西方蔑視中華文化,辜因熱愛國學而譯《論語》,傳播中華文化。此外,辜不滿西方儒經譯本是其英譯的直接原因,他寫道:“理氏的儒經翻譯向普通英文讀者所呈現的中國人的思想和道德觀,就如同普通英國人眼里的中國人的穿著一樣,必定有一種離奇怪誕的感覺。”[1]翻譯目的和文化背景直接影響翻譯策略。
理雅各(1815-1897)是傳教士,近代英國第一位著名漢學家。其從小學習《圣經》,宗教使命感濃厚,深信基督教義;英文文法水平較高。其首要目的是異邦傳教:學習漢語,了解中華文化,采用融入本土文化策略;翻譯儒家經典。這直接影響其領悟程度和翻譯策略。
三、分析策略和理論基礎
(一)分析策略
兩譯本應結合時代文化背景和翻譯目的分析,才能理解譯者翻譯策略和其局限的原因。翻譯方法本身沒有優劣,對于不同文章,多個翻譯方法度的把握,由譯文體現優劣。從兩譯本當時廣泛影響和較其他譯本來看,兩譯者的翻譯方法是自身時代局限中采用的最好策略。因此,應肯定其英譯《論語》的杰出貢獻,同時辯證分析譯本,總結翻譯民族經典策略。
(二)理論基礎
就翻譯本身而言,其有語言轉化功能,也有跨文化意義的闡釋功能。跨文化闡釋與翻譯相輔相成,適度辯證使用。
從跨文化闡釋視角,《論語》英譯不應僅重文化闡釋而脫離原文語言本身涵義,語言層面的翻譯不能離開跨文化闡釋單方面分析。“跨文化闡釋式的翻譯,受制于語言的限制,即有限的跨文化闡釋”[2](王寧,2014:5)。“在這種跨文化闡釋(翻譯)的過程中,要適當把握闡釋的度:過度地闡釋就會遠離原作;而拘泥于語言層面的忠實又很難發掘出翻譯文本的豐富文化內涵,最后以過于追求形式上的忠誠而喪失譯者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為代價”[2](王寧2014:5),甚而不能把握經典作品本質價值觀和精神內涵,落入“形似”非“神似”的局限中。辜譯本部分文化術語過度闡釋和誤譯;理譯本部分缺乏闡釋和誤讀原文精神內涵。從翻譯視角,應忠實原文內容和形式,保持其文化和風格。同時《論語》是中華文化核心經典,因此重哲學思想、精神內核本質把握和整體意識構建。
奈達“功能對等”理論有深入具體指導作用。理論以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對接受信息能否有基本一致反映為依據,不論哪些翻譯方法,均為達到功能對等。直譯和意譯即對內容和形式的把握,當兩者可兼顧時采用直譯,當兩者不能兼顧時采用意譯,優先傳達譯文效果和實質,體現譯文功能對等或忠實規范。同一內容有不同表達方式,即藝術的一面,譯者選其一,需有藝術鑒賞和文學素養,需與原作心靈契合以敏銳判斷。如用歸化還是異化,歸化益于譯語讀者理解,異化益于了解異邦文化,注重描述事實文化習俗時可用異化,注重傳達本質思想時可用歸化,單句或語篇需把握兩者間的度,減少誤解以功能對等。“接受者從中所獲得的一切理解和感受,包括主要精神,具體事實,意境氣氛三大要素”[3](金隱1998:18)、原文和譯文三要素對等則完成翻譯任務。理譯本部分過于直譯,機械對應句式和文化詞語,未把握好句子異化的度,讀者了解文化但不理解精神本質,因而有文化困惑感。辜部分譯文未把握好歸化的度,采用過于歸化方法,部分譯文翻譯有失偏頗,但其直譯意譯結合,對兩者度把握較好,透徹理解儒家精神,達到功能對等。
四、譯本翻譯特色分析
(一)理氏譯本特點
1.注釋式譯本
理譯本注釋內容翔實,注釋具學術性:引用《論語》注疏觀點注釋文化術語;具有系統連貫性:每章概括提示,邏輯嚴密,自成一體,符合西方思維習慣,為學習原文提供教材式注疏式文本,具有學術型特點。
2.直譯翻譯方法
(1)理用直譯順譯方法,盡可能傳達原文,形式上嚴格復制原文句式,即詞法句法層面嚴格忠實。此原則有一定積極作用。
例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
理譯:“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4]
辜譯:“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5]
理用直譯方法忠實再現源語文化風貌,易于西方讀者理解。辜把反問句譯為陳述句,準確表達原文涵義,但譯文較長,不夠簡潔直接。
(2)對于文化內涵易于理解的部分,直譯語義句式可行,但文化內涵略深,相對難于解讀的部分,過于直譯語義句式有消極作用。
例2: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
理譯:“Let there be a careful attention to perform the funeral rites to parents,and let them be followed when long gone with the ceremonies of sacrifice...”[4]
辜譯:“By cultivating respect for the dead,and carrying the memory back to the distant past...”[5]
此例中,理機械復制詞字面意思,過于拘泥句子形式,部分用詞別扭,結構冗長生硬。再者,中西方祭祀文化不同,直譯字面意思沒有深層解讀,給西方讀者帶來理解障礙和怪異之感,部分譯文僅語言文化表層異化,文化內涵已偏離。而辜用意譯方法,準確傳達原文深層文化內涵。
(3)對于上述文化內涵深厚的部分,部分譯文冗長難懂,仿佛隔層看文,敏銳者深入思考有理解可能性,但儒家文化核心精神和哲學思想解讀有誤,對西方理解中國文化阻礙最大。
例3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
理譯:“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4]
辜譯:“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5]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較大,此例中理機械復制,極易使西方讀者誤解。從翻譯視角,這反映其過于直譯忽視意譯,未把握好歸化異化的合理分布。句子表層意思過度對應式異化,即機械復制漢語語序和文化符號,傳達原文精神本質有誤。從闡釋學角度,語言層面過度對應難于把握譯本深層思想,過于拘泥形式對應喪失譯者闡釋和創造作用;同時機械譯字面意思和復制句式,沒有適當能動的填補和闡釋文本,增加西方了解中國文化難度。綜上反映其未深刻理解《論語》本質文化價值觀,不得精髓。
(4)理譯本改變《論語》高度精練,含蓄雋永,詼諧靈動文學作品的風格形象,降低可讀性,刻板行文失去文學價值中美的追求和欣賞。
例4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論語》)
理譯:“They will do;but they are not equal to him,who,though poor,is yet cheerful,and to him,who,though rich,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4]
辜譯:“It’s good.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to be courteous.”[5]
此例體現譯文僵化,文風呆板,部分譯文離開注釋晦澀難懂;對修辭手法和文化詞語解讀有誤,甚至偏見,缺乏文學品位。
3.文化詞匯翻譯的學術型特點
理書面用語正式嚴謹,《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中“仁”譯成“benevolent actions”[4],“孝弟”譯為“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4];辜譯為 “a moral life”[5],“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5],體現用詞書面化,但部分譯句用詞過于正式,不符合原文對話體風格特征,而辜用詞地道易懂,明白曉暢。整體看,理直譯策略體現翻譯內容和形式準確性,但有過度直譯傾向,注釋系統一定程度上彌補譯文的不足。其注釋式連貫的直譯譯本,給人博學嚴謹學術之感。
(二)辜氏譯文特點
1.闡釋式譯文
辜譯本注釋篇幅相對較少,注釋方式和內容高度歸化,以西喻中: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名家類比《論語》內容,多闡釋評論;貼近譯語讀者思維方式,克服一定的文化障礙,給讀者親切感。類比分析使讀者對儒家精神內核和哲學思想了然于心,感受中華文明博大精深。但是部分譯本過度用西方文化闡釋原文,有失《論語》文化特性;過于添加自身理解和闡釋,對《論語》原文翻譯略失偏頗。
2.意譯和歸化翻譯方法
譯本在思想及內容和形式上直譯意譯結合,以意譯為主,重傳達《論語》精神本質。如例2,辜沒有直譯字面意思而以意譯傳達本質思想。辜省去原文地名和大部分人名,使讀者關注原文思想。風格上辜重前后銜接和整體把握,體現原文靈動的行文氣勢風格,文采飛揚,親切自然。通過高度歸化方法,《論語》核心思想以較少文化障礙得到較大傳達。辜氏將堯舜時代類比亞伯拉罕和以撒時代,闡釋為“A man rises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work persistently all day long,for what?For righteousness;that he is a son of Abraham(Shun)”[5],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西方讀者的理解障礙。
從闡釋學視角,“原作不可能窮盡原文意義,常常留下大量的空白給讀者,而譯語讀者在理解上的空白更大”[2](王寧,2014:6)。辜憑語言知識儲備和對《論語》精神本質的理解,適當能動地闡釋填補原著與譯語讀者理解間空白,為讀者、譯者和孔子對話提供載體。如辜適當闡釋填補體現對話體語氣特征,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但闡釋過程中,其部分過度文化闡釋,略偏原義。“以空虛,意義更廣的名詞來解釋儒家基本概念;以西洋哲學解釋此書”[6](王國維,1925),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儒家文化特性。
3.文化詞匯翻譯的文學型特點
辜用地道普通英文詞匯和句法結構,語言簡練,富于文采傳達《論語》思想,如例3、例4,其用普通英文詞匯自然傳達文意,給人舒適感。辜盡可能不著翻譯痕跡,使譯文流暢易讀,娓娓道來,具有文學作品特點,給讀者文學美感。總體上,辜闡釋式的歸化意譯譯本,給人活潑生動,富于美感的文學型翻譯之印象。
五、兩譯本的局限性
(一)理氏譯本
理譯本局限:譯本過于機械復制原文,形式異化未達到精神實質異化或忠實傳達;部分譯文誤譯,缺乏闡釋,沒有透徹理解儒家思想精髓。誤譯原因:從譯者角度,其翻譯目的是傳教,非真正意義站在人類文明角度,其翻譯前提是:基督教文明高于儒家文明,因此未能真正領會儒家思想內核。從時代角度,維多利亞時期帝國意識膨脹,其認為東方文化是弱勢文化,對儒經有根本偏見。從譯本難度角度,《論語》高度凝練,代表中華民族核心文化價值觀和精神根基,不同于一般文化讀本,其哲學思想高深,精神本質獨特,國外較國內譯者更難透徹理解《論語》精髓。
“價值觀是文化中最深層的部分,它支配著人們的信念,態度和行為”[7](胡文仲,1999:175)。習俗文化方面適應不是最難,難在價值觀念適應。對于一般文化作品英譯,適當采用直譯具可行性,益于真實表現源語文化;但高度濃縮代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儒家經典,不僅文化知識豐富,還要從整體意識出發,理解儒家經典精髓,把握其哲學思想和精神本質。理作為傳教士受時代和自身文化背景局限,對儒經有內在偏見,文學品位不足,不能把握《論語》的精髓。
(二)辜氏譯本
辜譯本局限:采用過于歸化翻譯方法。從西方文化角度,其以西方哲學和宗教文化過度闡釋,夸大文化詞匯概念,忽視《論語》文化特性;部分譯文忠實程度不足。局限原因:當時西方對中華文明偏見頗深,為挽回中華文明形象,辜采用高度歸化方法使用普通詞匯,不可避免以西方思想解讀《論語》;辜早期接受西方浪漫主義思想,對工業革命后極端物質主義和剝削壓迫猛烈抨擊;受啟蒙運動中伏爾泰尊孔影響,均加劇其保守主義文化觀,甚至夸大儒經救世價值。
六、結語
雖理部分譯文加深當時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但其譯本成為海外學習研究中國儒家思想無法繞過的文獻,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文化傳播。辜譯本雖有不足,但秉著拳拳愛國之情和對原著之熱愛,深入研究,深譯精髓,為西方社會所推崇,一定程度上改變西方對《論語》的誤解。如孔子不是刻板嚴肅而是仁慈熱心、幽默大度的老師形象,使西方感受《論語》的哲學魅力、精神力量和文學美感。
兩譯者均有以本族文明拯救譯語民族的雄心[9]。在當時背景下可理解,但我們要從辯證思維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觀看此,深刻認識各族文明平等獨特,只有世界各族文明互相理解尊重,共同發展,才能促進各民族文化繁榮。這益于縮小自身和時代局限,對我國民族文學經典走向世界和翻譯外國民族經典意義重大。
兩譯本比較發現,句子或語篇中,對直譯與意譯、闡釋與翻譯、歸化與異化度的合理把握非常重要。歸化方法易于貼近譯語讀者思維模式,但不能犧牲源語文化特征,也不能過于異化,脫離讀者實際文化背景不現實也沒有必要。適度直譯和意譯,翻譯和闡釋益于讀者理解原文深層精神內涵和哲學思想,達到“功能對等”,即具體事實,主要精神,意境氣氛對等,建立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梁。翻譯過程中譯者加入適當能動的跨文化意義闡釋,助讀者正確理解以減少誤解,促文化傳播。
總之,譯者應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傳播人類文明成果的態度翻譯原著。譯者需胸懷博大,思維開闊,熱愛原著,領會文學和哲學經典思想本質,把握翻譯基本原則,采用跨文化闡釋式翻譯,合理把握翻譯方法間的度,再現源語作品精神內涵和文化風格,體現其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的美。
[1]辜鴻銘.辜鴻銘文集[M].第一版.黃興濤編.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43-353.
[2]王寧.翻譯與跨文化闡釋[J].中國翻譯,2014(2):5-6.
[3]金隱.等效翻譯探索[M].第一版.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7-18.
[4]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kong: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1861:49-218.
[5]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M].第一版.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6]王國維.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后(1925)[M].王國維文選[M].第一版.林文光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310-312.
[7]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第一版.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175.
[8]金學勤.論語英譯之跨文化闡釋——以理雅各辜鴻銘為例[M].第一版.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
[9]辜鴻銘.李晨曦,譯.中國人的精神[M].第一版.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此論文為大學生科研立項成果。
指導老師: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