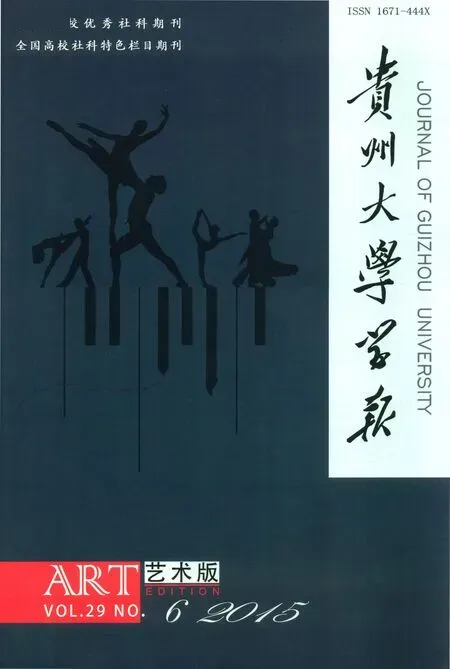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樣板戲”研究:緣起與思路
[法]王 曌,李 松
(1.弗朗什 孔泰大學 文學院,法國 貝尚松;2.武漢大學 文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王曌(以下簡稱王):李老師您好!我拜讀過關于您的很多“樣板戲”研究成果。從您的著作不難看出,您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樣板戲”專家。圍繞您對“樣板戲”的研究,我有一些問題想要跟你探討一下,第一個,為什么您會研究“樣板戲”?又是怎樣的契機使您開始這個領域的研究呢?
李松(以下簡稱李):我覺得任何一個人做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這當中呢,必然性是由很多的偶然性促成的。而就我個人而言,我研究“樣板戲”的必然性是由以下的偶然性促成的。
首先,我攻讀博士階段研究的課題是中國十七年的文學批評史,即1949年到1966年期間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狀況。我主要是以文學經典為核心來考察批評觀念的演變。而當我聚焦十七年這一階段,這個博士選題需要持續發展下去的話,就需要找到與他相關的其他話題。那么,從時間上和觀念上,以及文學發展的現象和線索來看,關于十七年文學批評的研究自然而然會延伸到文革時期的文藝生態,也就是從1966年到1976年間文藝創作和觀念與十七年之間的延續和斷裂。在2003年,我開始考慮研究“樣板戲”這個領域的時候,發現學術界出現的成果并不是很多,尤其是真正的學術成果比較少,而報告文學類的著述比較多。關于文革文學的研究,從美學意義上來說,我認為最具有價值的就是“樣板戲”了。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在做長篇小說研究,還有地下詩歌等等研究。我研究文革這段歷史本身,以及文革文學、藝術發展的一些狀況之后,發現學術研究必須尋找一些可以發掘的空白地帶,或者說還有待擴充的領域。之所以“樣板戲”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對象,理由在于:第一,從文學史的角度,“樣板戲”是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舊戲改革的延伸,也就是“改戲、改人、改制”——所謂“三改”的成果之一。而“三改”中的改戲,就從對舊戲的改革推進到了對戲曲現代戲的創新,以及新編歷史劇的發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從“兩條腿走路”(戲曲現代戲劇目與傳統劇目齊頭并進),到三者并舉(傳統戲曲、戲曲現代戲與新編歷史劇),再到文革期間百花凋零唯獨“樣板戲”一枝獨秀、獨占舞臺。從“樣板戲”的藝術譜系來看,它屬于吸取現代戲的一個部類。而從戲曲史發展的長遠過程看,“樣板戲”的發展還有一個深遠的淵源,即1938年延安時期開始的“舊劇革命”,包括《夜襲飛機場》、《劉家村》、《趙家鎮》等抗日題材的京劇現代戲。
王:是的,我在您的書里讀到過這一段,您說延安時期是“樣板戲”的起源階段。
李:對,那是“樣板戲”的一個前史階段,并不是“樣板戲”正式出現的時間,但是,它是一個醞釀時期。從何種意義上這么認為呢?迫切要求戲曲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和時代主題,從而發揮文藝的政治功利性作用,直接為現實政治目標服務,也就是審美的直接功利化。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理論上進行了權威闡釋和論證,從此這一《講話》精神深刻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性質、方向和功能。延安時期也可以算作是當代戲曲現代戲的淵源。從文學和藝術角度來看,樣板戲是延安文藝的延伸。另一個方面,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政治領袖、政治路線方針政策、或者說一些政治思想的觀念與樣板戲主題、人物、題材、情節之間的深層關聯。政治史的研究有很多透視的方式,如果去透視政治史的精神生態的話,那么,戲曲、或者說“樣板戲”是一個很好的標本。“樣板戲”從起步到鼎盛,毛澤東、周恩來、彭真、周揚、林默涵等大批中央高層領袖或者說中宣部、文化部、文聯等各個部門的領導人物,他們都曾經積極關心推動“樣板戲”。“樣板戲”集中了當時這么多的人力物力,這多領導的關心推動,這在中西方藝術史上都是特殊的現象。從“樣板戲”這個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高層內部對于中國藝術文學發展的方向,對于“樣板戲”改編、創作、藝術發展方向上的一些觀念上,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內在的分歧,例如江青與彭真、周揚等人的對立。總而言之,通過大量的“樣板戲”史料來觀察的話就會發現,“樣板戲”凝聚了幾代戲曲藝人的智慧和心血,被打上了鮮明的政治烙印和時代標記。而“樣板戲”最鮮明的特點就是它的政治印記,即激進革命、不斷革命的政治思路在藝術作品上的形象化傳達。從政治史的角度來說,我們也許可以換個角度,不再從領袖英雄人物出發,不再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政治事實,而是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去解析它。從這個角度我發現,從藝術和美學角度理解“樣板戲”其實是個很好的窗口。
王:我非常認同老師的觀點。我在弗朗什孔泰大學文學院選擇這個課題的原因,也和老師一樣,分為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緣于在一次演講報告里跟我的戲劇哲學老師的談話,我無意中發現了“樣板戲”這個中國當代藝術劇目在法國漢學研究中的缺失,因此引發了強烈的好奇。必然性,是在我遇到了那個偶然性以后對“樣板戲”的深入了解,所產生的自然而然的強烈興趣。在對“樣板戲”有過初步了解后,我發現它的藝術價值相對來說是很高的,可以說小小的戲劇作品卻包羅萬象,融匯了中西藝術多種形式和元素。而我所傾向于的研究方向是,不做簡單的政治評判的前提下,單從“樣板戲”的舞臺藝術入手。比如說,“樣板戲”的舞臺走位,舞臺排布在塑造戲劇美學方面的效果。
李:你發現的問題是很好的,在這個方面還真的很少有人去研究關于“樣板戲”的舞臺走位,舞臺設計方面。當時國家出版部門的確印刷了大量的“樣板戲”編排過程的資料,但是還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入手研究“樣板戲”的舞臺形象塑造。
王:我之所以會選擇這個方向,我想也是因為我的戲劇評論和研究是在國外學習的,處身于一種中西交匯的文化沖擊的氛圍之中,我試圖從藝術對象尋找我的文化身份。而我的研究方法與視角,是從西方戲劇理論的慣有角度出發,在法國的戲劇研究里舞臺的設計、排布、演員的走位都是很受重視的。因為這種形式的設計會表達出劇作家的想法,會通過舞臺的設計來表達一些自己不敢寫、不能寫的思想和情感。
李:你的這些觀點對我也很有啟發。不僅可以文學藝術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分析“樣板戲”,還可以從精神史的角度來看待。其實“樣板戲”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而流行歌曲恰恰能夠最鮮明反映一個時代的人們內心的愿望、情感以及寄托,在這樣一種寄托當中體現出一種內在的、深層的精神結構。如果從文革的深層精神結構來說,“樣板戲”視野中的當代人的心理狀態可以看得很清楚。人們的領袖崇拜,對于京劇的那種狂熱,對于英雄人物的謳歌,以及崇高、莊嚴的情感的抒發。所以說“樣板戲”是一種與當時的政治熱潮高度統一的藝術形式。如果從意識形態管制的方面來看的話,“樣板戲”很好地實現了意識形態凝聚社會情感、形成社會動員的社會功能或者說政治功能。“樣板戲”劇目包含了很多不同類型的藝術。當然也會有人覺得樣板戲并沒有什么研究價值。關于“樣板戲”,如果不認真仔細地去勘察材料跟劇本,或者進入劇場、進入劇本結構的話,產生以上的那種想法一點都不奇怪。這是對“樣板戲”的偏見和盲見,也還有一些認識方法上的問題,覺得我不喜歡“樣板戲”就不想去研究。
王:老師,會不會還存在一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因為患有PTSD,也就是創傷后遺癥,一種心理上的疾病導致他們對“樣板戲”的排斥以至無法接受。就好比我在老師的書里看到的,巴金聽到“樣板戲”就會心驚肉跳。
李:是的,確實也存在這個方面的問題。情感的判斷會影響對“樣板戲”研究的學術判斷。所以,任何學術上的判斷都應該與研究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應該將學術立場與情感體驗分開來看待。當然,不是說學術判斷不可能受情感判斷的影響,但是兩者之間應該保持一定的理性距離。
從2003年開始,我關注樣板戲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相對來說比較少,當時我發現這個領域具有潛在的發掘價值。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文革文學這一塊,認為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諱莫如深,甚至談虎色變。確實,這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存在文章不好發表,著作不好出版的問題。有時會因為這些障礙而感到沮喪,但是,當大家都覺得此路不通的時候,也許最難的路就會變成最簡單的路,因為競爭者相對比較少,發現問題的機會就比較多。其實,這種純粹的學術研究不涉及國家機密,不進行人身攻擊,與我們中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并不沖突,所謂的政治敏感只是無知導致的偏見而已。解放思想,開放心胸,立足學術,講究方法,才會具有學術勇氣。科學研究往往需要一種懷疑精神,當大家都覺得此路不通的時候,當大家都去追趕學術主潮的時候,我們需要反思:到底什么是主潮,是一種什么意義的“主潮”?
王:我想,其實研究工作有時候也會存在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情況,因而,制約了研究進程的并不是我們所研究的課題本身,而是我們的思想局限與偏見。
李:是的,有時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思維與道路給堵死了。既然這個領域的開發價值很大,為什么要以禁忌為借口作繭自縛呢?
王:我覺得,您應該說是勇敢地開辟了一條荊棘之路。就我自己的“樣板戲”研究來說,資料的收集過程我花費了好長時間,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您的著作以及您的聯系方式。謝謝您幫助我郵購了《“樣板戲”編年史》、《“樣板戲”的政治美學》、《“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等書籍。也許對您來說這些史料不過是您研究計劃的一小部分而已,可是對于我們來說確實是很寶貴的資料。而對于法國漢學家來說,其實他們現在最感興趣的并不完全是中國古代社會所留下來的那些文化遺跡,還有新中國建國以后所誕生的那些新生的文化與藝術。外國學者對于我們經歷過文革那場浩劫以后,但卻能迅速發展起來的原因感到十分好奇,對于我們文革發生的原因當然有更多的新奇。而這些問題恰巧是您所研究的范圍,也許您自己并不知道,您所做的資料收集為海外學界提供了多少幫助與便利。您所收集的這些材料是“樣板戲”研究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參考。而且相較于歐洲傳統的希臘戲劇,其實國際學者們更感興趣的是我們當代的戲劇作品以及這個方面的研究成就。我所了解的法國的太陽劇團和中國的“樣板戲”,都是20世紀帶給我們震撼與感悟的戲劇。
李:其實你在國外的這種生活經歷,是一種非常好的體驗,你在留學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并且體會到西方研究者對發現東方的一些需求和動向。了解西方需求心理是中國文化西行的必要準備,我希望你利用海外背景的學術優勢,架設起中法戲劇交流的橋梁。
王:老師過獎了,我希望能夠中國當代戲曲研究的海外學術推介工作,希望我們的文化能夠走出去。老師您在前面談到過研究“樣板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么,在您研究“樣板戲”的過程中,最大的感觸又是什么呢?
李:最大的感觸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樣板戲”是京劇發展的巔峰。近百年來京劇從徽班進京到慈禧大力推舉京劇的發展,到1930年代中國京劇四大名旦的出現,另一個高峰可以說是1960年代“樣板戲”的出現。第二,人們對“樣板戲”的認識還并不全面。從歷時性發展來看,“樣板戲”分為前后三個批次;從是否定型來看,既有成熟的典范,也有試驗演出的漸進型,還有計劃中的作品。“樣板戲”的數目可以分別從狹義和廣義的角度來概括。從狹義角度來看,“樣板戲”包括第一批8 部和第二批10 部,合計18 部。從廣義角度來看,它包括第一批和第二批,試驗演出中的7 部,以及第三批尚未出籠的7 部,合計32 部。第三,我覺得32 個“樣板戲”里藝術成就最高的是京劇,京劇里的唱腔、行當、角色、扮演等等方面,我認為藝術成就最高的就是音樂,京劇的音樂。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待,“樣板戲”是個特別有價值的劇種,而且是京劇藝術里的一個高峰,并且這個高峰是三十多年以來,我們很難說已經趕上和超越。如果說我們現在回頭去聽京劇,最經典的還是1930年代的那一批,然后就是“樣板戲”了。我想這也是為什么每年春晚都會安排“樣板戲”的片段了。這應該不僅僅是為了勾起那個時代的人的回憶,也確實是因為它是我們文化藝術史上的一個高峰。當然,藝術作品也不能簡單地分出絕對的高低水平,我只是從相對的角度認為,從一個藝術品流傳的價值看來,“樣板戲”并不會很容易被埋沒。
王:這方面我非常同意老師的觀點。就我自己的家庭來說,我的父親母親都是1963年出生的,我的外婆是1937年生的。他們對“樣板戲”的記憶都是很深的,當我跟他們提起我所研究的課題后,他們都是張口就可以唱的,雖然會有些什么詞遺忘或者跑調,卻都是朗朗上口的。您的著作里所收錄的那些“樣板戲”的名言名句,他們也都是記憶猶新的,例如“人走茶涼”那些話。從這里看出,其實“樣板戲”對我們的影響并不能單單從政治上面看,也應該從藝術成就方面出發,它是一個深入到了我們生活中并且根深蒂固,伴隨了我父母親他們那一代人的成長。“樣板戲”在他們孩童時期進入他們的生活,影響了他們的思想,生活以至于以后的人生。如果從社會學這個角度來說,“樣板戲”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以及后續影響是非常巨大的,而這些影響就恰恰來自于它那非凡的藝術成就。
李:確實如此,看來你也從你父母那里感覺到了。那個時代“樣板戲”的影響真的太大了,太深入人心了。可以說是深入人的靈魂,從靈魂上影響了幾代人,所以我最大的感觸就是,我們對于“樣板戲”的認識還遠遠不夠,現在“樣板戲”的研究做的最多的就是8 個,對于第二批的10 個涉獵不多,那么后來在文革快結束的那幾年里面還在打磨、鍛造之中的那14 個,研究者的關注就更少了。如果說純粹從審美自律的角度來看它的價值的話,這些作品也許乏善可陳,因為過于濃烈的政治色彩往往會遮蔽藝術的自由,可是如果說結合社會史、政治史、藝術史,還有人們的精神接受史去了解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樣板戲”作為一個學術的問題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
另外一個很大的感觸,對文革社會運動的驚訝。我自己并沒有經歷過文革,我出生于1974年,那時候文革已經接近于尾聲了,我對文革的印象就只停留在了那些大字報、旗幟還有標語上,當然也聽過很多過來人的說法,但懂事的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政治運動了。所以,我沒有親歷過文革,只是知道一些文革在語言以及實物方面留下的痕跡。帶給我感觸最深的就是通過后來的語言和文字,通過報紙、雜志還有書籍。那個時代真的有太多瘋狂、荒謬的東西,所以我說我最大的感觸就是驚訝。驚嘆于竟然有這樣一個時代,這些驚嘆帶給了我無數的疑問,這些疑問在研究的過程中有些慢慢從理性理解。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的回憶錄里你也看到了,巴金聽著“樣板戲”接受的批斗,我想要是這個場景用我們現今的電影技術表達出來的話會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一方面,崇高莊嚴雄壯的“樣板戲”音樂作為背景,它要面對的敵人卻是那個時代的締造者、推動者以及再現者——巴金,巴金在顫顫巍巍、膽戰心驚接受革命小將們的批斗;另一方面,這樣一種莊嚴的音樂卻被用來抨擊這個社會的推動者和建設者。真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我個人其實是有點歷史的窺視癖,對于很多歷史問題有很多自己很特別的想法,也有去發現的欲望和沖動,——為什么歷史上的這些人會這樣。
王:在我看來,老師并不是有什么歷史窺視癖,只是因為感興趣,所以不舍得放開一點點的蛛絲馬跡,才會這么細致的研究這段歷史。
李:也可以算是吧。做歷史的研究的話,對于材料的掌握,還有歷史現象的摸爬就變得很重要了。任何一點歷史風云的波動,都會對自己產生很大的震動和沖擊。保持這種對歷史變動的敏感性以后,自然就會發現歷史中的那些耐人尋味、引人深思的細節。
王:我和老師算是不謀而合吧,對于“樣板戲”,我覺得它的大起大落也是由于這些歷史上的波動而引起的。文革為“樣板戲”帶來了巨大的輝煌也為它帶來了無法避免的滅亡。
李:是的,文革給“樣板戲”帶來了無可比擬的輝煌,同時也注定了無可挽回的宿命,所以它的退出也是必然的。從這些看來,其實“樣板戲”的發展歷程并不是一種藝術發展應該具有的常態。
王:藝術應該是慢慢地緩緩地像京劇那樣經過沉淀而留存下來的。
李:“樣板戲”的衰亡與落敗其實都是與政治有關系。實際上“樣板戲”充當了激進政治意識形態觀念的推廣者、宣傳者,所以它確實是成為了一個工具。“樣板戲”創作者如何處理好政治說教和藝術熏陶,這是一個難題。
王:這應該就算得上“樣板戲”它本身所包含的那種兩極矛盾了吧。其實我之所以把“樣板戲”選擇作為我的研究課題就是因為我覺得“樣板戲”是很有意思的戲曲,它本身包含了很多的藝術形態,這些藝術形態有很大部分是兩極化的,自相矛盾的。它的文化包含了西方和東方文化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然后它的藝術形態又是自相矛盾的,感覺上就是把兩個相同的磁極硬塞到一起去。“樣板戲”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自身的矛盾結合和不可調和性。
李:是的,確實如此,“樣板戲”其實算得上是一個古今中外藝術觀念上的結晶,包括了藝術技巧,藝術思想方面。所以它就體現了毛澤東說的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比如說芭蕾舞就融合了“樣板戲”,雖然芭蕾舞是西方古典藝術的高峰,可是“樣板戲”打破了芭蕾舞的陳規。再說交響樂不是西方音樂的高峰嗎,“樣板戲”給西方音樂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可以說在東西文化混合上,“樣板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王:您在從事“樣板戲”的研究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什么困難呢?
李:要說遇到困難的話,我覺得首當其沖的是原始文獻的問題,我們現在在圖書館里能找到的文獻資料大都只是劇本。可是與劇本相關的研究資料就相對比較少了。當時結集出版的論文集,實際上就是“樣板戲”在藝術輿論上的宣傳品。無論是在武漢大學圖書館還是國內其他圖書館,這類的資料都不多,所能找得到的無非就是劇本、樂譜以及小部分的研究資料,有些結集而成的這種論文集,大多能在報紙、雜志上找得到。而這種論文集其實是對于這些文章的聯合整理以及出版,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這些資料遠遠不夠。況且這只是文字方面的資料,而另一方面的則是音頻、影像方面資料的匱乏,雖然可以找到一些,但卻不全。能找到的主要是最著名的八個“樣板戲”,市面上有賣,還有圖書館的音像部一般也找得到,但是不全面。因為樣板戲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在1963年、1964年“樣板戲”崛起的過程中的各種版本都是缺失的。總之,第一手的“樣板戲”資料是很難得到和掌握的。這是在研究“樣板戲”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
第二個困難,應該算是我自己個人的困難。我在研究的過程中經常會想,我研究“樣板戲”時,對于文本的細讀、思想的分析,到底科學與否呢?這涉及我個人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之所以引起方法論的自我質疑,是因為存在太多關于“樣板戲”的多種多樣的看法,不同立場、不同判斷彼此對立,而這些不同看法都源于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經歷。所以我想,有沒有一種客觀的、中立的、有說服力的、又有學理依據的研究,或者研究方法、研究結論,可以讓大家都坐得下來心平氣和地對話并且接受它?如果說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種片面的偏見或者盲見的話,或者說一種自以為是的看法的話,那么,我覺得就稱不上是學術研究。在我眼里學術研究擁有的是那種理性、嚴謹性、普遍性以及對話性的特點,也就是說學術研究應該可以形成共同話語的對話平臺。我從方法論的反思中認為,到底如何看待“樣板戲”應該有四個方面:一是文本本身的藝術性在哪里;二是從作家創作的動作來說,他到底希望表現什么;三是當時“樣板戲”誕生的那個時代,以及滋養它的土壤到底是什么;四是作為觀眾和讀者,他們對于“樣板戲”的看法說明了什么。我想從這四個方面重新解讀“樣板戲”,然后再在這個基礎上在形成對“樣板戲”的認識和判斷。
王:這么看來,您在研究“樣板戲”的過程中既遇到了硬性條件上的困難,又遇到了軟性條件上的困難。有材料缺失這些方面的硬性條件,也有思想方法方面的軟性條件。
李:是的,也就是說主觀和客觀兩方面的困難都存在。主觀方面,有讀者、觀眾的心理之類的,而文本資料和劇本以及史料屬于客觀方面。應該認識到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有它的客觀性。
王:是的,但我想對于我們來說,現在存在的這段歷史資料也是不充足的。
李:是的,大家可以找得到的資料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里面的藝術材料給發掘出來。而藝術門類也就包括了以下的這些方面,它在發展過程中演變的各種音頻或者影像文本。由于“樣板戲”的演出場次很多,所以導演、創作者也進行了巨大的改變。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什么代表性的文本,文本主題如何變化的?研究這個過程需要大批的材料,比如說音頻、文字。“樣板戲”是如何被卷入了這場政治熱潮當中的?這些都需要藝術材料來解答,這些疑問就只能通過藝術材料來體現。在我所出版的《“樣板戲”編年史》里就收集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我現在正在編排一本《“樣板戲”編年史》的補編,也是對這段藝術史資料的一個補充了。我還在編纂《“樣板戲”版本整理與研究》,不同版本的文本都收錄到一起,比如好幾個版本的《紅燈記》和《沙家浜》。收集不同版本的文字資料也是研究“樣板戲”的困難。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王:您付出的99%的努力,換來了1%的展示成果,可謂厚積爆發吧。
李:你過獎了。我覺得研究過程開心就好,如果覺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正確的、有意義的事情,再多的付出都不會去計較得失成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