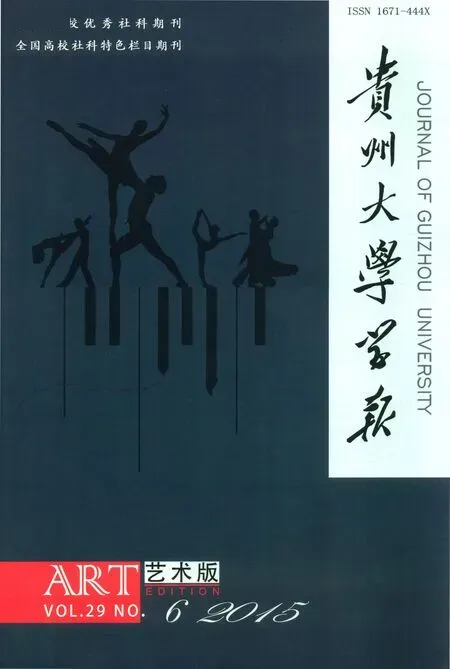當代西方博物館的資本與權力更新
劉永孜
(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124)
1970年代末以來,隨著西方城市由工業生產功能轉向消費功能,文化經濟在歐美都市蔚然興起。城市規劃也日益重視提高城市的視覺化與體驗感,政府鼓勵興建各種各樣的娛樂和購物空間,增加消費機會;在全球競爭中,城市也通過投資文化基礎設施與活動,提高當地的宜居性,吸引游客、投資者和高級人才。當代文化,無論作為一個群體的生活方式,還是精英與理想的藝術,勢不可擋地深入整個社會領域。拉什與厄里 (Scott Lash&John Urry)在《符號經濟與空間經濟》一書中討論說,后現代社會中,經濟過程與符號處理過程“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織,互為話語…文化與經濟的邊界日益模糊,它們不再互為系統和環境而起作用”。[1]64當代的文化經濟或后福特主義的經濟是基于靈活累積的和專門性的生產,以滿足利基市場的消費。人們通過在階級間和階級碎片間制造個體差異來實現消費,這種差異不是由產品的使用價值制造出來的,而是透過產品的符號特征體現出來。[1]4-6在這個全面符號化和審美化,同時也是商業化的雙向運動中,博物館展現出特殊而復雜的角色。與電影業和旅游業這類本身就極具商業性的實踐不同,博物館一直作為非營利性和公益性的文化機構,是西方高級文化的象征。如今,博物館藏品的經濟價值和博物館創富的能力也成為評價博物館的顯性指標,同時,追逐經濟效益也另博物館遭受批評。無論是擔憂博物館過度商業化,或是急于尋找博物館市場化手段的讀者,本文都希望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我們將從文化機制的角度,揭示博物館如何以其獨特資本實現與經濟資本的交換,并創造和引導城市的文化經濟。同時,博物館在當代文化經濟中的行為邏輯和動力不完全是外部市場和商業壓力的結果,而是源自文化機制內部參與者間的競爭與互動。文化領域和博物館領域的自我更新導致其更具靈活性的文化生產,因而也滿足了當代文化和市場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的需求。
一、博物館①的資本與生產邏輯
①英文Museum泛指“博物館”,Art Museum中文多譯作“藝術博物館”或“美術館”。由于西方博物館大多為藝術類博物館,所以在西方公眾的普遍印象中,Art Museum和Museum并未做嚴格清晰的概念區分。Gallery中文可譯作“畫廊”、“藝廊”、或“美術館”。在英文中,gallery既可以用于公共的非營利性的美術館,也可以用于私人的畫廊,即銷售藝術品的商業企業。在北美英文的使用中,gallery往往意味著私人畫廊,而public gallery公共美術館更可能使用藝術博物館的稱謂。在英國英文和英聯邦的使用中,gallery意味著公共美術館,博物館museum一詞被理解為收藏歷史、人類學或文物機構,而不是美術品的機構。以上說明綜合了維基百科museum的詞條,以及美國芝加哥博物館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在新浪微博上的內容。
博物館的原型可以追溯到18世紀歐洲王公貴族用來展示收藏與相互炫耀的珍寶閣。直到19世紀,民族國家興起,博物館才真正確立了為公眾服務的社會目標。在現代博物館的成長過程中,其定義歷經改變,國家和地區間也存在差別。本文采用2007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對博物館的定義:博物館是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利性的永久機構,并向大眾開放。它為教育、學習和欣賞的目的而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有形遺產和無形遺產。[2]在各國,博物館的分類方式也多有不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按照功能將博物館分為三大類,即藝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和科學博物館;其中,藝術博物館是展示具有美學價值的藏品,包括一般性繪畫、雕塑、裝飾藝術、實用藝術和工業藝術,主要是視覺藝術的博物館。[3]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藝術博物館與其他類型博物館的根本區別在于,它代表一種文化的等級,是定義藝術,區分藝術品與日常物品的權威機制。這種區分的能力與權力也便構成藝術博物館在文化經濟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它用于投資文化經濟的資本。不過,博物館經濟的運行邏輯與商業企業不同。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是最早揭示這一邏輯差異的作者。他富于創建性地提出了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的概念。它們同經濟資本一樣,也是換取社會權力的資源。不過,根據19世紀確立的文化自主的原則,文化生產的運行邏輯是通過否定經濟的功利性來達成的。在他稱之為文化場域的抽象空間中,文化生產者通過各自獨特的文化資本進行生產,贏取和積累自己的聲譽,即象征資本,此后,象征資本可以在市場中或多或少地轉化為經濟利益。[4]作為文化機制中的權威機構,博物館的角色非常微妙。博物館擁有富足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是文化生產者和文化產品扎堆的地方。首先,博物館通過收藏的功能,擁有代表一個地方,甚至世界范圍最珍貴的文物與藝術品,即文化資本的客觀化形式,并因此享有文化聲譽;第二,通過研究和展示的功能,掌握著解碼和定義藝術的知識、能力與機制,即文化資本的主體化形式和機制化形式;第三,博物館作為教育機構是培養審美能力,是觀眾積累和應用文化資本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以象征資本為中介,博物館與社會場域間存在著隱性的轉換關系。布迪厄分析說: “博物館在文化上必須有崇高的信譽,必須受人尊重才能爭取贊助人。畫家也一樣。…畫家必須在博物館展出作品才能進入市場,才能得到國家津貼。博物館必須被政府機關承認才能得到贊助人,而這一切形成了錯綜交叉的壓力與依附關系…。”[5]也就是說,博物館的運行首先要通過文化資本的長期積累,贏得文化聲譽,再以象征資本換取外部的經濟來源。依此循環往復,一種圍繞博物館的經濟其實早已存在。
在文化經濟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博物館具備的這種文化與經濟的兩面性也愈發清晰可見。如今,博物館的文化資產與聲譽比以往更有機會轉化為經濟財富。在市場環境中,博物館與各種依賴文化、設計與符號提升附加價值的行業、企業和品牌合作,因此,當代的博物館越來越具有經濟實體的特征。
二、博物館的文化經濟
博物館通常作為非營利性的文化機構而存在;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博物館固定成本非常高也難以取得實質性的盈利。在歐洲,公共博物館的運營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補貼。這一傳統源自中世紀的藝術恩主制,之后資助藝術的職責轉移給現代國家的政府,成為社會民主與文化優越的體現。美國則建立了一套特有的藝術慈善體制,基金會和私人捐贈是精英藝術保護與發展的重要保證,政府資助在博物館收入中的份額非常小,僅具有一種象征性的意味。美國擁有相當多的私人博物館,相較歐洲博物館的生存模式,運營上偏向企業化,但同樣具有非營利性和反市場的行為。①美國文化社會學家迪馬喬的研究發現,1850-1900年間,美國波士頓的城市精英通過兩種組織化的形式——非營利機構和營利性機構的對立,將高雅文化與流行文化區別開來,自此,博物館和歌劇院成為美國高雅文化的象征。不過,這種區分并未發生在美國的所有城市中,比如紐約。迪馬喬認為,不同于歐洲的世襲貴族,美國有一批文化資本家,一群處于社會統治地位的精英群體。這些家族具有資本家的身份,他們利用在紡織、鐵路和礦業中積累的財富投資于高雅文化機構,發展了對藝術的定義與分類,以及用以支持它們的機制。同樣是對布爾迪厄文化資本概念的沿用,迪馬喬使用文化資本家一詞是強調美國社會精英的特性和他們掌握著社會所認可的藝術的知識與能力。參見:Paul Dimaggio,“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Boston:The Cre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Base for High Culture in America”,Culture and Society,1982,4,P33-50以及”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e,”in The Nonprofit Sector:A Research Handbook,ed.Walter W.Powell(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204 -205
無論采取哪種模式,在20世紀的后30年里,歐美各國形成了廣泛的博物館文化。主要原因在于,二戰后高等教育和藝術教育不斷普及,更多的年輕人愿意以藝術為職業,或從事具有藝術性的工作,同時,教育還準備了相應的觀眾和消費者。19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環境下,文化領域出現了轉軌,文化機構被迫走向市場化。博物館對經濟的影響力,尤其是與當地旅游業的結合獲得美國、英國和法國等城市管理者的高度認可。作為一個保存和展示地方文化和集體記憶的機構,博物館確實對國內外游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如吉姆·布萊特所說,“傳統與旅游是相互協作的產業,傳統將位置轉化為目的地,而旅游使它們變為經濟上可行的展覽。”[6]15即便是在 1980年代英國經濟低迷的時期,國立博物館仍是政府首要的撥款對象。[7]當代文化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間的轉化關系,明確了文化與商業間的合作。2011年,時任英國文化部長的杰瑞米·亨特 (Jeremy Hunt)對博物館免費政策評價說:“兒童、學生、家長、退休人士以及游客首先在國立博物館內愛上藝術,或是培養了探索的精神,而后他們也將成為文化的消費者。我對所有博物館和美術館可以提供免費參觀表示歡迎。”[8]這樣一來,博物館成為公民-消費者兩種身份自由轉換的重要媒介。高雅文化機構同時也是旅游目的地,是社會交往、休閑娛樂和消費的空間。博物館不僅因其高級文化的守護者和傳承者的身份,獲得政府或私人的慈善支持,在當代也成為一個頗富潛力的投資對象。相應的,博物館也需要證明自身的商業能力與潛力才能取得政府持續穩定的補貼。
伴隨不斷增加的參觀者,歐美各國在這30年里紛紛投資建設博物館。美國擁有8200個博物館,其中有一半是在這段時間出現的;1960年美國博物館參觀人次是5000萬,到1980年時這個數字超出了2.5億的美國人口總量;古根海姆博物館修建了一座價值8億美元,高45層的綜合性文化建筑;法國的蓬皮杜中心最早是為滿足每天5千名參觀者而修建的,30年后,它平均每天接待的游客數量翻了5倍,為此,它進行了一次耗資8800萬美元的整修;同一時期,倫敦的泰特現代美術館由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個舊發電廠改造而來;在柏林,政府也開啟了一項10億美元的計劃,重建其博物館島的五個主要場館。[9]在這些建設計劃中,博物館的工作重心正在向服務觀眾傾斜。以盧浮宮擴建為例,其展示面積擴大了2倍,而服務于觀眾的空間比以前增加了13倍,包括上百坐席的餐廳,容納四百多人的多功能空間,以及龐大的地下商店和停車場。[10]
不過,高額資金的投入,擴大的空間與日常訪問的門票收入很難取得經濟上的平衡。那些藏品豐富,享有世界聲譽的博物館充分利用館藏的經典作品組織特展,并借助新增的附屬商業服務,比如咖啡廳、餐廳、禮品店,并與酒店建立合作關系來創造短期收入。博物館將名家的經典藝術印在拼圖游戲、服裝、書包、文具、杯子、鑰匙鏈等等產品上,拓展了博物館的紀念品生意。在2013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所得收入共9400萬美元,其中會員費2940萬美元,門票收入3820萬美元,銷售和其它輔助性服務收入超過746萬美元。[11]布魯諾·福瑞(Bruno Frey)將之稱作“超級明星博物館”現象。[12]如同電影投資為了取得穩定的票房總是集中在少量明星身上,博物館經濟也往往圍繞著少量的知名博物館、藝術家和經典作品進行生產。然而,這些收入不能真正反映博物館創造的經濟。2013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針對參觀者所作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博物館在當年春夏季舉辦的三個特展共吸引了一百多萬國內外游客;在來自紐約市以外的游客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大都會博物館是他們選擇來紐約市觀光的主要原因;游客在住宿、娛樂、觀光、購物、博物館門票方面的花費為紐約市帶來了大約7.4億美元的收入。[13]實際上,博物館已經成為都市文化經濟的催化劑。作為集體記憶的保存者和高級文化的象征,博物館通過文化與象征資產為城市建立起強烈而鮮明的地方性,喚起受眾對一個地方的積極聯想。博物館與其他文化、娛樂、服務設施以及各種活動相互激蕩,誘發了更廣泛的文化與消費行為。這就是文化經濟環境下博物館的溢出效應,在其承擔的文化和社會功能之外,博物館以其鮮明的符號和審美特征另城市別具一格,還與各種文化和創意實踐共同構成活躍的文化氛圍,培養整個社會的文化慣習。
在歷史文化名城,博物館和文化遺產一直是當地重要的文化資本,旅游業也一直是當地經濟的重要組成。但對那些原先承擔著工業生產功能的城市而言,就需要在后工業的文化經濟中尋找出路。因此,城市管理者與投資者將投資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視為發展的戰略工具。畢爾巴鄂現象是最為著名的例子。位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畢爾巴鄂市,原先以煤礦開采為經濟支撐。1990年代,由于缺乏自然和文化資源發展旅游業,地方政府決定修建一座博物館。當時,專門收藏現代藝術的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考慮為館藏的大量藝術品創造更多展示空間。這樣一來,地方政府的復興戰略與博物館提高文化資本使用效率的目標相協調。博物館由美國建筑師弗蘭克·蓋里設計,特異的造型和結構,熠熠閃光的外覆材料,超離了當時人們對建筑的經驗,立刻博得游客和藝術愛好者的矚目,成為熱門目的地。該博物館建設共花費2.28億美元,自1997年開業以來,每年可以為小城創造907個新的工作崗位和近4000萬美元的財富。[14]這種以高投資創造超級博物館的模式與電影業投資拍攝大片十分相似,可能取得高額回報,也有極高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即便如此,許多地方政府與投資者還是愿意復制這個模式,借此發展旅游業,實現地產增值,更新城市形象。古根海姆博物館在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亞、紐約曼哈頓商業區、阿布扎比都建立了分館,開創了博物館領域的連鎖經營。法國的盧浮宮和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也嘗試以相似的方式進行空間擴張。2014年,李克強總理訪英期間簽署了一項全新的合作項目,中國招商局集團與英國國立維多利亞和艾爾伯特博物館將在深圳合作建設一座大型設計博物館。這充分說明,中國城市也正轉向文化經濟的發展模式。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一些知名博物館通過豐富的符號產品和闡釋能力,連同整個博物館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流程一同輸出到世界各地。這與全球化商業企業的地理擴張非常相似,只是其擴張的基礎是充足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以及促使這些資本可能轉化為經濟財富的市場需求。
另外,由于文化經濟對無形資產的高度依賴,博物館的藏品、展覽、教育項目、空間環境都有機會與商業企業的品牌活動產生關聯。在合作過程中,博物館將高雅藝術的光暈映射在企業和商品上,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最終轉換為商業品牌的附加價值。在藝術與商業的合作中,企業贊助藝術和收藏藝術成為新的資助方式,改變了慈善捐贈與私人收藏的傳統。科林·特威迪是英國非營利性組織“藝術與商業”的執行官,這個組織致力于為藝術提供商業贊助。他說,“每當我參觀瑞士、德國或美國的辦公室,到處都是當代藝術…在企業娛樂活動中,藝術比體育更有價值,因為女性不喜歡體育。”[15]確實,贊助藝術已經構成企業品牌戰略的一部分,因此,也總免不了對品牌特質、社會聲譽和市場分層的考量與匹配。時尚業、奢侈品業和金融行業往往是博物館和藝術活動最熱切的贊助者。尤其是一些跨國企業與品牌,它們在開拓新市場時爭取進入當地最具聲譽和象征性的博物館的機會。同樣是充斥著符號與設計的產品與藝術作品在博物館空間內似乎相得益彰,甚至難分彼此。那么,在這些行業中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館或展示空間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文化經濟的需求下,博物館的視覺文化也由其空間溢出,創造出一種廣泛的審美與展示的文化。在各種倡導生活方式的雜志中,我們不難見到這樣的圖片:極為日常的一個物件,被獨立地置于畫面中央,簡單的背景里沒有能夠轉移或牽絆讀者視線的元素。如此一來,這個物件便脫離了讀者的日常經驗。讀者的目光會因此停留片刻,并努力搜尋甚至賦予圖片中的物件與眾不同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博物館特有的閥域機制也被廣泛地應用于城市的商業空間和公共空間。近年,日本百貨業巨頭完成了去百貨化的轉型,通過美術館化和劇場化的手段,不斷將文化主題納入商業活動,提升消費者的體驗,刺激他們的購買欲望。費瑟斯通對此曾總結說,在后現代社會中,通過商品世界的審美化,也就是將創造性轉移到多樣化的大眾日常物品的生產中,日常生活也具有了審美的意義。[16]33-36而博物館充分證明了,自己作為后現代社會的大眾審美啟蒙者的身份。
綜上所述,在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壓力下,博物館以其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參與投資,換取經濟來源,導致其服務對象與經營方式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在設計密集型和符號密集型的生產與營銷策略的驅動下,博物館似乎生逢其時。它將審美能力、符號技巧與展示方法傳授給更廣泛的商業企業和品牌,整個城市也日益視覺化和審美化。同時,博物館資本的獨特性也因為社會普遍的文化化而淡化,其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面臨貶值。不過,假若我們因此認為博物館全面服務于市場需要,并將喪失其文化性和獨立性,這個結論也過于倉促和表面化了。實際上,博物館領域內部一直在進行自我更新,它依照文化生產的邏輯,努力保持文化資本的獨特價值,積累文化聲譽,進而強化其在當代文化與經濟中的權力和地位。
三、博物館的資本與權力更新
布迪厄提醒我們,在觀察文化生產時,不僅要考慮作品在物質上的直接生產者,還要考慮全體行動者與他們所在的制度;并且,行動者的行為,哪怕是極微小的行為,都不是對直接刺激的瞬間反應,而是行動者及其關系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孕育而生的。因此,我們不妨將視野擴大一些,透過博物館過往的行為,它與其它行動者間的競爭與互動,認識博物館在當代文化與經濟中的角色。
如前文所述,作為文化權威,博物館授予部分藝術家和作品以經典地位,并保證了它們在市場中的交換價值。也因此,博物館也成為新生文化生產者發起挑戰的對象。新人進入文化場域時,要么選擇復制經典 (這也是符合市場需求的選擇),要么通過否定經典來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化資本。[17]費瑟斯通分析說,正是那些處于邊緣的年輕藝術家和批評家群體首先提出了后現代主義,將高雅藝術視野擴展到大眾文化,借此提高自己的文化資本的特殊性。[16]41,71,149后現代主義意味著清除藝術與生活、藝術家與觀眾間的距離。這種努力早在1917年就已展開。當時杜尚為一個男性小便器題寫了《泉》的名字,提交給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但未獲展出。二戰后,藝術家和評論家群體內部展開對集權主義和政治審美化的批判和反省,當代藝術朝向去權威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在經歷了波普藝術、偶發藝術、大地藝術、身體藝術、觀念藝術等等五花八門的流派的沖擊和演變后,藝術與真實世界和日常生活間的觀念圍墻被推倒。文化機制內部的其他參與者為了維持自身的地位和權力,也必須做出相應改變,博物館亦然。美國社會學家貝克爾(Howard Becker)曾就文化體制內的這一現象分析說:
“創新打破了常規的合作模式...一些革命性的改變通過發表宣言、撰寫批評文章、批判舊的偶像、歡呼新的作品,并對藝術界內的標準活動發起攻擊,目的是取得來自其他參與者的關注和資源。…對美學信條的挑戰終歸是對藝術界既有社會結構的攻擊,…藝術家身邊的參與者都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做過投資…一個博物館策展人對收藏的決定將影響一個藝術家的職業發展…當某個人成功地創造了一個新世界,那么舊世界中的每個人若不能確立自己的新位置就將被淘汰。”[18]
因此,我們會看到,一些新興的博物館會選擇展示新的藝術風格,以樹立自己的文化聲譽;一些知名博物館則通過增加新的藝術樣式和展覽來實現文化資本的更新和增值。1920年,杜尚與美國的一位收藏家和贊助人組織了“無名者協會:現代藝術博物館”。在20多年的時間里,這個博物館組織了大量新藝術的展覽。1937年成立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以現代主義的非具象藝術為收藏重心,也是1960年代以后眾多藝術家和藝術樣式的支持者。1970年代以后在各地涌現出的不同規模的公立和私立博物館,也通過發展各自的主題、學術標準和收藏體系,區別于那些擁有悠久歷史和經典收藏的前輩,以及當代的同輩。
新近發生的一個事件值得在此做一簡短討論。2013年底,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了“水墨藝術:當代中國的過去即現在”的展覽,展出了35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作品門類涉及繪畫、書法、攝影、木刻版畫、影像、雕塑等70多件不同媒材的作品。這個展覽在我國藝術界也引發討論,比如,認為這不是真正的關于水墨藝術的展覽,而是西方人以學術為名,以資本炒作中國當代藝術;大都會博物館以往并不聚焦當代藝術,舉辦此展名不正言不順,等等。不能否認,博物館再次以曲折的方式參與了當代的藝術經濟活動,但更有意味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生產早已跨越了本土的地域和文化范圍。西方博物館積極地對各種新的藝術風格進行收集和闡釋,改變了全球的文化結構。它們不是對異域文化做亦步亦趨的拿來和繼承,也根本不可能這樣做;而是大膽地吸取和雜交地方性的文化資本,并以自己的觀念對之重構,生成新的文化資本。也只有通過不斷地更新和創新,博物館才能在文化場域中鞏固自己的位置與權力。而在我們的批評聲中隱約聽到的是被殖民者的憂憤,以及在掌握各種資本時的乏力。對國內文化機制中的行動者而言,更為艱巨的任務是如何完成對本土文化資本的繼承與更新,為中國當代水墨提供堅實而明確的學術規范和藝術評價;另外,我們是否也能夠在當代全球文化中吸取和再造屬于自己的,新的文化資本呢?
除去通過藏品與展覽實現更新,博物館的建筑和空間也不是純粹和靜止的,同樣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在18-19世紀,現代博物館發軔之初,博物館空間的塑造與同一時期的藝術,通過純粹和超功利的訴求與日常物品相分離是同步的,也暗示著文化機制內各個行動者間存在的互動與默契。邁克爾·吉百爾豪森在《建筑即博物館》一文中分析說,18世紀后半葉,作為新型功能的建筑,公共博物館并無先例可循,因此,最初的設計構思汲取了羅馬建筑的影響。在整個19世紀,博物館建筑設計都拒絕實用性,通過大體量的宏偉建筑,另人產生敬畏感。并且,博物館一直是現代城市文化與成長的見證,到19世紀末,博物館成為國家不斷增長的工業威力和現代性的象征。[6]48博物館的內部空間與展示設計同樣努力創造出一種神圣的儀式感。博物館學家卡羅·鄧肯 (Carol Duncan)認為: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博物館將人們的日常生活與他們在博物館內的體驗劃分開,以此來強調博物館的神圣性;展陳依照藝術史的線性敘述,在一個連續的空間中展開,參觀者依照這個既定的順序,在燈光和建筑細節的指引下行走、停留和觀看,完成一次藝術的朝圣,實現個體的升華。[19]1920年代末,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在開放之初舉辦了一次建筑展覽,倡導一種“國際風格”的建筑原則,即“關注體量而非數量和強度,講求規律而非對稱,以及禁止隨意使用裝飾”。[20]從外表看,現代藝術博物館是一個由白色大理石和玻璃幕墻構成的方盒子,內部是由單色,沒有裝飾的墻壁、天花板、地面圍合而成的展示空間。自此,博物館建筑的古典范式被打破。
1970年代,后現代主義首先獲得建筑領域的接納。后現代主義的建筑設計試圖擺脫建筑物承載的社會目標與功能,追求自己獨立的美學目標和外部空間的符號性。換句話說,建筑本身就要成為一件藝術品。上文我們談及的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即是一例。如果我們將建筑領域也看做是一個生產的場域,那么,許多當代博物館和它們的設計師都在努力踐行這種建筑作為藝術的唯一性和獨特性,并借此積累聲譽。一些歷史悠久,聲明顯赫的博物館,無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范式,也嘗試著在翻修和擴建中透露出一些后現代的精神與風格。比如,在盧浮宮古典建筑群中插入玻璃金字塔,或者像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那樣,將新增的建筑空間作為城市的微縮景觀,強調自己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民主空間。由于當代藝術不再拘泥于繪畫和雕塑,因而對博物館墻壁與空間的依賴性都在降低。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各種新的藝術樣式與觀念釋放了博物館建筑設計的野心。對博物館而言,通過建筑外在的視覺化和符號化,無疑也建立和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獨特性,意味著文化資本的多樣化;同時,藏品的多元化和建筑的景觀效應將文化觀眾的范圍擴展到大眾市場。
另外,伴隨著1960年代文化體制內部對現代博物館的去魅與批判,比如布迪厄和本尼特的研究,博物館學領域經歷了觀念性的改變。1970年代孕育發展起來的新博物館學,嘗試打破傳統博物館作為文化機構的權威性,以及審美價值高于一切的原則;同時,新的博物館將邊界擴展到博物館建筑之外,以一個社群為基礎,收藏、保護和闡述他們整個生活領域中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并且鼓勵參觀者的參與和批評。[21]在這一觀念指導下,藝術品和藝術歷史不再是博物館展示的核心,觀眾和觀眾體驗成為事業的出發點。如今,博物館假設“不可能有兩個人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參觀一個展覽,”參觀者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被教導的半文盲的大眾,而是積極、活躍和具有自反性的主體。[6]232
隨著藝術與日常生活的距離被打破,受到規訓的沉靜的軀體也獲得解放。觀眾可以自由選擇,穿梭在不同的時空里;參觀也由單一的視覺體驗轉化為多感官的體驗。為了真正實現擔負的社會和文化目標,博物館必須去面對掌握著不同程度的文化資本,有著不同行為慣習的觀眾,并對他們的差異化需求做出回應。在引發觀眾對內容的反應時,博物館需要將信息與娛樂,教育與消遣結合在一起。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一位策展人的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當今博物館在文化生產中需要具備的靈活性:
(博物館)的“個性”…源自各種各樣古老的社會組織形式。…雜合了教堂、皇宮、劇院、學校、圖書館、根據一些批評家說的,還有百貨商店。隨著興趣或活動的轉變,組織的個性也在改變。當博物館用于娛樂的空間,它就展現出劇場的戲劇性,當它服務于學術目的,它就是象牙塔,在進行教育活動時,它就是學校。…在人類發明的社會機構的大家庭里,博物館不是固定的死板一塊。它是富于彈性的,可以在多個方向上發展,有時候可以同時朝多個方向發展。[22]
當代博物館正在由圣殿轉變為跨媒介的多元文化中心,一切可以豐富和強化觀眾體驗的功能與內容都可以被整合進博物館。1977年開業的法國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或許是最早的嘗試者。其外部設計散發著后工業的氣息,中心的內部結構大膽集中了現代藝術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工業設計中心、音樂和聲學研究所等。各個機構在內容生產與服務上相互關聯,又有著各自獨立的日程。如今,一整套的文化、教育、娛樂和商業設施已經構成當代博物館或者說是文化中心的標配。在服務差異化的和不斷翻新的需求這一點上,博物館具有當代文化和經濟都需要的核心稟賦,就是能夠進行更富靈活性的內容生產。
為了惠及最廣泛的觀眾,博物館界早就曾提出和實踐“無墻博物館”和“移動博物館”的理念。1947年法國人安德里·馬爾羅 (André Malaux)出版了《無墻博物館》一書。他在書中采用大量圖片,集中展示了世界各地的造型藝術,借由印刷媒體為讀者創造了一個非現實的,想象中的博物館。[23]同時,印刷媒體比之物理空間更便于傳播,擴大受眾的范圍。最初的移動博物館是以車載的形式將展覽和教育內容送達到偏遠地區的觀眾。但是,由于地理、媒介和技術的限制,想象中的,無邊界的博物館并未真正實現。20世紀末以來,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攜帶的自由與開放的文化基因有可能令博物館實現真正的受眾最大化。1960年代也是黑客文化興起的時代。黑客的核心準則是信息免費,自由分享。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自由分享的倫理讓位給知識產權保護和版權交易。不過,黑客的烏托邦精神或許可以在博物館這類非營利性文化機構中得到繼承和發揚,博物館將真正擺脫各種物質形式、空間和時間的限制。
互聯網架設起實體博物館與世界各個地參觀者之間的聯系,并提供了各種簡單、直接或曲折的參觀通道。博物館360度的全景地圖,大量數字化的內容,觀眾可以足不出戶觀看作品和空間的細節,創建個人收藏或個人博物館,提出問題或發表評論。對于沒有明確目標的網絡沖浪者,他們可能會在某個社交網站、聊天室、網絡廣告或一個話題中,通過超鏈接進入博物館,體驗一次邂逅或探險之旅。在人機互動中,觀眾的主體身份得到認可和強化,觀眾和博物館間形成雙向溝通。觀眾的選擇和行為由系統記錄,并不斷整合進新的軟件程序和鏈接。原先,博物館存在的基礎是真實的人類遺存和藝術品,如今,多媒體綜合應用于展示和教育功能,實現一個完全虛擬的博物館。我們不需要依附任何物質形態的展品,而是通過主題設計,結合真實的與創造出來的圖像、影像、聲音、動畫等等為觀眾還原出一個情境,豐富觀眾對內容的體驗和認知。在無線技術和智能手機的支持下,博物館也真正實現了移動,和隨時隨地的參觀和體驗。泰特現代美術館開發了一款名叫“泰特魔球”的APP,融合了藝術、游戲和科技。APP內置環境探測技術,用戶搖一搖手機, “魔球”開始定位用戶所在的地點和時間,感知氣溫和噪音等環境因素,然后根據結果在美術館的數據庫中調取一件藝術作品與用戶的環境相匹配;“魔球”還會提供匹配的原因和作品簡介;最后,用戶可以儲存圖片并對外分享。實際上,這樣一款APP并不限于本地的用戶或博物館參觀者,身處現代都市繁雜空間中,活躍于社交網絡的用戶都有可能被它吸引。在游戲中,博物館擴大了觀眾范圍,并通過富于知性的闡釋深深嵌入當代人的日常生活。借助數字技術,博物館進一步展現了文化資本所具有的延展性與靈活性。
總 結
在當代文化經濟環境中,博物館的社會與文化角色發生了改變,并展現出商業化潛力。博物館通過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的輸出實現經濟財富。它將審美能力、符號技巧與展示方法傳授給更廣泛的商業企業和品牌,整個城市也日益視覺化、審美化和博物館化。文化經濟的市場策略就是在生產和營銷中不斷創造差異,滿足變動不居又難以預測的消費者需求。因此,無論是因循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化生產的邏輯,還是力圖在當代文化經濟中創造財富,博物館都必須保證擁有獨特的文化資本和充足的象征資本,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和競爭力。作為文化體制中的權威,博物館總是處于維護經典還是支持創新的張力之中。文化上的崇古與復制行為如同印鈔機,也會令博物館的文化資本貶值;在僵化和教條中緊攥自己的權杖將有可能被體制淘汰。博物館的生命力來自文化體制內部行動者之間的競爭與互動;在被挑戰、批判和新生的文化現象中,博物館有機會更新和擴展自己的文化資本,建立和鞏固文化聲譽。當代西方博物館正在脫離圣殿的傳統模式,朝向多元的,綜合性的文化中心發展。正是這種更具靈活性的文化生產使它更能適應當代文化和經濟的多樣化要求。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超級博物館憑借自身的文化資本和象征資本成為全球文化流動的指令中心。我國的博物館和文化生產者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全球文化的交流與競爭中。水墨藝術作為最具中國性的文化資本也成為全球文化市場追逐的對象。它的處境與熊貓和花木蘭進入好萊塢的英雄行列有幾分相似。作為一種獨特的符號樣式,水墨藝術同時成就了西方博物館文化資本的多元化,豐富了藝術品市場的銷售目錄,同時,其中國文化的語境也因此淡化了。對中國文化生產者的挑戰絕不是經濟資本的收編,而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當代的,獨特的文化價值體系,在全球文化場域中占得一個位置。近年,國內也掀起博物館建設的熱潮。國家新近的博物館政策確認了民辦博物館與公立博物館的同等地位,這無疑將促進更多新的博物館的產生。但是,我們也面臨一個普遍的問題,許多新建博物館追求外部景觀化,內部卻展品匱乏,并且,管理者們普遍缺少學術性視野和經營文化的能力。國內博物館領域也在熱議產業化發展,創意產品設計等等問題,但是在缺少充足的和具有差異化的文化資本與象征資本的前提下,都淪為空談。中國欲實現博物館經濟和文化經濟,應依照文化生產的邏輯,從投資和積累差異化的文化資本開始,從文化體制內部行動者的創造、競爭和互動開始。
[1] [英]Scott Lash,John Urry.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SAGE,1994.
[2] 國際博物館協會:http://icom.museum/the-vision/museum -definition/.
[3] 王宏鈞.中國博物館學基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3.
[4] [法]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38,P49.
[5] 布爾迪厄,漢斯·哈克.自由交流[M].桂裕芳,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10.
[6] [美]珍妮特·馬斯汀.新博物館理論與實踐導論·前言[M].錢春霞,陳穎雋,華建軍,苗楊,譯.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8:15.
[7] [英]Christopher H.J.Bradley,Mrs.Thatcher’s Cultural Policies:1979-1990,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lobalized Cultural Syste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145 -148.
[8] [英]Dave O’brien,Cultural policy:management,value and modernity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Routledge,2014,P45.
[9] [美]Toby Miller& George Yúdice,Cultural Policy,SAGE Publications,2002,P147.
[10] 盧浮宮官網 http://www.louvre.fr/zh.
[11] Report of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2012–2013,大都會博物館官網:http://metmuseum.org/about-the-museum/annual-reports/~/media/Files/About/Annual%20Reports/2012_2013/Annual%20Report%202013.pdf.
[12][美]Bruno S.Frey:Superstar Museums:An Economic A-nalysis,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2:113 – 125,1998.
[13] Three Metropolitan Museum Exhibitions Stimulate $742 Million 2013 Economic Impact for New York,大都會博物館官網:http://www.metmuseum.org.
[14][美]Beatriz Plaza,“The Bilbao Effect(Gugenheim Museum Bilbao)”,Museum News,Volume:86 Issue:5 P13,2007,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5][美]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Global Cultural Industry:The Mediation of Things,Polity,2007,P80.
[16][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7][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化場的生成與結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12.
[18] [美]Howard Becker,Art Worl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32.
[19][美]Carol Duncan,“The Art Museum as Ritual”,Edited by Malcolm Miles and Tim Hall,The City Cultures Reader,Routledge,2000,P74-79.
[20]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www.moma.org/.
[21] Andrea Hauenschild,Claims and Realities of New Museology:Case Studies in Canada,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Smithsonia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Museum Studies,http://museumstudies.si.edu/claims2000.htm#1.Introduction.
[22][美]Edward Alexander,Museums in Moti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 of Museums,Rowman Altamira,1979,P14.
[23]張婉真.論博物館學[M].臺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