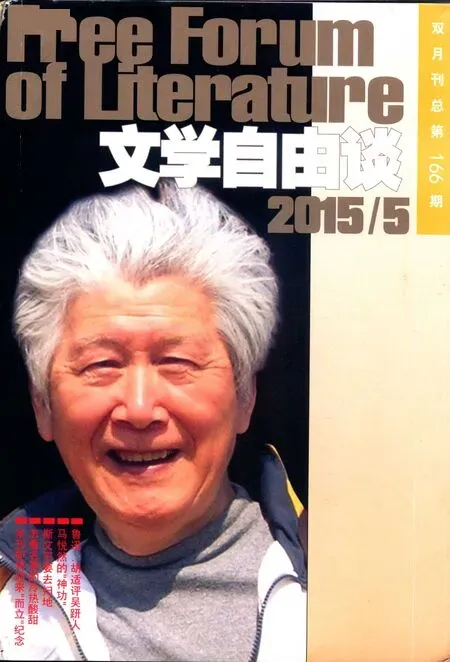一枚 “這一個”的鮮活樣本
●文 劉金祥
一枚 “這一個”的鮮活樣本
●文 劉金祥
上帝是不甘于成為木偶生產流水線上的熟練工人的,他總是想盡辦法把造人的枯燥工作花樣翻新,讓每個產品都盡可能標新立異。化學試劑瓶來回翻倒,隨意配制,有的“愚蠢”放多了,有的“固執”含量明顯超標,有的只倒了“痛苦”的藥水忘了加哪怕一點點糖。上帝隨心所欲地玩著他開心的游戲,做出來看也不看便棄置一旁,只等負責搬運的天使用簸箕撮走,從窗口像倒垃圾一樣扔給塵世。
對上帝而言,這就像放上米兌好水煮一鍋粥一樣輕松。而對他的產品們而言,在越煮越稠的粥鍋里想搞明白怎么回事談何容易?由此產生了不計其數的職業和權威: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精神病學家……甚至對諸如政治家和商人這些世俗事物中的奮斗者來說,把別人內心的秘密像透視儀一樣清晰地照射出來,對于左右周旋、立于不敗也是至關重要的,這種今天和昨天、自己和對手,甚或自己和自己相互猜謎的活動,總是頑強地消耗著人們的一大部分精力,好像是上帝為增加自己工作的樂趣有意給我們安排的與生俱來的職責。就是在制造猜謎的能力上,他也依然配方不同,多少不一。對有的人,他甚至放了一些無色藥水,好讓這個造物把他的化學車間變得像戲劇舞臺一般豐富有趣。
這個人必須不辭辛苦,懷著極濃厚的興趣在人類心理的大峽谷中一路探索。對于他,所有的歷史都是壯闊的風景,所有的心靈都是神秘的礦藏,所有的同類都是造物主的杰作,所有的事件都是用線索編制的奇妙的網,所有的分秒都在等待戲劇的高潮,總之一句話,只要存在的便是洞悉的對象、剖析的目標。在這個靈魂的大自然中,衡量價值的尺度不是高尚與卑都、美麗與丑陋這些通常意義上坐標,而是一個人內在力量的強大程度。奇特的丑陋比呆板的美麗更能撩撥欣賞者的興趣,狡詐的卑鄙比平庸的高尚更值得揭示,規規矩矩的人是受歡迎的鄰居,卻無法引起探索者的好奇,世俗事物的佼佼者未必比失敗者更具有天資。人不僅僅是上帝造的謎,更是斑斕的繪畫、精致的雕刻、雄偉的建筑、起伏不定的小說和涵義暖昧的電影。藝術只為能夠欣賞其奧妙的人敞開面紗,自然只為能夠把握潮汐的人提供遠航的工具。
當茨威格的傳記擺在我們面前,好像上帝造就那些最棘手的實驗品所用的秘方被公布了出來。人世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狂躁不羈、不堪回首又難以忘卻的戲劇,竟是這小小的秘方在作怪。那些生前不安分的靈魂此時又在文字的網中翻躍,試圖再次攪動世界。只不過不同的是,他們無法再用激情向藝術的傳統發動攻勢,無法再以惡魔的精神與魔鬼對抗,無法用陰謀奪取百萬人的生命,無法再一次在血腥中走向斷頭臺。但他們的心帶著隱藏的秘密又回來為我們翻開了或燦爛、或悲壯、或無情的歷史。茨威格像微觀世界的攝影師一樣,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搜尋昆蟲們的巢穴,然后用透明的玻璃代替筑巢的沙土——他要讓研究對象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讓讀者像他一樣把戲劇當作變幻無窮的風光去欣賞,像探索深不可側的大海一樣體味人性的奧秘。
在能找到的茨威格所寫的傳記作品中文版中,《一個政治家的畫像——約瑟夫·富歇》最集中地體現了他洞察力的艱深和好奇心的廣袤。在傳記海洋中,幾乎再沒有一冊能像茨威格為富歇寫的傳記一般,記述者和被記述者的性格和能力如此契合:茨威格是一等一的心理學大師——不僅能認知,而且更擅長于描寫。對他來說,每一個人的言行和內心都十分重要,而人群也絕對不僅僅是用一系列統計數字描述的鐵板一塊,而是瞬息萬變的個體的匯集。他不僅看到集體的變化所帶來宏觀上的結果,更重視每一處微不足道的個體波動是如何累積起影響久遠的全社會的驚濤駭浪。
約瑟夫·富歇——這位南特的托洛茨基,里昂的帖木兒,巴黎的松永久秀,一步步在大革命的人性廢墟中站立起來,學會了不去對自己被鮮血浸透的袖口和領巾有任何敏感或者不適,也不對自己的公爵紋章抱有任何的榮譽感,甚或失去自我的認知。他不為人預設任何立場,也并不期待社會能夠處于任何理想的美好狀態——正因為沒有理想,才使他的巨大才能不受任何束縛。他深知所謂的道德不過是每個時代的切片標本,是凡庸之人對歷史那生硬的確定性的孜孜追求,而拘泥于此只能使自己在新的潮流中慢慢腐朽崩壞。他太大膽,有時甚至故意讓自己居于險境。他以一人之力打翻羅伯斯庇爾和拿破侖這時代的兩大巨頭,在法國掀起革命又徹底埋葬它。富歇從來不留戀自己過去的輝煌,對他而言唯一的樂趣(甚至連這唯一的一點都很值得懷疑)僅僅在于充當歐洲的傀儡師的巨大快感:操縱歷史,創造歷史!他的警察機關(從契卡和納粹黨衛軍到克格勃和摩薩迪,全都源于這么一位祖師爺)是遍布法國的神經網絡——在那個時代法國唯一從來不停止思考和工作的網絡——匯總進富歇這唯一的大腦。他利用巴拉斯,三次耍弄卡爾納,和塔列朗亦仇亦盟,全歐洲被拿破侖的大炮威懾的國家卻把皇帝的警察大臣當作最可信任的人,梅特涅和威靈頓都對他的信使畢恭畢敬。一生歷經戎馬戰陣——更多的是在無人能見的隱秘戰場,而最后又作為一個平凡而寧靜的老人溘然逝去。來到這個世界時沒有人為他慶祝,離開這個世界時也無人注意。然而他改變世界的政治力量和技巧,巨大的影響力沖流至今。
這兩個巨人之間的斗爭是完全無聲無息的——一個足夠堅定而享有巨大才華的作家,對上西方政治斗爭中最杰出的大人物。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傳記或者說用來換稿費的紙稿,毋寧說是茨威格忠實地記下了他和富歇搏斗了整整一年有余的戰爭過程——進入他那從不愿意被人進入的內心,把他從遍布歐洲的無數精巧復雜的提偶絲線后面拽將出來,赤裸裸地摔在眾人面前。一切的戰術策略和最后的結果,盡在其間,展露無遺。
當然,僅靠這種戮穿歷史的責任感去創作是遠遠不夠的。和所有被選中立傳的人一樣,茨威格研究富歇,更多是基于一種純粹心理學角度的興趣。對他來說,富歇越陰險,越違背常禮,他越被牢牢地吸引。富歇的人性越復雜越古怪,茨威格越要弄個明白,好像醫生遇到了罕見的病例,職業習慣促使他抓住不放:上帝到底在這個冷酷卑鄙的陰謀家身體里放了些什么?敏銳的嗅覺使他明白,富歇將把自己帶到從未探測到的地層深處。越是向前探尋,茨威格越是興奮不已。他在富歇心靈深處的旅行,將使這一領域的探素者們更接近人類事務中許多難解之謎的答案,也為人類了解同類提供了活生生的樣本。
當然作為作家的茨威格并不滿足于此。他的“傳記”讀者大多不像他那樣能幸運地擁有一雙敏銳的眼睛。要讓所有人都明白他描摹的人物意味著什么,茨威格必須將人類心靈中流動著的看不見的東西,用文字化作唾手可得、呼之欲出的形象和起伏跌宕的情節。究競哪種因素使茨威格的傳記作品不斷地被廣泛閱讀,是他深刻的思想、準確的洞察,還是栩栩如生的文筆?中國的出版人肯定更喜歡前兩者。因為在茨威格的十幾部傳記中,被中國反復出版的只有七八種。盡管另外那些并不枯燥乏味,但卻多遭冷遇白眼,筆者不知其因由和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