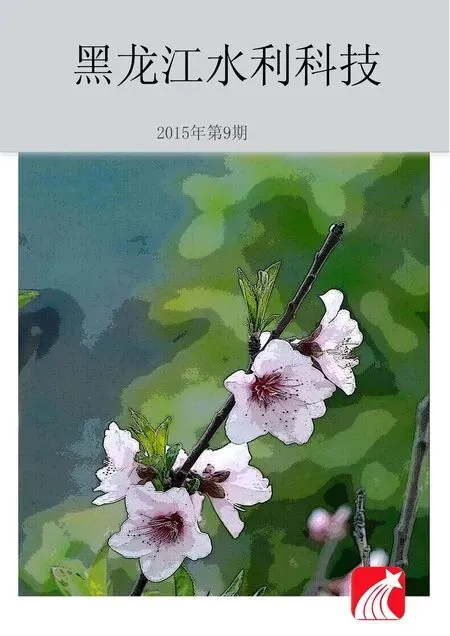基于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剖析
王 洲
(哈爾濱師范大學,哈爾濱 150025)
?
基于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剖析
王洲
(哈爾濱師范大學,哈爾濱 150025)
摘要:在過去的50多年里,翻譯研究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最初的語言學、文學、解構主義理論觀等不同研究角度的探索,到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研究室主任Michael Cronin(邁克爾·克羅寧)最先提出了“生態翻譯學”的概念。國內,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在2004年首次提出了“翻譯的適應選擇理論”。文章探討了生態翻譯學的3個核心概念,即:適應與選擇理論,翻譯的生態環境及譯者中心理論,并就翻譯生態學10多年的研究做出綜述。
關鍵詞:生態翻譯;譯者中心;適應與選擇;生態環境;翻譯觀
1生態翻譯學的起源和發展
眾所周知,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曾在著作《物種起源》[1]一書中提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定律和生物進化的規律。
百年之后,作為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人文科學系主任,Michael Cronin(邁克爾·克羅寧),首次將物競天擇、適應與選擇的概念與翻譯相結合,提出了“生態翻譯學”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往常對翻譯的界定,與眾不同的是,Michael從生態學視角的考慮出發,對翻譯進行了仔細認真的一系列調查研究。
研究表明,翻譯的生態學視角像一座橋梁一樣,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聯系起來。這一獨特視角的提出,立刻引起翻譯界的熱議。翻譯生態學,其以翻譯學和生態學作為自己的理論依據和基礎,在內容上和方法上,不僅和其它分支學科有著緊密聯系,也有著重疊和交叉。但是,生態翻譯理論不但具有其抽象的理論系統,一套不同其他理論的翻譯觀點,而且具有其獨特的研究方法和角度,生態翻譯學也并不是字面上理解的那樣:翻譯學和生態學的單純羅列組合,而是共同起著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作用。
著眼于國內,我國的生態翻譯學研究最早是由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并在2009年達到研究的最高峰[2]。在其 2004年發表的著作《翻譯適應選擇論》[3](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其中一章節中,胡教授明確指出:譯者在翻譯原著的過程中,也符合適者生存的定律,即譯者必須適應翻譯的生態環境,做出最適合的翻譯,否則就有可能被翻譯生態環境“淘汰”。
從生態翻譯學的研究角度來看,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是生態翻譯研究的實質,這種相互關系尤其體現在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的研究。如果譯者在翻譯活動過程中不但適應了其翻譯生態環境,而且在這個的基礎上做出了最恰當的選擇,即稱作為最佳翻譯[4]。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指整合適應度最高的選擇,對最佳翻譯的研究能夠幫助翻譯界更好地評價譯本與譯者之間的關系。
2008年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解讀,這本書中綜合探討了3種翻譯境界,即:翻譯研究的轉向、超越和回歸。書中還提到,從生態翻譯學視角,胡教授將翻譯廣義的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此后10多年里,生態翻譯學逐漸成為一門新興前沿的翻譯理論[5]。
2生態翻譯學的核心概念
主要包括3個方面的內容:
2.1 理論范式:翻譯的適應與選擇
“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作為適用于世間萬物的客觀真理,眾所周知是由生物學家達爾文經過多年的苦心鉆研得出來的重大研究成果。21世紀初,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翻譯適應選擇論,在《翻譯適應選擇論》(A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一書中明確指出:譯者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譯者也是“適者生存”。在國內其首次將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概念,如“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等原理創新應用到翻譯研究中來,將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6]。
胡庚申教授將翻譯定義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創意性的概念首次提出即在國內引起轟動,一方面從人文科學的角度看,翻譯是一種人類行為,譯者會在翻譯過程中需要做出大量的適應、選擇的操作,從而挑選出適合的翻譯。另一方面,他也從宏觀角度思考問題,他相信 “求存擇優”的自然法則與翻譯活動必然存在著一些聯系,通過把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與選擇”學說作為基本指導思想,經過仔細研究與深入的探討,最終理清了在翻譯活動中譯者適應與選擇行為的關聯性和通融性,表現在基本特征、密不可分的聯系、相互作用的機理。
其中,胡教授認為這種相互選擇、相互適應的機理表現為:不僅譯者可以作用于翻譯的生態環境,在翻譯的過程中做出選擇與適應,并且翻譯的環境也可以反作用于譯者,生態環境也可以“淘汰“譯者。在2004年出版的《適應與選擇論》一書中,胡教授從譯者與翻譯環境的相互適應與選擇的角度對翻譯的基本概念作出了全新的定義,對翻譯的本質、原則、機理和規律都作出新的描述和詮釋,從而論證和創建了一門全新的理論:“翻譯適應選擇論”。
作為一門新興的譯學理論體系,在2009年,胡教授發表了—生態翻譯學詮釋:譯學研究的“跨科際整合”[7]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對生態翻譯學的概念作出了進一步的闡釋和更加全面的描繪,他指出翻譯適應選擇論的提出具有重大意義,該學科的研究從傳統角度上看是一種跨學科研究,并且將生態環境放進譯者翻譯活動中進行考慮,這種對翻譯的全新定義與分析,開闊了翻譯研究者的視野,從而擴大了翻譯研究的范圍。
2.2 理論基礎:譯者中心論
2004年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發表了題目為: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8]的論文,這篇重要的論文刊登在我國譯界最權威的期刊《中國翻譯》上,文中主要探討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直接實施者,在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念,打破了以往“以原著為中心”的枷鎖,目的在于為譯者的“譯有所為”尋找理論依據。
這個概念的提出彰顯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功能和地位,彰顯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選擇,胡庚申教授認為確立譯者在翻譯活動的“中心”地位,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從理論上、特別是從機制上真正對譯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給予明確的定位。
“譯者中心論”揭示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突出強調了譯者的能動作用,是總結了以往譯者研究的成果。它將譯者放在翻譯過程和翻譯生態環境中進行考察,譯者、原文本和譯文本便構成了翻譯活動的三要素。他以譯者中心的身份做出積極回應和創造性選擇,靈活運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從而凸顯出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能動作用[9-15]。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譯者為中心”概念的目的在于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從而形成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即:從譯者為中心的視角對翻譯活動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
對于“譯者中心論”的翻譯觀,胡教授補充到:譯者主體性不足以表明譯者的“中心”地位和 “主導”作用。確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與只是力爭和確認譯者在作者、讀者等諸者“主體間性”中的“主體性”是有區別的。
還有很多學者也就此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如,季宇、王宏(2010)對“譯者中心論”提出了反對意見。他們認為,翻譯的“中心論”的弊端在于,“譯者中心論”將譯文作者過度神圣化,譯作應該貼合原作,譯者的再創造忽略了文本意義的客觀性。龍佳紅在2005年發表的論從邊緣到中心——對譯者地位的思考[16]中提到,確立譯者為中心的理念,并不是孤立譯者主體,而是有利于提高譯者的地位和責任感,因為他們翻譯行為具有制約作用。同時他也提出,研究譯者主體性要有“度”的把握,“譯者中心論”要避免出現過分夸大譯者作用、譯作偏離原著的現象。
2.3 決定性因素:翻譯的生態環境
根據生態翻譯學理論,“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文、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
胡教授認為,“翻譯生態環境”構成的三要素就是原語、原文和譯語系統,譯者和譯文的產生離不開這三要素構成的整體環境,這個翻譯環境既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從文化、交際、語言等多維度適應與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又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原因。胡庚申教授指出,“譯者是在接受了翻譯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又轉過來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最佳行文的選擇”[17]。
生態學翻譯研究是一種與以往角度不同的對翻譯的研究,打破了前人對翻譯的定義,無法單純地歸納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作為一門跨學科的研究,以“翻譯生態”為整體視角,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對翻譯理論和實踐進行分析,將 “自然生態”和“翻譯生態”進行參照類比,經過全面綜合的闡釋,將翻譯理論研究回歸到“翻譯生態環境”中去解讀,其理論意義不可小覷[18]。在我國翻譯界理論研究基礎薄弱、原創理論研究相對匱乏的情況下,開創了一片新的視野,其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3結語
生態翻譯理論作為一門新興的翻譯理論,僅僅發展了 10多年,但在國內乃至世界的發展趨勢卻不容小覷[19-20]。
就生態翻譯的三大核心觀點:“適應與選擇理論”、“譯者中心論”和“翻譯的生態環境”,對其研究效果做了整體評價。翻譯的發展歷經多次洗禮,從最初以文本為中心,到譯者為中心,都只是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因此,文中提出無論“以文本為中心”,或“譯者為中心”的理論都有其局限性。然而,就“譯者中心”論而言,本人認為其作為生態翻譯學的核心思想有所主觀,有失偏頗[21-22]。對此,本文認為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進行進一步商榷和討論。
作者希望有更多的譯學研究者加入到翻譯生態學視角研究,并不斷深入下去。世界發展,翻譯的作用功不可沒,與此同時,翻譯生態理論的提出及發展循環往復及螺旋式的上升也使得翻譯生態系統整體得到升華與進化。
參考文獻:
[1]達爾文.物種起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胡庚申.生態翻譯學解讀[J].中國翻譯,2008(06):11-15.
[3]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基礎[J].外語研究,2010(04):62-67.
[5]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J].中國翻譯,2011(02):5-9.
[6]胡庚申.對生態翻譯學幾個問題“商榷”的回應與建議[J].中國翻譯,2014(06):86-89.
[7]胡庚申.生態翻譯學詮釋:譯學研究的“跨科際整合” [J].上海翻譯,2009(02):3-8.
[8]胡庚申.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J].中國翻譯,2004,25(03):10-16.
[9]李楠.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研究[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5(10):314-315.
[10]翁金.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科技英語翻譯[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2(10):101-102.
[11]鄭慧娟.生態翻譯學參照下的譯者中心論—以《玉米》翻譯為例[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
[12]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異”和“新”—不同翻譯研究途徑的比較研究并兼答相關疑問[J].中國外語,2014(05):104-111.
[13]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生態理性特征及其對翻譯研究的啟示[J].中國外語,2011(06):96-99.
[14]胡庚申.翻譯生態vs自然生態:關聯性、類似性、同構性[J].上海翻譯,2010(04):1-5.
[15]胡庚申.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J].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2009,32(02):47-53.
[16]龍佳紅.從邊緣到中心—對譯者地位的思考[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5,18(04):630-633.
[17]祖利軍.全球背景下的生態翻譯[J].中國外語,2007,4(06):89-93.
[18]張麗紅,劉祥清.生態翻譯論對外宣翻譯的啟示[J].中國科技翻譯,2014,27(02):43-46.
[19]祖利軍.翻譯的意義建構模式[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1):111-116.
[20]祖利軍.偏離與翻譯[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2):107-112.
[21]祖利軍.翻譯的意義建構:管道—認知模式[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14,22(01):36-40.
[22]祖利軍,李曉紅.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譯本體論[J].邯鄲學院學報,2007,17(04):99-102.
[作者簡介]王洲(1990-),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碩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6-28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7596(2015)09-0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