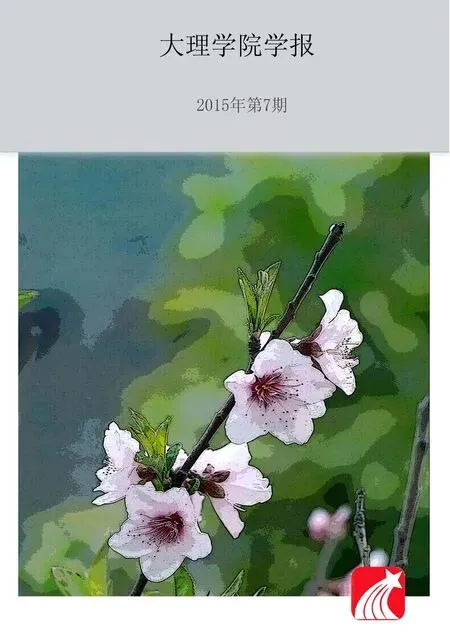“朱”有“小”義考
朱 棟
(鹽城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蘇鹽城 224002)
形聲字由義符和聲符構成,在通常情況下,義符表示該字所記錄的語詞的意義類屬,聲符表示該字所記錄的語詞的讀音。但是,早自宋代的王圣美就已認識到聲符兼有表意的功能,并創立了“右文說”。此項學說雖有不足,但聲符兼表意的事實卻逐漸被后來學者所重視。如聲符字“扁(piān)”獨用有“小”義。《廣韻·仙韻》:“扁,小舟”〔1〕。《漢書·貨殖傳》:“乃乘扁舟。”唐李白《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云》:“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相應的,以“扁”為聲符所組構成的形聲字就含有“小”這一義素。如“甂”指小瓦盆。《說文·瓦部》:“甂,似小瓿,大口而卑,用食。從瓦,扁聲”〔2〕118。“”指小車。《字匯·車部》:“ ,小車也。”“褊”本義指衣服狹小。《說文·衣部》:“褊,衣小也。從衣,扁聲”〔2〕296。那么,我們通過分析以“朱”為聲符的形聲字的表義情況,就不難探求出聲符字“朱”的某些意義來。
《說文·木部》:“朱,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2〕172。據此,我們不難看出,許慎將“朱”字歸為指事字,用“一在其中”凸顯“朱”這種樹木的中心為紅色。后人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將“朱”與其他語素組合成詞時,就多采用其“紅色”義。如“朱門”指紅漆大門,舊多借指豪門望族。古時王公貴族的宅院大門多漆成紅色,以示尊貴。唐杜甫的詩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用“朱門”借指當時腐朽的封建貴族。再如“朱丹”指紅色或一種紅色的寶石。《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的詩句:“口含如朱丹。”就是用“朱丹”一詞來描述焦仲卿妻子的唇色之紅潤。
現代的語文工具書對“朱”的解釋多沿襲其“紅色”義。如我們常用的《新華字典》對“朱”的解釋分為兩個義項:“①大紅色。②朱砂,即辰砂,礦物名。化學成分是硫化汞,顏色鮮紅,是提煉汞的重要原料,又可作顏料或藥材”〔3〕。義項①直接解釋“朱”為大紅色;義項②“朱砂”,紅色礦物質,紅色為其顯著特征。據此,我們不難看出,“朱”表“紅色”義已廣為接受。《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等權威辭書對“朱”的解釋也均與“紅色”義相關。但是,經過研究,我們認為“朱”還具有辭書所未收錄的“小”這一義素。具體論述如下。
珠《說文·玉部》:“珠,蚌之陰精。從玉,朱聲”〔2〕13。其本義為蛤蚌因沙粒竄入殼內受到刺激而分泌形成的珍珠。形態為圓形小顆粒,有光澤,可入藥,亦可作裝飾物。可見,“體積小”是“珠”的一個義素。“珠”在與其他語素組合成詞時也含有“小”這一義素,如淚珠、汗珠、露珠等。至于“珠”這一形聲字的意符字“玉”,只能表示“珍珠”屬于玉石珍寶類。
株《說文·木部》:“株,木根也。從木,朱聲”〔2〕118。其本義為露出地面的樹根。如成語“守株待兔”,梁沈約《詠山榴》:“長愿微名隱,無使孤株出。”可見,“株”含有“離地面不高、短小”之義素。“木”作為“株”的意符,只表明“株”和樹木有關。
蛛《說文·黽部》:“鼄,鼅鼄也,從黽,朱聲。蛛,鼄或從蟲”〔2〕285。“蛛”指蜘蛛,其體形相對短小。“蛛”的意符字“蟲”,表示“蜘蛛”屬于昆蟲類,至于“蜘蛛”的其他特性它無法表示。
銖《說文·金部》:“銖,權十分黍之重也。從金,朱聲”〔2〕296。其本義為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單位,一兩的二十四分之一為一銖。漢代一百粒粟的重量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一斤。《禮記·儒行》:“雖分國,如錙銖。”孔穎達疏:“十黍為參,十參為銖,二十四銖為兩。”“銖”這一單位所指重量極小,多喻極微小、精細。如極輕的舞衣叫“銖衣”;生活中說某人特別小氣,對很少的錢或很小的事都特別計較叫“錙銖必較”。“金”作為形聲字“銖”的意符,僅表示“銖”是古代的衡制單位。
侏本義為“侏儒”,指身材矮小的人。《廣雅·釋詁》:“侏儒,短也。”《國語·晉語四》:“侏儒不可使援。”韋昭注:“侏儒,短者,不能抗援。”“侏”的意符“人”,只是表示“侏”所指的意義類屬“人”。
茱《說文》:“茱,茱萸,茮屬。從草,朱聲”〔2〕21。“茱萸”又叫“吳茱萸”,蕓香科。落葉小喬木。植株矮小。意符字“草”,表示“茱萸”屬于植物類。
《說文》:“ ,栙雙也。從竹,朱聲”〔2〕98。《廣雅·四江》曰“栙雙者,帆未張也。”帆未張開則相對小。意符字“竹”,表示“ ”由竹子構成。
鮢《集韻·平虞》:“鮢,魚名。《山海經》:鮢鱬,似蝦無足”〔4〕。《正字通·魚部》:“鮢,魚似蝦無足。《雜俎》:‘負朱魚,每鱗有一點朱。’俗作鮢。”“鮢”即鮢鱬,本義為一種長相似蝦的小魚,鱗上有紅色斑點,所以也稱“負朱魚”。此魚不但體有紅色,而且體形甚小。“鮢”的意符字“魚”,表示“鮢”這一動物屬于魚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以“朱”為聲符的形聲字“珠”“株”“蛛”“銖”“侏”“茱”“ ”“鮢”等均包含“小”這一義素,而這一義素的承擔者均應為其聲符字“朱”,它們的意符字僅表示它們各自所屬的意義范疇。
“右文說”正式提出,始自北宋王圣美。據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載:“王圣美治字學,演其義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皆從木。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之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5〕。“右文說”認為古之漢字右邊聲符皆表義,雖難脫“以偏概全”之嫌,但其有一定合理性。它糾正了長期以來認為形聲字聲符僅表音的偏見,認為形聲字左邊意符僅表示意義類屬,右邊聲符才真正表義。這雖有不妥,但其發現了漢字音義關系之間的一條重要規律。一些形聲字,我們若知道其聲符字的本義或引申義,就可以推斷出該組形聲字所表示的共同義,如“皮”本指人和動植物表面的一層組織,有覆蓋功能,那么以“皮”為聲符的一組形聲字“披、旇、陂、坡、被”等就均有覆蓋義;相反,一些使用同一聲符的形聲字,我們若知道它們的共同義,就可以推斷出它們所采用聲符字的某些意義,前文所論述的一組形聲字“珠、株、蛛、銖、侏、茱、 、鮢”均蘊含小義,所以我們可推斷出它們共同的聲符字“朱”應含有“小”義。
〔1〕陳彭年.廣韻〔M〕.北京:中國書店,1982:119.
〔2〕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3〕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新華字典〔M〕.10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33.
〔4〕丁度.集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01.
〔5〕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