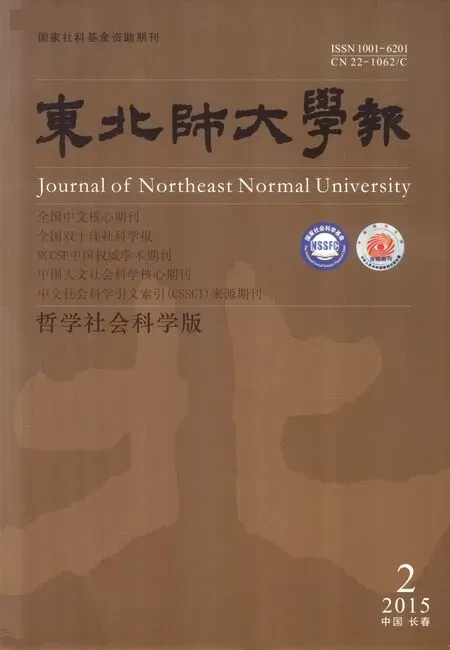從馬克思的兩種世界歷史視野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選擇
禚麗華,孔 揚
(1.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吉林 長春130012;2.空軍航空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系,吉林 長春130022)
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持續升溫和中共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得“唯物史觀與中國問題”成為一大學術熱點。唯物史觀的最高形態是世界史觀;中國問題是世界歷史當中的中國問題。只有透過世界歷史視野,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國的命運。馬克思的世界歷史范疇最初是特指資本擴張使所有民族都被卷入現代化浪潮的現象——世界性的歷史,后來則擴展到對古代社會的研究尤其是俄國公社問題。因此,學術界在提及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時,也將之納入到世界歷史范疇之中[1]。這樣一來,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就分出了古代與現代兩個維度,前者是地域性的世界歷史,特點是生產方式的多樣性;后者是全球性的世界歷史,特點是市場經濟的同一性。這兩大世界歷史視野及其融合,構成了我們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選擇的三把金鑰匙。
一、地域性的世界歷史:破解中國“從何處來”
地域性世界歷史是與現代社會相對的概念,系指在西方取得現代世界的主導地位之前,各個不同地區的國家彼此獨立發展的歷史之總和。需要指明的是,馬克思的原著中并沒有“地域性世界歷史”這一概念,相反,在馬克思嚴格使用“世界歷史”范疇的地方,它指稱的恰恰就是“地域歷史”的反面。我們之所以要確立地域性世界歷史概念,是出于這樣兩個考慮:一是馬克思由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結果的世界史而上溯到對前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地域歷史的研究,因此地域歷史研究已經整合進了世界歷史研究;二是國內外理論界實質上也把馬克思的地域歷史研究(主要為東方社會理論)納入了世界歷史大范疇。因此,為了區別于馬克思的(全球性)世界歷史,我們以“地域性世界歷史”指稱古代各國彼此孤立發展的歷史的總和。地域性世界歷史的特點是文明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正是打破抽象歷史哲學(單一發展模式論)的關鍵證據。馬克思晚年為了研究東方社會問題而不惜中斷《資本論》的寫作,就是要研究各種生產方式的特殊性,從而為找到適合各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奠定基礎。換句話說,不能機械套用西方模式來推測東方各國的歷史形成機制。我國學界特別是教科書當中有一種教條主義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史和西方一樣,不過是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再到封建社會的一般演化。這就把中國“從何處來”的特殊性給遮蔽了,也就把我們的民族基因給遮蔽了。為了正本清源,必須認真研究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歷史思想,具體來說就是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從而解開中國社會的秘密。
20世紀80年代張明敏的一句歌詞極富深意:“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中國心究竟從何而來?它為什么不同于印度心、美國心?可以說,不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就解不開這個“心結”。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屬于亞洲各國的傳統生產方式,馬克思主要研究了俄國,次要研究了印度和中國;但是在關于俄國的系統研究中,卻提示出研究印度和中國問題的寶貴方法論。比如《給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三稿》寫道:“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壟溝痕跡的小塊土地組成的棋盤狀耕地,那你就不必懷疑,這就是已經消失的農業公社的地產!”[2]今天我國到處都可見此種耕地,這就是中國曾經存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重要證據。馬克思這樣揭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質:“東方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甚至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3]根據馬克思的提示,我們可以將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概括為高度中央集權下土地國有的村社經濟。國家限制地主經濟的惡性膨脹,牢牢掌控土地的最終所有權和小農的人身自由。這種生產方式的原因和結果就是中國社會基因的秘密。
有三個主要原因,使得中國高度集權、土地國有。一是共同治水:治理長江、黃河與淮河需要龐大的社會合力,這促使中華民族逐漸走向集權,因為任何地方和個人勢力都沒這個能力。二是抵抗侵擾: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復侵擾,必須集中全國的人、物、財力,這也使中央集權不斷加強。三是地理封閉:太平洋、云貴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北大沙漠等天然屏障,造成中國長期閉關自守,最終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印度和俄國的獨特發展道路[4]。這種道路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從生存特點來看,與其他文明相比,中國心最強調整體至上,唯家唯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印度村民面對侵略無動于衷,中國人則用血肉筑起新的長城。從政治特點來看,中國政治家國同構,政治關系家庭化,家庭關系政治化。“天地君親師”是一塊排位,百姓叫官員“父母(官)”,官員叫百姓“子民”,用溫情脈脈的宗法倫理來統治天下,也導致裙帶關系嚴重。從文化特點來看,中國心最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喜歡因循守舊,反對個人獨立。“狠斗私字一閃念”“出頭椽子先爛”“棒打出頭鳥”“殺雞給猴看”。所以黑格爾才說,中國的人與人之間沒有一種個人的權利[5]。可見,“我的中國心”從亞細亞生產方式而來。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既是創造中華文明的基因,又使社會長期停滯不前——中國是被拖著進入現代世界的。如果說,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歷史回答了中國從何處來的問題,那么,他的全球性世界歷史則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二、全球性的世界歷史:破解中國“向何處去”
全球性世界歷史是與地域歷史相對的概念,指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擴張使得全世界都被卷入市場經濟的發展軌跡,此后再也沒有哪一種文明形態能夠孤立發展。它的特點是文明同一性,確切說來是市場經濟文明的同一性。馬克思指出,資本擴張“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6]277。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性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1840年的鴉片戰爭,從中國角度來看是遭受侵略,從世界歷史角度來看就是資本擴張。為了救亡圖存,中國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三次高潮:學技術的洋務運動,學制度的辛亥革命和學文化的新文化運動。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先是追隨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事實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跨域,而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則無法跨越。鄧小平以極大的政治勇氣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是中國五千年來所發生的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因為它的本質是人的發展形態的飛躍,也就是從“人的依賴”形態,向“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7]的飛躍。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理解資本的邏輯。
首先,資本具有文明性,優越于自然經濟,這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市場經濟。在自然經濟當中,人的存在狀態是人對人的依賴。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為土地掌握在家長手里。土地是不動產,人依賴于不動產,也就跟著靜止,被限制在一塊狹小的空間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是變了形的自然經濟,其依賴關系表現為人對單位的全面依賴。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取得了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獨立性。“物”就是貨幣,貨幣是最高層級的動產,通過動產的機動人就取得了機動性、獨立性。以上是從人的形態角度去看;從財富創造角度來看,市場經濟也遠勝于自然經濟。自然經濟是自給自足,因此生產規模不怎么擴大,“家有房屋千萬座,睡覺只需三尺寬。”而在市場經濟當中,生產物品不是要其使用價值而是要其交換價值,是向廣闊的消費方而生產,這就打破了自給自足對生產力的狹隘限制。《共產黨宣言》寫道:“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6]277市場經濟像魔術一樣創造財富,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才談得上未來社會人的自由個性,否則所謂社會主義將是空中樓閣。這就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市場經濟。
其次,資本具有盲目性,依賴于政治引導,這決定了中國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從馬克思的全球性世界歷史理論來看,這根源于對資本的揚棄要求。資本的出發點是利潤最大化,為此它不斷擴大生產能力,但利潤實現卻依賴于社會的購買能力。2007年以來,美國的次貸危機蔓延到全球。這場危機表面看來跟馬克思所揭示的生產危機不一樣,是由金融導致的。但究其實質,信用卡泛濫的原因仍是消費力不足,商品過剩。所以說到底它還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還是私有制與社會化對抗的危機,還是資本盲目運動的危機[8]。社會主義中國必須以強有力的宏觀調控來限制資本的盲目性。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證券業的監管,云南綠大地等造假案被嚴肅處理。這是其一。其二,資本造成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這更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社會主義的本質,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任由資本的馬太效應擴大,那么改革開放的成果就無法惠及十三億人,就跟共同富裕的目標南轅北轍。因此,正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再次強調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毫不動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三、兩種世界歷史視野的融合:探求中國道路選擇的辯證法
地域性世界歷史的特點是文明多樣性,各國有各國的發展道路;全球性世界歷史的特點是文明同一性,所有國家都必須經歷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兩種世界歷史視野的融合,也就是堅持文明多樣性與同一性的統一,對我們來說,就是堅持本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統一。這就是中國道路選擇的辯證法。從馬克思的兩種世界歷史視野出發,我們引申出關于如何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以下思考。
一要在理論根基處防止兩種思想傾向。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9]防止“封閉僵化”與“改旗易幟”兩種思想傾向。朝鮮、中國和俄羅斯,都曾經是蘇聯模式國家。冷戰結束后,三個國家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朝鮮固守“封閉僵化”的教條,我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俄羅斯則向右轉。事實勝于雄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就是對道路選擇正確性的最好證明。但是,發展中的矛盾又使這兩種思想傾向一直伴隨著我們,防止這兩種思想傾向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任重道遠。那么,如何在理論根基處防止這兩種傾向呢?馬克思的兩種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科學依據。
首先,全球性世界歷史視野是防止“封閉僵化”的思想武器。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也不斷增大,再加上體制不健全,問題富豪層出不窮,弱勢群體心懷不滿。一方面是仇富心理泛濫,仇恨富人;一方面是愁窮心理泛濫,為貧窮而發愁。這就為封閉僵化的“左”傾思想提供了社會土壤,這種思想認為,改革開放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是“打著左燈向右轉”,搞“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因此,他們懷念毛澤東時代,幻想回到平均主義。如何看待這種思潮呢?我們認為,必須堅定地站在全球性世界歷史視野,防止封閉僵化思想的干擾。前面提到,全球性世界歷史理論揭示了人類發展的最一般規律,那就是任何國家都必須經歷從自然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無一例外。列寧曾經想搞例外,從戰時共產主義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但他很快就意識到犯了錯誤,于是轉而實行新經濟;斯大林曾經想搞例外,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也取得了寶貴成果,但隨著弊端越積越多,蘇共不得不改革,最后以失敗告終;毛澤東曾經想搞例外,“一大二公”“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反倒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朝鮮還想搞例外,它是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的“活化石”,體制僵硬,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改善。所以說,幻想跳過市場經濟而創造一個高于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根本不可能[10]。這就是馬克思全球性世界歷史思想給予我們的最大啟示。歷史不能開倒車,我們要正確看待社會矛盾,一定要鉆研好全球性世界歷史理論,“防止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其次,地域性世界歷史視野是防止“改旗易幟”的思想武器。與封閉僵化的思想不同,還有一種思潮向右轉,嫌中國太保守,他們主張接受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打破枷鎖搞改革”,甚至要求中國再給西方“當三百年殖民地”。左的思潮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市場經濟造成的,而右的思潮則認為是社會主義造成的。如何批判右的思潮呢?有兩種批判的角度。第一種角度是從外部威脅性來看,也就是把右的思潮視為境內外敵對分子對社會主義政權的顛覆。這種批判角度的特點是單純防御。第二種角度是從內部合法性來看,也就是我們理直氣壯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合乎歷史規律的正確選擇。這種批判角度的特點是以攻為守。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歷史理論,揭示了文明的多樣性,也就為我們從第二種角度批判右的思潮提供了武器。中國當然應該走屬于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盲目跟著西方走。其實,所謂的西方模式也不是絕對的,比如英法屬于早發內生型市場經濟,日俄屬于晚發外生型市場經濟;政治上,真正實行三權分立的西方國家也只有美國,歐洲各國則多采取立法與行政權一體化的政體。中國由于特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了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是以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作為文化基礎的。同時,社會主義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將亞細亞的整體主義優勢發揮到市場經濟中,從而有力地控制資本,既發揮資本的文明性,又節制資本的盲目性,最終為人民服務。右的實質就是全盤西化,放棄民族特色,它只承認歐美的市場經濟模式,不承認其他模式,覺得“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由于西方國家在發達程度上遠高于我們,因此右的觀點也很有市場,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威脅很大。所以,我們也一定要鉆研好地域性世界歷史理論,“防止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二要在實踐根基處把握民族命運。通過探討地域性世界歷史,我們能夠初步理解中華民族的性格基因。通過探討全球性世界歷史,我們能夠初步理解市場經濟的必然選擇。兩種世界歷史視野的融合,要求我們實現民族性格與市場經濟的有機互動。
首先,要從地域性世界歷史視野中得出這樣的啟示:利用民族性格中的積極因素,發展市場經濟。前面分析過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塑造了中華民族整體至上的性格基因。這種民族性格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有利于節制資本的無政府狀態,有利于“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握手。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11]。他所說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實際上是建立在整體主義民族性格基礎上的。三峽工程、青藏鐵路,這些巨大工程的順利實施,都是社會主義的優勢,也就是整體主義民族性格的優勢。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反思個人主義泛濫的危害,同時也就給予中國的整體主義以很大期望,希望以中國文化來挽救西方的沒落。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期,需要整體主義來統籌全局;在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面前,需要整體主義來提高建設效率;在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面前,需要整體主義來提供向心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性格是我們的天然優勢,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優勢。充分利用民族性格來發展市場經濟,我們就有望創造出超越資本主義的更高文明。
其次,要從全球性世界歷史視野中得出這樣的啟示:利用市場經濟,改造民族性格中的消極因素。性格決定命運,性格的辯證法就是命運的辯證法。中華民族的性格,既使我們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又束縛了我們步入現代世界的腳步。我國獨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造成了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權力要集中,就必須依靠龐大的國家機器,就要養大批軍隊和官僚。官僚由上級任命而不是民主選舉產生,因此他們對上不對下,結果就是權力缺乏監督,腐敗嚴重[12]。亞細亞傳統對中國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我們時時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中國社會轉型難,難就難在亞細亞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特別是在政治思想領域。鄧小平總結了政治領域封建殘余的四個表現:第一是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第二是權力過分集中,實際辦事的大多數人反而倒無權決策;第三是家長制作風,下級惟命是從;第四是宗法觀念,裙帶關系[13]。胡錦濤、習近平同樣總結了四大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這些危險,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無一不是亞細亞傳統的消極產物。不過,我們現在也具備了魯迅時代所不具備的、改造民族劣根性的條件,那就是市場經濟。不妨從商品、貨幣、資本和全球化這四大市場經濟因素的作用來看。其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其等價交換原則能夠有力促進市民平等觀念的培育。在我國,商品交換越不發達的地區,封建特權思想越濃,反言之,商品交換越發達,平等觀念越強。其二,貨幣代替土地等不動產成為人的生存基礎,能夠有力促進獨立意識的形成。市場經濟中的人具有以物的依賴為基礎的獨立性,而不再依賴于特定的人或者單位。經濟獨立,人格隨之獨立。其三,資本增值的沖動刺激了人的創造力和致富欲,而資本競爭的壓力又克制了人的懶惰和小富即安。這是醫治中國傳統因循守舊心理的一劑猛藥。其四,全球化為人的普遍交往提供了條件。馬克思認為,孤立地區的人只是偶性的人[6]122,無法“開眼看世界”,也就跟不上時代。而世界歷史當中的人才是全面的人,因為他把一切文明成果作為自己的發展前提。我國的市場經濟才剛剛起步,它對人的塑造效果還只是初步顯現,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自覺自為地利用市場經濟來改造民族性格。
[1] 豐子義.走向現實的社會歷史哲學——馬克思社會歷史理論的當代價值[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380.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2.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80.
[4] 孫承叔.真正的馬克思——《資本論》三大手稿的當代意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8-309.
[5]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130.
[6] 馬 克思恩格斯 選 集:第1 卷[M].北 京:人民 出 版社,1995.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7.
[8] 孔揚,姜大云.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目的論的真實關系——從馬克思對“異化”范疇的三次運用來看[J].長白學刊,2013(1):31-36.
[9]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八大報告[N].人民日報,2012-11-09(001).
[10] 賈麗民.反思達致真理:馬克思《資本論》的思維方式意涵[J].學習與實踐,2013(4):120-126.
[11]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40.
[12] 李新,趙連章.當代中國民主建設的政治生態環境論析[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52-57.
[13] 高飛.馬克思資本批判的邏輯主線[J].長白學刊,2014(2):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