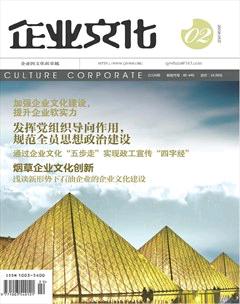對中國式家族企業機制以及變革方向的探討
劉森林
摘 要:通過對比美國和日本典型家族企業,指出了我國家族企業傳承機制上的問題,提出了對于中國式家族企業繼承機制設計上需要注意的問題,并進行了簡要的探討。
關鍵詞:家族企業;繼承機制
家族企業是企業的一種組織形態,它既古老又短暫。從企業形態角度來說,家族企業的歷史非常悠久。而從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說,它又非常短暫。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是家族企業往往都“富不過三代”。從這點來說,中國式家族企業體現的更為明顯。
家族企業是一種相當古老的企業形式,在美國已經誕生了將近400年,并且迄今為止依舊對美國經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國歷史上也有許多赫赫有名的大型家族掌控著美國的各個經濟命脈,如洛克菲勒家族,沃爾頓家族,摩根家族等。而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翻天覆地的增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取代了計劃經濟,民營企業發展異常迅猛,成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推動力量。由于歷史、文化、經濟環境等各個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民營企業絕大多數是家族制企業。在當前中國,以家族模式來控制治理企業的方式在民營經濟體中依然會在可預見的將來占主流地位。如今,中國的大部分家族企業已經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開始的企業創始人逐漸開始或已經進入退休年齡。很多家族企業開始或即將面臨傳承與換代。因此,對家族企業問題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很多人都有一個很直觀的感覺,那就是進入到新千年以來,報紙雜志等媒體上對于民營企業創始人退休或者歸隱幕后、新人上位的報道逐漸多了起來,我國似乎已經開始進入了家族企業換代非常頻繁的時期。事實也確實如此。
既然我國現存的繼承機制或多或少的有著這樣那樣的不足,尚沒有形成一套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繼承機制,那我們是否可以直接將歐美日已經發展的非常成熟的家族企業的傳承模式直接拿到中國來呢?想要得出結論,先來看一下發達國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和日本的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
美國的家族企業發展歷史十分悠久,比如著名的杜邦公司創建于1802年,距今已有212年的歷史了。而成立于1903年的福特公司在上百年的歷史中,經歷了一代又一代的家族傳承。顯而易見的是,美國的家族企業相比那些非家族企業競爭對手更具競爭力。美國同樣是家族內部任用與聘用職業經理人相結合的模式,同樣是以家族內部傳承為主。所不同的是,美國的大型家族企業非常注意接班人的培養,都會拿出專門的經費甚至在董事會設立“高官人員聘用委員會”專門負責對高層管理人員的挑選和培養。同時,美國的一些家族企業甚至會聘請專業公司參與對接班人的培養。讓專業公司幫助挑選出有潛力的接班人,制定培養路徑,同時物色外部機構的候選人作為比較標桿或者補充。
實際上,美國家族企業比較傾向于在公司持續穩定的發展時,從內部遴選接班人,而當公司處于危機之中時,則從外部挑選職業經理人來擔任CEO。據統計:在美國,通過聘任家族外職業經理人來擔任企業CEO的家族企業的比例并不算高。那么,這一途徑獲得的滿意度又是什么樣的情況呢?以下的一組數據或許可以回答這一問題。在通過雇傭家族外職業經理人擔任CEO的家族企業中,有31%的人認為這一途徑極成功,有40%的人則認為非常成功,而認為這一途徑一般或不成功的比例僅為29%。也就是說滿意程度高達71%。
再來看一下日本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眾所周知,日本人對自己工作的企業有一種天然的忠誠與休戚與共的精神,這在家族企業里也不例外。實際上,對于日本的家族企業而言,企業就是家,家就是企業。在日本,創業家族往往掌握著家族企業的所有權,企業資產和創業家族的共同資產之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企業的盈虧完全由家族成員共同承擔,依照的是非市場原則。在我們看來,日本的家族企業尤其重視家族內的傳承,但他們對于“家”這個概念與中國人并不盡相同。實際上,比起傳統的血緣關系,日本的家族企業對家業的情感更為重視。日本人的家族企業中不僅包括有血緣關系的人,也包括沒有血緣關系的人。在傳承企業時,因為首先考慮的是有利于家業的延續這一點,所以日本的家族企業有可能選擇將企業傳給并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但前提是此人一定要成為家族中的一員,而往往是通過過繼為養子或者招婿入贅這兩條途徑。據統計,日本的家族企業主將繼承權給養子而不是親生兒子的比例高達25%-34%。這樣的關系對于家族企業的發展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例如有“經營之神”之稱的松下幸之助,在1961年選定松下正治作為接班人,而松下正治,本名本田,正是其婿養子。但是在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家族企業的管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日本家族企業的經營權與所有權也逐漸分離,一些家族企業也從外部招來主管家族企業事務的職業經理人“總管”。不過家族業主依然沒有放棄所有權和公司的實際控制權,許多家族立下規矩,不準將股票出售給外人。
中國的家族企業只有三十余年的發展歷史,尚沒有形成成熟完善的繼承機制。因此,以美日為代表的西方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無疑會對我們有著很實際的借鑒意義。然而,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國與日本的家族企業繼承機制并不相同,這種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從文化到經濟體制的差異。美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非常成熟,同時又具有完善的法制,是一個契約型社會,美國的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是建立在信用機制非常完善的基礎上的,美國的家族企業可以放心的把職業經理人作為一個選擇,并且事實證明這種選擇也是確實有作用的。而日本雖然也如同中國一樣受到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影響比較大,不過卻把家的概念擴大了,而不是僅僅局限在血緣關系,這無疑有助于企業選擇更合適的接班人。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由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等的差異,我國的家族企業確實無法照搬西方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我們應該在借鑒他們的成功要素的基礎上,探索出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家族企業繼承機制。
結合上述分析,我們是可以探索出一套在現階段具有普遍適應性的中國家族企業的繼承機制的。而首先應該放棄的,是從外部聘請經理人接班這種傳承模式。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立的時間較短,經濟運行尚缺乏完善的信用制度,這使得家族企業在聘用職業經理人時面臨著職業經理人巨大的道德風險。職業經理人在掌握企業的控制權的同時并沒有企業的所有權,在沒有完善的信用機制的約束下,很容易選擇不忠誠的戰略。家族企業主很難真正對外來的職業經理人產生完全的信任,而這種不被信任感會加大職業經理人背叛企業的可能性。同時,職業經理人本身對企業的情況并不會非常的了解,需要在探索中學習領導這個企業,這個過程不利于企業的發展。再者,外來的職業經理人在工作中很可能遇到來自家族內部其他人的不信任,沒有足夠的威望與業績會使得其在工作中遇到較大的阻力,這同樣不利于企業的發展。況且,雇傭職業經理人本身需要較大的成本,這會對企業帶來不小的成本負擔。綜合以上因素,在現階段,中國的家族企業選擇外聘職業經理人并不是明智的選擇。
既然這樣,中國的家族企業就應該選擇家族內傳承的繼承機制。然而,家族內傳承尤其是“子承父業”同樣具有不少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在傳統的家族內傳承的基礎上,探索出全新的家族企業繼承模式。這種模式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條件:首先,家族應該摒棄“長子繼承制”,而改為從所有有親緣關系的家族內部人士中優中選優。家族企業本身就是又有血緣關系的親族建立起來的企業,當創始人的子女能力出色,能夠擔當管理企業的重任的時候,自然應該被優先作為繼承人。然而,當創始人的子女的能力較為平庸,不足以擔此重任,或者子女本事對接班比較排斥的情況下,就不應該把接班人局限于創始人的子女,而應該在所有有親緣關系的家族內部人士中優中選優。再者,對于不適合接班的創始人子女,應該明確其沒有在家族企業事務中的決策權,最多只擁有參與權,同時分給其股份或者設立特殊基金作為對其補償,以此最大限度的避免家族內部權利的爭斗。其次,如果具有親緣關系的家族內部人士中確實無法找到合適的繼承者,應該從企業內部工作多年的員工中選拔培養接班人。對于內部選拔的員工,應該給予足夠的信任,視為家庭中的一員,同時也要注意指導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