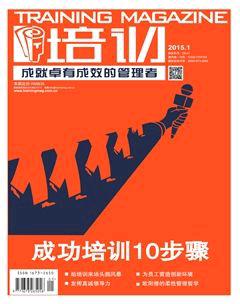情境的力量
章森
涉足培訓行業十余載,上過無數培訓管理類課程,唯有“情境領導”這門課程讓我記憶猶新、感觸最深。從初識課程,到內化開發,再到后期優化完善、實踐應用,我不光收獲了職場技能和思維的提升,還開啟了自身理解生活的新方式。或許這就是培訓管理者職業的特殊性,一門好課能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影響和改變。
領悟理論的真諦
2008年,我在攜程大學擔任培訓主管,在公司對“情境領導”課程的內化開發與廣泛推廣中,我正式開始了對課程的深入學習,并且逐漸領悟到情境領導的精髓:領導者應隨組織環境及個體變換改變領導風格及管理方式;領導者的行為只有與被領導者的準備程度相適應時,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而如赫塞所言:“情境領導并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模型”。“情境領導”之所以優秀并能廣泛普及,正是由于其模型帶給我們的兩個“幫助”。
幫助學員理解和記憶
情境領導模型圖能清晰地定位員工的分類和階段,以及需采取的管理行為。更難能可貴的是,它將領導理論的所有變量都集中體現在一個模型圖上,便于學員理解與宏觀把握,而這在其他同類課程中均很少見。因此,很多學員在課程結束之后,都會習慣性地將模型圖打印出來貼在自己的工位附近,時刻指導并規范自己的領導行為。
幫助講師控制演繹過程
講授領導力課程時,我們通常會先尋找一個邏輯,而情境領導理論本身就包含了員工發展階段的邏輯,符合學員的認知過程,也充分體現出情境領導理論的核心——情境。因此,每到課程開發時,我都會先確定課程邏輯和模型,再定位課程的內容范圍,力爭做到課程的模型簡單、邏輯清晰。
熟練掌握理論知識后,我便結合業內通用課程內容以及公司的實際案例情景,成功撰寫出課程的標準課件和講師手冊。同時,基于課件的使用情況,我還在講師手冊中持續對每一步教學細節進行備注,逐漸形成了標準完善的課程包。這些嘗試都為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并掌握情境領導的真諦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實踐中檢驗提升
基于以上積累,2010年,當我在貝塔斯曼集團擔任培訓經理時,我成功應用“情境領導”理論完成了一大挑戰:在沒有任何外部資源支持的情況下,自主對整個服務中心的一線服務人員進行測評,然后將人才發展建議提供給直線經理。
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我思考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讓測評指導管理行為?什么對管理行為最具指導意義?當時,腦子里首先閃現的便是情境領導。于是,通過工具分析和比較,我制定出了項目的解決方案(見圖表2)。
首先,基于情境領導模型,確定出能力和意愿兩大維度,再與運營團隊管理者通過團隊共創的方法確定通用崗位任務下的能力與意愿因素(見圖表3)。
其次,整理并輸出基于崗位任務的評估表,根據共創過程中研討出的各因素的重要程度,進行權重調整。
第三,通過360度反饋,讓團隊成員、管理人員、質量團隊基于評估表輸入員工的能力與意愿兩個維度下各個因素的評估值(見圖表4);基于各個反饋角度的權重,得出每個員工在通用崗位任務下的情境領導參考值。
最后,通過群體分析和團隊分析,給管理者提供從宏觀到微觀的團隊解讀和管理意見。因為清晰地呈現出團隊的現狀及管理行為的優化方向,這一方案最終得到了運營團隊和領導的充分肯定。
情境領導的兩個維度“能力”和“意愿”具有普遍價值。因此,在實踐中,我最大的創新就是基于公司實際崗位的典型情境將兩大維度進行細節分解,并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將模型延伸,把“評價依據”加入領導過程模型,形成可通過測評進行評價的過程指導。
因此,讓模型真正具有模型的價值,是成功管理者的一種思維。在設計測評內容以及對管理行為輔導講授的過程中,我又一次系統地更新了自己對“情境領導”的理解,并將之內化為自己開發項目時的獨門工具。對我而言,這是一次學習的超越,是從“知”到“行”,從“智”到“慧”的轉變。
“情境領導”課程就如同一根線,為我串起了領導力相關理論的一顆顆珍珠——它們或許是精彩的理論,或許是實用的管理工具……但都為我之后繼續進行內訓課程的開發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思維提升 職場“三控”
除了專業知識技能的提升,“情境領導”課程還讓我養成了三個典型的職場習慣,甚至成為一種個人偏好。
矩陣控
情境領導模型體現的是一種矩陣,“兩維度、四分法”的分析思維作為一種有效的結構化思維,在分析問題和定位策略的過程中非常有用。因此,不論是分析問題、做方案,還是在總結觀點時,我都習慣性地將矩陣思維作為輸出工具。
曾有一位同事,總是向我抱怨領導管得太緊。我的第一反應便是給他畫了一個矩陣(見圖表5)并分析道:主管管得緊是你所處的客觀環境,關鍵還是看自己是否主動,積極主動的人能在這樣的管理風格下迅速成長從而達到職業化目標,否則就會加快自身的職場退步。
我也經常用這一方法進行自我剖析。作為培訓管理者,我常常思考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此時,我會為自己建一個矩陣(見圖表6),從“精通培訓”和“理解業務”兩個維度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培訓管理者都是培訓或咨詢專家,要想成為公司的戰略伙伴,我就必須在業務理解方面多花精力。
正因此,公司有人給我取了外號叫“矩陣章”。我也經常被問到“矩陣控”的習慣是如何養成的,我會告訴他們:這是“情境領導”課程的學習和開發帶給我的益處。如果一門課程能夠讓學習和借鑒它的人形成習慣范式,毫無疑問,這門課程是偉大的。
周期控
情境領導模型的另一思想精髓就是強調“基于員工的發展周期”,這個思維模式也帶給我極大的啟發。在課程學習的過程中,我會聯想到:企業有哪些周期規律?于是,我系統學習了企業生命周期、產品生命周期、團隊發展周期、職業發展生命周期等理論。最終,我發現這些理論的本質都是相通的,即基于時間軸的一根波峰曲線,有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endprint
因此,“情境領導”課程為我打開了一扇門:不論遇到什么問題,我都會去主動提煉發展周期。比如,在開發公司培訓體系時,我首先會思考公司處于發展周期的哪一階段,員工又處于其自身發展周期的哪一階段,在兩個周期中找到平衡點是培訓體系的基調;在推廣項目管理體系時,我首先會去盤點公司中各個項目管理團隊所管理的項目都有怎么樣的周期,項目管理的方法論在公司中處于哪一周期階段,然后再基于周期特點去做策略定位。
情境控
作為權變理論的一種經典模型,情境領導模型如同它的名字,強調管理的“情境”,要因時、因事、因人制宜。在課程開發的過程中,特別是技巧類培訓,我都會先界定“情境”,明確該技能在什么樣的情境下可用。同時,我也最喜歡用情境來開發任務導向的課程,明確該任務有哪些情境,每一情境下,我們應該如何去做,為何要這樣做。
在工作中,我已不自覺地養成了習慣:不論何事,我都不喜歡說得過于絕對。在與他人交流時,我都習慣性帶上一句:看情境。
成為生活的情境領導者
“情境領導”把“情境”一詞帶到了管理中,也帶到我的工作和生活當中。因此,不論是培訓,還是生活,我們都需要“情境的力量”。
在與好友閑聊時,我經常建議他們去學習“情境領導”課程,因為任何技能的應用都是相通的。比如,在輔導孩子功課這一問題上,我的觀點是:應先診斷孩子是否有學習的意愿,再判斷其是否具備相關能力,不同情況需不同的輔導策略,同時教育方法和風格也會有所差異。因為每個孩子的學習情境不同。
甚至在看書、看電視劇時,我都習慣性地用“情境領導”的方法進行解讀。閱讀《易經》時,我發現其權變思想與“情境領導”的一致性。在看《三國演義》“揮淚斬馬謖”一集時,我認為諸葛亮不是一個情境領導者。馬謖應屬于“沒能力、有意愿或不安”的下屬。此時,諸葛亮應視情形對馬謖做出“逐漸降低工作行為”的舉措;然后在“增加關系行為”的培養措施下調整自己的領導行為,告知馬謖應該改進的地方;最后,通過逐步增加馬謖的工作能力使其擔當大任。若能按此法來領導馬謖,則馬謖可能也不會落得被斬的悲慘結局。
在生活中,我也經常思考: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快樂。根據情境領導“能力”和“意愿”兩個緯度,我將快樂也分為兩大維度:物質訴求和精神訴求,在人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我們的訴求也各不相同。因此,達到一定境界或是“情境”后,我們就必須給自己找一個興趣、一份信仰,甚至是一個精神上的依靠來實現自我、感受快樂……這些都是情境領導帶給我的啟發。
遇見一門課程,結緣一套理論,打開一扇知識的大門,在實踐中不斷改變自己,情境領導課程帶給我的不僅是理論與知識,更多的是對生活和人生的思考。相信這也是很多培訓管理從業者的快樂所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