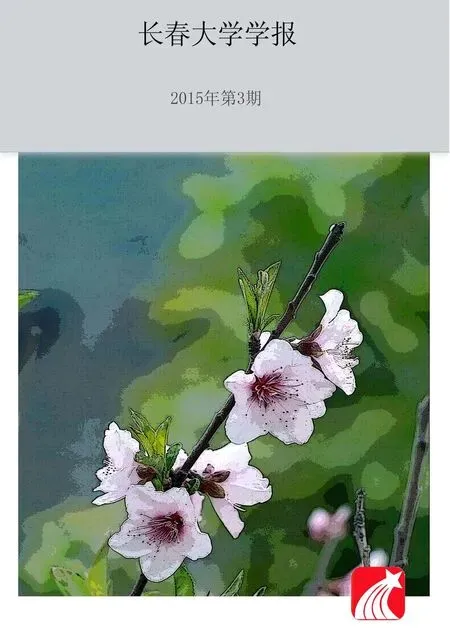——基于2011-2013 年滬市橫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機構投資者對股價波動率的影響研究
童元松,王光偉
(1.蘇州大學 商學院,江蘇 蘇州215021;2.無錫市廣播電視大學 經濟管理系,江蘇 無錫 214021)
0 引言
近10 年來,我國股市大起大落,遠遠大于歐美國家股市的波動程度,上證綜合指數從2005 年到2007 年10 月上漲了6 倍多,高達6124 點;此后僅1 年在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的雙重影響下大跌73%;之后6 年多一路震蕩下行,至2014年6 月末收盤為2048 點,然后上漲至10 月末2420點。從單個股票的表現來看,股價的日內波動、日間波動有時波瀾不驚,有時大漲大跌。股價波動如此劇烈自然與多重因素有關,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很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
機構投資者往往能提高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并影響到股市的穩定。我國的專業機構投資者包括投資基金、QFII、保險資金、社保基金、自營券商和資產管理機構等等。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年鑒(2014 卷)顯示,我國專業機構在2013 年末持有滬市股票19817.31 億元,占滬市總市值的14.58%,其中投資基金持股市值6176.54 億元,占比為4.54%。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對股價波動率有多大程度的影響?上市公司的業績和流通市值是否也會影響股價波動?探討這些問題有利于進一步認清機構投資者的作用與影響,有利于國家制定促進機構投資者發展的相關政策,從而更有效地對股市加以監督管理。
1 相關文獻回顧
關于機構投資者對股市波動率的影響,不同研究者從不同機構持股及其變化等角度展開了分析。
1.1 機構投資者持股減弱了股市的波動性
Lipson and Puckett(2007)認為,機構投資者在市場下跌時增持而在上升時減持股票減弱了股市的波動性[1]。周學農、彭丹(2007)實證研究發現,在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后,股指收益率波動減小,波動的平穩性增強,波動的杠桿效應減弱,這表明機構投資者能夠有效地降低股市的波動性[2]。楊竹清(2012)基于基金與股價的關系視角研究發現,證券投資基金持股與股價同步性明顯負相關,比較而言合資基金更能降低股價同步性[3]。這證明基金持股增強了市場的穩定性,避免了單邊上漲或者下跌而造成股票波動過大。
1.2 機構投資者增強了股市的波動性
Gompers 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數量和持股結構的變化,1980-1996 年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數量翻了一番,增加持股的大公司股票價格上漲了將近50%,這為同期小公司股票溢價的減少提供了一種解釋[4]。Sias(2006)研究發現,機構持股變化越大,股票價格波動越劇烈[5]。不少國家的股市波動率明顯受到機構投資者各種相關行為的影響。姚頤、劉志遠(2007),肖欣榮(2009)對基金重倉股檢驗發現,無論基金的投資風格如何,其持股都高度集中,而且高度相似,因此加大了股票的波動性[6-7]。然而,重倉股難以代表市場的整體情況。胡援成、胡喬(2009)實證研究發現,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持倉比例的變化在不同時期對股票價格波動的影響呈現不同的正負效應,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負效應更為明顯,對股價推波助瀾[8]。鄒宇帥、田存志(2010)研究發現,基金持股增加,股價波動未必降低,有時甚至會加劇波動;基金持股變化會加大股價的異常收益率[9]。這些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基金尚未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朱偉驊、廖士光(2012)研究發現,基金買入越多對股價的波動率沖擊越明顯[10]。該研究分析了基金行為對股市的流動性、波動性等多方面的影響。
1.3 機構投資者對股市波動性存在差異性影響
區分不同市場狀態和不同機構投資者而展開的研究將更為細化。Sushil Bikhchandani(2001)研究了機構投資者對股市波動性影響的非對稱性,結論表明機構投資者在牛市期間買入股票比賣出股票能引起股價更大幅度的波動;相反,機構投資者在熊市期間賣出股票則導致股價更大波動[11]。韓金紅(2012)實證分析表明,在股市上升階段機構整體持股加速了市場波動,而在其他階段則穩定了市場。比較后發現,在上升期基金加速了市場波動,而保險、信托公司持股則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在下降期保險、非金融公司持股加劇了市場波動,而基金的作用相反[12]。陳軍、陸江川(2013)實證分析發現,我國機構投資者持股加劇了股市波動,而且在牛市比熊市表現得更加顯著,在各類機構中僅有保險公司起到了穩定股市的作用[13]。魏立佳(2013)研究發現,偏股、平衡混合型基金凈值占股市流通市值與股市波動性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負相關關系,而偏債混合型基金凈值與股市波動性存在著正相關關系[14]。他還對不同類型的基金對股市波動的差異性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有利于這方面研究的細化和深入。
總之,上述研究大多以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機構代表,其結論難免以偏概全,而且所選取的解釋變量除了機構持股比例外,較少涉及上市公司的規模與業績。本文將從2011-2013 年橫截面角度,選取滬市幾乎全部股票作為樣本,以所有專業機構持股量、上市公司規模與業績為解釋變量展開研究,以檢驗機構投資者整體對股價波動率的影響。
2 機構投資者影響股市波動率的實證分析
2.1 研究設計
選取2011-2013 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全部A 股作為研究樣本,剔除沒有相關統計數據的個別股票,剔除凈資產為負數的股票,3 年分別獲得880、941 和940 個樣本資料。從多個角度考察股市的波動性狀況,作為被解釋變量的指標包括:日內波動率、超額波動率和收益波動率;解釋變量主要從專業機構的持股、上市公司的規模和業績3 個方面考察,選取的代理指標分別是機構持股比例、個股流通市值和每股凈資產。
2.1.1 被解釋變量方面
一是日內波動率,即日內每5 分鐘的相對波動率,公式為:
二是超額波動率,即衡量由噪音交易、交易機制等因素導致的臨時波動性的近似指標。超額波動率等于日間波動率和日內波動率的差額的絕對值。公式為:
三是收益波動率RR_Volatity,即日內5 分鐘內收益率標準差。收益波動率越大,價格波動越大。
2.1.2 解釋變量方面
專業機構投資者年末的持股比例代表了其對個股的投資程度,是其是否看好該股票的最有說服力的指標。機構大量或者少量持有某個股票必然對其股價波動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若這種影響在市場中對其他投資者起到了示范效應,則其影響力更為明顯。
上市公司的規模以其流通市值為代表,隨著股改的股票上市,流通股的比例已經大幅提高,流通股的市值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股價的波動程度。至于非流通股份,不是普通投資者所能交易的對象,因此不列為變量之一。
每股凈資產(元/股)代表上市公司的業績及多年來的發展程度,其對股價波動率很可能存在相應的影響。但是,當年的業績對股價波動率也可能有一定影響,由于當年每股收益是每股凈資產的一個很小部分,因此可依據每股收益把股票分為三類:績優股、業績一般股和虧損股。在2011-2013 年盈利的股票中,以每年接近中位數為界,按每股收益分為績優股和業績一般股。為考察不同收益股票波動率的差異,設計虛擬變量D1,當每股收益≥M 元時,代表績優股,其他情況下D1=0;M 在3 年中取值分別為0.30、0.28 和0.26。設計虛擬變量D2,當每股收益<0 元時,代表虧損股,3 年中分別有76、109和84 個樣本,其他情況下D2=0。
2.2 提出假設
首先,若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較高,股權相對較為集中,機構買賣數量較大,股票走勢相對活躍,股價波動率可能較大。相對而言,多數機構基于交易成本考慮,不會過于頻繁地短線操作,因此在股價下跌以及小幅震蕩時,機構雖說難以阻擋下跌趨勢,但至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緩跌勢,機構的持股有可能起到穩定股市的作用。但是若在下跌趨勢末期,機構投資者可能會采取負反饋策略,增加交易量和持股量,同時對其他投資者有一定的引導作用,并吸引他們跟風買入,相應的股票交投活躍,有可能使股價波動率升高。
假設1 在不同市場環境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市場穩定性所起的作用不同。
其次,股票流通股份的數量越多,流通市值越大,越不易受到莊家操縱,無論是上漲還是下跌同樣的幅度,比起市值小的股票均對應了更大的交易量,漲跌更不容易實現,股價波動率較小。但是,隨著機構投資者的快速發展及其投資能力的增強,以及不同年份股市行情的活躍度不同,流通市值較大的股票的股價波動率也未必較小。如圖1 所示,2013 年流通市值與日內、超額波動率基本呈正相關關系,但與收益波動率則略顯負相關,不過在整體上變化幅度相對較小。
假設2 個股流通市值越大,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越大,股市收益波動率越小。

圖1 2013 年按流通市值分組的滬市股價波動率 (單位:基點)
再次,上市公司業績越好,越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特別是中長線的理性投資者,該類股票交易相對活躍,交易量較大,因此對價格沖擊較小,買賣價差較小,波動率較低。相反,對于虧損股,理性投資者關注度較低,交易既可能因為無人關注而欠活躍,波動率較低,又可能因為受到盲目的、短線的投機者的炒作而大起大落,波動率自然較高。
假設3 每股凈資產越高,股價波動率越低。
假設4 績優股的波動率明顯較低,而虧損股的波動率缺乏確定性方向。
2.3 指標與數據選取及特征描述
機構持股比例指2011-2013 年包括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QFII、保險公司和券商自營及資產管理等專業機構所持上海股票市場A 股的比例合計數。2011-2013 年個股流通市值因數值較大且為了消除異方差現象,取其對數值,數據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統計年鑒2012-2014 卷,各類波動率數據來源于上海證券交易所市場質量報告2012-2014 卷。
由表1 可見數據的統計特征,2011-2013 年股票平均的日內波動率、超額波動率先減后增,收益波動率則持續上升,因此股市波動程度有所擴大;機構持股平均比例持續下降,流通市值略有增加,每股凈資產則持續上升,績優股的比例略有波動,虧損股的比例2012 年占11.58%,2011 年、2013 年則略大于8%,因此整體上股票業績略有提升。

表1 模型中各變量的基本統計描述
2.4 相關性分析
首先,對將建立的多元回歸模型的變量進行相關性檢驗,發現2011-2013 年各變量之間大多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但是系數并不高。以2013年超額波動率為例,由表2 可見,相關系數均小于0.5,這說明了可以用上述指標反映股價波動率的不同角度的原因,同時基本判定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其次,檢驗FR、Lnmv 和Netassets 的方差膨脹因子,VIF 平均值為1.22,明顯較小,而容忍值1/VIF均在0.8 以上,故可以認定幾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可以進行下一步的多元回歸分析。

表2 2013 年影響股價超額波動率的關鍵變量相關系數表
2.5 實證模型
基于上文的理論分析,并充分考慮有關因素的影響,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i=α+β1FR+β2Lnmv+β3Netassets+β4D1+β5D2+ε,Y 為從不同角度定義的股市波動性,i=1、2、3,對應
2.6 實證分析結果
表3 匯報了模型Y1和Y2的回歸估算結果。的Yi 分別代表被解釋變量日內波動率、超額波動率和收益波動率,并按年份(2011-2013)進行回歸分析。FR、Lnmv 和Netassets 以及D1與D2為解釋變量,分別從機構持股比例、個股流通市值、每股凈資產和每股收益的角度分析各自影響的大小。

表3 股價波動率與機構持股等相關因素的多元線性模型的回歸結果
在樣本數均在900 個左右的情況下,模型的6個回歸方程的P 值均是0.0000,說明整體結果高度顯著,方程的調整后R2在5%-27%之間,鑒于影響股價波動率的因素較多,該水平的擬合度尚可,可以接受。根據表4 還可發現,自2011-2013 年方程的擬合度明顯上升,說明機構持股比例等因素的解釋力在逐步增強。
(1)機構持股比例越高,對應2011-2012 年的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越低,在2011 年表現得更為顯著,2012 年在統計上不顯著;但是2013 年卻不同,機構持股比例越高,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越高,機構投資者持股每提高1%,對應的波動率分別提高0.15 和0.04 個基點,且高度顯著。結合上證指數來分析,2011 年滬指大幅下跌21.68%,最高點與最低點之差達933 點,2012 年小漲3.17%,2013 年小幅下跌6.75%。這說明:在大幅下跌市道中以及下跌中繼小陽線情況下,機構投資者縮小了股價波動率,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在大幅下跌之后,隨著成交量的增加,股市震蕩幅度加大,機構投資者持股越多,對應的股價波動率越高,從而使市場活躍度提高,穩定性下降。這證明了假設1。
(2)個股流通市值對各項波動率指標的影響正負不一。對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基本為正向影響,隨著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以及2011-2013 年股市行情漸趨活躍,股價波動率升高,但整體上流通市值的大小對波動率影響不大,這也印證了上文對圖1 的統計分析。不過,下文進行穩健性檢驗時發現,流通市值對收益波動率的影響在3 年中均為負值,即流通市值越大,股市收益波動率越小,且在統計上高度顯著。這證明了假設2。
(3)每股凈資產基本上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股價波動率。以2013 年為例,每股凈資產每提高1 元,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相應下降0.876 和0.567 個基點,因此凈資產的提高明顯有利于股價的穩定。這證明了假設3。
(4)考察兩個虛擬變量,D1=1 對應了當年業績優秀的股票,其對應的股價波動率全為負值,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于1%的P 值水平上高度顯著,這說明績優股的市場走勢較為穩健;D2=1 對應了當年虧損的股票,其股價波動率沒有固定方向,且在統計上基本不顯著,這也印證了績優股的顯著性。由此證明了假設4。
2.7 穩健性檢驗
首先,以收益波動率代表股價的波動程度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絕大多數變量的方向和顯著程度與上述對應年份的方程基本一致,而且3 個方程的整體解釋力除2013 年略低外,2011 年和2012 年的調整后R2分別為18.2%和32.9%,略高于上述方程,表明以收益波動率代表股價波動程度也是合適的。其中,2012 年的回歸方程為:
RR_Volatity_2012=55.08-0.01FR-2.24Lnmv-0.37 Netassets-1.56D1+0.81D2+ε。
其次,以上市公司總市值代替上述模型的流通市值,以每股營業利潤代替每股收益,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后得出的結論與上文沒有本質區別。基于文章篇幅所限,不再列出回歸結果。總之,上述模型是穩健的,結論可靠。
3 結論及建議
3.1 結論
(1)機構持股比例越高,從大跌到微漲的2011-2012 年的股價波動率越低,震蕩小跌的2013 年則相反,說明在不同市場環境下機構投資者持股對市場穩定性所起的作用不同。
(2)隨著機構投資者的壯大以及股市行情漸趨活躍,個股流通市值越大,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越大,股市收益波動率越小。
(3)上市公司每股凈資產越高,股價波動率越低;績優股的波動率明顯較低,而虧損股的波動率缺乏確定性方向。整體上說明業績越好的股票其穩定性越強。
3.2 建議
(1)國家應繼續發展機構投資者,從國外更多地引入QFII、RQFII,在國內進一步壯大社保基金、人壽保險基金和企業年金等長期投資者隊伍,避免同質化發展。作為市場第一主力的證券投資基金應當發行差異化基金產品,并減少羊群行為造成的股價波動率過高,避免機構投資的股票與整個市場同漲共跌。監管機構必須根據市場波動率的大小適度控制基金產品的發行規模與頻率,在下跌市道且波動率過大的情況下提高發行的速度以平抑波動。
(2)上海證券交易所可以適當擴大股票流通市值,給機構投資者更多的選擇余地,使操縱股價更為困難。不同行業、不同特色的上市公司能滿足不同機構投資者的需要,當供求均比較充足時,股價的波動會相對平緩一些。另外,由于流通市值20 億以下的股票的日內波動率和超額波動率相對較低,因此應適當增加中小盤新股的發行上市,有利于市場的穩定。
(3)上市公司須勵精圖治提升業績,加強市值管理,在保證公司特有品質的同時做大做強。在國內,上市公司應利用市場深化改革的契機進行并購重組,注重研發能力的提升,避免靠政治聯系獲得資源的關系型發展模式[15];在國際上,上市公司可在世界多個資本市場中爭取融通資金,通過跨國合作、并購以及銷售產品與服務搶占國際市場份額,以實現擴大公司規模與提升公司業績之間的良性循環。對于虧損股,應當嚴格執行證監會于2014 年10 月發布的退市意見,若上市公司因財務造假給投資者造成了損失,那么該公司及相關中介一定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以維護投資者的信心,降低股市波動率。
[1] Lipson M, W A Puckett Wolatile.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Trading[DB/OL].[2014-10-20].http://www.ssrn.com.
[2] 周學農,彭丹.機構投資者對中國股市波動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系統工程,2007(12):58.
[3] 楊竹清.證券投資基金持股與股價同步性研究[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12(6):51.
[4] Gompers Paul A,Metrick Andrew.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Equity Price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ocs,2001,116(1):229-259.
[5] Sias R W,Titman S.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stock returns:Assessment and methodolog y[J].Journal of Business,2006(79):2869-2910.
[6] 姚頤,劉志遠.基金投資行為的市場檢驗[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7(11):109-113.
[7] 肖欣榮.證券投資基金對中國股市的穩定作用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9(8):138-139.
[8] 胡援成,胡喬.基金持倉比例對股市波動性影響的實證研究[J].河北學刊,2009(5):167-168.
[9] 鄒宇帥,田存志.證券投資基金交易行為與股價穩定[J].金融市場,2010(5):46-51.
[10] 朱偉驊,廖士光.投資者行為與市場波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4.
[11]Sushil Bikhchandani,Sunil Shmara.Herd Behavior in Financial Markets[R].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1:279-310.
[12] 韓金紅.機構投資者類型對股市波動的影響[J].商業研究,2012(4):109-115.
[13] 陳軍,陸江川.我國機構投資者持股與股市穩定性關系研究[J].福建論壇,2013(8):44-49.
[14] 魏立佳.機構投資者、股權分置改革與股市波動性:基于MCMC 估計的t 分布誤差MS-GARCH 模型[J].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2013(3):545-556.
[15] 趙巖.政治聯系、負債融資與企業過度投資研究[J].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4(1):7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