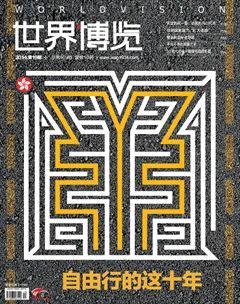沖突的根源
常民強
日前,懷孕30周的北京網友“如許姑娘”赴香港旅游,在香港機場被特區政府入境處拒絕入境。“如許姑娘”隨即在微博上發布一篇名為《大月份孕婦赴港旅游遭海關羈留遣返經過》的帖子來控訴遭遇,受到網民關注。她在文章中寫道:“在海關出示了往返機票和酒店付款訂單、醫院B超單,和北京私立醫院的產檢分娩合同以及北京月子中心的合同,我認為已足夠證明來港目的并非分娩,并且表示如果需要其他材料我也隨時能夠提供,但仍被無視。”隨后的9月23日下午,特區政府入境處答復稱:懷孕28周或以上的內地孕婦,進入香港須出示由香港醫院發出的預約分娩確認書,否則可能被拒絕入境,并即時遣返。
入境處介紹,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2013年實施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零配額政策。所有香港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均不會接受內地雙非孕婦預約分娩服務,單非孕婦則可通過特別安排在私家醫院預約分娩服務。為配合有關政策,入境事務處會執行對內地孕婦的入境配套措施:懷孕28周或以上的內地孕婦,在進入香港時須向入境處人員出示由本港醫院發出的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如未能出示預約分娩服務確認書或入境目的存疑,入境處可能會拒絕有關人士入境,并即時安排遣返。入境處在執行此措施時,衛生署會在有需要時安排醫護人員協助,就孕婦的懷孕及其他身體狀況提供專業評估和意見。過去數年,入境處每年平均對約3.5萬名非本地孕婦作進一步訊問。在2013年,有5077名無預約分娩服務的內地孕婦按照入境條例被拒絕入境及遣返內地,較2012年被拒的4202名增加超過20%。在今年前8個月,已有3532名內地孕婦被拒絕入境。
心靈中的隱形圍墻
有著如此之大爭議的“港產”事件,不由得令我們回想起在1954年,美國人類學家卡萊沃·奧伯格首次在他的博士論文《克林基特印第安人的社會經濟》中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1960年,奧伯格提出自己的“U形模式”(U-cure Model),這是解釋文化適應的流行模式,該模式認為一個人在異文化旅居時,必然會經歷一段困難和起伏才能獲得舒適感和平常感,文化適應大體有四個基本階段:“蜜月期、危機期、恢復期和適應期。”
但是,我們如果簡單套用奧伯格的上述理論解釋2012年(甚至延續至今)香港人和內地客的文化沖突,顯然會陷入理論的尷尬:首先,大多數學者談論的“文化休克”現象都是針對進入陌生異文化環境時,東道文化對其產生的心理沖擊,香港人身處本港,能遭遇“文化休克”嗎?其次,香港早在1997年即回歸,在經歷長達15年之久的“文化適應”后,還在“休克”嗎?
1990年,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他的名作《社會學之思》中進一步優化了“文化休克”理論。他解釋說,由于進入陌生文化或遭遇陌生人闖入,“我們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經給我們安全感和使我們感到舒適的生活方式,現在被挑戰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我們被要求的,關于它進行辯論、要求解釋和證明的東西,它不是自證的,所以,它看起來不再是安全的”。 “文化休克”理論不斷注入新鮮血液,這為我們深入思考香港人和內地客的沖突提供了不少新思路。固然,香港人身處本港,但是其“遭遇陌生人闖入”時,不同樣遭遇了“文化休克”?而且我們能感覺到他們“休克”的癥狀已經相當嚴重——從整版“蝗蟲”廣告到“蝗蟲歌”,再到圍攻辱罵內地旅客“Chinese pig”……如果我們再結合古拉霍恩的“W形模式”(1963年古拉霍恩提出的描述文化適應過程的“W形模式”,其在“U形模式”的基礎上,添加了人們在重新回到本文化環境時,個體必然會經歷的“返回本文化休克”階段和再度社會化階段),對香港人的“文化休克”現象會有更全面的理解:1841年英國占領香港,香港開始成為英屬殖民地,港英政府的文化策略是偏重教育港人做“遵紀守法”的公民,鼓勵認同英國文化。直到1997年之前,按照奧伯格的“U形模式”,在英國文化的濡染下,港人經歷了蜜月期、危機期、恢復期三個階段后,已經完全進入適應期。香港回歸后,港人本應該由殖民性“文化休克”再進入“返回本文化休克”階段。但是由于“一國兩制”的成功過渡,“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返回本“文化休克”的進程明顯滯緩;然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加快了香港和內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大大提速的“香港自由行”本來是刺激疲軟香港經濟的強心劑,不過也成為“遭遇陌生人闖入”的“返回本‘文化休克”的催化劑。毋庸諱言,如果說香港人的“蝗蟲歌”是“文化休克”的過敏反應,那么內地客的“地鐵進食”則是“文化休克”滯緩反應。
“文化休克”其實并不可怕,跨文化傳播學者對此現象已經開出很多的“文化適應”藥方。現在有針對性地總結如下:
1.克服“族群中心主義”
有學者將“族群中心主義”翻譯為“我族中心主義”或“民族中心主義”,美國社會學家威廉姆·奇·薩姆納第一個提出這一概念,他認為“族群中心主義”者在判斷事物時以自身文化為中心,對其他文化一概按照自身文化的標準來評判“好”“壞”。薩姆納還把“族群中心主義”區分為兩部分:“一方面認為自己的群體是優等的,另一方面認為其他群體是劣等的。認為自己的東西是最好的,以自己的文化為榮,這也是比較自然的心態,問題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依此就給其他文化加注‘劣等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因此族群中心主義阻擋了對不同文化的理解,妨礙了跨文化交流的進行。”“蝗蟲”廣告之后,導演張堅庭曾在《明報》撰文說:“當香港人以生活習慣差異作為根據攻擊詆毀同文同種的同胞時,我們煽動仇恨的借口比種族歧視還要惡劣。”20世紀20年代,美國文化人類學者弗蘭斯·博厄斯就提出文化相對主義的觀念化解“族群中心主義”的隔膜。文化相對主義強調包容社會文化中存在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當我們認識到差異不可避免,以“和而不同”的心態接受差異,進而從差異中對比學習,那么我們跨文化的敏感意識會不斷增加,彼此的溝通交流也會自然順暢。當然,香港人和內地客都要積極做文化相對主義者。endprint
2.克服“刻板印象”
很多香港人認為內地消費者是香港物價飛漲的罪魁禍首,而更糟糕的是某些內地客沒有表現出與富裕程度相匹配的文明:內地客不排隊、大聲說話、隨地吐痰。這就是傳播學中“刻板印象”的典型體現。
1922年,“刻板印象”首先由美國著名記者沃爾特·李普曼提出。李普曼用這一概念,起初是描述法官基于他人民族身份對其進行不公正的審判,如今這個詞語已經廣泛用于對任何群體身份,如種族、性別、身份,甚至家庭、職業等做出的正面或負面判斷。
西方學者將“刻板印象”的不準確性總結為三個方面:“第一,‘刻板印象將某種文化特點進行簡單歸類并推及每一個人,推導圈外人同一性結論,從而忽略其個體差異;第二,通常對某一文化的‘刻板印象都是夸大、不準確的;第三,因人們態度不同(或積極,或消極),對其他文化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誤讀或夸大的程度也不同。”
“刻板印象”會使我們在跨文化交流時,用“他們”將自己與其他文化人分開,夸大我與他者文化的差異,并認為他們的文化都不好,尤其是自己處于消極狀態時,過分夸大他者文化的劣勢,最終導致“偏見”產生,造成溝通障礙,甚至使兩種文化間的人們彼此形同陌路,不相往來。
要克服“刻板印象”,必須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認識到任何“刻板印象”都不可能適用于該群體中的所有成員——白馬是馬,但是絕對不是所有的馬都是白的;基于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要以挑剔的目光審視“刻板印象”,進而更加客觀地評價自己的文化。
3.樹立“對話的傾聽”意識
“對話的傾聽”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由約翰·斯圖爾特和米爾特·托馬斯逐步完善形成的。該理論強調對話時,“傾聽”和“說話”應平等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依托,不單純地說,或者單純地聽。根據斯圖爾特和托馬斯的解釋,要做到“對話的傾聽”,需要滿足四方面的要求:“第一,把對話視為一種共享活動,或者說,將對話的焦點置于‘我們的立場以及對話本身可能產生的結果上;第二,強調參與對話的開放、活躍的態度,特別是要求傳播者之間建立一種相互謙讓、信任的關系;第三,關注那些發生在傳播者之間的具體事物,而不是關注發生在對方腦海里的事情;第四,應當首先關注當下的目標,而不是去留意未來或過去的目標。”應該說,對抗沒有出路,對話才是解決問題的鑰匙。香港人和內地客同根同族都是中國人,只有通過有效的平等對話,才能真正推倒心靈之墻,重新建筑和諧溝通之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