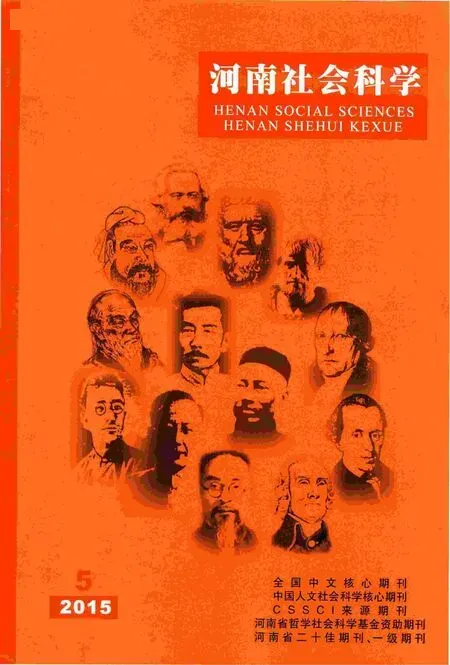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和需要克服的幾個誤區
林毅夫
(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 100872)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一、前言
新常態是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份在河南考察時提出的一個重要判斷,如今成為使用最多的詞語。在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有多快?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有多大,以及挖掘這個潛力的外部條件和內部條件是不是具備。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和條件
我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十幾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經濟增長的內涵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已經在全世界處于最前沿,進一步創新、升級的難度大,所以長期以來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只有3%。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有后發優勢,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的成本和風險跟發達國家相比小得多,速度和效益可以比發達國家高得多。改革開放以后30多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平均9.7%的增長速度,原因就是利用了后發優勢。
現在中國到底還有多少后發優勢?有一種看法是,二戰后各國發展經驗表明,一個經濟體在快速增長20年以后通常增長速度會降到7%以下,中國已經維持了36年快速增長,所以中國增長速度也會很快降到7%以下。另一種看法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達到11000美元后,經濟增長速度會降到7%以下。中國很快會達到這一標準,所以經濟增長速度也會降到7%以下。
我認為上述兩種看法并沒有完全了解發展中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要知道中國還能有多長時間的快速增長,該看的不是過去增長了多少年,也不是現在絕對水平有多高,而是看經過這30多年的快速發展跟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差距還有多大。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也代表這個國家的產業和技術的水平,和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的一個指標。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美國的20%多。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新加坡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時候,它們的人均收入也相當于美國的20%多,隨后它們實現了20年8%~9%的增長。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中國還有20年8%的增長潛力的依據。
增長潛力只是代表一種可能,能不能實現要看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外部條件現在相對不好,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沒有完全從2008年的危機當中復蘇過來,中國的出口增長緩慢。外需不行就要靠內需,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中國在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和城鎮化方面都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而且也有投資能力。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在全世界來講是好的,民間儲蓄率世界最高,美元外匯儲備全世界最多,如果把這些有利條件利用起來,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投資率,就業和消費增長就會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2015年定的7%左右的增長目標相信就會實現,而且不僅是在2015年,整個“十三五”期間實現7%左右的增長目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中國能夠實現7%左右的增長,對全世界增長的貢獻會在25%~30%,也就會成為對全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到了2020年兩個翻一番的目標就能夠實現,人均GDP也可以跨過1.26萬美元的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這是中國在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總體態勢,當然還要看是否很好地利用了現有條件和資源。
三、思想上的誤區需要克服
外部環境相對不利,要利用國內有利的條件實現8%左右的增長,需要克服幾個認識上的誤區。首先,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環境明顯惡化,霧霾也相當嚴重。很多人就產生了一個誤解,以為環境惡化是因為中國經濟增長太快造成的。如果把經濟增長放慢一點,環境就會好。這個看法并不準確。其實霧霾跟增長有點關系,但不是因果關系。最好的證明就是印度過去30多年經濟增長速度比中國低3到4個百分點,但是印度霧霾和環境污染的情形比中國還嚴重。印度和中國霧霾之所以嚴重一是因為都處于中等發展階段,制造業是最主要的生產領域,能源消耗和排放的密度高。任何國家,包括歐美的老工業化國家和東亞的日本、韓國等新工業化國家,在這個階段環境問題都會比在以農業為主的低收入階段和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嚴重。二是印度和中國的能源都以煤炭為主,污染的程度比其他能源嚴重。三是因為環境執法不嚴。在這種情況下,加強環境執法,環境問題會有所緩解,但前兩個問題仍然會存在。放緩經濟增長的速度,只會延長制造業為主的中等發展階段,延緩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
其次,有很多人把投資等同于產能過剩,這個看法也不準確。現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基本上就是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減少了投資以后對這些產品的需求減少了,產能過剩更厲害。投資會不會造成產能過剩取決于投資的方向。如果是對已經過剩的產業繼續投資的話當然會產能過剩,如果投資是沿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方向去做的話不僅會減少現有產業的產能過剩,而且還會提高經濟的競爭能力。
再次,是在經濟下行時政府是否應該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反周期的措施。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政府做了很多基礎設施投資,在這段時間里我國的投資回報率下降,有人說政府做的投資回報率低,所以政府不應該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反周期措施。我認為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基礎設施建設周期長需要好幾年,在未建成前只有投入沒有產出,回報率自然較低。同時,基礎設施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減少了交通擁堵、降低汽車輪胎的耗損等,這些都可以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但并不包含在基礎設施的回報中。即使把這些都考慮在內,政府在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還是比企業在產業上投資的回報率低,那么政府是否就不應該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反周期的措施呢?一般企業投資基礎設施的積極性低,基礎設施出現瓶頸又會制約經濟的增長,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如果政府需對基礎設施的建設負責,那么,是在經濟上行時來做好,還是在經濟下行時來做好?經濟上行時企業已經有很高的投資積極性,政府再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只會使經濟過熱;經濟下行時企業沒有投資的積極性,失業增加,政府可以發失業救濟,或是投資基礎設施啟動需求,創造就業減少發失業救濟的必要,到底哪一種比較好?顯然,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一石雙鳥的較優選擇。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考慮,2014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改過去的政策主張,認為在經濟下行時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機。
最后,國內還有一種看法是經濟增長慢可以倒逼改革。這個看法也值得商榷。我認為,如果經濟增長慢了,失業問題就會增加,企業盈利狀況變差,金融呆壞賬和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危險上升,政府就會像救火隊一樣不斷地解決短期問題,實際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經做的改革又會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