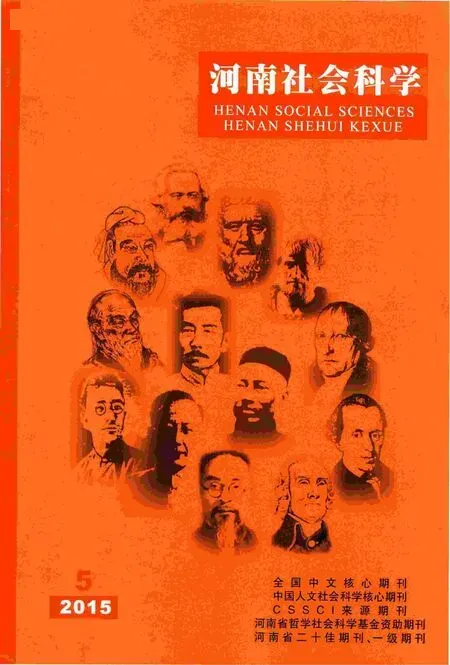《周易》的風險治理觀研究
雷云飛
(西安理工大學 思政部,陜西 西安 710048)
現代化的發展為人的生存與發展創造了豐富的物質基礎的同時也加劇了人與自然、社會等方面的矛盾,這就使得人們對于所生存的現實狀況日益擔憂。風險社會理論就誕生于此,而且業已引起越來越多的理論家對其進行孜孜不倦的深挖、拓展和反思,為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風險進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基本經驗。但是,要提出一套適合中國現實狀況的風險社會理論,首先要從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著手,并從中汲取能夠用來指導解決當代中國社會風險的理論、觀點和思想。《周易》是集聚中國傳統風險思想的經典著作,其中包含著豐富的風險治理的基本思想和方法,這為解決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諸多風險問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方法和啟示。
一
綜觀《周易》,“乾”卦為始,即“元、亨、利、貞”。而且這四個字散見諸卦之中。其實,這四個字的基本含義在《周易》中也有明確的注解。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明確地指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1]也就是說“元”是諸多善當中最大的善;“亨”就是諸多美好事物的集合;“利”就是與屬于人的義相對應的外物,也就是使人得到利益的意思;“貞”就是能夠主持大局。君子如果能夠堅守這四個德行,也就是真正地踐行了乾卦之“元、亨、利、貞”的本意。
其他相關著作中對這四個字的理解也有各自獨到的見解。據《左傳》記載,魯襄公之母穆姜在逃亡前占卜,得“隨”卦,“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2]。她以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正,稱之為“四德”,給它們賦予道德規范的含義,如果背棄“四德”,就不會“無咎”而必遭禍殃。唐代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乾卦》中轉引《子夏傳》,他認為:“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3]認為乾卦“四德”意味著陽氣始生萬物,物生而通順,能使萬物和諧,并且堅固而得其終。邵雍在《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中指出:“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言時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秋也,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利,義者不通于利,故言時不言德也。貞者,冬也,智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兇,故言德而不言時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4]
總之,在《周易》中,“元”主要指的就是“仁”抑或“善”,“亨”主要指的就是“禮”,“利”主要指的就是“義”,而“貞”主要指的就是“堅守正道”。如果把這四個字的本意能夠弄明白,在通讀六十四卦的時候就能從根本上厘清各卦所指的深層次內涵,為探索其中包含的風險治理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提供指南。
二
《周易》中包含著豐富的風險思想。那么,什么是“風險”呢?在中國古漢語里面,對其有著深刻的闡釋。所謂“風”,意為“風動蟲生,八日而化”[5],就是指事物發展變化的外在條件和原因,而“險”就是指“阻難也”[5],指事物在變化發展過程中的阻力和困難。那么,人們又如何應對其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風險呢?《周易》對此做出了許多富有原創價值的探索,它從古人認識和應對風險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科學的解答。
《周易》的風險觀主要包含以下幾種類型:
(一)過猶不及的風險觀
《周易》中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君子所為必須堅守中正、秉持正道,必須做到恰到好處,而不能有所偏頗,否則,就必然釀成兇險的后果,這在卦象上的表現就是每一卦的第五爻都是該卦中最中正的位置。關于如此主題的卦俯拾皆是。譬如乾卦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過猶不及”。它的主題就是“元亨利貞”,其中的含義前文中已經敘述過了,它的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如果不能堅守中正,就會陷入風險的悔吝境地,甚至大兇。“九四,或躍在淵,無咎。”[1]就是沒有達到中正的、即使無咎但是欠佳的具體表現,而“上九,亢龍有悔”則形象地表達了過于中正必將有悔的境地,而只有“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1]才是真正剛健中正以居尊位的狀態。這就形象地表明了不管是“不及”還是“過”都不是最佳的選擇,只有堅持中正恰到好處才能夠避免悔恨、過失和災禍產生的風險。
(二)防微杜漸的風險觀
防微杜漸,就是要防止風險就必須從當下做起,從小事做起,只有這樣才能夠將風險隱患的萌芽在其還沒有蔓延的條件下予以制止和消除。譬如,坤卦就是對這一風險觀最典型的表達。它所包含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初六,履霜,堅冰至”[1]。這句話字面的意思是當腳下開始踩著寒霜的時候,地上開始凝結堅冰的時候就將隨后而至。其所暗含的意思就是事物的發展變化有一個量變的過程,如果平時不從除“霜”這樣的小事做起,就有陷入“堅冰”困境的風險。正如“坤”卦的《文言》中指出的,“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1]這就更加明確地說明了一種以謹小慎微的態度認真直面風險并從容應對的策略和智慧。
(三)慎始慎終的風險觀
在《周易》中的諸多卦辭和爻辭中多次出現了慎始慎終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重視事情的始終,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這樣才能夠順利防治風險,使人的處境轉危為安,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風險觀。譬如,屯卦,其主要思想就是為我們揭示了事物初生之時其中就已經蘊含了許多難以預測和控制的災難,因此要求我們審慎地重視開始。正如屯卦《彖辭》指出:“剛柔始交而難生。”[1《]周易》認為萬事萬物都是陰陽(剛柔)相互作用的結果,從一開始就包含了無盡的風險,所以乾卦(純陽)和坤卦(純陰)之后緊接著就是陰陽(剛柔)相互交錯的第一卦——屯卦。此外,《系辭》中指出,“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1]。這就更加明確地指明,對于事情當中所包含的風險始終保持警惕之心是《周易》的基本精神。
(四)韜光養晦的風險觀
它指通過掩其鋒芒、向外示弱,將自己的缺點和不足充分地向外展示,從而使自己在危難的險境當中得以保全,對自己生死攸關的風險得以有效規避。譬如,明夷卦:“內文明而外柔順,一蒙大難,文王以之。”[1]就是說通過外表“柔順”而內心“文明”的辦法,才能夠經受大難、化險為夷。周文王之所以能夠成就大業,就是這樣做的。在此卦中,韜光養晦的風險觀還被推向極致。“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1],就是說本卦最核心的意思就是韜晦,讓這樣的思想居于最為中正之位,充分說明了這樣的行為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美德。
這四個方面的風險觀為我們正確應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基本理念,更重要的是它那富有寓意的文句和一字千金的價值均體現在對風險加以殫精竭慮的治理和運籌帷幄的控制方略之中。
三
在《周易》中,關于風險最有代表性的卦就是坎卦,再推進一步就是習坎卦。它主要代表的是“水”,意味著難以駕馭的風險和災難。所謂“坎者,陷也”[5],就是指道路崎嶇高低不平、遭遇險難的意思。那么,習坎卦就是指險阻和困難重重的意思,即“重險也”[1]。《周易》在此基礎上還深入細致地闡述了風險治理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德治險
中國文化有一種特殊的氣質,就是自古至今的無數仁人志士都致力于培養自身的道德精神,因為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一直潛藏著一個信念,即始終相信只有具有“德”的人才能夠真正地當身立世,才可以感召人并與人共患難,也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夠領導人們進行生產和生活,以規避風險。這在《周易》中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周易》中,德是治理風險的前提條件。譬如,“坤卦”就典型地體現了這一點:“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就說明了人的德行像大地一樣厚重深沉才能夠容納萬物,才能夠具備“履霜,堅冰至”的慧眼,從而見微知著、防微杜漸以防止難卜的風險。在蒙卦中,其《彖辭》就明確地指明了“山下有險,險以止”[1]。其卦象本身就蘊含著“君子以果行育德”[1]的含義,在這里,培育果敢的德行與阻止風險是密不可分的。在蹇卦中,其卦象就是“君子以反身修德”[1]的意思,而本卦所處的境況則是“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1],這就更加形象地闡釋了以德修身就是防止和規避風險的前提條件。其次,德是《周易》的核心思想。在《周易》中,能夠將其中的諸多卦聯為一體的概念就是德,在《系辭下傳》中記載道:“《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1]這就充分表明了《周易》中以德治險的基本思想,而且諸多卦都緊密地圍繞著德這個中心從不同角度及德的不同內涵進行全面而又翔實的詮釋,這也使得不同的卦都因為德而緊密地相互聯結。再次,德是治理風險的主要途徑。在《周易》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只有具備德行才能夠避免風險,而且也只有具備德行才能夠建功立業。《系辭下傳》中指出:“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1]意思就是說,由于乾坤至健至順,所以能夠恒易恒簡,以至于能夠深諳前景的險阻。朱熹對此有一段非常經典的闡釋,他指出:“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1]由此可知德行的恒易恒簡就能夠知險并且不陷于險。《系辭上傳》一開始就明確指出:“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1]這就更加明確地闡明了《周易》中乾坤的恒簡恒易與賢人的德與業的內在聯系。
(二)以禮治險
中華民族以“禮儀之邦”著稱,其實,在中國社會中,“禮”不僅指表面上的禮儀的意思,還有通過“禮”才能夠保得平安、規避風險的深層內涵。在《周易》中,有許多關于“禮”的思想。根據乾卦《文言》的理解,《周易》中“亨”就包含了“禮”的內在含義。一方面,“禮”能夠幫助人化險為夷。在履卦中,卦辭就形象地指出:“履虎尾,不咥人,亨。”[1]就是說,即使身犯險境也不會遭受傷害,其緣故就在于遵守禮法。在彖辭中則更加明確地指出“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1]。就是說只要能夠符合禮法,就能夠剛健中正,即使踐祚帝位也不會有什么內疚的,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在既濟卦中,卦辭中說:“亨,小利貞。初吉終亂。”[1]此卦中所含的深意非常豐富,筆者暫立足于風險的視角對其做以淺表的會意和解讀。它的意思就是,當事情達到極致的圓滿的時候就必須嚴格遵守禮法,并將其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而把為了實現圓滿的所采取的利和貞這樣的手段則要放在次要的位置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一件事情實現圓滿的時候也是敗亡的開始,盡管圓滿很吉利很好,但只是開始,其最終還是要走向沒落的。所以,君子在事成之時就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以應對瞬息萬變的風險,在勝利圓滿的兇險境況中保持冷靜。故,在象辭中才指出了“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1]的警示。另一方面,“禮”能夠幫助人預防和規避風險。在渙卦中,卦辭就明確指出:“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1]根據乾卦《文言》的主旨,就應該這樣對渙卦加以理解:它主要講的是“禮”。王來到祖廟進行祭祀,這就是對“禮”的表率,能夠做到“禮”,若有所為必將無往不勝,任何困難都能夠順利通過,也只有貫徹“禮”,才能夠讓大家都得到“禮”的好處,才能夠堅守正義、承擔重任、擔當大事,也才能夠實現其中上九所說的境界,即“上九,渙其血,去逖出,無咎”[1]。這就是說,只有用“禮”才能夠祛除憂患,也只有用“禮”祛除憂患了才能夠使人提高警惕防范風險,這沒有任何壞處。這一思想在節卦“ ”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節卦的卦辭中說:“節,亨,苦節,不可貞。”[1]就是說節卦包含著“禮”的意思,如果以禮節為苦就不會有什么好的結果,只有堅守禮節,才能順利規避和度過風險,正如其彖辭中所說:“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1]意思就是說只有堅守禮節,即使身處險境也能夠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因此,節卦反對“苦節,貞兇。悔亡”[1]。不能以禮節為苦,這樣肯定會陷于險境,而主張“甘節,吉,往有尚”[1]。應該對禮節甘之如飴,這樣才能夠大吉大利,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能夠得到好的結果。
(三)以賢治險
在《周易》中,不管是以德治險還是以禮治險,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說明以賢治險的根本法則。在前文中,已經闡釋了《周易》中以德治險和以禮治險的風險治理思想,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德”和“禮”都是君子所必須具備的基本內涵,也就是說,君子只有具備了這些操守和品德——尤其是“德”與“禮”才能夠成為萬民敬仰的圣賢,才能夠領導人民正確治理風險從而躲災避難、化險為夷。當然,《周易》中對圣賢的要求并沒有局限于此,它還要求作為圣賢必須具備以下幾方面的品質:首先,言與行是君子榮辱成敗的關鍵因素。言與行的妥當與否直接關乎君子的榮辱。《系辭上傳》中指出:“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1]由此可見言行對于一個君子是何等的重要,甚至言行的慎于不慎之間具有極大的風險,它不僅直接關乎事情的成敗,還關乎君子的身家性命,“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1]。其次,君子謙謙才能夠規避風險有成有終。君子只有做到謙而又謙,才能夠在地位顯達的時候得到真正的榮光,即使地位卑微,也不會遭受災禍,只有這樣才能夠順利規避風險從而得到善終。正如謙卦中指出的:“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1]綜觀此卦中的六爻可以得知,只要能夠做到謙而又謙就會有所作為并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再次,誠信是君子治理風險從而安身立命的保證。《周易》中多處間接地涉及了君子講求誠信的論斷。譬如,需卦就指出:“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1]需卦的含義就是講求誠信是對“禮”的發揚光大,只要能夠堅守誠信必將有所作為。彖辭也指出:“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也。”[1]這就更加形象地點出了講求誠信與風險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能夠做到誠信,即使面對兇險也能夠峰回路轉、化險為夷。
綜上所述,只要能做到以德治險、以禮治險和以賢治險,就能夠平安順利地渡過險境、規避風險。歸根結底,之所以如此地盡人事,還是為了能夠實現來自上天佑助從而達到大吉大利的上乘境界。譬如,《系辭上傳》中指出:“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1]這就說明了只要能夠全心全意地盡人事,那么,得到上天的眷顧和護佑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當然,這里盡管把盡人事精確到“履信”的地步,但這并沒有忽視除過“信”以外的其他方面。此外,《周易》在《系辭上傳》的開篇就開宗明義地闡釋了這一至高理念,指出“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1]。雖然這里說的“象”“辭”均指的是《周易》中的內容,但是透過這層表象不難看到其中先盡人事然后獲得上天護佑以規避和治理風險的意蘊。
四
《周易》中的風險治理觀深深地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土壤之中,經過漫長歷史的淘洗從而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在全球化時代,運用《周易》中所蘊含的治理和規避風險的基本理念和具體方法,給我們正確認識風險和治理風險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首先,高度重視個人的歷史作用。《周易》中風險治理的方法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就是非常注重君子個人的德行修為。這給我們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進行風險治理提供了以下兩方面的啟示:一方面,要正確治理風險就必須從自身做起,不僅要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還要提高個人辨識風險的能力;不僅要樹立正確應對風險的思想意識,還要培養個人治理風險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要正確治理風險就要高度重視每一個人的發展。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人類要正確應對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不能依靠個別人的力量,而是要依賴每一個人的發展,使所有人能夠共同努力以使人類有效地應對風險,從而渡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重險關。更值得注意的是,注重每一個人的發展不僅是根除風險的科學途徑,而且還是社會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內在要求。馬克思曾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
其次,高度重視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社會意識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轉型,但是傳統文化仍然占據著一個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而不斷凝結和積淀,最終形成一個民族特質的基因。因此,在當代,我們治理社會發展中的風險的時候,務必積極汲取傳統文化中的民族智慧。一方面,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出符合我國歷史文化背景的風險治理決策,從而才能為有效地解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風險提供科學的基本思想和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做到用自己的智慧解決自己的問題,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道路,從而不僅彰顯了本民族的文化及其當代價值,還擺脫了外來文化及其思想意識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控制。
再次,積極借鑒國外治理風險的先進經驗。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源于西方的科技理性侵襲了整個世界,由此產生的風險社會也隨之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蔓延,西方國家針對風險進行的科學研究不僅早于后發國家,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多于后發國家并且至今仍然站在時代的前列。其所獲得的經驗教訓和先進科學技術,為后發國家特別是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風險治理提供了富有借鑒意義的參考。因此,一方面,借鑒西方的先進文明成果和風險的認知與治理策略,有助于我們科學認知和應對風險,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對風險的治理達到比較好的效果,從而實現風險治理和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發現我國文明成果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諸多不足之處,才有利于幫助我們取長補短,這不僅可以鞏固和完善我們已經取得的現有成果,還有助于我們做到“古為今用”和“洋為中用”,從而游刃有余地應對我國當前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風險。
[1][宋]朱熹.周易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九年[M].北京:中華書局,2009.
[3][唐]孔穎達.周易正義·乾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4][宋]邵雍.皇極經世[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5][漢]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