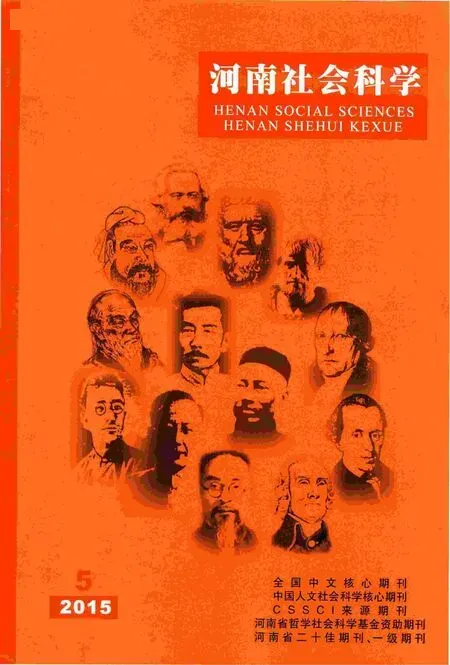“一帶一路”戰略改變全球經濟格局
盧 鋒
(北京大學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建設”,“把‘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全國“兩會”期間,31個省區市表示將積極參與“一帶一路”規劃實施,“一帶一路”有望成為貫穿2015年國家和地方對外開放與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
實施以互聯互通、基礎設施投資為重要內容的“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需要投融資機構平臺的支持。中國倡導建立“一行一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亞投行與早先成立的金磚銀行,在國際經濟治理結構方面具有相對獨立的創新含義,尤其引發全球范圍的廣泛關注。亞投行具有開放性,以亞洲國家為主,歡迎區域外國家參加。
西方大國是否參與發起亞投行立場發生戲劇性變化:先有英國不顧美國杯葛,2015年3月12日率先申請成為亞投行意向發起國。后有2015年3月17日法、德、意歐元區三大主要國家結伴申請加入。折射“一帶一路”規劃的重要影響力,是新興經濟體改變全球經濟格局的標志性事件之一。美國國際經濟學研究所前所長Fred Bergsten在2015年3月19日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抵制亞投行是美國犯下的一個巨大錯誤——它抵制了一家旨在幫助亞洲滿足能源、電力、交通、電信和其他基礎設施領域數萬億美元投資需求的銀行。”
“一帶一路”戰略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一是把互利共贏與互聯互通結合起來,寓和平發展理念于“一帶一路”戰略之中。二是把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結合起來,使得規劃實施具有廣泛切實的經驗基礎。三是把國內發展與經濟外交結合起來,成功調動其國內外各方面的參與積極性。四是把設計創新與高效執行結合起來,展現中國決策層對重大政策的設計、布局、執行力。五是把合作建設與機制創新結合起來,對改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進行探索。
“一帶一路”戰略之所以成效彰顯,是因為我國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特有的生產技術能力與開放宏觀經濟兩方面具有關鍵優勢。生產技術能力的優勢體現為“中國制造”“中國建造”與“中國創造”。體現“中國制造”優勢的一個量化指標,是2010年美元衡量中國工業制造規模第一次超過美國,目前約為美國的1.3倍左右。中國工業結構高度化一般水平雖然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仍有相當差距,然而其產能結構特點與發展中國家大規模開發需求的契合度更高,對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便利條件。
得益于幾十年來改革開放和大規模城市化建設,我國在大型基建工程建造能力方面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階段性比較優勢。“中國建造”能力在國際比較意義上的比較優勢,表現之一是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完成額從世紀初不到100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1400多億美元;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員工數從21世紀初5萬~6萬人,上升到近年30多萬人。另外,我國企業在高鐵、大型設備、工程建造等領域的技術集成創造、產品創造、標準創造能力正在形成和發展。另外,中國擁有最大規模的國民儲蓄、資本形成和外匯儲備,為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提供開放宏觀經濟方面的支持保障條件。
“一帶一路”戰略有助于培育全球經濟增長新動力。目前全球經濟仍處于早先失衡的深度調整過程中,G-20增長框架通過宏觀政策協調尋求“強勁平衡可持續”目標至今效果欠佳,“一帶一路”有助于培育新增長點提振全球經濟。就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要致富先修路,基礎設施是制約增長的關鍵瓶頸。即便是發達國家,也需要更新基礎設施為持續經濟增長提供支撐。對于中國而言,實施新戰略,有助于更好利用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產能,有助于調整國內經濟結構,有助于擴大國內各類配套投資,有助于擴大中國出口,有助于目前宏觀經濟穩增長目標。經驗研究結果顯示,控制住各國經濟規模、距離、貿易壁壘等因素后,中國對特定國家直接投資增加能夠顯著增加我國向該國的出口。“一帶一路”戰略對改進全球治理也具有積極意義。
“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必然產物,也必然會面臨各種困難阻力。需要堅持“親誠惠容”、合作共贏的基本方針,通過長期持久的合作努力實現計劃目標。企業“走出去”要找準定位,謀而后動,發揮核心競爭力,避免一哄而起和無序擴張。項目設計實施要兼顧市場贏利與社會責任目標,避免短期行為和竭澤而漁。應重視一些制造業勞動密集型工序環節的逐步轉移,充分發揮這類轉移對承接國在就業和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項目設計實施要加強與包括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務實合作,學習借鑒國外行之有效的做法。還需要不斷總結我國相關實踐的經驗教訓,大力進行各層次人才培養,保證新戰略行穩致遠。
中國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其經濟成長必然意味著對全球經濟格局的重構。“一帶一路”是這個簡單邏輯的現實展開!雖然存在諸多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新戰略有望在推進中外共同發展、改善國際治理結構、中國大國成長歷練等方面彰顯成就。對企業而言,“一帶一路”或許正成為又一個“風口”,助推長了翅膀的企業能飛得更高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