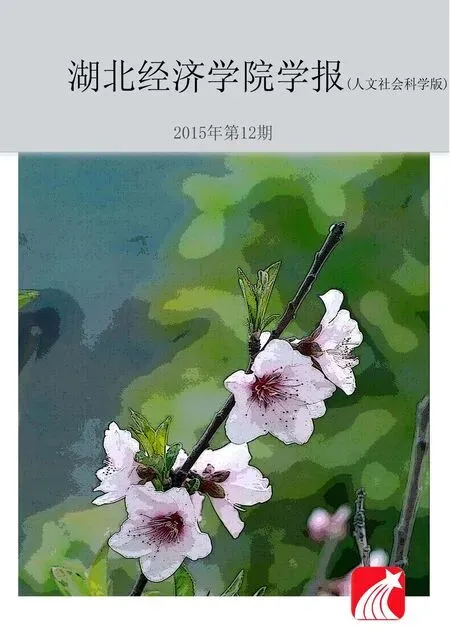論《失樂園》中撒旦形象的本質
孫殿波
(滁州學院,安徽滁州239000)
論《失樂園》中撒旦形象的本質
孫殿波
(滁州學院,安徽滁州239000)
作品《失樂園》中的撒旦形象具有太多爭議,但究其本質,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始終是魔鬼的化身,是“惡棍英雄”。他利用偽裝和詭辯來達到自身的目的。他狂妄的言辭,虛假光輝的外表,嘩眾取寵的主張無一不說明他虛弱而又邪惡的本質。而撒旦惡魔的本質又成因于他追求錯誤的東西——欲望、貪婪、野心。作為讀者,只有抓住人物形象的本質,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
失樂園;撒旦;本質
一、概述
在不同的時代及文化環境背景下,不同讀者對某部作品或者某個文學人物形象會產生不一樣的解讀,抓住人物形象的本質特點能使讀者以全新的視角去詮釋作品的內涵。彌爾頓的作品《失樂園》中撒旦的人物形象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和爭議性,一般分為唯撒旦論,反撒旦論,兩重撒旦論三種。浪漫主義詩人是唯撒旦論的擁護者,時代賦予他們強烈的個人色彩,使得他們在分析彌爾頓筆下的人物時往往從自己的主觀印象出發。到了新古典主義時期,伴隨著夢想的破滅,浪漫主義詩人開始以反叛者自居,出于對同是反叛者的《失樂園》中撒旦形象的認同,他們很自然的將彌爾頓視為同道,他們認為彌爾頓身為魔鬼的同黨而不自知。但是,需要注意到是彌爾頓和雪萊完全處在兩個不同的時期,新古典主義時期和浪漫主義時期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浪漫主義評論家無法接受也不能理解彌爾頓的神學思想體系。所以應該看到的是唯撒旦論不過是浪漫主義評論家在夢碎時所抓住的殘影,不過是撒旦形象的一個側面而已。只有抓住彌爾頓筆下撒旦形象的本質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1]
雖然撒旦這個形象具有矛盾性和復雜性,但是撥開層層表象,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始終是魔鬼的化身。在《失樂園》中,作者一開始就對撒旦的形象進行了本質性描述:無論做事或受苦,但這一條是明確的,行善決不是我們的任務,作惡才是我們唯一的樂事。這樣的形象與《失樂園》開篇描寫的高大、偉岸,英勇雄壯的撒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他身穿金甲,腰佩利劍,背負巨盾,手持長矛,身軀魁梧碩大,有帝王般的尊嚴,能夠上天入地,潛身變形,還面帶憂慮。詩人在無意中塑造了一個符合悲劇英雄原型的撒旦——偉岸而憂慮。但這并不能改變撒旦的真實面目:他仍是一個無惡不作的魔鬼惡棍,這一點是不隨時空而改變的。[2]
二、撒旦的本質——魔鬼的化身
(一)魔鬼狂妄的言辭
上帝創造了撒旦,使他的能力最為完美,但撒旦為了一己私欲,妄圖與上帝一爭高下,從而招起一群天使反叛天庭,可見其卑劣自私的人格。仔細探究撒旦墮落的過程,讀者可以發現從撒旦在準備發動叛亂反對上帝的統治的那一刻,其就已墮落,而“罪”的出生,則更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而撒旦真正走向丑惡墮落則是在他毀滅人類計劃并取得成功之后。此時的撒旦已經失去光輝偉岸的形象,化身于獸形,成為一個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小丑。
撒旦的本質依然是魔鬼,他的邪惡本性可以從他狂妄的言辭看出。撒旦認為自身對上帝的反叛是對上帝專制統治的挑戰,是正義的。長詩開始時撒旦不戰不休的氣勢確實具有某種叛逆者的氣概,但最后呈現給讀者的只是一個魔鬼和一群惡魔爪牙的表演而已。“畢竟,即使是罪大惡極的壞蛋,在他們絕望的時刻,為了捍衛自己的惡行,也會裝出一付爭取自由的面孔,狂叫著反對他們稱之為暴君的人。”[3]撒旦在圣子受位以后的煽動性演說是他用造謠藝術以假亂真的一個典型范例。他在演講中試圖讓追隨者相信“自生,自長”,天使們的地位和上帝圣子都是平等的,這種嘩眾取寵的自由主張獲得了墮落天使的迎合,更能煽起他們的嫉妒和怨恨。但是撒旦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所有天使的自由與平等,而是出于個人的野心,“……我們的名號理應治人而不是治于人”,這正體現了撒旦的狂妄與自大。自由和平等的主題貫穿了彌爾頓作品的始末,而撒旦口中的“自由”有一種特殊的含義,幾乎和“治人”是同義詞。他所謂的“自由”集中在他個人權利的問題上,下面就是他從火湖中醒來,對別西卜說的話:“至少在這兒/我們將是自由的;……/在這兒我們可以稱王稱霸,而我/寧可在地獄里稱王,大展鴻圖。/在天堂侍奉,倒不如在地獄稱王。”“稱王”的話音完全壓倒了“自由”的聲音。撒旦沉迷于對權利的追求,正如亞必迭所指出的:“你自己并不自由,做了自身的奴隸”[2]撒旦的真實行為和他的豪言壯語形成鮮明的對比,他激昂的言辭、煽動性的演說恰恰表現他的狡詐和偽善,剝去撒旦的層層偽裝,暴露給世人的正是他“惡棍英雄”的本質。這也符合《圣經》中撒旦的原型:魔鬼的化身、上帝和世人的敵對者、教唆人們犯罪的元兇。為了突出撒旦卑劣的形象彌爾頓特意安排了兩個情節。一是撒旦遇到了他的女兒“罪”,他竟和她亂倫,生了個怪物“死”。這是這段描寫突出了撒旦亂倫者的形象。二是萬魔殿開會時的場景,除了撒旦和幾個主要成員保留原形外,那些無名之輩都縮成侏儒,因為宮殿再大也容不下千萬惡魔龐大的原形。法國文豪伏爾泰認為“這些惡魔都變成了矮子這件事與假英雄的主題是一致的”。
(二)魔鬼虛假的光輝
撒旦就是一個戴著面具的人物,利用假象和詭辯來扮演他的各種角色。對于騙子,就應摘掉他的面具及駁斥他的謊言。《失樂園》中,魔鬼“虛假的光輝”不僅是在形體還是在言語上均多次被揭穿。第六卷中,“身裹金剛石和黃金盔甲”[4]的撒旦和忠誠于上帝的天使亞必迭在兩軍對壘的陣前進行了一場決斗,乍看之下,雙方的實力十分懸殊:當“高傲的勁敵用輕蔑的目光斜視”[4]對方,夸口要讓他嘗嘗厲害時,讀者著實為亞必迭捏了一把汗。然而在亞必迭的英勇攻擊下,撒旦像泥足巨人一般倒了下去:“他踉踉蹌蹌/向后倒退了十步,到第十步處,/才終于用重矛支撐住了屈膝。”[4]亞必迭的英勇頑強足以反襯惡魔光鮮外表下的虛弱本質。
撒旦的超凡魅力和動人言辭只是“徒有其表,并無實質”。在《失樂園》中,彌爾頓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描述撒旦的偽裝及其對真理的歪曲。當撒旦第二次進入伊甸園時,他就在重新考慮如何偽裝自己,并決定蛇是最適合他計謀的工具。詩中詳細描述了撒旦如何搜遍山野,搜尋他所想要的那條蛇,以及他如何占有了這個狡猾的生物。當惡魔從蛇的口里鉆進去,占據它的心胸時,后者的酣睡竟然未曾被打斷:“從蛇的口里/魔鬼鉆了進去,并很快就占據了/蛇那獸性的感官、心臟和指揮/其行動的頭腦;但是并沒有將它/從睡夢中驚醒”[5]這條蛇代表了兩重含義:一方面詩人在道義上譴責它,稱它是惡魔,人類的敵人,并詛咒它的蛇舌和欺詐性誘惑;但另一方面,詩人又刻意強調它迷人的偽裝:那高高昂起的頭,紅寶玉般的眼睛和金碧輝煌的頭頸。[5]這再一次呼應了撒旦光鮮外表下本質邪惡的主題。
(三)魔鬼的偽善和作假
撒旦對夏娃的誘惑最能說明他的偽善和作假,魔鬼通過這些伎倆樹立的只是一個虛假的形象。撒旦的偽裝是蛇,這條蛇最能蒙蔽夏娃的手段在于它居然具有說話的能力。當夏娃聽到蛇的聲音時感到驚異萬分:“這是怎么回事?人的語言/竟出自獸類之口,并能表達思想?”[4]夏娃因為好奇心而落入撒旦為其設置的圈套,撒旦起初對夏娃委蛇奉承,稱她為天仙和女神,夏娃在撒旦的引誘下真的認為自己是高于凡人的女神和天使,正是她對這種虛幻的妄想使她誤入歧途,違背了上帝的命令。一旦恭維解除了夏娃的戒心,撒旦接著暗示食禁果也許是上帝對她勇氣的考驗,夏娃感到這個謎語的答案一定是上帝要她去吃禁果。擁有思維能力和說話能力的蛇,這一荒謬事實更使夏娃對撒旦的蠱惑堅信不疑。
(四)魔鬼墮落的根源
撒旦墮落,邪惡偽善本質的原因在于他錯誤的追求。這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條重要思想——無窮的追求。每一種文化都有基本的象征物,以此來體現根本精神。對此,德國戲劇家萊辛曾有過著名的論述,“如果上帝在右手里握著所有的真理,在左手里握著是對真理的不斷追求,那條件是永遠得不到滿足,然后說:‘選吧’!我會謙卑地懇求讓我選左手,并說:‘真理只是你一個人的’”。正是對無窮的追求并為之付出的努力使人的生活有了意義,克爾凱郭爾更是把無窮的追求和人類存在的本身等同起來。撒旦的墮落在于他追求了不應該追求的東西——欲望、貪婪、野心,即便墮落之后仍執迷不悟。撒旦引誘夏娃吃禁果的一段話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無窮的追求”這一思想。“這個宇宙的女王啊,千萬別相信/那些關于死亡的威脅,你不會死的./你怎么會因為果子死呢?它給/你的生命知識。威脅者給嗎?看看我,/我這個碰過又吃過的人,然而活著,/過著一種比我的命運給我安排的/更完美的生活,因為我比宿命向望得更高。/人就得不到那野獸都能得到的/東西嗎?難道上帝會對這樣一個/可愛的過失大發雷霆?而竟不/贊揚你無畏的美德、輕視死亡的痛苦的/美德?無論死亡是怎么一回事,/不要怕得到它,它可能威來/一個更幸福的生活,還有善和惡的知識……”[5]撒旦的詭辯利用的正是無窮的追求這一思想,從而使人類上當受騙,無窮的追求固然是積極的,但如果出發點不正確,追求錯誤的東西只會讓惡魔泥足深陷,走向毀滅。在詩人創作的那個時代,無止境的追求與詩人所信仰的清教主義思想相背馳。清教崇尚簡約樸素的風格,主張信奉上帝來保持內心的寧靜。彌爾頓作為虔誠的清教教徒意識到并得壓抑這一無窮追求的思想。而長詩中撒旦懷著自私利己的動機,追求錯誤的東西,只是欺騙自己而已。
三、結語
總之,撒旦的本質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惡魔。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始終是魔鬼的化身。帶領眾惡魔發對上帝,誘惑人類走向墮落,撒旦已然是一個鬼鬼祟祟而且陰險狡詐的懦弱者。撒旦的墮落是內心的墮落,不因外在的變化而改變。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他不惜以犧牲人類為代價。所以,撒旦自始至終都被自己的罪惡所奴役,墮落與毀滅也是罪有因得。時代不同,文化環境不同,讀者在自然會對作品產生不同的理解。傳統的觀點認為:結合詩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時代背景,以及滿腔的革命熱情,撒旦是追求自由的英雄化身,這就使讀者不能很好區分人物的本質形象和他的英雄主義光環。那么,應該提醒讀者的是,閱讀也需與時俱進,抓住人物形象的本質才能更好詮釋作品的內涵。
(注:本文系滁州學院科研啟動項目“從失樂園對圣經題材的傳承與超越解讀彌爾頓的宗教思想”,項目編號:2014qd064)
[1]裘小龍.論《失樂園》和撒旦的形象[J].外國文學研究,1984,(1):25-31.
[2]黃德林.《失樂園》中撒旦形象的重新審視[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1):47-52.
[3]杜艷紅.《失樂園》中撒旦形象的重新審視[J].青年文學家,2009,(2):82-83.
[4]徐淑娟.撒旦形象下的藝術:談《失樂園》[J].短篇小說(原創版), 2012,(10):86-87.
[5]彌爾頓.《失樂園》[J].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