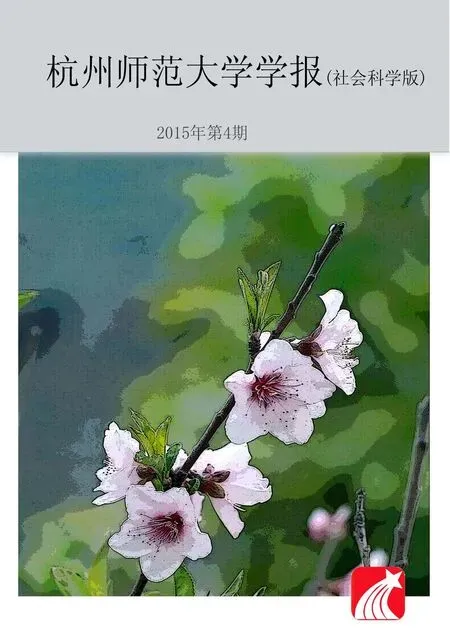同情及其超越
[英]羅杰·克瑞斯普著, 陳喬見譯
(1.牛津大學 圣安妮學院暨哲學系, 英國 牛津; 2.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哲學研究
同情及其超越
[英]羅杰·克瑞斯普1著, 陳喬見2譯
(1.牛津大學 圣安妮學院暨哲學系, 英國 牛津; 2.華東師范大學 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 200241)
摘要:討論同情或憐憫這種情感及其相應的德性,可首先把同情這種情感置于道德概念圖景中,經由批判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即由瑪莎·納斯鮑姆發展出的一種亞里士多德版本的觀點,轉而支持同情作為情感的非認知性概念。由此可以勾勒出另一種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解釋。同情之德性與其他德性的關系由此得以展開,同時也播下了同情之實踐意義的懷疑種子。
關鍵詞:同情;情感;德性;亞里士多德;納斯鮑姆
同情(compassion)在情感(feeling)或情緒(emotion)①譯者注:原文feeling和emotion經常同時使用或混淆使用,基本沒有區別,本譯兩者一般都譯作“情感”,偶爾分別譯作“情感”和“情緒”。中的不尋常之處在于,這同一英文單詞既用于情感或情緒,又用于相應的德性(相比較害怕/勇氣[fear/courage]、憤怒/和氣[anger/even temper]、快樂/節制[pleasure/temperance而言)。這或許是因為人們傾向于認為感到同情總是或幾乎總是值得贊賞的。本文的目的之一是表明這種傾向的誤導性,但首要目的在于考量這一情感或情緒本身的本質。
首先,讓我試著把同情置于相鄰的道德概念圖景中。同情(compassion)與可憐(pity)、感同身受(empathy)和同情(sympathy)的關系如何?我簡短提下亞里士多德關于同情的解釋。亞里士多德的eleos的傳統翻譯是pity,不過,我跟隨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②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p.301-302.又見Kimball.APleaforPity.Philos Lit , 2004. p. 303, Kimball注意到,“pity”和“compassion”直到新近才大致同義。不取這一術語,部分是因為其屈尊或輕蔑的現代涵義。可憐現在也經常被認為是膚淺的和動機上無效的。一個人對乞丐感到難過,卻忽視他們,這更應該說是感到可憐(feel pity);然而,一個人停下來去幫助他們卻是感到同情(feel compassion)。斯蒂芬·夏皮羅(Stephen Shaprio)論殘疾人公民權利的書《不要可憐》(No Pity )完全不能叫做“不要同情”(No Compassion)。[1](p.2)“感同身受”(empathy)的用法有時大略等同于“同情”(compassion or sympathy)。但是,我們應該再次留意納斯鮑姆的有益規定,感同身受在于對他人經驗的任何種類的想象的重構,而無關乎任何諸如它是好的、壞的或中性的評價。通常,感同身受的重構會涉及同情,但是,就我的理解,同情不一定需要感同身受,因為同情可以在他人的痛苦和悲傷出現時取得純粹痛苦和悲傷的原始形式,而無需任何想象的重構(就像在嬰兒的例子中)。sympathy和compassion的共同結構使得我們認為它們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存在一種微弱意義的同情(比如:“我贊同[sympathy]你的目標,但是……”);但是,如果就我們對他人苦境真正感到悲傷而言——正如18世紀哲學作品中經常談及的那樣——那么,sympathy與compassion就是一回事。然而,我們確實需要為這種情形留有概念空間,即我們消極反應,沒有任何的感到悲傷。例如,想想亞當·斯密有關中國地震的例子,這是納斯鮑姆自己[2](pp.360-361)討論過的。1556年的中國大地震造成了830,000人的死亡,超過了任何地震的歷史記錄。彼時中國人經歷的傷痛我斷定非常糟糕,但是,一如斯密所言,做此判斷并未導致我有“真實的心神不安”。類似地,人們經常為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am)定期捐款,但對他人的遭遇沒有任何地感到悲傷,僅僅是認為這樣做是好事。我稱之為慈善之事。
迄今為止,對同情最有影響力的解釋是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提出的。近來持續不斷地對同情的考察,以一種修正的形式為此解釋辯護的是納斯鮑姆,首要的是她的《思想的劇變》(UpheavalsofThought)。[2]納斯鮑姆的討論含有許多洞見,但有幾個亞里士多德立場的主要成分是有問題的,因為她總體上反對亞里士多德解釋中的非認知性因素,而贊成斯多葛派有關情感的認知主義觀點。她同樣未能認識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對德性之本質的總體解釋,潛在地服務于一種更為綜合與平衡的有關同情作為德性的觀點。現在,在更為總體上反思情感在規范倫理學和知識論中的作用的結論之前,讓我嘗試為這些主張辯護。
亞里士多德對同情(eleos/compassion)的定義如下:
同情是對明顯的壞事(evil)*譯者注:這里的evil有“惡”、“壞事”、“不幸”、“災禍”、“倒霉”等含義,本文譯為“壞事”,因為“壞事”可涵蓋以上所有情形。的一種傷痛,這種壞事具有毀滅性或令人痛苦,它發生在一個不該遭受(doesn't deserve)的人身上,并且,人們會料想它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與己相近的某人身上,當它來臨時。[3](PP.1385b13-16)*這段全文的英文翻譯為作者自己所譯。
此刻,我只要你們注意在此提到的包含在同情中的痛苦或悲傷。稍后對此會有詳論。納斯鮑姆[2](p.306)在亞里士多德的定義中發現了同情的三個“認知性必要條件”:(一)嚴重性條件:壞事(evil)*納斯鮑姆的意思是指神學家所謂的“自然”的惡(“natural”evil)。必須被認為是重要的而非瑣屑的。(二)應得條件:壞事必須被認為是不該遭受的。*Leonard Kahn向我指出,如果加上“或者比該受的更為嚴重”,那么,這個必要條件將會更加合理。(譯者注:此所謂“應得條件”的實質是“不應得條件”。)(三)類似可能性條件:壞事必須是這樣的事情,即正在感受同情的人可能認為這種事情會降臨自身或與己親近的某人身上。納斯鮑姆接受前兩個必要條件,但以其自己的另一個條件替換了“類似可能性條件”。我會拒絕所有四個條件。
首先,關于嚴重性條件。*它同樣被Blum L.Compassion. In: Kruschwitz RB, Roberts RC.eds.Thevirtues:contemporaryessaysonmoralcharacter. Wadsworth, Belmont, CA,1987. p. 230; Snow NE.Compassion. Am Philos Q 28,1991.p. 198; 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2000. p. 237所接受。Cannon指出,被認為是瑣屑的事情通常并不瑣屑,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 pp. 99-100.納斯鮑姆說,“我們不會”“可憐某人,他丟失了一件瑣屑的物件,比如一只牙刷或一個紙夾,甚或是一件容易被替換的重要物件”。[2](p.307)然而,她繼續引用了一份坎迪斯·卡拉克(Candace Clark)[4]在現代美國訴諸同情的研究中的調查對象談及的“苦境”清單。[在此清單中]*譯者注:方括號中內容為筆者所加,便于讀者理解,下同。除了貧困、疾病和蕭條外,我們發現還有“車子麻煩、房屋麻煩(如漏水的屋頂)”和“不舒服(如……交通擁堵)”等。現在,可能是,人們不應該習慣性對他人感到同情,當他們遭遇挫折,而這些挫折與貧困、疾病和蕭條相比似乎不過是瑣碎的。但是,他們應該還是不該同情不是此時要討論的議題。*又見Hestevold HS.Pity. J Philos Res 29, 2004.p. 334。盡管他區分可憐(pity)和同情(compassion),從而否定了前者的“嚴重性條件”。
同情是一種類似害怕或憤怒的情感或情緒,沒有先天理由要求某個突然中斷的臨界點。針對他人的不幸,同情被感覺到,如果他們的不幸較小,那么,默認假定一定是同情感也將較小或微弱。請考慮下兩個例子。其一,你從自行車上跌倒,你的腿被一輛路過的車壓碎,你在創痛中。其二,你的指尖被訂書機夾到,你有輕微的痛苦。為什么我們必須假定我對你在兩個例子中的遭受所感到的傷痛形式反映了種類的不同而非只是程度的不同?*我這里使用復數,是因為感受同一情感有不同的方式:持續性、強烈性等等。
其次,關于應得條件。*可能更合理的條件是,懲罰不僅應得而且正當,因為從應得的懲罰不能得出它應當執行。這里請考慮下塔西佗有關尼祿對基督教的殘暴行為的解釋:“由此,甚至對應受懲戒性懲罰的罪犯產生同情,因為似乎他們被毀滅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滿足一個男人的殘暴”,Tacitus. Furneaux H. ed.Annals, vol 2, ClarendonPress, Oxford (2nd edn.,rev. Pelham H, Fisher C), 1907.15.44。納斯鮑姆說,就我們認為一個人的苦境是其自身的缺點而言,我們會責備他們而不是感到同情。[2](p.311)也就是說,同情本質上涉及這樣一種想法,即他人正在經受的折磨不是自作自受。[5](pp. 330,335)對我來說,這一看法是錯誤的,理由有以下三點。
首先,似乎有相反的例證。*又見Blum L. Compassion. In: Kruschwitz RB, Roberts RC.eds.Thevirtues:contemporaryessaysonmoralcharacter. Wadsworth, Belmont, CA,1987. p. 233; Carr B. Pity and compassion as social virtues. Philosophy 74,1999. pp.411-429 ; Hestevold HS. Pity. J Philos Res 29,2004.pp.333-352再次談及可憐; 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pp 97-110; Weber M. Compassion and pity: an evaluation of Nussbaum’s analysis and defense. Ethical Theory Moral Pract 7, 2005.pp.487-493.請考慮下《舊約》中的上帝,他的“同情并不缺乏”,“雖然他造成了苦難,但是他根據他的仁慈仍會有同情”(La.3.22,32,KJV)。*這個例子同樣給納斯鮑姆的以下主張提供了反例,即:“對自己造成的苦境哭泣純粹是偽善”,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313。然而,她可能被如此理解:偽善僅僅出現在起因該受責備的情形中。但是,我們會認為《舊約》中的上帝該受責備卻不會控訴他偽善。也許同情要求旁觀者相信他不會為壞事而受責備。但是,旁觀者會后悔,然后感到同情。即便沒后悔或遺憾,同樣也是可能的。考慮下某人成功地從巨額的養老基金中騙取部分錢財。他會承認他所為是錯的且該受責備,但并不后悔他的所為,也沒有絲毫懊悔或自責的跡象。不過,當他反思其所為造成的不幸時,他會對那些由于其犯罪而帶來的生活貧困的人感到同情。或者監獄訪問者對囚徒的有同情心的關心,至少在一些案例中,這些囚徒認為他們被公正地關押。或者設想下,一個自身友善卻因誤解而犯了一項“無受害人”的犯罪,比如詐騙大型跨國公司;當此人走進牢房開始服刑(我們相信,完全應該)時,難道我們對他不會感到同情嗎?或者對被其自尊所擊倒的某人,比如安提戈涅的父親克瑞翁,[難道我們不會對他感到同情嗎]?
實際上,亞里士多德自己承認,我們會被極壞之人從好運跌入厄運的故事所感動[6](PP.1453a1-7),但是,亞氏這里所說的品質不是激發同情,而是博愛(philanthropon)。這里的確切意思是什么不是完全清楚[7]( p. 47),但是,根據自然的友善,亞氏相信人對人能感覺到這種友善[8] (PP.1155a16-21),我們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理解其意思。納斯鮑姆自己在回應John Dengh時,承認同情這一情感有道德的與“非道德的”的區分,對前者的分析包含了應得條件,后者則意味著完全聽從情感。[9](p.481)
這里引出我對應得條件的第二個反對理由。因為“完全”聽從感情幾乎是不可否認的,所以,包含應得條件的解釋結果證明是冗余的和太過復雜的。廣而言之,描述情感與德性的最好方法其實就是廣義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把人的生活及其情感的各個方面劃分為不同的領域,然后根據這種劃分為核心的情感和德性提供解釋。[10](pp.133-134,138-139)我說的是“廣義的亞里士多德主義”,亞氏自己有時表現出過度分析的傾向,背離了他作為一個植物學家的原初方法。例如,當他區分慷慨大方的德性(generosity,與給予和持有金錢有關)和高貴宏偉的德性(magnificence,與同一類事有關,只不過在規模上更大)時,亞里士多德獲得了什么優勢?[8](PP.4.1-2)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在每一領域中發明不同的“大規模”德性,比如“超級節制”(與大規模的肉體快樂和痛苦有關)、或者“超級勇敢”(與大規模的害怕和自信有關)?通常,通過放大同一單一領域中的情緒或情感什么也得不到。這當然是真的,我們對某人遭遇的關心可能會消失,當我們發現他是自作自受時。但是,那是有關同情的偶然事實,并不表明其他一些不同的情感或情緒也如此。請考慮以下類比:聽從情感本身通常,雖然并非總是,受到厭惡的阻礙(這當然就是為什么納粹宣傳試圖引起人們對猶太人和其他人的厭惡情感)。這一事實可以被充分考慮而無需假定兩種類型的聽從情感,僅有其中之一關乎非厭惡條件。
我的第三個擔憂是應得條件代表著一種錯誤的注意方向。同情作為一種情感的核心是我們對他人之不幸或苦難所感覺到的。*正如Brad Hooker向我指出,我們應該把“苦難”理解為“對某人是壞事”。不需要把它僅僅理解為一種精神狀態。任何否認這一點的解釋最好被理解為是在討論其他一些情感,如義憤,或者其他德性,如正義。如果我們承認對他人苦難的關心是貫穿不同類型的同情的主要方面,那么,我們全部要做的就是說出這些不同類型中的異同,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問題,如那些所謂的情感或情緒之間的界限問題。納斯鮑姆自己關于情感之本質的認知解釋,就經常引起了這種類型的困難。納斯鮑姆假定任何一種狀態,如果要把它視作一種情感,需要滿足不同條件(后文對此有詳論),這樣一來,她被迫在道德同情、非道德同情(與道德情感一樣,但缺乏應得條件)與機械地聽從情感(feeling)(這根本不是情感[emotion])之間做出區分。[9](pp.482-483)但是,所有這些最好被理解為同一主題的不同變化而不是盡管相關卻分離的情感。
現在討論亞里士多德的第三個條件:類似可能性條件。[11](PP.101-102)亞里士多德談及它的兩種含義。有兩種人不會感到同情,一種是完全被毀滅的人,他們相信不可能再遭受進一步的壞事;一種是認為自己生活很幸福且無法被摧毀的人。[3](PP.1385b19-23)然而,首先請考慮下晚期病人的例子:他相信自己幾小時內即將死去,但他頭腦免于身體痛苦的制約,很清醒,她正在觀看一些毀滅性自然災害的電視新聞報道;看到那些人的遭遇,她深深地被感動了,盡管她真的相信她現在經歷這種災害的幾率是極小的。那些認為自己完全會好運的人又怎么樣呢?根據亞里士多德,他們對他人之苦難的反應將會是傲慢的。
這里請考慮下一個斯多葛派者,他認為唯一的善好在于德性以及他總是且將總會有德性。難道他對其他人不會感到同情,這些人(自身也許完全沒有缺點)最終處于邪惡的狀態?一般而論,亞里士多德和納斯鮑姆為同情描繪了一種太過細節化的認知背景。實際上,你不需要認定所有那么多才會感到同情,正如我們在下面討論非人類中的同情時將會看到的。
類似可能性條件奠基于亞里士多德所假定的同情與害怕之間的聯系,他說:“人們對他人感到同情,當他們自己所害怕的事情發生在他人身上時”。[3](PP.1386a27-29)大衛·康斯坦(David Konstan)很棒地解釋了亞里士多德如此聯系的理由。亞里士多德以假定同情是一種感覺開始,這意味著它要么與快樂要么與痛苦的感覺相關。在此例子中,當然是痛苦,亞氏引入與害怕的關聯來解釋痛苦:對臨近的傷害的料想和印象是一種對痛苦的微弱感知,它本是痛苦的,但程度上次于直接和當下的經驗。[1](p.134)[2](p.316)。
亞里士多德應該會承認的是,一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幾乎自出生就存在于人類和其他動物*例如,見Konstan D.Pitytransformed. Duckworth, 2001. p. 14,參 Hoffman and to Denham;Sherman N. “It is no little thing to make mine eyes to sweat compassion”: APA comments on Martha Nussbaum’s upheavals of thought.PhilosPhenomenolRes68,2004.pp. 463-464,nn. 6-10;De Waal F. Morality and the social instincts. In: Peterson GB.ed.Tannerlecturesonhumanvalues25.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Salt Lake City, 2005.pp.16-22;尤其是其中引用Carolyn Zahn-Waxler的研究:一歲多的小孩會對明顯處于痛苦中的他人提供安慰,以及有證據表明老鼠和猴子中有同情(其中包括倭黑猩猩對一只鳥的安康表現出具有理解力的關心的著名例子)。關于神經科學對情感的論述,見Panksepp J.Affectiveneuroscience:thefoundationsofhumanandanimalemo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8.p.4:“許多古代人演化地獲得了所有哺乳動物所共有的大腦系統,它依舊為人類心靈深刻感受情感的傾向起了基礎作用。這一大腦系統在具有大量認知技巧的人類新大腦皮層出現之前已經演化了很長時間。”最近的研究已經表明,自身感受痛苦和心愛某人所感受的痛苦意識激活了同一種大腦中的情感痛苦電路(Singer T, Seymour B, O’Doherty J, Kaube H, Dolan RJ, Frith CD Empathy for pain involves the affective but not sensory components of pain. Science 303,2004.PP.1157-1162; Singer T.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Neurosci Behav Reviews 30,2006.PP.855-859)。 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證據開始使得對諸如同情這種情感的認知主義解釋的倡導者堅持對痛苦本身也可能采取認知主義的解釋。中的一種被其他存在的不幸或遭受壞事直接感動以及可能即刻感到傷痛的自然能力。
考慮到潛藏在亞里士多德“類似可能性條件”背后的同情與痛苦感之間的聯系,納斯鮑姆自己拒絕了它而以下面第四點來替代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可以稱之為:(四)好生活(eudaimonistic)判斷條件:正在感受同情的人必須把壞事視為他自己目標或目的之規劃的一個有意義的部分。[2]( p.319)
納斯鮑姆宣稱,即使在一些情形中,反思某人相似的脆弱性有助于“好生活的想象”,但是,這種判斷能夠被做出而無需明確聚焦于他人與判斷者的關系:真正的全知全能的神應該知道人類受難的意義而不會考慮它自己的風險或壞前景,真正有愛的神會熱切地關心降臨凡人身上的疾病而無需過多考慮個人的損失或風險。*一個比意向性版本較為溫和的弱版本的好生活判斷條件,可以基于納斯鮑姆這里所說的建構起來,它會主張:一個人一定不樂意把壞事視為她的目標規劃的無意義部分。但是,即使這個版本仍然受到下文反例的挑戰。
好生活判斷條件來自對情感更為總體的好生活解釋。[2](pp.31-33,49-56, passim)因此,如果這個條件在同情的例子中是可疑的,那么,它就會給這一總體的解釋帶來困難。對我而言,“類似可能性條件”的那個反例,略加改編,就能很好地適用于好生活判斷條件的情形。*進一步的批評,見Deigh J. Nussbaum’s account of compassion.PhilosPhenomenol Res 68, 2004.PP.465-470;Cannon L.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 2005.pp102-103.因此,首先考慮下我們的晚期病人,你會記得,他相信自己只有幾小時的生命。設想他現在處于這樣的狀態:太累了而不能從事哪怕是輕微費力的活動,唯有等待生命的結束。從他自己和他人的角度看,他的“目標或目的之規劃”幾乎萎縮到零。他不可能把他電視上所看到的那些人遭遇的壞事視為“正在影響他自己的好生活”,因為他一生中的任何好生活都成過去。但是,我找不出什么好理由來否定他被同情所感動的可能性,這種同情與任何其他人一樣深沉。
我的第二個例子是那個斯多葛派者,他相信其好生活正處于最大可能的程度,而且不受時運變遷的影響。現在假定繼續這種好生活的德性操練是有關心靈的理智德性:對他而言,所有的事情就是沉思。進一步設想他為之感到同情的那個人是一個完全缺乏嚴肅思考的人。現在的情況可能是,這位斯多葛派者為此人不能與他哲學對談這一事實而遺憾。但是,讓我們設想他認為,沉思最好是獨自一人,又或,無論如何他有充足的機會與別人交談。換言之,沒有明顯的方式,在其中,影響他人的壞事影響或能夠影響到他自己的好生活。難道他不會感到同情?我不明白為什么不會?因此,我認為,姑且不論納斯鮑姆拒絕了類似可能性條件的事實,我們看到納斯鮑姆與亞里士多德一樣未能理解親身的、直接感知的同情他人的本質和意義。
根據納斯鮑姆,一種感受要是同情必需滿足三個條件:嚴重性、應得和好生活判斷。我已證明,實際上,沒有一個是必需的。但是,它們三個集合在一起是充足的嗎?如果是這樣,那么,納斯鮑姆自己對同情的解釋(不采納亞里士多德對痛苦的強調)可能是對的,而且,她受斯多葛派影響的認知主義解釋至少在此情況下是正確的。
在納斯鮑姆為其主張(即滿足三個條件對同情來說是充足的)辯護中最有意義的工作是嚴重性條件。[2](pp.322-327)她承認斯多葛派圣徒可能具有我們所說的“人道關懷”,他的感受滿足第二、三個條件,但是,這樣的圣徒將會否認他人的不幸具有重要意義。相反,如果我們設想一個自足的存在,他真的深切地關心世事變遷,并且真的認為那是一件大事……那么,我認為我們確實想說三個條件不僅對人道關懷而且對激起那種情感本身[即同情]都是充足的。[2](p.325)
請注意納斯鮑姆的自足的存在不只認為時運變遷是件大事,這對她而言足夠滿足嚴重性條件。自足的存在關心世事變遷。*稍后,在討論涉及同情的“痛苦”應該是何種類型,納斯鮑姆問道:“但是,這種精神痛苦是什么,如果不是把受難者在意的不幸視為一樁可怕之事?”(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26)再次,[納斯鮑姆]把關心(或在意)的情感與認知某事是壞的結合在一起。這對我來說似乎更加難以否認其感受滿足所有三個條件且懷有關心的某人不是感到同情這一情感,因為在感受同情之“痛苦”的意義上而言,同情的一個明顯(雖然不是唯一的)顯示便是關心。問題是,納斯鮑姆這里所設想的自足的存在是否可能做出嚴重性判斷而不會有那種方式的關心。無疑,他可以——反思下我們自己對遠距離事件(如亞當·斯密的中國地震例子)所做的判斷,我們發現有這種可能。換言之,某人的判斷可以滿足嚴重性條件而不會形成好像同情特征的那種關心。
納斯鮑姆問道反認知主義者頭腦中的痛苦是什么類型。她認為,如果是像胃痙攣的某種東西,那么,堅持認為任何如此特殊的痛苦在每一同情的情形中都得到呈現是不合理的,因為人們感受情感的方式不同,或物理地感受,或現象學地感受。這似乎是對的,某人可以補充說,一旦我們把全部的同情感受納入考慮范圍——比如從嬰兒聽到其他嬰兒哭聲的同情感受到古希臘悲劇見廣識多的閱讀者的同情感受——其方式還會更具多樣性。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在”壞事中的痛苦*比較下Peter Goldie的“朝向[某人]感到”(feeling towards)的觀念Goldie P.Theemotions:aphilosophicalexploration. 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 pp. 4, 16-28, 58-62, 72-83,also Deigh J.Cognitivism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s. Ethics 104,1994.PP.837以及參考Greenspan and Roberts; D’Arms J, Jacobson D. The moralistic fallacy: on the “appropriateness”of emotions. Philos Phenomenol Res 61, 2000.p.67,n.4。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現——純粹原始的不適、關切、焦慮,諸如此類。但是,對我而言,斯密稱之為“人性中的原初(情感)”(斜體為筆者所加)是對的,它們都是為他人之遭遇和苦難而幾乎普遍性地感到傷痛的形式,這解釋和證明了它們可以被歸在“同情”這一單一的類目下。
另一個納斯鮑姆所使用的總體上反對非認知主義者的證明,在同情的例子中,是基于她所說的“無意識”情感的可能性。[2](p.326, passim)她認為某人可能有同情但卻沒有意識到它,比如,當人們不反思其情感時,或者被引導認為真正的男人感覺不到它:“人們可以很好地被思想所驅動,而不會處于任何可覺察的現象學狀態”。
然而,無意識同情對反認知主義者來說并不是個問題,因為無參與的痛苦現象是普遍的且很好地被證實了的。*關于這一普遍現象的絕佳例子,見Goldie P.Theemotions:aphilosophicalexplora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2000. p. 62;?hman A, Flykt A, Lundqvist D. Unconscious emoti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 psychophysiological data, and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In: Lane RD, Nadel L.eds.Cognitiveneuroscienceofemo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0. pp.296-327提供了一種進化論的解釋。實際上,分散注意力的技術是標準的治療痛苦的方法。痛苦還是一樣,但由于主體較少注意它而更多注意其他事情而變得較少痛苦。*這種解釋對于快樂和痛苦的所謂“內在主義”概念來說更為合理,據此種概念,有某種東西類似現象學地貫穿每一種感受。這是英國經驗主義的標準觀點,我在Crisp R. Reasons and the good. Clarendon Press, Oxford,2006.ch. 3. and Crisp R. Hedonism reconsidered. Philos Phenomenol Res 73,2006.PP.619-645為其提供了一些辯護。
總結一下,我已經證明了亞里士多德和納斯鮑姆施于同情的各種認知條件是錯誤的,以及證明了同情的核心在于對他人痛苦或悲痛的非認知因素的痛苦或悲痛。我們可以把納斯鮑姆的解釋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感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的開場白做一比較:
無論人如何自私,其本質中有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則,這些原則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使他們的幸福對他而言成為必要,盡管他從中沒有獲得任何東西,除了領會它所帶來的愉快。這就是憐憫或同情,即我們對他人之不幸而感到的那種情感,當我們要么看到他人不幸時,要么我們通過一種鮮活的方式確信他人不幸時。[12](p. 8)
同情是斯密所恰當的稱為“人性的原初情感”之一。在其最原始的形式上,就像嬰兒似乎悲傷于其他嬰兒的哭聲(所謂的“情緒傳染”[emotional contagion][13]),這種本能的悲傷與其說是由他人之遭遇引起,不如說是置身于他人的遭遇。當它發展后,它會經常涉及(或作為原因,或作為結果)各種不同的其他認知的或非認知的狀態,諸如這樣的信念:失去伴侶是悲傷的、緩解痛苦的欲望、或者不要碰上壞事的愿望。*比如,見Hume D.Green TH, Grose TH.eds. A dissertation on the passions, in his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new edn, vol 2. Longmans, London, 1889. p.157,他把同情定義為對他人幸福的欲望;Piper AMS. Impartiality, compassion, and modal imagination. Ethics 101,1991. p. 743;Snow NECompassion. Am Philos Q 28,1991. p. 197; Carr B. Pity and compassion as social virtues. Philosophy 74,1999. pp. 411, 414; Goldie P.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Clarendon Press, 2000. pp. 213-214.; Cannon L. 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 In: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theor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Lanham, MD,2005.p.103.但是,即使是最后一項對非原始的同情來說也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們在對接受應受懲罰的人的同情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這一點。像害怕或憤怒一樣,同情是基本的人類情感,在所有這些情感的例子中,我們不應當被這樣的事實所誤導,即它們經常以微妙和復雜的形式被感覺到,或者由于復雜的原因而以過分狹隘的和認知主義的方式來看待它們。*這里提下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我們在非人類的動物中經常發現這種類似的復雜的人類情感(Aristotle.Balme DM.ed. Historia Animalium, bks.7-10. Loeb, Cambridge, MA,1991.8.1, 588a18-b3)。
現在我們轉向討論同情的德性。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所謂“中道”(doctrine of the mean)的陳述中,亞里士多德給出了一些與情感相關的品質德性(virtue of character),如:害怕、自信、欲望、憤怒和同情。[8](PP.1106b18-19)令人失望的是,僅僅前四者在“勇氣、節制與和氣”的標題下被詳加討論。但是,中道本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藉此可以建構我們自己[對同情]的解釋。就這些情感而言,亞里士多德繼續說:在恰當(right)的時候擁有它們,關于恰當的事情,朝向恰當的人,為了恰當的目的,采取恰當的方式,就是中道和最好的,這也是德性之事。類似地,在行動中有過度、不及和中道。德性關乎情感和行動,其中過度或不及沒中目標,而中道則被贊揚并切中目標,兩者都是德性的特征。[8](PP.1106b21-27)
這份情感清單誤導了很多評論者去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每一德性都涉及一種特殊的情感,而且,每種德性的領域都根據那種單獨的情感來理解。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例如,慷慨的領域是金錢的贈與或獲取,它非常清晰地具體化了亞里士多德這里所陳述的觀點,即德性既關乎情感,也關乎行動。因為德性是一種涉及理性選擇的狀態[8](P.1106b36),任何德性一定既關乎情感,也關乎行動。因此,有同情心的人不僅感到同情,而且也同情地行動。
當他尋求理解人性時,如前所言,亞里士多德的一般方法是,尋找人類生活中廣泛而有意義的領域,然后對每一領域提出合適的解釋。我們已經看到這一方法在德性中的運用:亞里士多德這里提到的情感或情緒對于任何人而言全部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任何人都需要知道他們應該如何去調節。
由于亞里士多德把每一種德性置于過度或不及之間,許多人被引導認為,總是有兩種惡德對應于每一德性。這是另一種誤解。沒中目標有很多種方式,盡管每一種方式結果證明是要么是過度的形式,要么是不及的形式;但是,我們可以在任一形式或兩種形式中都發現大量的惡德。[8](PP.1126a8-31)這并非事實——再次,它經常被這樣認為——即每種品質都可以被安置在過度與不及的范圍里。[實際上],一個人的品質可能同時結合了過度或不及,以至于這個人最終有兩種相反的惡德。這一點在慷慨的例子中看得很清楚:向錯誤的人贈與金錢(這是過度)很可能導致此人不能向恰當的人贈與金錢(這是不及)。[8](PP.1121a30-32)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同情這一情感。其德性在于傾向于對恰當的事情,在恰當的時間等等感到同情。什么是其過度呢?具有吸引力的看法是——部分是因為當他給出他的清單時,亞里士多德言及“太多或太少”地感受這些情感——它必定在于傾向于感到過多的同情,再次,許多評論者沿此思路進行思考。但是,實際比這更為復雜:亞里士多德提到的事實不僅僅是數量性的,而且涉及(例如)在恰當的時間感到這種情感。在錯誤的時間感到同情,這可能是過度的一種形式。但是,也有可能在恰當的時間感到同情同樣錯誤,那是不及的一種形式。同樣地,在其他條件下:例如,對恰當的人感到同情,將會是有德性;然而,對錯誤的人感到同情將會是過度,而對恰當的人未能感到同情則是不及。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在同情的例子中目標有多種方式。不幸的是,不及總是比較常見,我們可以叫它“麻木不仁”。考慮下某些人當他面對遭遇災難的人群圖像時未能感到同情。他們未能感到同情,因為他們應該同情,在恰當的時間,就恰當的事上,對恰當的人群,為了恰當的目的。假如他們感到一陣輕微的同情,除此外再也沒有什么,那么,他們就是在恰當的方式上未能感到同情。過度的惡較不常見,因此,很少聽到“過度同情的”這一術語。*例如,見http://www. deathwithdignity. org/ voices/ opinion/ lewrockwell.11.14.05.asp;以及韋伯(Weber M.Compassion and pity: an evaluation of Nussbaum’s analysis and defense. Ethical Theory Moral Pract 7,2005.p.507)有關尼采對同情之態度的討論。但是,某人向殘疾人顯示屈尊或不恰當的憐憫,這是向錯誤的人,在錯誤的時間感到同情。在此例子中,對殘疾人的同情是需要的,但是,旁觀者對殘疾人感到可憐僅僅是因為他們如何看待殘疾人(而不是因為通過他們如何看待殘疾人而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責任),那么,這就是在錯誤的事情上,以錯誤的方式感到同情。某人或許在恰當的時間,在恰當的事情上,向恰當的人,在恰當的程度上感到同情,但是,她這么做,是因為她通過反思自己是如何有愛心,從而享受她獲得的自我滿足;那么,這種同情就是為了錯誤的目的或出于錯誤的理由。
在對單個德性的討論中,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提煉了惡德的種類。例如,在和氣(even temper)的例子中,他注意到一個人可能很快地憤怒,或者持續很長時間,超過了恰當的時間。[8](PP.1126a13-20)很快發怒的人是易怒的,甚或是暴躁的,但是他至少很快又平靜下來;而慍怒的人卻保持憤怒很長時間。這里,我們再次看到過度同情的不同形式的模型——很快或很容易感到同情的人,與極端地不容易感到同情的人相比,后者一旦感到同情,就會沉湎其中而不忍離去。
同情的德性如何調節行動?作為德性的同情與勇敢、節制、和氣屬于同類范疇,因為其領域首要地是根據情感而非行動來描述。與此相對照的德性如慷慨、誠實守信,其領域分別是根據贈與或獲取金錢、對自己真誠來描述的。我們可以稱其為情感中心的德性與實踐中心的德性(pathocentric and praxocentricvirtues)之間的對照。情感中心的德性的行動特征本身應參考適當的情感來描述。因此,勇敢的行動將會是某種具有適當地感到害怕特征的行動。例如,某人感到過度害怕,很可能使得他不該逃跑時逃跑了;而某人感到不害怕,將會促使他魯莽地沖入敵人的陣線。同樣,具有同情德性的某人,將會以他恰當地感到同情的方式來行動。他將以恰當的方式,提供恰當類型的幫助,而不是忽視他人的苦境,或者提供錯誤類型的幫助,比如以他的關心來溺愛他人。
關于同情的德性及其諸多相應的過度或不及的惡德形式,還可以講更多,但是,我相信,我在這里所說的已經足夠表明,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如何提供有用的模型來安置我們所討論的不同的品質狀態。我當然稍微修正了亞里士多德對情感的解釋,但是,我把德性置于他的中道框架中討論,這引起了一個問題,即這一德性如何與其他品質德性相關。可以找到交集點的明顯地方是友誼的德性,它既不是情感中心的,也不是實踐中心的。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第八、九章對此德性的長篇討論中,亞里士多德把它與正義相關聯,因此,人們會認為它面臨正義德性在中道中所面臨的同類問題(這是眾所周知的),因為似乎沒有情感或行動能夠被中性地描述并且如此適合于中道的框架[14](pp.83-93)。但是,在友誼中實際上有中性的因素,盡管其解釋比在其他任何德性的情形中更為復雜。比如,互相的善意是友誼的特征,正如表達敬意,在每一次實例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一個人在過度或不及的方向上是如何錯誤的。例如,對錯誤的人感到善意,或者未能以恰當的方式表達敬意。進而,很容易看出同情的情感與行動是如何與友誼密切相關。對恰當的人,以恰當的方式感到同情,經常被發現與善意相連。在互相支持和增援的關系中,同情所需要的行動通常就是友誼所需要的行動。
亞里士多德自己宣稱,同情需要距離,在壞事降臨親近之人的情形中,我們感到的是害怕:因為這個理由,他們說,雅瑪西斯(Amasis)在看到其兒子被帶向死亡時沒有哭泣,但是在看到其兒子的朋友乞求時卻哭泣了。后者激起了同情,前者則是恐怖。恐怖之事不同于激起同情的事。它容易趕走同情并通常促使產生其對立面。*見Herodotus. Hude C.ed.Historiae. Clarendon Press, Oxford,1908.3.14。亞里士多德似乎混淆了雅瑪西斯和他父親。相關討論,見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2000.pp.342-343。[3](PP.1386a20-24)
亞里士多德在此有關恐怖的說法是對的,但是,他把恐怖與壞事發生在親近的人身上相關聯則是錯誤的。發生在某些陌生人身上的恐怖同樣會使我的同情能力癱瘓,至少是暫時性的。在初始震驚平息之后的情形中,對親近的朋友或親屬會感到同情。設想下雅瑪西斯的兒子,不是被拉去處決,而是死于罹患數月的疾病。
另一個與同情密切相關的亞里士多德的德性是慷慨大方及其同類高貴宏偉,后者本質上是大規模的慷慨大方。正如我提到的,慷慨大方沒有情感特征,但是,慷慨大方的行動通常為同情所促使。在其他德性的例子中,重疊較稀罕:勇敢、節制、和氣、才智等等。但是,這些德性經常起到了執行者的作用,促使具有同情心的人感到同情或同情地行動,當他們應該如此時(例如,戰場上的勇敢、私人生活中的和氣)。
最后,同情如何與善良(kindness)、仁慈(benevolence)或行善(beneficence)的德性相關,這些德性在當代德目表中當然比亞里士多德那里占據更為突出的位置?一旦去掉嚴重性條件,在下面的方式上,同情很自然地被認為是善良的一種。同情的焦點在于他人的苦難,而善良的范圍則更寬,以至于善良之人會很好地被驅使去幫助已經做得很好的人去做得更好。然而,同情被認為只有在此種情況[即有苦難觀念的呈現]下才會感覺到,[比如下面這兩個例子]。考慮下Scott Hestevold的丟失彩票的絕佳例子: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即你曾經贏得一張全國性彩票,但是你沒有檢查你的號碼而未能索取獎金。我也知道,雖然你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時候,你無能力贈送你的伴侶你想給他的禮物,或者向你的孩子提供你認為最好的教育。當我設想你的生活[因為中獎]本可以發展得更好時,我會對你感到同情。但是,即便在這里,苦難的觀念還是呈現了。你已經從損失中受苦并且還得受苦。但是,麥克塔伽(J.M.E. McTaggart)的貓又如何呢?麥克塔伽據說對他的貓感到可憐,僅僅因為它是一只貓——從貓的標準看,它的生活本該可以更好。然而,即使在這里,我想如果我們要對麥克塔伽做一有意義的回應,我們也可以以苦難來給予回答。他的貓受苦于它沒有更高的品質(這是貓本可有的,比如大腦本可發展得比目前好)。那是一種古怪類型的苦難,但是,也許麥克塔伽的同情就是一種古怪的同情。
善良很好地涉及同情這一情感,并被它所促使而行動。但是,善良更加寬泛,不僅在于善良之人無需經由回應他人苦難而被驅使去幫助他人,而且在于善良可以在行動中被單獨地發現,這種行動被純粹的義務感而非體貼的或其他各種各樣的關心所驅使。如此,善良或許是實踐中心的,它的焦點是幫助他人。仁慈,即一般地愿望他人進展好,不可能是實踐中心的。愿望也不是一種情感。因此,我們這里需要其他范疇,或許可以叫做欲愿中心的(orexocentric)或基于愿望的德性(wish-based viryues)。這一范疇可涵括希望和仁慈。
具有同情心的人會感到同情并同情地行動,去減輕他人的苦難和不幸,在恰當的時間,向恰當的人等等。但是,這里的恰當(rightness)的標準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完全開放性這一事實表明,德性倫理學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是如何在兩個層面發揮功能:形式的和實質的。在形式層面,我們有中道。在實質層面,我們有具體的理論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情形下什么使得情感和行動是恰當的。亞里士多德自己非常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區分,他說,提供中道作為一種實質性的倫理建議,就好像告訴病人他應該接受醫學所要求的治療一樣。[8](PP.1138b18-34)在高尚(noble)觀念的中心,他確實提出了一種關于恰當的理論,但是,當涉及亞里士多德的有德之人會像什么時,結果表明他(廣義而言)很符合亞里士多德自己時代的貴族理想。這種依附于常識道德中的守舊觀念在當代德性倫理學家的著述中也能看到,他們傾向于為常識道德辯護,并反對更為激進的不偏不倚的功利主義和康德主義的理論。但是,在形式層面,沒有什么會阻止功利主義者和康德主義者提倡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作為倫理學的一個參照體系。
那么,倫理學理論是否應該尋求吸收同情,正如在我們自己的常識道德中所理解的那樣?很清楚,關于同情,有很多值得贊賞的。同情使我們領會他人正在受苦,領會這是具有實踐意義的一樁事,以及一般而言同情促使行動做得更好,有時比不行動做得更好。但是,同情具有偶然的演化和文化歷史的因素很明顯,盡管對于其歷史是什么尚未形成一致意見。因此,我們應該對此主張表示懷疑,即同情完全精準地追尋到了倫理學的真理。
考慮下以下四種方式,在其中,同情可能不可靠。*參Slote M. Moral sentimentalism and moral psychology. In: Copp D.ed.Theoxfordhandbookofethical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2006.pp.227-228有關Batson and Hoffman的論述。Slote自己傾向于接受這些“偏見”(bidses),或者用他自己的詞“偏好”(preference),承認他的道德動機的理想形式是完全發展了的人類的感同身受(empathy)。這里的要點是,一個人的規范性認識論至少受其一階觀點的影響。在一階層面認為不偏不倚性合理的人不太會接受帶有偏向性的情感在認知上是可靠的。其一,它具有偶然性。取決于早上我什么時候打開收音機或我閱讀何種報紙,我可能被感動去幫助一些有關精神健康的慈善團體,如PDSA,或者幫助身邊需要手術搶救的人。其二,它的線索通常繞過了理性。一部電視上的災難片比報紙上顆粒狀的圖像可能更加感動我,年紀輕的小孩的圖像比年紀稍大的小孩的圖像可能更加感動我,小孩眼睛的圖像比其整個身體的圖像可能更加感動我——而且,更重要的是,與我親近的人的苦難比遠距離遭受更大苦難可能更加感動我(比如斯密的中國地震例子)。與此相關,其三,同情被觸發是根據這些苦難與觀察者的親近關系如何,這取決于觀察者的感知。這里,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為同情的缺乏提供了一個明顯的例證,[在其中,納粹]就好像對待高級靈長類動物那樣做了很多實驗。其四,同情有各種各樣不確定的障礙。我就“應得條件”已經講了許多,在許多情形下[如前文所說的自作自受],它們被普遍正當地認為妨礙了同情。*這個和先前的觀點再次得到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證據的支撐,見Singer T. The neuronal basis and ontogeny of empathy and mind reading: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Neurosci Behav Reviews 30,2006.p.859。這似乎繼續是錯誤的,不僅對于那些發現自由意志論或“軟”的決定論難以接受的人來說,而且對于這樣一些人來說也是如此,他們認為自由意志問題如此具有爭議,以至于應該暫時假定那些犯了所謂錯誤的人沒有錯。另外幾乎普遍的妨礙同情的是我們傾向于服從權威。在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實驗的受測者中,當他們的“受害者”伴隨明顯痛苦而尖叫時,大多數人繼續提升電壓,小部分人的反應是緊張地笑出來。①譯者注: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傾向于服從權威,而在面對他人遭受苦難時較少表現出同情。
因此,同情本身不可能為我們的義務(就回應他人受苦而言)提供深刻理解的可靠來源。同情可以讓我們對苦難有所警覺,并且經常提供一種可敬的動機來源去減輕它。但是,由于它的不可靠性,我懷疑最終真正有德之人感到的同情不會格外強烈,或許相當稀薄,他會通過如何盡己所能去幫助的理性思考來回應減輕他人的苦難。②就先前草稿和討論的評論而言,我要感謝Fillenz, Leonard Kahn, David Konstan, 以及2007年英國倫理學理論協會(British Society for Ethical Theory)會議的參與者。
參考文獻:
[1]Konstan D.PityTransformed[M]. London :Duckworth , 2001.
[2]Nussbaum M.UpheavalsofThough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Aristotle.ArsRhetorica[M]. Ross WD.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59.
[4] Ben-Ze’ev A.TheSubtletyofEmotion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5]Clark C.MiseryandCompany:SympathyinEverydayLife[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6] Aristotle.DeArtePoetica[M].Kassel R.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5.
[7]Konstan D.PityTransformed[M]. London :Duckworth, 2001.
[8]Aristotle.EthicaNicomachea[M]. Bywater I. ed. Oxford:Clarendon Press, 1894.
[9]Nussbaum M.Responses[J].PhilosPhenomenol,2004,(68).
[10]D’Arms J, Jacobson D.The Significance of Recalcitrant Emotion (or Antiquasijudgmentalism)[M]//PhilosophyandtheEemotions,RoyalInstituteofPhilosophysuppl. 52.Hatzimoysis A.e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Cannon L. Compassion: a Rebuttal of Nussbaum[M]//FeministInterventionsinEthicsandPolitics:FeministEthicsandSocialTheory. Andrew BS, Keller J, Schwartzman LH.eds. Lanham, MD: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12]Smith A.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M]. Raphael DD, Macfie AL.eds.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76.
[13]Hatfield E, Cacciopo J, Rapson R.Emotionalcontagion[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Williams B.JusticeasaVirtue,repr.inhisMoralLuck[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責任編輯:吳芳)
Compassion and Beyond
Roger Crisp1, tr. CHEN Qiao-jian2
(1. St. Anne’s College & Faculty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s a discussion of the emotion of compassion or pity, and the corresponding virtue. It begins by placing the emotion of compassion in the moral conceptual landscape, and then moves to reject the currently dominant view, a version of Aristotelianism developed by Martha Nussbaum, in favor of a non-cognitive conception of compassion as a feeling. An alternative neo-Aristotelian account is then outlined. The relation of the virtue of compassion to other virtues is plotted, and some doubts sown about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Compassion; emotion; virtue; Aristotle; Nussbaum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7
中圖分類號:B8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5)04-0059-10
作者簡介:羅杰·克瑞斯普(Roger Crisp,1961-),牛津大學圣安妮學院暨哲學系教授,主要從事倫理學、政治哲學和古希臘哲學研究;陳喬見(1979-),男,云南陸良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從事儒家哲學、倫理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