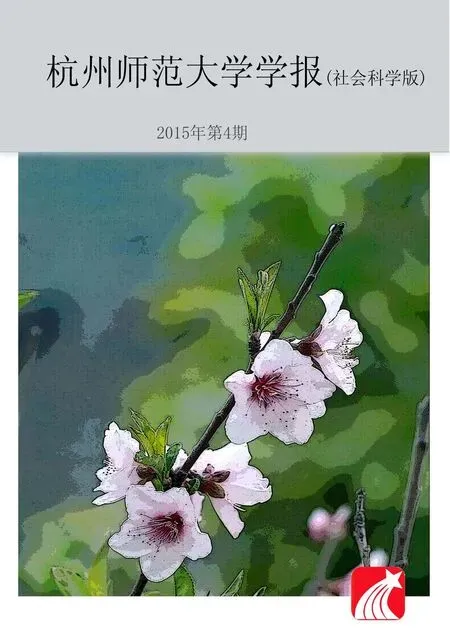跛行的哲學(xué)——梅洛-龐蒂的“哲學(xué)贊詞”或哲學(xué)辯護(hù)
張堯均
(同濟(jì)大學(xué) 哲學(xué)系, 上海 200092)
哲學(xué)研究
跛行的哲學(xué)
——梅洛-龐蒂的“哲學(xué)贊詞”或哲學(xué)辯護(hù)
張堯均
(同濟(jì)大學(xué) 哲學(xué)系, 上海 200092)
摘要:《哲學(xué)贊詞》盡管以“哲學(xué)贊詞”為題,但實(shí)際上卻是對(duì)哲學(xué)及哲學(xué)生活的辯護(hù)。哲學(xué)為什么要辯護(hù)?梅洛-龐蒂主要從認(rèn)識(shí)、表達(dá)、行動(dòng)(其中也涉及到哲人與大眾的沖突、哲學(xué)的現(xiàn)實(shí)處境等)這三個(gè)方面出發(fā),對(duì)哲學(xué)知識(shí)的曖昧性、哲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的潛在沖突及哲學(xué)與其他學(xué)科的復(fù)雜關(guān)系等作了深入闡發(fā),最后指出哲學(xué)的生活具有“跛行”的特征,從中也體現(xiàn)出了梅洛-龐蒂哲學(xué)自身的“曖昧性”特征。
關(guān)鍵詞:梅洛-龐蒂;《哲學(xué)贊詞》;“哲學(xué)辯護(hù)”
標(biāo)題出自梅洛-龐蒂的“哲學(xué)贊詞”一文①梅洛-龐蒂在“哲學(xué)贊詞”這一講稿中兩處提到了哲學(xué)或哲學(xué)家的“跛行”,盡管他用了不同的詞,參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59, p.61。,這是梅洛-龐蒂1952年當(dāng)選為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時(shí)發(fā)表的就職演講稿。然而,耐人尋味的是,盡管這場(chǎng)講演題為“哲學(xué)贊詞”(élogedelaphilosophie,或譯“哲學(xué)頌”),但在講演稿中,從頭至尾都沒(méi)有出現(xiàn)“贊頌”一詞,與此相反,它倒是明確地提到了對(duì)哲學(xué)的“辯護(hù)”[1](P.59)。因此,這與其說(shuō)是一篇“哲學(xué)贊詞”,毋寧說(shuō)是一篇“哲學(xué)辯護(hù)”。
但是,既然是一種辯護(hù),梅洛-龐蒂又為何要冠之以“贊詞”呢?或者說(shuō),“辯護(hù)”能夠成為一種贊頌嗎?更進(jìn)而言之,如果它是一種辯護(hù),那么哲學(xué)又因何需要辯護(hù)呢?
對(duì)第一個(gè)問(wèn)題,我們也許可以說(shuō),是這一講演本身的性質(zhì)需要它采取這樣一個(gè)肯定性的標(biāo)題。盡管法蘭西學(xué)院一貫強(qiáng)調(diào)它的自由原則②梅洛-龐蒂在他的演講的一開(kāi)頭就提到:“自法蘭西學(xué)院創(chuàng)立伊始,其職責(zé)就不是給予其聽(tīng)眾以既有的真理,而是一種自由研究的理念。”Merleau-Ponty, 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13.,但它也有它的某些習(xí)慣性做法。比如說(shuō),在新院士的就職演講詞中,它要求個(gè)人表達(dá)其由衷的感激,而且它還“必須對(duì)(取其而代之)的去世的院士進(jìn)行真實(shí)可信的頌揚(yáng),并對(duì)其著作進(jìn)行正確無(wú)誤的分析”[2](P.36)。梅洛-龐蒂的演講詞無(wú)疑也遵循了這樣一種規(guī)范,我們可以看到,他一開(kāi)頭就表達(dá)了對(duì)法蘭西學(xué)院的景仰,甚至覺(jué)得自己不配廁身于其中;他也表達(dá)了他的榮幸和感激。緊接著,他說(shuō):“我能做的最好的感謝無(wú)疑是在你們面前考察哲學(xué)家的職能,首先是我的前任們已經(jīng)恢復(fù)和履行的職能,同時(shí)這種職能還體現(xiàn)在考察哲學(xué)的過(guò)去及其現(xiàn)在。”[1](P.14)他隨后提到的他的哲學(xué)家前任主要是拉威勒(Louis Lavelle,梅洛-龐蒂接任的就是他的席位)和柏格森(Heri Bergson)。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梅洛-龐蒂明確地把對(duì)哲學(xué)家職能的考察與對(duì)哲學(xué)本身的考察并列在一起,也就是說(shuō),哲學(xué)與哲學(xué)家密不可分,而哲學(xué)家又體現(xiàn)為哲學(xué)家的生活,這樣,哲學(xué)最終與哲學(xué)家的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哲學(xué)就是一種關(guān)于哲學(xué)的生活。因此,如果哲學(xué)值得贊頌或需要辯護(hù),那么,實(shí)際上值得贊頌或需要辯護(hù)的就是一種哲學(xué)的生活。
那么,哲學(xué)家的生活又如何與眾不同呢?
一
在其講演的一開(kāi)頭,梅洛-龐蒂就承認(rèn),他是一個(gè)了解“自己的內(nèi)在混亂的人”,混亂的根源在于“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個(gè)經(jīng)典的哲學(xué)自述,無(wú)疑讓我們想起蘇格拉底,而事實(shí)上梅洛-龐蒂也的確講到了蘇格拉底)。正是因此,他覺(jué)得自己不配廁身于這“永垂不朽”的學(xué)術(shù)萬(wàn)神殿中,但另一方面,正由于他明白自己的內(nèi)在混亂,他也從這一混亂中解脫出來(lái)了。在這個(gè)意義上,他又是特別適合于這一神圣之所的,因?yàn)榉ㄌm西學(xué)院素以“自由研究”著稱,而哲學(xué),只有哲學(xué)才真正契合于這一理念,“這是因?yàn)檎軐W(xué)的非知(non-savoir)達(dá)到了它的這種研究精神的頂點(diǎn)”[1](P.13)。哲學(xué)之為哲學(xué),正在于它以探索整全為己任,但哲學(xué)的“非知”或“自知其無(wú)知”則又使它不把任何既有的事實(shí)看作真理,由此才保證了它向整全的自由敞開(kāi)。因而,“造就一個(gè)哲學(xué)家的是不停地從知導(dǎo)向無(wú)知,又從無(wú)知導(dǎo)向知的運(yùn)動(dòng),以及在這一運(yùn)動(dòng)中的某種寧?kù)o……”[1](P.14)
這里的“寧?kù)o”就是指從開(kāi)頭所提到的“內(nèi)在混亂”中解脫出來(lái)。之所以說(shuō)當(dāng)意識(shí)到這種混亂時(shí)混亂就被超越了,是因?yàn)樵谶@一轉(zhuǎn)向中,混亂自身成了主題。梅洛-龐蒂把這一意義莫名的混亂稱為“隱晦”(ambigu?té)*Ambigu?té是梅洛-龐蒂哲學(xué)的基本特征,或者可以說(shuō)是他的哲學(xué)標(biāo)簽。這一標(biāo)簽似乎有三個(gè)來(lái)源:首先是Ferdinand Alqui關(guān)于梅洛-龐蒂的長(zhǎng)篇評(píng)論用了“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té”這一標(biāo)題(載Fontaine,1949年4月號(hào)),隨后,由Alphonse de Waehlens撰寫(xiě)的關(guān)于梅洛-龐蒂哲學(xué)的第一部研究著作也用了這一標(biāo)題(UnePhilosophiedel’ambigu?té,Paris,Editions Beatrice- Nauwelaerts, 1951)。最后,當(dāng)《行為的結(jié)構(gòu)》于1949年出第二版時(shí),梅洛-龐蒂把Alphonse de Waehlens的一篇同樣題目的評(píng)論文章放在前面作該書(shū)的前言,借此表明他本人也接受了對(duì)他的哲學(xué)的這一標(biāo)簽。參S.F.Sapontzis.A Note on Merleau-Ponty’s‘Ambiguity’, inPhilosophyandPhenomenologicalResearch, Vol. 38, No.4(Jun., 1978),note 1.在梅洛-龐蒂的哲學(xué)中,Ambigu?té至少有如下幾層含義:首先是指意義(主要指“知覺(jué)意義”或“表達(dá)意義”)的多樣性,不確定性,甚至歧義性,進(jìn)而表明意義的敞開(kāi)性和生成性。當(dāng)涉及這種含義時(shí),我在本文中一般把它譯為“隱晦”。其次也指哲學(xué)自身位置的不確定性,哲學(xué)無(wú)處不在而又無(wú)所在。最后,梅洛-龐蒂也用這個(gè)詞來(lái)表明行動(dòng)或立場(chǎng)的不確定性。當(dāng)涉及后兩層含義時(shí),我把它譯為“曖昧”。。隱晦是不可消除的,它根植于我們?cè)谑来嬖诘奶幘常梢哉f(shuō)是我們的生存有限性的體現(xiàn)。但是有兩種不同的隱晦:一種是好的隱晦,一種是壞的隱晦。哲學(xué)的任務(wù)不在于消除隱晦,而是以隱晦為主題,把隱晦帶入到光亮中,賦予它以意義或方向,從而消除它所帶來(lái)的不確定的威脅。這就是好的隱晦。相反,壞的隱晦則“滿足于接受隱晦”[1](P.14)而不試圖超越它,這是一種真正的混亂。
哲學(xué)因而與隱晦不可分解。梅洛-龐蒂認(rèn)為,能夠引向那種“好的隱晦”的人是大哲學(xué)家。他把他的兩位前任拉威勒和柏格森都看作是這樣的大家。拉威勒盡管以“存在的整體”(tout de l’être)或“總體的存在”(un être total)作為研究的對(duì)象,但他非常清楚,要通達(dá)這一存在,必須經(jīng)由我們自身,正是因此,他提出了“參與”(participation)和“在場(chǎng)”(présence)的概念,以此來(lái)界定我們自身與整體存在之間的關(guān)系。顯然,這種關(guān)系是曖昧的:一方面,我們屬于整體存在,后者預(yù)先就宣告了我們之所是和能是,另一方面,整體存在又離不開(kāi)我們,沒(méi)有我們,它就不再是整體存在,在這個(gè)意義,它也屬于我們。
在柏格森那里,同樣存在著這種曖昧性。他提出了著名的“直覺(jué)”概念。哲學(xué)通過(guò)直覺(jué)與事物交融,從而達(dá)到對(duì)存在的一種整體把握。然而,在梅洛-龐蒂看來(lái),這只是柏格森主義的表面。真正的直覺(jué)并非指哲學(xué)家消融在存在中,而是回到意識(shí)的直接預(yù)料或直接經(jīng)驗(yàn)中去。在直覺(jué)中,我們并不是走出自身以通達(dá)事物,相反,我們是更深地潛入到自身,體驗(yàn)到自身的綿延,并在我的綿延中體會(huì)事物的綿延和宇宙的綿延。這種作為綿延的直接經(jīng)驗(yàn)本身就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地生成和展開(kāi)的過(guò)程,因此,直覺(jué)也是處在發(fā)展中的,它內(nèi)在地包含著“否定性和隱晦性”的因素。但直覺(jué)并不神秘,梅洛-龐蒂甚至說(shuō),直覺(jué)就是我們的知覺(jué)的深入和擴(kuò)大。如此,梅洛-龐蒂就把他自己的哲學(xué)工作與其前任的工作聯(lián)系在一起了。“哲學(xué)家的絕對(duì)知識(shí)就是知覺(jué)。……知覺(jué)奠定了一切,因?yàn)榭梢赃@樣說(shuō),它教導(dǎo)給我們一種與存在的糾纏不清的關(guān)系:存在就在我們之前,可是它從里面通達(dá)我們。”[1](P.24)
然而,單純的知覺(jué)是不夠的。在另一個(gè)地方,梅洛-龐蒂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單純的知覺(jué)只是一種“壞的隱晦”,因?yàn)樗皇歉嬖V我們一種“有限與無(wú)限、內(nèi)在與外在的混合物”。[3](P.290)為了消除混亂,我們必須借助于語(yǔ)言:“在表達(dá)現(xiàn)象中存在著一種好的隱晦,一種能夠?qū)崿F(xiàn)在我們只是觀察各種孤立的因素時(shí)看起來(lái)不具有可能性的事情的自發(fā)性:這種自發(fā)性把單子的多樣性、把過(guò)去和現(xiàn)在、把自然和文化匯聚到一個(gè)單一的整體中。”[3](P.290)只有表達(dá)才能解開(kāi)混亂的知覺(jué)之網(wǎng),從中抽繹出順暢的意義絲線。因此,經(jīng)受著隱晦之混亂的哲學(xué)家如果要擺脫這種威脅,就離不開(kāi)表達(dá)。梅洛-龐蒂說(shuō),拉威勒和柏格森都明白這一點(diǎn),所以他們最后都走向了一種表達(dá)哲學(xué)。
事實(shí)上,表達(dá)也是知覺(jué)內(nèi)在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和結(jié)果。在知覺(jué)中,現(xiàn)象自身就分泌著意義,而表達(dá)則是這種意義的凝化和結(jié)晶。“人們?nèi)ザ匆?jiàn)事物本身的意向越是強(qiáng)烈,我們?cè)绞强吹绞挛锝逡垣@得表達(dá)的現(xiàn)象和我們借以表達(dá)事物的語(yǔ)詞充塞于事物與我們之間。”[1](P.27)
因此,知覺(jué)自然地導(dǎo)向表達(dá),只有在表達(dá)中,知覺(jué)到的意義才獲得一種具體的在場(chǎng),意義的進(jìn)一步的積淀和傳播也才有可能。更進(jìn)一步說(shuō),無(wú)論是知覺(jué)還是表達(dá),都呈示著我們與存在的關(guān)系。知覺(jué)原初地就貼近存在,它見(jiàn)證了我們與存在的一體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甚至因過(guò)于貼近和致密,反而使存在本身晦暗不明,甚至被我們忽略(這就是梅洛-龐蒂“知覺(jué)的隱晦”的原因)。因而,為了使存在的意義向我們涌現(xiàn),我們需要略微松開(kāi)我們與存在之間的這種粘連關(guān)系,表達(dá)正好滿足了這一需要。表達(dá)在我們與存在之間撐開(kāi)了一個(gè)語(yǔ)言空間,它使我們不再面對(duì)面地遭遇存在,它在兩者之間布起了帷幕,它拉開(kāi)了我們與存在之間的距離。也是這一間距使存在恢復(fù)了它的神秘,使我們有得以領(lǐng)會(huì)存在之意義的閑暇。在這個(gè)意義上,語(yǔ)言是通達(dá)存在的必由之途,或者說(shuō),“語(yǔ)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爾)。
但另一方面,表達(dá)與存在的關(guān)系仍是曖昧的,表達(dá)并沒(méi)有消除知覺(jué)的隱晦,而只是把它轉(zhuǎn)變成了另一種隱晦,即使它是一種“好的隱晦”,但它仍然是隱晦,甚至是包藏危險(xiǎn)的一種隱晦。而正視這種隱晦,并坦然地面對(duì)它所隱含的危險(xiǎn),則是哲學(xué)的“奇異性”(étrangeté)之所在。可以說(shuō),唯有哲學(xué)才真正懂得表達(dá)之隱晦的特質(zhì),也只有在哲學(xué)中,表達(dá)之隱晦才達(dá)到了它的最高點(diǎn)。在哲學(xué)的表達(dá)中,“哲學(xué)家與存在的關(guān)系不是觀眾與表演之間的正面關(guān)系,而是一種共謀,是一種傾斜的、暗中的關(guān)系。”[1](P.23)
二
表達(dá),更確切地說(shuō),哲學(xué)的表達(dá)之所以具有危險(xiǎn)性,是因?yàn)檫@種表達(dá)同時(shí)設(shè)定了“進(jìn)行表達(dá)的某一個(gè)人,他要表達(dá)的真理及他對(duì)之表達(dá)自己的其他人。表達(dá)和哲學(xué)的公設(shè)就是要能夠同時(shí)滿足這三個(gè)條件”[1](P.36)。也就是說(shuō),哲學(xué)的表達(dá)涉及的不僅僅是哲學(xué)家與真理的關(guān)系,還有哲學(xué)家與他人的關(guān)系,但這兩種關(guān)系并不總是能夠同時(shí)共存的,甚至可以說(shuō),它們是內(nèi)在地相沖突的。這樣,哲學(xué)家所體驗(yàn)到的曖昧就不再只是一種知覺(jué)的歧義和內(nèi)在的混亂了,它更是人與人之間,或者說(shuō)哲學(xué)家與他人之間的沖突,是哲學(xué)家所信奉的真理與大眾的意見(jiàn)或信仰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是不可消除的,正因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在這篇以頌揚(yáng)為名的演說(shuō)中,梅洛-龐蒂更多的卻是在替哲學(xué)辯護(hù)。
梅洛-龐蒂首先舉了柏格森的例子。柏格森在內(nèi)心里贊賞天主教的教理,但是,作為一個(gè)猶太人,當(dāng)他看到歐洲的反猶主義浪潮洶涌裹卷時(shí),他還是堅(jiān)決地選擇了“留在那些明天將受到迫害的人們中間”,并拒絕了權(quán)力機(jī)構(gòu)愿意為他提供的種種方便。柏格森以他的行動(dòng)證明,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不存在一種他可以不惜一切代價(jià)地追求或擁護(hù)的真理。“我們與真實(shí)的關(guān)系得經(jīng)由他人。”[1](P.37)但我們真的能夠與他人一道通達(dá)真理嗎?當(dāng)人們懇請(qǐng)柏格森寫(xiě)一本關(guān)于他的道德觀的書(shū)時(shí),柏格森卻明確地說(shuō):“從來(lái)沒(méi)有哪個(gè)人被迫去寫(xiě)一本書(shū)。”[1](P.37)這表明,哲學(xué)家既不愿為了真理而放棄大眾,也不愿為了大眾而降低真理的層次,他想同時(shí)維持與這兩者的關(guān)系。這樣,哲學(xué)家的立場(chǎng)就必然是曖昧的:
我既不是根據(jù)真實(shí),也不只是根據(jù)我自己,也不只是根據(jù)他人來(lái)進(jìn)行思考,因?yàn)檫@三者中的每一個(gè)都需要其他兩者,犧牲任何一個(gè)都是無(wú)意義的。哲學(xué)的生命永不停息地在這三個(gè)基本點(diǎn)上得以提升。哲學(xué)之謎(和表達(dá)之謎)在于,生命在自我面前,在他人面前,在真實(shí)面前有時(shí)是同樣的。它們就是為哲學(xué)提供保證的諸環(huán)節(jié)。哲學(xué)家只能依賴于它們。他永遠(yuǎn)都既不接受讓自己對(duì)抗人類(lèi),也不讓人類(lèi)對(duì)抗自己或?qū)拐鎸?shí),也不讓真實(shí)對(duì)抗人類(lèi),他愿意同時(shí)無(wú)處不在,甘冒永遠(yuǎn)都不完全在任何一處的危險(xiǎn)。[1](PP.37-38)
但哲學(xué)家能夠維持這三者之間的平衡嗎?柏格森的例子也許并不是最典型的。他確實(shí)既沒(méi)有放棄對(duì)真理的追求,也沒(méi)有因此而對(duì)抗人類(lèi),同時(shí),他也多少避免了讓人類(lèi)對(duì)抗自己或?qū)拐胬淼奈kU(xiǎn)。但是,這種危險(xiǎn)不是始終存在嗎?應(yīng)該回想起蘇格拉底!
梅洛-龐蒂說(shuō):“蘇格拉底的生與死乃是哲學(xué)家——在他還沒(méi)有受到文學(xué)豁免權(quán)的保護(hù)時(shí)——與城邦諸神,亦即與他人,及由他人力圖提供給他的凝固的‘絕對(duì)’形象之間維持著艱難關(guān)系的歷史。”[1](P.39)從表面上來(lái)看,蘇格拉底的生活無(wú)可指責(zé)。他跟其他人一樣接受城邦的宗教,給諸神獻(xiàn)祭,出席公民大會(huì),在廣場(chǎng)上與人交流,參加保衛(wèi)雅典的戰(zhàn)爭(zhēng),甚至當(dāng)雅典人判處他死刑時(shí),他也拒絕出逃,還論證法律的權(quán)威。但人們?yōu)槭裁催€是贊同處死他呢?
梅洛-龐蒂認(rèn)為,人們指責(zé)蘇格拉底的不是他所做的事,而是他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動(dòng)機(jī)。蘇格拉底確實(shí)信奉宗教,但他為他的這種信奉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釋和理由,而“被解釋的宗教,對(duì)其他人來(lái)說(shuō)就是被取消了的宗教”[1](P.42)。同樣,蘇格拉底順從城邦的法則,但不是出于“國(guó)家的理性”,而是出于他自己的理性。蘇格拉底為他的遵從賦予了一種新的基礎(chǔ),以此暗中取代了早先為城邦及城邦宗教所奠定的基礎(chǔ)。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說(shuō):“人們?cè)诳释淖兎芍凶袷胤桑缤藗冊(cè)诳释推街型度霊?zhàn)斗。”[1](P.40)因此,蘇格拉底的活動(dòng)并不是無(wú)辜的,他有著一種“實(shí)為拒絕的服從方式”。盡管從表面上看,蘇格拉底和其他人一樣,但在其他人眼中,蘇格拉底始終是獨(dú)立的,他的所作所為仿佛受著一種“秘密原則”的驅(qū)使,人們沒(méi)法理解他,當(dāng)然更不能支配他。在雅典城中,蘇格拉底像一個(gè)外鄉(xiāng)人。
蘇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是最典型的哲學(xué)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最典型地體現(xiàn)了哲學(xué)與意見(jiàn)、哲人與大眾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一方面,哲學(xué)需要城邦,哲學(xué)家只有和他人一道才能通向真理,“不存在沒(méi)有他們的真理”。正是因此,即使面臨雅典人的指控,蘇格拉底也拒絕出逃。他一直生活在雅典,他知道他即使跑到別的地方,也不會(huì)更能得到人們的容忍。他也很清楚,雅典是最適合于哲學(xué)存在的地方;也只有在雅典,哲學(xué)才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并能在民眾中產(chǎn)生它的效能。所以梅洛-龐蒂說(shuō):“蘇格拉底拒絕逃跑,這不是因?yàn)樗姓J(rèn)法庭,而是為了更好地否定它。如果逃跑,他就成了雅典的敵人,他就證實(shí)了對(duì)他的判決。如果留下,不管法庭判他有罪無(wú)罪,他都是贏家,因?yàn)樗赐ㄟ^(guò)讓陪審團(tuán)接受他的哲學(xué),要么通過(guò)自己接受判決而證明了他的哲學(xué)。”[1](PP.40-41)蘇格拉底以他自身的言行,把哲學(xué)帶入了“與雅典的活生生的關(guān)系”之中。另一方面,城邦也需要哲學(xué)和哲學(xué)家。“人們正是在哲學(xué)家的世界中通過(guò)理解拯救了諸神和法律,而且,為了將哲學(xué)的領(lǐng)地安置于大地上,需要的恰恰是蘇格拉底這樣的哲學(xué)家。”[1](P.42)
但與此同時(shí),哲學(xué)又超越城邦。城邦滿足于它自己的利益和價(jià)值,哲學(xué)卻試圖把城邦引向更高的善。蘇格拉底不停地向各種各樣的人提問(wèn),但這不是為了顯示他有更高的智慧。他在《申辯》中傷感地說(shuō):“每當(dāng)我讓某人承認(rèn)他的無(wú)知時(shí),旁觀者都以為我知道他們所不知道的一切。”但其實(shí),“他并不比他們知道得更多,他只是知道不存在絕對(duì)知識(shí),而且正是基于這一缺陷,我們才向真理開(kāi)放”。[1](P.43)城邦中的每一個(gè)人都受其偏見(jiàn)的支配,蘇格拉底卻試圖訴諸理性,來(lái)克服他們的偏見(jiàn)。但理性對(duì)于大眾來(lái)說(shuō)是不可見(jiàn)的,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說(shuō),理性于他們只是空疏,虛無(wú)和饒舌。[1](P.42)
因此,哲學(xué)與城邦不可避免地處于一種緊張關(guān)系中。每一個(gè)城邦都是特殊的,而哲學(xué)卻要訴諸普遍的原則。城邦要求人們無(wú)條件地甚至是盲目地服從,而哲學(xué)卻試圖為這種服從提供理由,“但需要理由的服從已經(jīng)是太過(guò)分了”[1](P.42)。城邦借助宗教來(lái)維護(hù)它的神圣性和權(quán)威性,而哲學(xué)卻試圖對(duì)宗教的原則作出解釋,并賦予其一種新的意義,從而暗中破壞了宗教的原有基礎(chǔ)。因此,哲學(xué)的存在對(duì)城邦來(lái)說(shuō)是一種威脅。在哲學(xué)家與他人的關(guān)系中就存在著這種不安,蘇格拉底之死并不是偶然的。
但梅洛-龐蒂認(rèn)為,這種不安對(duì)于哲學(xué)來(lái)說(shuō)是必不可少的,它乃是哲學(xué)的活力之所在。哲學(xué)表達(dá)的隱晦正是這種不安的產(chǎn)物,著名的蘇格拉底式反諷其實(shí)就是這樣一種隱晦的藝術(shù)。真正的反諷利用了在事物中確立起來(lái)的雙重意義,這是哲學(xué)表達(dá)所具有的“好的隱晦”的體現(xiàn)。“蘇格拉底的反諷是與他人的一種有距離然而真實(shí)的關(guān)系。它表達(dá)了這一基本事實(shí):每個(gè)人不可避免地只是他自身,但與此同時(shí)又在他人那里認(rèn)識(shí)自己。反諷試圖解開(kāi)彼此的約束以通達(dá)自由。”[1](P.42)反諷在指向他人的同時(shí)也反涉自身,它通過(guò)揭示人們言行中的矛盾來(lái)激發(fā)思考,進(jìn)而超越其自身的局限。無(wú)疑,反諷也會(huì)刺痛人,使人惱怒,但它以一種輕松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其善意。此外,反諷由于展現(xiàn)了事物和情境所具有的多重意義,因而能給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啟發(fā),也頗為有效地掩蓋了哲思本身的尖銳性。總而言之,蘇格拉底的反諷既是一種保護(hù)自身的策略,也是一種展現(xiàn)真實(shí)的方法,更是一種指引他人的藝術(shù)。在這種反諷中,自我、真理、他人,這三者達(dá)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每一項(xiàng)的地位和價(jià)值都得到了肯定和維護(hù)。
梅洛-龐蒂對(duì)于哲學(xué)表述之隱晦性的論述無(wú)疑可以讓我們聯(lián)想起列奧·施特勞斯所揭示的“隱微教誨”(esoteric teaching)。隱微教誨與顯白教導(dǎo)(exoteric teaching)相對(duì),同樣涉及到哲人與真理和大眾的關(guān)系。就真理而言,施特勞斯認(rèn)為,所有的古典哲人都認(rèn)識(shí)到,真理不可公示,只能秘傳,這首先是因?yàn)檎胬砼c公眾的信仰和意見(jiàn)相沖突,絕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不關(guān)心甚至也不需要哲學(xué)和真理,如果公示真理,只會(huì)激化哲人與大眾間的沖突。因而為了保護(hù)哲人自身,也保護(hù)哲學(xué),同時(shí)也保護(hù)大眾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免受哲學(xué)的沖擊,哲人就以雙重的面具說(shuō)話,他以顯白的言辭擁護(hù)城邦和習(xí)俗道德,同時(shí)又以只有少數(shù)人才能理解的隱微表達(dá)講述真理。當(dāng)然,有些表面顯白的言說(shuō)同樣可能具有隱晦性,因而只有少數(shù)真正有哲學(xué)天賦的人才懂得這種區(qū)分,并透過(guò)其言說(shuō)的表面布局(前后矛盾、反諷、不精確的復(fù)述等等)去探究背后潛藏的真理。因此,在施特勞斯看來(lái),哲學(xué)的隱微表達(dá)不僅僅是哲人在城邦中自我保護(hù)的方式,也是激發(fā)潛在的哲人進(jìn)行獨(dú)立的思考、進(jìn)而培養(yǎng)未來(lái)哲人的方法。
不過(guò),梅洛-龐蒂對(duì)于哲學(xué)的秘傳性不以為然*“蘇格拉底的反諷并不是以說(shuō)得少來(lái)打動(dòng)人心,以便證明靈魂的力量,或讓人推測(cè)有某種秘傳的知識(shí)(quelque savoir ésotérique)。” Merleau-Ponty, 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 Gallimard,1953.P.43.,他也不關(guān)心隱微言說(shuō)與顯白言說(shuō)之間的區(qū)分。他認(rèn)為隱晦是表達(dá)本身固有的特征,而與所謂的秘傳知識(shí)無(wú)關(guān)。隱晦源自語(yǔ)言本身的特性,但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又是知覺(jué)含混性的反映,就此而言,隱晦或曖昧是不可消除的,它是我們生存固有的特點(diǎn)。但當(dāng)哲學(xué)以求真為目的時(shí),它就與這種根植于生存本身的曖昧性拉開(kāi)了距離,也因此導(dǎo)致了哲學(xué)家的生活與大眾生活的距離。不過(guò),哲學(xué)家并不因此就消除了隱晦,毋寧說(shuō),他從自身中體驗(yàn)到含混與明晰、實(shí)存與本質(zhì)的距離,而這種內(nèi)在的間距又進(jìn)而導(dǎo)致了哲學(xué)本身的隱晦和哲學(xué)家自身生活的曖昧。由此,哲學(xué)家與大眾的緊張?jiān)谀撤N程度上只是他的內(nèi)在分離的反映。當(dāng)然,哲學(xué)家的內(nèi)在分離一般不會(huì)導(dǎo)致其個(gè)人生活的危機(jī),但它一旦反映在社會(huì)層面上卻可能帶來(lái)危險(xiǎn)的后果。正是因此,為了緩解或消除這種可能的沖突,就需要哲學(xué)的表述本身也采取一種隱晦的手法。在這個(gè)意義上,隱晦是哲學(xué)的面紗。哲學(xué)家借助這一面具既守護(hù)著真理的高貴與隱秘,又小心地維持著他與眾人的關(guān)系。因此,這是一種好的隱晦,是哲學(xué)之生機(jī)與活力的體現(xiàn)。
三
然而,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哲學(xué)的這種活力正在喪失,哲學(xué)家與他人的關(guān)系日益疏遠(yuǎn)。“現(xiàn)代哲學(xué)家常常是一個(gè)公務(wù)員,通常是一個(gè)作家,留給他的著作自由承認(rèn)對(duì)立的觀點(diǎn):他所說(shuō)的話一開(kāi)始就進(jìn)入了學(xué)術(shù)界,在此生活的選擇弱化了,思想的契機(jī)也被模糊了。”[1](P.39)哲學(xué)不再直接面對(duì)大眾,面對(duì)生活,它被封閉在學(xué)院內(nèi),被凝固在書(shū)本中。但是,“書(shū)本中的哲學(xué)停止了對(duì)人進(jìn)行的拷問(wèn)”,因此,梅洛-龐蒂說(shuō):“有理由擔(dān)心,我們的時(shí)代也在拒斥生活在這個(gè)時(shí)代的哲學(xué)家,哲學(xué)只得再一次高處云中。”[1](P.45)
梅洛-龐蒂在這里提到了古希臘著名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的劇作《云》,該劇描寫(xiě)了一個(gè)坐在高掛的吊籃里冥思苦索、形容憔悴的蘇格拉底形象,他開(kāi)辦學(xué)院,招生收費(fèi),并無(wú)所顧忌地向他們傳授詭辯術(shù),如神靈并不存在,打雷只是自然現(xiàn)象,正義沒(méi)有力量,歪理可以戰(zhàn)勝真理等等。這種詭辯的邏輯顛覆了普通民眾素來(lái)信奉的城邦的宗教和道德基礎(chǔ),但也招致了哲學(xué)自身的危險(xiǎn)。最后,蘇格拉底的“思想所”在民眾的怒火中灰飛煙滅。
據(jù)說(shuō)阿里斯托芬的蘇格拉底是年輕時(shí)的蘇格拉底,因?yàn)樘K格拉底本人也承認(rèn),他年輕時(shí)曾追隨過(guò)阿那克薩哥拉,研究幾何學(xué)和天文學(xué),也就是說(shuō),他的靈魂曾經(jīng)“高處云中”。梅洛-龐蒂似乎也認(rèn)同這種說(shuō)法。而且,盡管蘇格拉底后來(lái)把哲學(xué)從天上拉到了人間,并發(fā)明了著名的反諷術(shù),但梅洛-龐蒂還是認(rèn)為,蘇格拉底最后的死亡與他的輕慢無(wú)忌有關(guān),也就是說(shuō),蘇格拉底并沒(méi)有完全腳踏實(shí)地,他也沒(méi)有把他的反諷藝術(shù)貫徹到底。比如說(shuō),在法庭上,他似乎過(guò)于輕視那些陪審團(tuán)成員,從而誘發(fā)了他們的殘暴:“他因此有時(shí)被傲慢和惡意弄暈了,有時(shí)則順從于個(gè)人的崇高和高貴的精神。”[1](P.44)梅洛-龐蒂似乎想說(shuō),如果蘇格拉底能在法庭上更謙卑一些,“為法庭提供讓其明白的機(jī)會(huì)”,那么,最后也許就能免于死亡,也能“將雅典從不體面中拯救出來(lái)”。[1](P.44)因此,蘇格拉底在一定程度上要為他自己的死亡負(fù)責(zé)。
當(dāng)然,梅洛-龐蒂在這里提及阿里斯托芬的《云》,更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與現(xiàn)代哲學(xué)作比較。如果說(shuō)古典的哲人(蘇格拉底)因?qū)砟畹募で槊钥穸兄铝宋kU(xiǎn),那么,現(xiàn)代的哲學(xué)卻可能因它的衰老淡漠而死亡。“我們的思想是一種退隱或自省的思想。每一個(gè)人都在為他的青春狂熱贖罪。”(Notre pensée est une pensée en retraite ou en repli. Chacun expie sa jeunesse.)“我們重新回到這種或那種傳統(tǒng),我們捍衛(wèi)傳統(tǒng)。我們的確信與其說(shuō)是建立在被洞見(jiàn)到的價(jià)值或真理之上,不如說(shuō)是建立在我們所不情愿的各種傳統(tǒng)的缺陷與錯(cuò)誤之上。”[1](P.45)哲學(xué)不再觀察現(xiàn)實(shí),不再與現(xiàn)實(shí)接觸。哲學(xué)因此被凝固或僵化了。這種凝固尤其體現(xiàn)在它對(duì)待上帝和歷史的態(tài)度上。
梅洛-龐蒂吃驚地看到,如今的哲學(xué)家已不再像托馬斯、安瑟倫和笛卡爾等人那樣論證上帝了。在對(duì)待上帝時(shí),如今的哲學(xué)家要么不容置疑地把它看作是一切的前提,要么就干脆否認(rèn)它的存在。于是哲學(xué)被分成了對(duì)立的兩極:要么是神學(xué),要么是無(wú)神論。然而,在梅洛-龐蒂看來(lái),這兩者其實(shí)是一樣的,它們都走向了某種獨(dú)斷的肯定,它們都漠視了真正的人本身。無(wú)神論只是一種顛倒的神學(xué),是一種把人當(dāng)神來(lái)看待的人類(lèi)神學(xué)(anthropothésime)。因此,它們都不能被稱作真正的哲學(xué),或者說(shuō),它們都排斥了哲學(xué)。
在梅洛-龐蒂看來(lái),哲學(xué)在另一種秩序中確立自己。它基于“認(rèn)識(shí)你自己”這一基本原則,如其所是地看待人本身。人既不是一種絕對(duì)的力量,也不是一種解釋性的原則,“他只是處于存在之核心的一種脆弱,是一種宇宙的因子,但也是所有的宇宙因子都通過(guò)一種永無(wú)完結(jié)的轉(zhuǎn)換來(lái)改變意義并生成為歷史的場(chǎng)所”[1](P.47)。人處于跟人相關(guān)的一切維面(dimension)的紐結(jié)之中,人就是這一紐結(jié)本身,但這一紐結(jié)的存在卻有賴于所有這些維面的存在,離開(kāi)了這些維面,人也就不再成其所是。哲學(xué)在這個(gè)意義上就是對(duì)這些維面及其纏結(jié)的認(rèn)識(shí),而上帝或神圣者(le sacré)只是與這一紐結(jié)相關(guān)的維面之一,因此,它也應(yīng)該始終將這一神圣者“置于物或詞的關(guān)節(jié)處”[1](P.49)。從這一角度來(lái)理解,那么,哲學(xué)就不應(yīng)該只是簡(jiǎn)單地肯定或否定上帝,甚至也不是把基督教的上帝(亞伯拉罕的上帝)改換成哲學(xué)的上帝(亞里士多德的上帝),而是應(yīng)該積極地對(duì)上帝提出疑問(wèn),與神學(xué)展開(kāi)爭(zhēng)論,尤其是在涉及對(duì)人自身的認(rèn)識(shí)及現(xiàn)世的苦難之際。如果上帝存在,它也不應(yīng)該是抽象地遠(yuǎn)離于人的,它應(yīng)該在人的實(shí)在中臨現(xiàn),在人的精神中生成。因此,“存在著這樣一種游移,它使我們永遠(yuǎn)也不知道,究竟是上帝在維持著人的人性存在呢,還是相反,為了認(rèn)識(shí)它的存在,應(yīng)該經(jīng)由我們的存在……”[1](P.32)
與此相應(yīng),歷史是人之實(shí)存的另一個(gè)維度。如果說(shuō)上帝涉及的是人之最超越、最神秘的維度,那么,歷史涉及的則是人之最現(xiàn)實(shí)、最貼近的維度。哲學(xué)應(yīng)如何看待歷史呢?長(zhǎng)期以來(lái),人們要么使兩者截然對(duì)立,要么把它們視為同一。前者可置而不論,因?yàn)樗颜軐W(xué)與歷史視作完全不同的畿域,因而可以說(shuō)是自己把自己給封死了;后者則值得重視,尤其是因?yàn)樗诤诟駹柲抢锏玫搅俗钔晟啤⒆钕到y(tǒng)、也最具影響力的論述。黑格爾把歷史看作是哲學(xué)觀念的生成和展開(kāi),歷史的發(fā)展和變化就像是一出由哲學(xué)家導(dǎo)演的戲劇,因此,哲學(xué)和歷史在他那里是同一回事,只不過(guò)一個(gè)是內(nèi)核,一個(gè)是表現(xiàn)。
然而,在梅洛-龐蒂看來(lái),這兩種觀點(diǎn)都錯(cuò)失了哲學(xué)與歷史的真實(shí)關(guān)系。尤其是黑格爾的歷史觀,它其實(shí)是基于一種自以為是的封閉哲學(xué)之上的。這是一種凌空蹈虛的哲學(xué),一種俯視的哲學(xué),它把現(xiàn)實(shí)看作是既成的,不再有發(fā)展和變化,而世界對(duì)哲學(xué)家來(lái)說(shuō)則是透明的,就像一幅畫(huà)卷那樣展現(xiàn)在哲學(xué)家的眼中,哲學(xué)家在這個(gè)意義上成了上帝:哲學(xué)“再一次高處云中”。
在梅洛-龐蒂看來(lái),哲學(xué)家既不應(yīng)排斥歷史,也不應(yīng)把自己的觀念塞到歷史中,毋寧說(shuō),他既深入歷史的核心,又超越于歷史之外。他尋求歷史的意義,但這不是一種普遍的、預(yù)定的意義。“歷史的意義內(nèi)在于人際事件中,并且同它一樣脆弱。”[1](P.53)它類(lèi)似于話語(yǔ)表達(dá)的意義,如果抽離來(lái)看,每一句話都是瑣碎的、偶然的,其意義也是斷裂的、破碎的,只有還原到特定的語(yǔ)境,這些個(gè)別的話語(yǔ)才聯(lián)貫起來(lái),意義顯示出它的邏輯,偶然性變成了必然性。但是這種邏輯和必然性不能超越這一語(yǔ)境而作抽象普遍的推廣,它們只有內(nèi)在于這一語(yǔ)境之中才有效。歷史的意義也是如此,它只處在特定的人際事件的內(nèi)部。追索這種意義的哲學(xué)同樣處于歷史之中,但“它不滿足于服從這種歷史處境(就像它不滿足于其過(guò)去),它通過(guò)向自己揭示這一處境,通過(guò)使這一處境有機(jī)會(huì)與其他時(shí)間、其他地點(diǎn)建立一種顯現(xiàn)其真理的關(guān)系來(lái)改變這一處境”。[1](P.58)由此,哲學(xué)與歷史重新統(tǒng)一起來(lái)了,但正如在上帝問(wèn)題上一樣,這種統(tǒng)一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的、開(kāi)放的統(tǒng)一。
總之,無(wú)論是上帝問(wèn)題還是歷史問(wèn)題,它們都與人的實(shí)存息息相關(guān),它們也都是哲學(xué)需要加以思考并且從未停止其思考的問(wèn)題。梅洛-龐蒂之所以重提這些問(wèn)題,是因?yàn)樵诋?dāng)時(shí)的思想處境中,哲學(xué)與其他人文學(xué)科之間有一種日益脫節(jié)的趨勢(shì)。這既有哲學(xué)自身的原因,如對(duì)其他學(xué)科的問(wèn)題漠不關(guān)心,或以為哲學(xué)的思考可以代替其他的思考。但更有來(lái)自其他學(xué)科的排斥,它們不歡迎哲學(xué)的橫加干涉,它們想要為哲學(xué)圈定位置,劃定領(lǐng)域。然而哲學(xué)是與其他學(xué)科同列的一門(mén)學(xué)科嗎?哲學(xué)像其他學(xué)科一樣有其固定的領(lǐng)域嗎?顯然不是。哲學(xué)的位置始終是游移不定的、曖昧模糊的。哲學(xué)的觸角既深入到上帝和歷史問(wèn)題中,也深入到生命、靈魂、政治、藝術(shù)、科學(xué)等其他的一切領(lǐng)域中,但這不是說(shuō)哲學(xué)想要取代神學(xué)、歷史學(xué)或任何其他一門(mén)學(xué)科。哲學(xué)超越這一切之外,說(shuō)到底,它不是與這些學(xué)科或任何其他學(xué)科并列的一門(mén)學(xué)科。就像梅洛-龐蒂所說(shuō):“哲學(xué)的中心無(wú)處不在,而其邊界無(wú)跡可尋。”[1](P.147)在這個(gè)意義上,哲學(xué)不得不“高處空中”。
四
至此,我們也許能夠明白“跛行的哲學(xué)”這個(gè)標(biāo)題的含義了。哲學(xué)之所以是跛行的,是因?yàn)樗鼪](méi)有固屬于自身的領(lǐng)域,是因?yàn)樗冀K有一只腳踩在空處,而且不得不踩在空處,因?yàn)椤八粷M足于已經(jīng)被構(gòu)成的東西”,它對(duì)一切現(xiàn)成的東西、堅(jiān)實(shí)的東西,對(duì)所有人們不假思索地肯定和贊同的東西提出疑問(wèn)。哲學(xué)之所以是跛行的,是因?yàn)橹挥姓軐W(xué)才洞悉人之生存的隱晦,它把這種生命和生存本身的隱晦轉(zhuǎn)變成了一種表達(dá)層面上的隱晦,它“以一種有意識(shí)的象征替代了生活的緘默的象征,以明顯的意義替代了潛在的意義”[1](P.58)。就此而言,哲學(xué)無(wú)疑彰顯了我們的生存所蘊(yùn)含的內(nèi)在豐富性,但與此同時(shí),它也使生活中本來(lái)只是隱含著的矛盾和張力突顯出來(lái),動(dòng)搖了生活的確定性和穩(wěn)靠性,給人帶來(lái)不安和騷動(dòng)。在哲學(xué)的凜凜審視下,人們的立足處不再平坦,哲學(xué)使人蹣跚而行。哲學(xué)家是跛行者。
哲學(xué)家是跛行者,這意味著哲學(xué)家是個(gè)內(nèi)在分離的人,在哲學(xué)家的身體和靈魂、行動(dòng)和思想之間存在著矛盾,這也導(dǎo)致了他的行動(dòng)的遲緩或滯后。哲學(xué)家是個(gè)思想者,但他的思想掣制了他的行動(dòng),或者說(shuō)他用思想代替了行動(dòng)。與此相反,大眾似乎只是直接地行動(dòng)而不思考,他們出于激情而行動(dòng),而行動(dòng)又進(jìn)一步鼓發(fā)著他們的激情,他們?cè)谛袆?dòng)中抱成一團(tuán),但也因此,他們的行動(dòng)常常帶有狂熱的性質(zhì)。“哲學(xué)家在這兄弟般的混亂中是一個(gè)外來(lái)者。即使他從來(lái)不背叛,人們從他的忠誠(chéng)方式也感覺(jué)出他可能會(huì)背叛,他沒(méi)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其中一員。他的贊同缺少某種厚實(shí)的、有血肉的東西……他并不完全是一個(gè)真實(shí)的存在。”[1](P.60)大眾不理解哲學(xué)家,哲學(xué)家的存在是曖昧的。
但盡管如此,梅洛-龐蒂還是認(rèn)為,“哲學(xué)家的跛行乃是他的美德”[1](P.61),因?yàn)樗苊饬丝駸岷兔斑M(jìn)。“論行動(dòng)的哲學(xué)家或許是最遠(yuǎn)離行動(dòng)的人:即使是嚴(yán)肅而有深度地談?wù)撔袆?dòng),這也等于說(shuō)一個(gè)人不愿意采取行動(dòng)。”[1](P.59)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梅洛-龐蒂說(shuō)馬基雅維里站在馬基雅維里主義的對(duì)立面。哲學(xué)家比任何人都更敏銳地關(guān)注嚴(yán)肅的人和嚴(yán)肅的事,比任何人都更嚴(yán)肅地關(guān)注行動(dòng),關(guān)注宗教和激情,但他并不因此而成為一個(gè)嚴(yán)肅的人,或狂熱的人。恰恰在他關(guān)注嚴(yán)肅本身的時(shí)候,嚴(yán)肅變得輕巧了,因?yàn)樗褔?yán)肅轉(zhuǎn)變成了一種思想,仿佛為它蒙上了一層輕紗。正像當(dāng)他注目他人的輕松嬉戲時(shí),這種輕松卻反過(guò)來(lái)在他的目光下變得凝重,變得陌生。哲學(xué)家總是保留著一種反思或一種審慎的隱思(arrière-pensée),他總是實(shí)行著一種奇怪的顛倒:在沉重的時(shí)候輕松,在肯定的時(shí)候否定,“在摧毀之際實(shí)現(xiàn),在保留之際取消”。在哲學(xué)家那里似乎沒(méi)有真正嚴(yán)肅的事,但反過(guò)來(lái),也可以說(shuō)在哲學(xué)家那里沒(méi)有不嚴(yán)肅的事。借用柏拉圖的話來(lái)說(shuō),哲學(xué)家同時(shí)體驗(yàn)了悲劇和喜劇,在這個(gè)意義上,他是最接近生命的整全的人。這是否足以替哲學(xué)家的存在辯護(hù)了呢?或者說(shuō),這是否就是對(duì)哲學(xué)的贊頌?zāi)兀?/p>
梅洛-龐蒂事實(shí)上還沒(méi)有走得這么遠(yuǎn)。在他看來(lái),哲學(xué)家與普通人之間其實(shí)并不那么截然對(duì)立。每個(gè)人身上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角色:行動(dòng)者和理解者。行動(dòng)者無(wú)疑是狂熱的,正如某個(gè)作家所寫(xiě)的:“所有的行動(dòng)都是摩尼教徒式的”,然而,人不會(huì)始終處于行動(dòng)中,即使行動(dòng)也需要思想的指導(dǎo)并追求某種思想,而且,“沒(méi)有哪個(gè)人在他本人面前會(huì)是個(gè)摩尼教徒”,這種狂熱的姿態(tài)只是從外在的角度去看才顯得如此。[1](P.61)同樣,也沒(méi)有哪個(gè)哲學(xué)家始終只思考而不行動(dòng),或者總是停留在哲學(xué)的高空而不回到生活。斯賓諾莎在專制君主的大門(mén)上寫(xiě)下“最后的野蠻”,拉繆(Lagneau)為了恢復(fù)一個(gè)不幸的候選者的資格而起訴大學(xué)當(dāng)局,這都是哲學(xué)家們的哲學(xué)行動(dòng)。但這一切做完之后,每個(gè)人都回到家中,依然過(guò)著平常的生活。哲學(xué)并不會(huì)完全改變現(xiàn)實(shí),在這個(gè)意義上,把哲學(xué)家與行動(dòng)者截然分割開(kāi)來(lái)似乎是不合適的。哲學(xué)家生活在現(xiàn)實(shí)中,行動(dòng)者也同樣追求真理,而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普通人,“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對(duì)哲學(xué)的反諷出奇得敏感,仿佛他們的沉默與他們的謹(jǐn)慎在哲學(xué)的反諷中得到了承認(rèn),因?yàn)檠哉f(shuō)在這里使他們一下子獲得了解脫。”[1](P.61)
哲學(xué)的存在似乎由此得到了更恰當(dāng)?shù)霓q護(hù),當(dāng)然,這一辯護(hù)隱含的前提是啟蒙。我們已經(jīng)生活在一個(gè)啟蒙后、或者說(shuō)哲學(xué)化了的世界中,因此,人們多多少少都能夠理解和接受哲學(xué),人們也需要哲學(xué),需要哲學(xué)為他們提供一種“心靈雞湯”式的意義和價(jià)值。哲學(xué)家是意義的揭示者,他讓人們明白大人物在心中所說(shuō)的某些東西,他更新著他自己和其他人都生活于其中的這個(gè)世界的形象。在這個(gè)意義上,隱晦的不再是哲學(xué),而是生活本身,曖昧的不再是哲學(xué)家,而是生活在曖昧之中的每一個(gè)人。但無(wú)論是哲學(xué)家還是普通人,“他們都在事件中思考真理,他們共同反對(duì)根據(jù)教條而思考的自大者,共同反對(duì)不按真理而生活的詭詐者。”[1](P.63)在這個(gè)意義上,每一個(gè)人甚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個(gè)哲學(xué)家,哲學(xué)家與普通人不再有高下之分,他們只是清醒者與夢(mèng)寐者、言說(shuō)者與沉默者的差別:“哲學(xué)家是警醒的人,是在言說(shuō)的人,而普通人則沉默地把哲學(xué)的悖謬包含在自身之中:因?yàn)椋瑸榱送耆蔀槿耍蛻?yīng)該要么稍微在人之上,要么稍微在人之下。”[1](P.63)
參考文獻(xiàn):
[1]Merleau-Ponty.élogedelaphilosophieetEssaisPhilosophiques[M]. Paris:Gallimard,1953.
[2]卡皮.法蘭西學(xué)院[M].張澤乾,黃貽芳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7.
[3]Merleau-Ponty.TheMerleau-PontyReader[M].edited. Ted Toadvine, LeonarLawlor.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
(責(zé)任編輯:吳芳)
Crippled Philosophy: On Merleau-Ponty’s “Praise of Philosophy”
or Apology for Philosophy
ZHANG Yao-ju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InPraiseofPhilosophywas a speech given by Merleau-Ponty when he was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French Academy. Although the title of the book was “In Praise of Philosophy”, it dealt with an apology for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al life. Why philosophy needs an ap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erception, expression and action (and also with the references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er and the masses, the real situ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 on), Merleau-Ponty explored the ambiguity of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the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ality,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Ultimately, he pointed out the “crippled” nature of philosophical life, which accordingly exemplified the “ambiguous” characteristic of his philosophy.
Key words:Merleau-Ponty;InPraiseofPhilosophy; apology for philosophy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8
中圖分類(lèi)號(hào):B565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2338(2015)04-0069-09
作者簡(jiǎn)介:張堯均(1974-),男,浙江新昌人, 同濟(jì)大學(xué)哲學(xué)系副教授,主要從事法國(guó)現(xiàn)象學(xué)與政治哲學(xué)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基金重大項(xiàng)目“《梅洛-龐蒂著作集》編譯與研究”(14ZDB02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