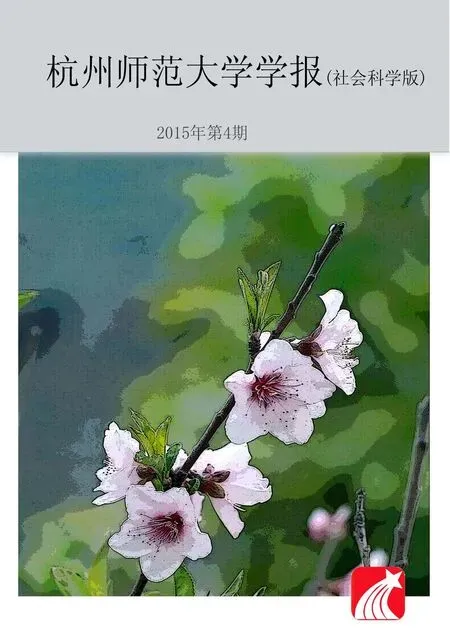華茲華斯筆下的深度共同體
殷企平
(杭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華茲華斯筆下的深度共同體
殷企平
(杭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英國學者懷特和紐琳最近揭示了華茲華斯詩歌中的共同體意識,但是他們的研究都有失偏頗:紐琳只偏重個人對共同體的責任這一角度,而懷特則把個人和共同體看作對立的概念,對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缺乏洞察。事實上,華氏對共同體的思考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因此我們的相關研究也應該在較為寬廣的語境中展開。雖然華氏并沒有用過“情感結構”這一術語,但是他的有關思考跟發明這一術語的威廉斯可謂不謀而合:在威氏那里,情感結構意味著一種“深度共同體”,而只有在這深度共同體中,“溝通才成為可能”;華氏在想象共同體時所關注的也恰恰是怎樣使上述溝通成為可能,因而他心目中的共同體實際上也是一種深度共同體。華氏的詩歌還讓人想起艾略特。后者直接把共同體的命運跟對待死者等陌生人的態度聯系在了一起,而華氏早于艾氏一百多年就表達了類似的思想,而且給予了詩意的表達。
關鍵詞:華茲華斯;深度共同體;《序曲》;溝通;陌生人
十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把目光投向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共同體情懷”。內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紐琳(Lucy Newlyn)跟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懷特(Simon J. White)之間的爭論。紐琳于2003年發表了以“《序曲》中的共同體”為副標題的文章,強調華氏的長詩《序曲》(ThePrelude)“旨在以‘詩人心靈的成長’為切入點,進而展示怎樣奠定仁慈社會的基礎。在華氏看來,從一個人對共同體的責任來審視自我,不失為最好的角度”。[1](P.59)這一觀點受到了懷特的質疑。后者一方面承認“該詩關乎共同體在個人成長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則斷定這種意識“被擠壓在整個敘述的縫隙之中”[2](P.59),或者說只是在敘述人口中得到了“壓制性描述”。[2](P.66)懷特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進而提出,“《序曲》在總體上缺失了有關工作和工作共同體的再現”,“缺失了近距離的工作意象”,其原因是作者“想要迎合上流社會讀者的期待”。[2](P.64)不過,懷特又強調華氏在其晚期作品《漫游》(TheExcursion)中“致力于探究通向具有正當功能的人類共同體的途徑”[2](P.67);“隨著《漫游》的殺青,華茲華斯的詩學完成了一種轉向,原先它扎根于對個人英雄的再現,此時則重視人與人之間的聯結”。[2](P.79)懷特和紐琳的共同優點是揭示了華氏詩歌中的共同體意識,但是他們的研究都有失偏頗:紐琳只偏重個人對共同體的責任這一角度,而懷特則把個人和共同體看作對立的概念,對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缺乏洞察。事實上,華氏對共同體的思考是多層次、多角度的,因此我們的相關研究也應該在較為寬廣的語境中展開。
為了比較充分地理解華茲華斯的共同體思想,我們有必要以共同體這一概念的基本含義作為思考的起點。下文就從共同體的定義談起。
一、深度共同體
在共同體研究史上,德國學者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是一個繞不過的探討者。他曾經在與“社會”相對的意義上,給“共同體”下了一個經典性定義:“共同體意味著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會不過是一種暫時的、表面的東西。因此,共同體本身必須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則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P.19)。這一定義跟華茲華斯的共同體情懷十分契合。
在華茲華斯所生活的時代,由于工業化浪潮的沖擊,傳統的鄉村共同體正處于土崩瓦解的境地,而新型的共同體還未出現,這情形就像阿諾德后來描述的那樣,處于社會轉型的人們“徘徊于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還無力誕生”。[4](P.288)那個時代同時也是催人思考怎樣建立一個新世界/共同體的時代,但是讓華氏十分擔憂的是,那個“不忠不義的時代”竟有一批“愚蠢先生與虛偽先生……將本不/口渴的羊拼命趕往它們/一向回避的水池”。[5](P.68)這幾行詩句劍指當時彌漫于英國社會的唯理性主義和機械主義思潮,詩行中的“愚蠢先生與虛偽先生”則是以葛德汶(William Godwin, 1756-1836)為代表的思想家。華氏曾經一度追隨過葛德汶,原因是后者在《政治正義論》(AnEnquiryConcerningPoliticalJustice,1793)等書籍中描繪了關于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華氏發現葛氏所構想的是一個由機械主義原則主宰的社會,也就是滕尼斯所說的“機械的聚合”(這在“將本不口渴的羊拼命趕往它們一向回避的水池”這一比喻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而華氏所向往的則是“高于一般機械因素”的[6](P.160)、情理交融的共同體,也就是滕尼斯所說的“生機勃勃的有機體”。丁宏為曾經令人信服地指出,華氏的“許多詩行可以說是與葛氏的公開商榷”[6](P.155),這一點在我們研究華氏共同體思想時值得優先考慮。事實上,華氏對理性至上的機械主義語境進行挑戰的例子很多,下面這幾行廣為人知的詩句就是典型的例證:“我們那好事的理智,/扭曲了事物美麗的形式:——/我們解剖一切,卻謀殺了生命。”[7](P.151)類似的表述在《序曲》中也可找到:華氏反思自己當初追隨葛氏時“也動用邏輯/推論,片刻間摧毀生命中的奧秘。然而,恰恰是/這些奧秘,曾經——并且將會/永遠——使四海一家,結為兄弟”。[5](P.314)此處的“使四海一家,結為兄弟”顯然是一種共同體情懷,并且顯然是跟“摧毀生命”的“邏輯推論”以及“謀殺了生命”的“好事的理智”格格不入的。換言之,華氏在憧憬人類的未來時已經意識到,共同體的建設首先要從破除對工具理性/機械主義的迷信入手。
至于該怎樣破除上述迷信,華茲華斯有著多方面的思考,如共同體的紐帶、人們的共同信念、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和辯證關系、人與人(包括死者和未出生者)之間的溝通、人與大自然的溝通,等等。對于這些因素的一些表述,即便未直接采用“溝通”一詞,也包含了溝通的意思。例如,人們的共同信念構成了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基礎。華氏考慮的各類溝通都有一個共同的要素,即情感——不僅是個人的情感,更重要的是社會的情感結構(the structure of feeling),而這正是唯理性主義和機械主義思想體系所缺乏的。雖然華氏并沒有用過“情感結構”這一術語,但是他的有關思考跟發明這一術語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可謂不謀而合:在威氏那里,情感結構意味著一種“深度共同體”(the deep community),而只有在這深度共同體中,“溝通才成為可能”[8](P.65);華氏在想象共同體時所關注的也恰恰是怎樣使上述各類溝通成為可能,因而他心目中的共同體實際上也是一種深度共同體。
換言之,華茲華斯為追求共同體的深度,十分關注上述溝通的深度。為確保這種深度,他不會就溝通而談溝通。例如,他在提倡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時,往往會考慮這些溝通的基石,如人的心智培育,而心智的培育必然會涉及個人獨思、反思的場景,尤其是從大自然汲取養料、靈感和啟迪的場景。正是在這一點上,他的論述常常遭到誤讀。前文提到的懷特就曾指責他一度沉溺于“個人英雄的再現”,另一位批評家克拉克也曾斷言《序曲》“宣揚個人主義思想”。[9](P.94)這些指責的理由是《序曲》的大部分篇幅所呈現的是詩人獨處的畫面。丁宏為曾經從華氏筆下“悲曲”意象所代表的“基本的、永在的、普遍的狀況”入手,駁斥了那些指責華氏“見河山而不見現實”的觀點。[6](PP.6-7)丁宏為還舉了《序曲》中批評現行大學的浮躁,同時憧憬理想學苑的例子(理想的大學應該成為):
一個嫻雅端莊的所在,反芻
動物的樂園,恬靜的生命能自由
徘徊;河旁有蒼鷺喜歡伴著
緩緩流水進餐,翠柏尖頂的
鵜鶘孤身獨憩,在冥思默想中
沐浴太陽的光芒。[5](P.69)
此處的“反芻動物”、“孤身獨憩”和“冥思默想”都有獨思獨行的意味,但是誠如丁宏為所說,“詩人作為‘反芻動物’(ruminating creatures)不是逃避生命能量,而是力求更多、更細地汲取生活滋養”。[6](P.5)筆者想要補充的是,在很多情況下,華氏筆下“孤獨者”的形象并非斷絕了與他人的交往和溝通。就《序曲》而言,雖然大量篇幅展現語者(第一人稱敘事者)獨處的情景,但是他并非為了獨處而獨處,而是為了更好地與人相處。
這么說的主要依據有二。
其一,《序曲》語者在孤獨中所思考的大都是人類的共同命運。還在學童時代,他便開始獨自思考一個人如何從小就“與生機盎然的/宇宙結下患難與共的友情”。[5](P.40)他還提到自己跟柯勒律治從少年時代起就“志同道合”,都“在孤獨中追尋著同樣的真理”。[5](P.48)詩中“沉思默想”和“獨自游蕩”的字眼頻頻出現,但是語者所觀所思的對象卻并不孤獨。例如,第四卷“暑假”中,寫他如何在漫游時“回到沉思默想的世界”,可是緊接著就出現這樣的文字:“當時/人間的生活也讓我產生/新奇感,我愛那些人的勞作,所指的/正是他們的日常生活。常常/驚奇地看到,這安寧的景象猶如/爭春的花園,數日不見就現出/不同的姿色,因為(當然不必/談論某個花園的變化),在這/狹小的山谷中,人們互為鄰舍……”[5](P.88)此處,尤其是“我愛那些人的勞作”和“人們互為鄰舍”那兩句,詩人的共同體情懷躍然紙上。在快接近全詩尾聲時,語者有這樣一段思考:“……當時我說:/‘該審視社會大廈的基礎,看一看/那些靠體力勞動為生的人們,/勞作之繁重大大超過其所能,/還要承受人類自我強加的/不公正,但他們擁有多少心智的/力量,多少真正的德行!’為做出/這一判斷,我主要著眼于自然界的/人類群落,農民耕作的田野/(何必再尋他處?)……我仍然渴望在騷亂中找出具體的事實與情景,引起更貼近我們個人生活的同情……”[5](PP.330-331)學術界對這一段文字的解讀一般都聚焦于華氏跟葛德汶的爭論(葛氏主張把美德建筑在學識之上,其理由是農民過于愚昧,不足以代表美德,而華氏則認為農民擁有心智的力量和真正的德行)。對此,我們需要加以補充的是,詩人在此表達了強烈的共同體關懷,或者說對共同體的深度關懷,因為它涉及了共同體的社會基礎、主要依靠對象,以及(由在大自然辛勤耕作的普通農民所引領的)共同體倫理。同樣具有深度意義的是“更貼近我們個人生活的同情”這一句,它所蘊含的思想跟愛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的“同情觀”毫無二致(愛略特深受華氏的影響,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高曉玲在研究愛略特時這樣說:“‘同情’,有時可以被理解為同胞感(fellow-feeling),強調共同的情感體驗,以區別于居高臨下的憐憫姿態……‘同情’則側重于主體對他人感受的認同體驗,或者說主體之間的情感流通。這種同情經常顯現出比冷靜的理智更為強大的社會整合力量,是維系社會和諧的重要紐帶”。[10](P.11)這段話同樣也適合于解讀華茲華斯。
其二,《序曲》語者常常獨憩于大自然的懷抱,為的是從中悟到共同體的真諦。他在第一卷中強調:“我的靈魂有美妙的播種季節,/大自然的秀美與震懾共同育我/成長……”[5](P.12)這種培育看似只跟個人有關,但是共同體的建設離不開個人心智的培育。前文提到,共同體的建設首先要從破除對工具理性/機械主義的迷信入手,而《序曲》語者從大自然中得到的啟示恰恰能幫助他破除上述迷信,如他在“開始追求她(筆者按:指大自然)”后得到的啟示:“……有誰會用幾何的/規則劃分他的心智,像用/各種圖形劃定省份?誰能/說清習慣何時養成,種子/何時萌發?誰能揮著手杖,/指出‘我心靈之長河的這一段源自/哪方的泉水’……”[5](PP.38-39)傳遞同樣思想的文字在詩中俯拾皆是。例如,《序曲》第六卷和第八卷中就不乏“擊敗理性主義的片段——驚奇、震懾、變故、機遇和厄運交替出現,抵制理性的鉗制”。[11](P.922)與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相對立的是審美情趣和審美判斷,而后者正是共同體建設所必需的,所以詩人-語者“常觀/大自然的形態,從中獲取了審美的/尺度”。[5](PP.133-134)對審美的訴求在第十三卷中又得到了加強;它的標題就是“想象力與審美力,如何被削弱又復元”,而使之復元的是大自然(語者從大自然中得到了如下啟示):“應以兄弟的情誼/看待卑微的事物,尊重這美好的/世界中它們那默默無聞的位置。/經過如此(筆者按:即大自然的)調教與安撫,我再次/發現,人類社會能給予歡樂,/能承接我的愛與真純的想象。”[5](PP.328-329)此處的共同體情懷再明顯不過了。在同一卷中,語者還坦言大自然幫助他“澄清什么會持久,什么將消逝;面對那些以世界的統治者自居、將意志強加給良民百姓的人們,我看出他們的傲慢、愚蠢、瘋狂,不再感到奇怪;即使他們有意于公共福利,其計劃也都未經思考,或建筑在模糊或靠不住的理論上;我也讓現代政治理論家的著作接受其應有的檢驗——生活的檢驗:人間的生活……于是看清,那冠以‘國家財富’大名的偶像多么可怕……”*基本參考丁宏為的譯文,個別文字作了更動。[12](P.518)這里的“公共福利”、“人間的生活”和“國家財富”都屬于共同體關懷的范疇。更重要的是,“冠以‘國家財富’大名的偶像”那一句顯然是針對亞當·斯密及其《國富論》的。華茲華斯嘲諷斯密的理論,稱其為“模糊或靠不住的理論”,這跟他對葛德汶理性/機械主義思維模式的批判是一致的。這種批判一方面有賴于從大自然汲取的審美尺度,另一方面則著眼于對共同體的深度關懷。
以上分析表明,在華茲華斯的共同體思想中,個人和社會這兩個概念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威廉斯發表過一個著名的觀點,即社會和個人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長的過程”,[8](P.118)這一觀點其實早在華氏那里就生根發芽了。學術界常常誤指華氏宣揚個人主義,其實是不理解他深諳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不深究個人,就沒有共同體的深度。
二、共同體中的陌生人
共同體思想的深度還體現在對待陌生人的態度方面。假如一個共同體容不下陌生人,或者讓陌生人受到冷遇,那它就毫無深度可言。華茲華斯在這方面有比較深入的思考。英國沃里克大學喬恩·米教授曾經注意到華氏喜歡描寫陌生人相遇、交談的情景,并稱之為“華茲華斯邂逅詩”(the Wordsworthian encounter poem)。喬恩·米雖然欣賞華氏對陌生人的關注,卻得出了如下結論:“在華茲華斯邂逅詩中,經常出現比較正式的交談,經常再現至少牽涉兩個交談者的場面,但是交談的結果很少是相互理解。人的內心抵制揭示。”[13](P.192)喬恩·米的這番話是對耶魯大學教授布羅米奇的呼應。后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提出,華氏詩歌給人以這樣的總體印象:“每個人的道德動機都很特殊,我們永遠無法深入了解這些動機,因而也無法對它們作出判斷。”[14](P.65)情形果真如此嗎?假如真的如此,那么華氏筆下的共同體就缺乏深度了——缺乏相互理解的“交談”談不上深度溝通,因而也構不成深度共同體。
不知為什么,喬恩·米在論證上述觀點時“醒目”地忽略了華茲華斯的《序曲》。然而,《序曲》不乏(陌生人相互)深度溝通的例子,哪怕如前文所述,它常常因所謂的“個人英雄主義”而受到詬病。在第七卷“寄居倫敦”中,詩人對人們“互為鄰舍,卻不相往來”的異化現象進行了批判:“……那里的人們/怎么可能互為鄰舍,卻不相/往來,竟然不知道各自的名姓。”[5](P.171)針對這一情形,詩中有許多正面的描述,都可以看作對共同體的提倡、想象和憧憬。在第二卷“學童時代(續)”中,詩人-語者對柯勒律治這樣傾訴:“我的朋友!你在都市中長大,見慣異樣的景象,但我們通過不同的途徑最終達到同一目標。為此我才與你交流……”[5](P.48)顯然,“為同一目標”而進行的“交流”是一種深度交流。在第四卷里,詩人-語者在旅途中跟一位疾病纏身的老兵邂逅,在開始交談時,后者有“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情不時流露,讓人覺得/陌生”,但是詩人-語者幫助他在一個農舍里找到安歇之處(在此,農舍主人的共同體情懷也不言自喻),隨后便出現了如下動人的一幕:“看到他能在舒適中安歇,我這才/放心,并懇求他此后不再在/路邊佇留,如此身體狀況,該及時求助于車夫或他人的幫助。/聽到我的責怪,他臉上又現出/那種幽靈般的溫柔,慢慢說道:/‘我信賴至高的上帝,我信賴從我/身旁經過之人的那雙眼睛。’”[5](PP.97-98)這里,“信賴”一詞的連續出現,以及“幽靈般的溫柔”,表明陌生人已經不再陌生,原先陌生的情態可以通過深度交流來化解。
在第九卷“寄居法國”中,詩人-語者與一位陌生的軍官邂逅,兩人一見如故,陷入“長談,/一次又一次,都具有相當的說服力”。[5](P.247)他們的交談涉及“一些十分美好的話題”,而且他們都致力于“通過/擴散而不衰竭的知識,使社會生活/公正有序,明凈清純”。[5](P.245)這樣的交談分明是關切共同體的深度。值得留心的是,第九卷幾乎有一半的篇幅被用來呈現上述長談,其共同體情懷呈遞進態勢。例如,在“使社會生活/公正有序,明凈清純”那一句之后,又出現了這樣的文字:“我們列出古代故事里的壯舉/……以及世間平民/百姓如何相互安慰,相互/激勵……分散的/部落如天上的云朵遍布各方,/卻能共持新見,結成一體。/……一邊交談,/一邊默思著理性的自由、對人類的/期望、正義與和平,啊,這是/何等的甘美!……”[5](PP.245-246)此處的共同體情懷已經超越了地域、國度,達到了人類大同的境界。尤其令人回味的是“遍布各方,卻能共持新見,結成一體”那一句,它體現了關于共同體之根的深度思考。共同體的根應該扎在哪里?是扎在某塊土地里,還是扎在某種見解/觀點中?這在英國歷史上曾引起過不少爭論。懷特曾把詩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看作“觀點派”的代表,因為他認為共同體“就扎根于某種世界觀”,或者說“一種具有凝聚力的世界觀”。[2](PP.152,177)依筆者之見,華茲華斯也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甚至更勝一籌。須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華氏的上述詩文還從深層次上回答了陌生人如何認同共同體的問題,以及每一個共同體成員怎樣對待陌生人的問題:對每一個具體的共同體成員來說,與陌生人相遇、相處乃至互相溝通是無法回避的日常生活現象;一個共同體是否有凝聚力,取決于每個成員怎樣想象自己所在的共同體,包括想象陌生人,這是“因為即便在最小的民族里,每個成員都永遠無法認識大多數同胞,無法與他們相遇,甚至無法聽說他們的故事,不過在每個人的腦海里,存活著自己所在共同體的影像”。[15](P.6)也就是說,對每個共同體成員來說,大部分同胞都是陌生人,那么怎樣才能在彼此陌生的人中間產生凝聚力呢?華氏的“共持新見,結成一體”實在是精辟的解答。
事實上,與陌生人相遇和溝通的情景在《序曲》中比比皆是。例如,在第十三卷中,詩人-語者強調自己“還珍視另一種經歷”:
在能讓我靜思的地方獨行數日,
采擷那些一步步將我引向
智慧的知識;或像個乘風遠來的
小鳥,輕盈,欣悅,向陌生的田野
或叢林高歌問候,而他們也不會
沉默,必做歡迎的回聲;或當這
快樂的跋涉不再有趣,我會
與人交談——在荒涼的曠野,面對
前伸的漫漫長路,或在農舍的
長椅旁,在旅人歇腳的泉邊;在這樣
的地方,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見。[5](P.332)
“每遇一人都似曾相見”,這分明是深度共同體才有的境界!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一境界與“獨行數日”并不矛盾——獨行的詩人“像個乘風遠來的小鳥”,這表明他是大自然的有機部分,而正是在有機生成的、與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共同體中,路人相見才會有似曾相見的感覺。這些深刻的寓意,顯然未能被懷特們理解,也遭到了喬恩·米們的曲解。我們不妨再舉一例,說明華氏心目中陌生人之間溝通所應達到的程度:“……當我開始打量/觀察、問訊所遇到的人們,無保留地/與他們交談,凄寂的鄉路變作/敞開的學校,讓我以極大的樂趣,/天天閱讀人類的各種情感,/無論揭示它們的是語言、表情/嘆息或淚水;在這所學校中洞見/人類靈魂的深處……”[5](P.333)這里,“無保留地與他們交談”、“天天閱讀人類的各種情感”以及“洞見人類靈魂的深處”都明白無誤地指向了深度溝通。在具有這樣深度的共同體里,即便發生喬恩·米所說的“內心抵制揭示”,也肯定是暫時的現象。
在華茲華斯的筆下,還有跟上述情景截然相反的描寫,如《序曲》中詩人-語者在劍橋經歷的社交場面:“所見惟有浮華的青年:漂亮的/蝴蝶紛紛在眼前招搖,喋喋/不休的鸚鵡在耳邊饒舌;人的/內心似無輕重,外部世界/只有浮華俗麗的場景。”[5](P.69)這段描寫屬于詩人-語者的反思部分——他反省自己曾經喜歡跟同伴們“高聲喧鬧,在無益的閑聊中/耗去……時光”;此時的分貝很高,卻毫無意義,因為交談者并“不尋求與他人共享內心的/歡愉”。[5](P.62)在這種場面的反襯之下,全詩中頻頻出現的陌生人相遇、相談、相助乃至相知的畫面就顯得更加感人。通過這種對照,華茲華斯傳達了一層深意:只要有共同的價值觀,即便是陌生人之間也會有深度溝通;相反,若無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即便是熟人之間也只能形同陌路,溝而不通。
在華茲華斯的詞典里,“陌生人”還包括所有的死者。他的許多詩歌中都出現了墳地和出殯隊伍的意象,如《漫游》第二卷中的一幕:詩人-語者和漫游者(the Wanderer)在旅行途中跟一支送殯隊伍相遇,他倆被出殯者所唱的挽歌深深打動:“在墳墓中您的愛是否被人感知?……”[16](P.63)對詩人-語者和漫游者來說,那位躺在靈柩里的死者肯定是陌生人,但是那段歌詞卻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那歌詞說出了華氏心中的境界:一個理想的共同體應該包括那些已故的人們,盡管他們可能只活在很遙遠的年代。當漫游者目睹出殯者莊重地、輕輕地安葬死者時,他情不自禁地說道:“哪一個旅者目睹此情此景,/不管他來自多遠的地方,不管他有多么陌生,/會不承認博愛的紐帶呢?……”[16](P.69)用博愛的紐帶連接生者和死者,這不失為一種共同體情懷。詩中更發人深省的是漫游者和獨居者(the Solitary)之間的一段對話:獨居者把他所看到的一個下葬者稱為“倒霉蛋”,而漫游者則稱那些安葬在郊區墓地的死者為“有福之人”,理由是“他們生前收獲千般愛,/死后總有人悼念”。[16](P.70)當時在場的詩人-語者也表明了態度:“獨居者(稱死者為‘倒霉蛋’時)帶著一絲有嘲諷意味的笑容,/這讓我頗感不快……”[16](P.70)也就是說,華氏對這個獨居者所代表的觀點是持批評態度的。在他描繪的圖景中,那些已故者往往是家庭、社會/共同體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例如,在名詩《我們是七個》中,七兄妹之一的小姑娘在姐姐珍妮和哥哥約翰相繼去世之后,仍然堅持自己家有七個兄弟姐妹(全詩的情節圍繞她跟詩人-語者“我”之間的對話展開):
“有兩個進了天國,”我說,
“那你們還剩幾個?”
小姑娘回答得又快又利索:
“先生!我們是七個。”
“可他們死啦,那兩個死啦!”
“他們的靈魂在天國!”
這些話說了也是白搭,
小姑娘還是堅持回答:
“不,我們是七個!”[17](PP.24-25)
這是一段感人肺腑的對話,除了傳遞小姑娘對家人的真摯情感之外,還具有一層更深的含義:小姑娘真情流露,實際上是給詩人-語者上了一課;對于后者來說,珍妮和約翰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是他確確實實被小姑娘的回答所打動了,因而對那些已故的、從未謀面的同胞們多了一種新的認識,一份新的情感——從“回答得又快又利索”、“堅持回答”和“說了也是白搭”等字里行間,我們不難體會到詩人-語者對小姑娘的欽佩、認同,以及有關文化層面的反思。
當我們重溫華茲華斯有關“陌生人”(包括已故同胞)的思考時,我們不禁會想起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相關思想。艾略特在《文化定義札記》(NotesTowardsTheDefinitionofCulture,1948)一書中對當代人的家庭概念(其實跟共同體概念有關)提出了批評,因為后者往往只包括生者,而且大都不超過三代人。針對這一現象,艾略特闡述了自己的文化思想:“當我說到家庭時,心中想到的是一種歷時較久的紐帶:一種對死者的虔敬,即便他們默默無聞;一種對未出生者的關切,即便他們出生在遙遠的將來。這種對過去與未來的崇敬必須在家庭里就得到培育,否則永遠不可能存在于共同體中,最多只不過是一紙空文。”[18](P.44)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艾略特此處直接用了“共同體”一詞,直接把共同體的命運跟對待死者等陌生人的態度聯系在了一起。應該說,華茲華斯早于艾略特一百多年就表達了類似的思想,而且給予了詩意的表達。
參考文獻:
[1]Lucy Newlyn. “ The Noble Living and the Noble Dead”: Community in The Prelude[M]//Stephen Gill.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Wordsw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Simon White.RomanticismandtheRuralCommunity[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Ferdinand T?nnies.CommunityandCivilSociety[M]. Trans.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Matthew Arnold. 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M]//Kenneth Allott.Ed.ThePoemsofMatthewArnold. London: Longmans,1965.
[5]威廉·華茲華斯. 序曲或一位詩人心靈的成長[M].丁宏為譯. 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9.
[6]丁宏為. 理念與悲曲——華茲華斯后革命之變[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7]William Wordsworth. The Tables Turned[M]//M. H. Abrams. Ed.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 Vol. 2.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86.
[8]Raymond Williams.TheLongRevolution[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61.
[9]Timothy Clark.TheTheoryofInspiration:CompositionasaCrisisofSubjectivityinRomanticandPost-RomanticWriting[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高曉玲. “感受就是一種知識!”—— 喬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認知作用[J]. 外國文學評論,2008,(3).
[11]Susan Wolfson. The Illusion of Mastery: Wordsworth’s Revisions of “The Drowned Man of Esthwaite”,1799,1805,1850[J].PMLA,1984,99(5).
[12]William Wordsworth.TheCompletePoeticalWorksofWilliamWordsworth[M]. London: Edward Moxon, Son & Co., 1869.
[13]Jon Mee.ConversableWorlds:Literature,Contention,andCommunity1762to1830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David Bromwich.DisownedbyMemory:Wordsworth’sPoetryofthe1790s[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5]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1991.
[16]William Wordsworth.TheExcursion:APoem[M]. New York: C. S. Francis & Co., 1850.
[17]華茲華斯. 華茲華斯詩選[M]//楊德豫譯.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
[18]T. S. Eliot.NotestowardstheDefinitionofCulture[M]. Croydon: Faber and Faber,1948.
(責任編輯:吳芳)
The Deep Community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YIN Qi-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Recent studies by Lucy Newlyn and Simon White have shed light on a sense of community as revealed in Wordsworth’s poems, but they have either laid an exclusive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individual in a community or put the notion of individual in antithesis with that of community, thus losing sight of their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ordsworth’s views on community are, in fact, multi-dimensional and develop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must therefore approach the issues concerned by examining them in a broader context. Although Wordsworth never used the term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his views coincide with those of Raymond Williams who invented the term: by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Williams means “the deep community” that makes “communication possible”. What concerns Wordsworth in his imagined communities is exactly how to make the above-said communication possible, so his ideal community is nothing short of a deep community. Reading Wordsworth’s poems is reminiscent of T. S. Eliot, who forged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fate of a community and the attitude towards strangers, including the dead. It remains to be pointed out that Wordsworth anticipated T. S. Eliot by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at their thoughts, though similar, were rendered more poetic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Key words:Wordsworth; deep community;ThePrelude; communication; stranger
收稿日期:2015-05-19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9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5)04-0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