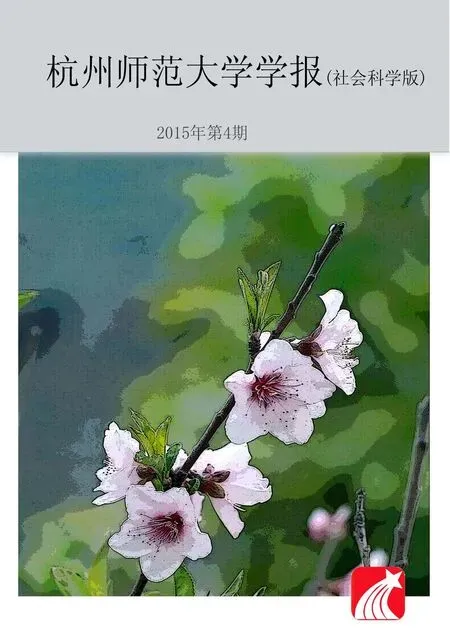從“少數(shù)人”到“心智成熟的民眾”——利維斯的文化批評(píng)與“共同體”形塑
歐 榮
(杭州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從“少數(shù)人”到“心智成熟的民眾”
——利維斯的文化批評(píng)與“共同體”形塑
歐榮
(杭州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不少學(xué)者對(duì)利維斯的批判大多立足于片面理解其“少數(shù)人文化”論,給利維斯扣上“文化精英主義”的帽子。然而,對(duì)利維斯“少數(shù)人文化”的理解必須結(jié)合利維斯對(duì)“大眾文明”的界定和批判,更不能忽視利維斯對(duì)“心智成熟的民眾”的關(guān)注和想象。利維斯批判的“大眾文明”是工業(yè)技術(shù)發(fā)展帶來的批量生產(chǎn)的文化后果,他所批判的“大眾文化”并非指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民間文化,而是指商業(yè)利益驅(qū)動(dòng)的現(xiàn)代傳媒對(duì)大眾的操縱、欺騙和誤導(dǎo)。他清醒地意識(shí)到,解決“大眾文明”時(shí)代的“文化困境”,光靠“少數(shù)人”的突圍是不夠的,而得到“心智成熟的民眾”的回應(yīng)和支持,文化傳承才有希望;因此,大學(xué)教育的各門學(xué)科都應(yīng)該以培養(yǎng)“心智成熟的民眾”為使命,文學(xué)研究尤應(yīng)如此。“少數(shù)人”與“心智成熟的民眾”之間的創(chuàng)造性合作就是利維斯對(duì)“共同體”的想象。
關(guān)鍵詞:利維斯;大眾文明;少數(shù)人;心智成熟的民眾;文化傳統(tǒng);共同體
英國批評(píng)家利維斯(F.R.Leavis,1895-1978)一向是個(gè)富有爭議性的人物。他一生好辯,樹敵甚多,對(duì)他的批評(píng)也是多種多樣,不少學(xué)者對(duì)利維斯的批判大多立足于其文化批評(píng)的開山之作《大眾文明與少數(shù)人文化》(MassCivilizationandMinorityCulture,1930)①此書在1933年首次被介紹到中國,譯為《大眾的文明與少數(shù)的文化》(常風(fēng)《利斯威的三本書》,《新月》1933年第6期,第108頁),后譯名有所不同,如“大眾的文明和少數(shù)人的文化”、“大眾文明與少數(shù)人的文化”、“多數(shù)人的文明與少數(shù)人的文化”等,本文此處暫用“大眾文明與少數(shù)人文化”的譯法,但筆者認(rèn)為這些譯名都無法傳達(dá)英文書名的“一語雙關(guān)”,造成很多讀者對(duì)利維斯的理解有失偏頗,后文將詳細(xì)分析這一點(diǎn)。,并止步于片面理解其“少數(shù)人文化”論,給利維斯扣上“文化精英主義”的帽子。例如,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與社會(huì)》(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1958)中斷言“利維斯的少數(shù)人,本質(zhì)上就是保存著文學(xué)傳統(tǒng)和對(duì)語言最精細(xì)的鑒賞力的少數(shù)文人”。[1](P.272)王寧批判利維斯“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精英意識(shí)和對(duì)高雅文學(xué)經(jīng)典的崇尚”。[2](P.117)周玨良提出:“利維斯既主張文化是少數(shù)人的事,當(dāng)然會(huì)注意培養(yǎng)精英人物。”[3](P.57)鄒贊聲稱:“利維斯理想中的文化就是文學(xué),尤其是他在《偉大的傳統(tǒng)》中設(shè)定的‘文學(xué)正典’!”[4](P.58)陸揚(yáng)、王毅也提出:“F.R.利維斯是把文化主要定位在優(yōu)秀的文學(xué)傳統(tǒng)上面,能否欣賞這一傳統(tǒng)的少數(shù)人,因此首先是趣味雅致高遠(yuǎn)的批評(píng)家。”[5](P.86)筆者認(rèn)為,對(duì)利維斯“少數(shù)人文化”的理解必須結(jié)合他對(duì)“大眾文明”的界定和批判,結(jié)合他的“共同體”想象,更不能忽視其對(duì)“心智成熟的民眾”的關(guān)注和思考。
一、“少數(shù)人文化”再探
要正確理解利維斯的文化批評(píng)和他的“共同體”想象,首先要明確他的“少數(shù)人文化”(minority culture),而利維斯飽受詬病的就是他提出的“少數(shù)人文化”。很多學(xué)者對(duì)其批判的立足點(diǎn)都是對(duì)《大眾文明與少數(shù)人文化》有關(guān)表述的選擇性引用:
在任何時(shí)代,敏銳的藝術(shù)和文學(xué)鑒賞要仰賴很少的一部分人:只有少數(shù)人能作出有創(chuàng)見的判斷(那些簡單的和大家熟悉的作品除外)。另外,能夠通過本真的個(gè)人反應(yīng)支持此類判斷的人雖然數(shù)量稍多,但在整個(gè)社會(huì)仍占少數(shù)……*此處省略的是利維斯引用的理查茲(I.A.Richards,1893-1979)在《文學(xué)批評(píng)原理》(ThePrincipleofLiteraryCriticism)中的一段論述:“……批評(píng)家關(guān)注精神的健康如同醫(yī)生關(guān)注肉體的健康,成為批評(píng)家就是成為價(jià)值的評(píng)判者……藝術(shù)家總是注意把自己認(rèn)為最值得擁有的經(jīng)歷加以記錄和保存……也是最有可能擁有值得記錄經(jīng)歷的人,他們是顯示人類精神成長的標(biāo)志。”這少數(shù)人不僅能夠欣賞但丁、莎士比亞、多恩、波德萊爾、哈代(僅舉主要幾例),而且能辨識(shí)出其最新的后繼者,因而在某一特定時(shí)期構(gòu)成這個(gè)民族(或其分支)的良知。這種鑒賞力不僅屬于孤立的美學(xué)王國,它意味著當(dāng)理論和藝術(shù)、科學(xué)和哲學(xué)可能影響人們對(duì)生存狀況以及生命本質(zhì)的感受時(shí),對(duì)其做出反應(yīng)。依靠這少數(shù)人,我們才得以從過去人類最美好的經(jīng)驗(yàn)中獲益;他們使傳統(tǒng)中最微妙、最易消亡的部分保持生機(jī)。依靠這少數(shù)人,美好生活的標(biāo)準(zhǔn)不言自明,據(jù)此我們明白什么更有價(jià)值?哪兒是前進(jìn)的方向?理想的中心在哪里?他們守護(hù)的是——用一個(gè)值得深思的隱喻和轉(zhuǎn)喻來打比方——美好生活賴以存在的語言及其變化的風(fēng)格,沒有它們,卓越的精神就會(huì)消亡而難以傳承。我指的“文化”就是對(duì)這樣一種語言的使用。[6](PP.3-5)
以上黑體字的部分經(jīng)常被利維斯的批評(píng)者所引用,并由此得出利維斯持“文學(xué)精英主義”的結(jié)論。這些學(xué)者往往忽視了利維斯對(duì)“鑒賞力”的進(jìn)一步闡釋:“這種鑒賞力不僅屬于孤立的美學(xué)王國:它意味著當(dāng)理論和藝術(shù)、科學(xué)和哲學(xué)可能影響人們對(duì)生存狀況以及生命本質(zhì)的感受時(shí),對(duì)其做出反應(yīng)。”[6](P.5)因此,利維斯眼中的“少數(shù)人”不僅具有文學(xué)藝術(shù)的鑒賞力,還具有對(duì)其他領(lǐng)域影響人類生存狀況的感知力。孟祥春對(duì)“少數(shù)人”的理解切中肯綮:“利維斯認(rèn)為文學(xué)最終通向文學(xué)之外,所以,‘少數(shù)人’就勢必不僅僅是‘文學(xué)內(nèi)’的少數(shù)人。”[7](P.84)
上述引文的最后兩句國內(nèi)學(xué)者一般不會(huì)引用。細(xì)讀原文,我們可以看出利維斯把文化看作“語言的運(yùn)用”,是一種隱喻和轉(zhuǎn)喻的說法。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最能體現(xiàn)“美好生活”和“卓越精神”的一部分。利維斯的這種說法難道不是事實(shí)嗎?我們提到希臘文化,必然會(huì)想到荷馬史詩。講到基督教文化,必然會(huì)聯(lián)系到圣經(jīng)。講到英國文藝復(fù)興,怎么能離開莎士比亞?一個(gè)時(shí)期的語言成就無疑是其文化水平的重要表征,語言的貶值不是文化貶值的重要標(biāo)志嗎?
更多學(xué)者把利維斯的“少數(shù)人文化”看作“少數(shù)人的文化”,把利維斯的“少數(shù)人”與“大眾”對(duì)立起來。常見的批評(píng)論調(diào)是:利維斯“堅(jiān)信文化總是少數(shù)人的專利。”[5](P.85)通讀原文,我們看到利維斯一再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少數(shù)人對(duì)“文化”的守護(hù)(in their keeping,利維斯從未說過文化是由少數(shù)人創(chuàng)造的),他們守護(hù)的是“過去人類最美好的經(jīng)驗(yàn)”,是“傳統(tǒng)中最微妙、最易消亡的部分”,而使“美好生活”和“卓越的精神”賴以存在的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如此看來,利維斯的文化觀仍然呼應(yīng)著阿諾德對(duì)文化的界定:“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言論(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8](P. viii),這種文化必然是全人類的創(chuàng)造,而非“少數(shù)人的專利”。殷企平曾經(jīng)令人信服地論證過一個(gè)觀點(diǎn),即“把‘精英文化’的標(biāo)簽貼在阿諾德身上,實(shí)在過于牽強(qiáng)”[9](P.88)。同樣,給利維斯貼上“精英主義”標(biāo)簽,也有些牽強(qiáng)附會(huì)。
利維斯在對(duì)“文化”下定義之前,以阿諾德的《文化與無序》(CultureandAnarchy,1869)作為參照,指出在阿諾德時(shí)代,文化被公認(rèn)為人類“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言論”,無需更多的闡釋;然而,在利維斯時(shí)代,有必要對(duì)“文化”再做界定,以別于流行報(bào)刊、電影、廣播等大眾媒介操縱下的“文化產(chǎn)物”。其實(shí)利維斯所謂的minority culture語帶雙關(guān),一方面指任何時(shí)代,優(yōu)秀文化都為少數(shù)人所守護(hù);另一方面,少數(shù)人守護(hù)的文化曾經(jīng)是強(qiáng)勢文化(major culture),是能引起大多數(shù)民眾回應(yīng)的文化,只是在利維斯時(shí)代,最優(yōu)秀的文化成為“弱勢文化”(minority culture)了。
因此,對(duì)利維斯“少數(shù)人文化”的理解必須結(jié)合其對(duì)mass civilization的界定和批判。mass civilization常被國內(nèi)學(xué)者譯為“大眾文明”,并等同于“大眾的文化”。這些學(xué)者進(jìn)而把利維斯及其擁戴者視為“大眾”的對(duì)立面:“他們首先是對(duì)大眾不滿,然后才遷怒于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的甚囂塵上又加重了他們對(duì)大眾的不滿。”[10](P.69)事實(shí)上,利維斯的mass civilization也是雙關(guān)語。mass一詞,在英語中既指“大眾、民眾”,也有“大批量”的意思,如工業(yè)化產(chǎn)品的大批量生產(chǎn)(mass-production)。在漢語中,“文明”和“文化”常被視作近義詞或同義詞,但在19世紀(jì)以降的英國文化批評(píng)語境中,“文明”(civilization)是與“文化”(culture)相對(duì)立的。現(xiàn)代“文明”是指以“機(jī)械的崛起”為標(biāo)志的工業(yè)文明,而“文化”概念也演變?yōu)椤皩?duì)工業(yè)文明的焦慮”、“對(duì)于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焦慮”,而文化的功能也就是“化解這種焦慮”。[9](PP.5-9)阿諾德在《文化與無序》中指出:“文化為人類擔(dān)負(fù)著重要的職責(zé);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這種職責(zé)尤其重要。與希臘羅馬文明相比,整個(gè)現(xiàn)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機(jī)器文明,是外在文明,且有愈演愈烈之勢。”[8](PP.14-15)利維斯繼承了阿諾德的文化觀,在本書開篇的題詞中就引用了這段話,強(qiáng)調(diào)“文化”對(duì)“機(jī)械文明”相抗衡的作用,并在后文中指出:“‘文明’和‘文化’正成為對(duì)立的兩個(gè)概念。不僅文化失去了力量和權(quán)威感,而且一些對(duì)文明最為無私的關(guān)注反而有意無意地加害文化。”[6](P.25)
關(guān)于利維斯所指的“大眾文明”,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huì)》中其實(shí)已經(jīng)有較清楚的闡述:
如果我們的文明已淪為“大眾文明”,對(duì)質(zhì)量和嚴(yán)肅性漠不關(guān)心,我們要問,何以至此?事實(shí)上,“大眾”究竟是何所指?是指依賴于普選權(quán)的民主,是指依賴于普及教育的文化,還是指依賴于能識(shí)文斷字的大眾讀者群?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大眾文明”的產(chǎn)物如此討厭,我們是否應(yīng)該把選舉權(quán)、教育或識(shí)字能力看作罪魁禍?zhǔn)祝炕蛘呶覀冇谩按蟊娢拿鳌敝复蕾囉跈C(jī)器生產(chǎn)和工廠制度的工業(yè)文明?我們是否認(rèn)為流行報(bào)社和廣告之類的機(jī)構(gòu)是這種生產(chǎn)制度的必然后果?或者說,我們是否認(rèn)為機(jī)器文明和流行機(jī)構(gòu)是某種重大變化和人類精神頹敗的產(chǎn)物?[1](P.275)
細(xì)讀利維斯,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利維斯的“大眾文明”指的是工業(yè)技術(shù)發(fā)展帶來的大批量生產(chǎn)的文化后果:
我們將會(huì)更高效,銷售得更好,然后有更多的批量生產(chǎn)和標(biāo)準(zhǔn)化。如果批量生產(chǎn)和標(biāo)準(zhǔn)化僅體現(xiàn)在麥樂購連鎖超市,我們還不至于感到絕望。但是,現(xiàn)如今批量生產(chǎn)的后果已比較嚴(yán)重地危及共同體的生活。例如,我們看到以出版業(yè)為代表的批量生產(chǎn)和標(biāo)準(zhǔn)化,顯然這必將伴隨著平庸化”。[6](PP.7-8)
值得注意的是,利維斯此處把“大眾文明”直接看成了對(duì)共同體的威脅:“大眾文明”/“大批量文明”的后果就是“劣幣驅(qū)逐良幣”,優(yōu)秀文化遭到“批量生產(chǎn)”的“標(biāo)準(zhǔn)化文明”(standardized civilization)的擠壓,淪為“弱勢文化”,而以量取勝的流行消費(fèi)文化則成了“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顯然,利維斯批判的“大眾文化”,并非指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民間文化,并非共同體文化。利維斯批判的是工業(yè)化、商業(yè)化的現(xiàn)代傳媒對(duì)大眾的操縱和誤導(dǎo)。他這樣描述“大眾文明”時(shí)代的“文化困境”:
和華茲華斯一起長大的讀者行走在數(shù)量有限的文化符號(hào)之間,其變體還未達(dá)到鋪天蓋地的程度。因此他一路前行的時(shí)候,尚能獲得辨別力。然而,現(xiàn)代讀者面對(duì)的是一個(gè)龐大的符號(hào)群,它們的變體和數(shù)量如此之多,叫人不知所措。除非他才具過人或天賦極高,否則委實(shí)難作甄別。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總體文化困境。[6](PP.18-19)
面對(duì)這樣的困境,“少數(shù)人”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堅(jiān)守和傳承顯得尤為重要。但利維斯的“少數(shù)人”并非一個(gè)孤立的概念,而是與“民眾”(public)緊密相連。他認(rèn)識(shí)到,要解決大眾文明時(shí)代的文化危機(jī),光靠“少數(shù)人”的突圍是不夠的;“少數(shù)人”的文化守成,必須得到“心智成熟的民眾”(the educated public)的回應(yīng)和支持,否則文化傳承就沒有希望,共同體的生活就沒有著落。本文以下將對(duì)這一話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二、心智成熟的民眾
在《大眾文明與少數(shù)人文化》中,利維斯已經(jīng)注意到普通民眾的重要性,那些“能夠通過本真的個(gè)人反應(yīng)”支持“少數(shù)人”發(fā)表獨(dú)立創(chuàng)見的人即是利維斯心目中的“民眾”,文化傳統(tǒng)依靠“少數(shù)人”和“民眾”的心氣相求才得以傳承和發(fā)展。令人遺憾的是,很多學(xué)者忽略了利維斯在其著述中對(duì)“民眾”和“心智成熟的民眾”(the educated public)的一再強(qiáng)調(diào)。
在《英詩新方位》(NewBearingsinEnglishPoetry,1932)中,利維斯再一次把脈時(shí)代的病癥:不少編者對(duì)詩人詩作的大量涌現(xiàn)而歡呼雀躍,卻沒有意識(shí)到詩歌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已變得無足輕重,因?yàn)檫@個(gè)時(shí)代“缺乏詩歌評(píng)價(jià)的嚴(yán)肅標(biāo)準(zhǔn),缺乏活躍的詩歌傳統(tǒng),也缺乏有見識(shí)和嚴(yán)肅興趣的民眾”。[11](P.6)利維斯推崇艾略特(T. S. Eliot)的詩歌“表達(dá)了一種現(xiàn)代性感受(a modern sensibility),表達(dá)了個(gè)人與其時(shí)代血脈相連的情感方式與生活體驗(yàn)”[11](PP.75-76);但反映時(shí)代精神的《荒原》只有少數(shù)人能欣賞的“被高雅”恰是現(xiàn)代文明喪失甄別力、良莠不分的癥候。[11](P.104)論及“詩歌的未來”時(shí),利維斯不無焦慮地指出:“這個(gè)時(shí)代缺乏心智成熟的民眾”[11](P.211);“現(xiàn)在有一定修養(yǎng)的讀者也棄詩歌而去”,因?yàn)榇笈可a(chǎn)的庸俗化讀物使他們“失去閱讀詩歌的能力”、“失去對(duì)新穎的、微妙的文字符號(hào)做出反應(yīng)的能力”,但“沒有民眾的支持,詩歌幾乎無以為繼”。[11](PP.211-214)
利維斯夫人(Q. D. Leavis,1906-1981)所著《小說與閱讀民眾》(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1932)呼應(yīng)著利維斯對(duì)“民眾”的關(guān)注。該書從人類學(xué)的視角對(duì)伊麗莎白時(shí)代以降英國民眾閱讀趣味的演變進(jìn)行了深刻的剖析。此書獻(xiàn)給利維斯,并引用了利維斯對(duì)“大眾文明”的表述,可見利維斯思想在其背后的影響。在利維斯夫婦看來,在前工業(yè)化時(shí)代,少數(shù)人守護(hù)的文化是能夠得到大多數(shù)民眾的理解和回應(yīng)的,那時(shí)的閱讀群體雖然人數(shù)有限,但他們是“一個(gè)真正的共同體”(a genuine community),能對(duì)文學(xué)作品產(chǎn)生“健康的自發(fā)的情感反應(yīng)”[12](P.85),如莎士比亞的戲劇雅俗共賞,班揚(yáng)的《天路歷程》家喻戶曉,“少數(shù)人”通過《旁觀者》《閑談?wù)摺返瓤锱c民眾有效溝通;19世紀(jì)英國民眾的閱讀趣味有所分化,但民眾接觸優(yōu)秀文學(xué)的渠道仍然是暢通的。然而,到了20世紀(jì),大眾傳媒、商業(yè)邏輯、商業(yè)標(biāo)準(zhǔn)影響一切,由此在讀者中產(chǎn)生了高眉、平眉和低眉的分野*高眉(highbrow)、平眉(middlebrow)、低眉(lowbrow)采用錢鍾書在《論俗氣》一文中的譯法(《錢鍾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12](PP.31-32)廉價(jià)雜志逐漸影響大眾的閱讀習(xí)慣,閱讀如同吸毒,變成不需思考的習(xí)慣性行為;在商業(yè)利益面前,真正的文學(xué)價(jià)值和標(biāo)準(zhǔn)遭到排斥。利維斯夫人在書中引用了一位“成功的”美國專欄作家的寫作指南:
如果想被好雜志接納就要記住,有些寫作主題是禁忌,不管小說的價(jià)值如何。很少有期刊愿意發(fā)表不道德的或悲慘的故事。像托馬斯·哈代那樣對(duì)人生持悲觀態(tài)度的作家們是不受流行雜志歡迎的,不管他們的文學(xué)藝術(shù)有多高超。[12](P.37)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民眾的閱讀能力每況愈下,“即使是受過教育的讀者也幾乎不愿意——或者說沒有能力——閱讀優(yōu)秀的詩歌”。[12](P.185)面對(duì)這樣的文化困境,利維斯夫婦并沒有悲觀失望,他們認(rèn)為“少數(shù)人”可以在兩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研究領(lǐng)域,通過著書立說,提高民眾的文化批判意識(shí);二是深入學(xué)校教育工作,培養(yǎng)英國年輕一代對(duì)美國流行文化的“抵抗意識(shí)”;他們相信“少數(shù)人”“自覺的、方向明確的努力”,可以匯集“潛在的”民眾的力量,重建“一個(gè)真正的共同體”。[12](PP.213-215)
利維斯與湯姆森(Denys Thompson)合著的《文化與環(huán)境》(Culture&Environment,1933)就是“少數(shù)人”與“民眾”溝通、喚醒民眾文化批判意識(shí)的又一次努力。在“使用說明”中,著者表明此書為普通讀者(general reader)所寫。[13](P.vii)在序言中,利維斯剖析了文化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利維斯認(rèn)為英國的前工業(yè)化社會(huì)是“一個(gè)體現(xiàn)鮮活文化的有機(jī)共同體(an organic community with a living culture it embodied);民歌、民間舞蹈、科茨沃爾德的村舍以及手工藝品是這個(gè)有機(jī)共同體的文化符號(hào),代表著更深層的意義:一種生活的藝術(shù)、一種有序規(guī)范的生活方式,它涉及社交藝術(shù)、交流的準(zhǔn)則,它源自遠(yuǎn)古的經(jīng)驗(yàn),是對(duì)自然環(huán)境和歲月節(jié)奏的因應(yīng)調(diào)整”。[13](PP.1-2)*從這一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利維斯對(duì)文化的界定已擴(kuò)大到“生活的藝術(shù)”、“生活的方式”而非利維斯批評(píng)者眼中以“文學(xué)藝術(shù)為核心的高雅文化”。這個(gè)“有機(jī)共同體”在工業(yè)文明的進(jìn)程中消失了,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傳統(tǒng)在文學(xué)作品中得以保存,通過文學(xué)教育而有所傳承;利維斯追憶往昔,并非要“復(fù)古”,而是希望英國民眾了解文化傳統(tǒng),思考在現(xiàn)代文明的高歌猛進(jìn)中失去了什么,從而培養(yǎng)“對(duì)文明總體進(jìn)程的意識(shí)”,認(rèn)識(shí)到“當(dāng)前的物質(zhì)環(huán)境和知識(shí)環(huán)境如何影響趣味、習(xí)慣、成見、生活態(tài)度以及生活質(zhì)量”[13](PP.4-5);工業(yè)文明造成消費(fèi)文化的“批量生產(chǎn)”,不僅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明對(duì)思想的機(jī)械控制,而且改變了民眾品性。面對(duì)這樣惡劣的“文化環(huán)境”,利維斯強(qiáng)調(diào)了教育的重要性,但他對(duì)“教育”的內(nèi)涵進(jìn)行重新界定:現(xiàn)代環(huán)境所能提供的“教育”就是批量生產(chǎn)的標(biāo)準(zhǔn)化讀物,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應(yīng)該主要是“反現(xiàn)代文化環(huán)境的教育”,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更艱辛的努力。[13](P.106)顯然,利維斯對(duì)“有機(jī)共同體”的回顧,對(duì)消費(fèi)文化的剖析以及對(duì)“教育”的甄別,都是為了培育“心智成熟的民眾”。
二戰(zhàn)后英國高等教育不斷發(fā)展。在《教育與大學(xué)》(EducationandtheUniversity,1943)一書中,利維斯提出:大學(xué)是“文化傳統(tǒng)的象征”,但文化傳統(tǒng)與“僵化的傳統(tǒng)主義”不同;文化傳統(tǒng)是“在傳統(tǒng)智慧指導(dǎo)下,對(duì)一種成熟的意識(shí)和價(jià)值感的傳承”,是機(jī)械文明的反制力量。[14](PP.11,15)在利維斯看來,現(xiàn)代文明中大學(xué)教育的專業(yè)化發(fā)展不可避免,關(guān)鍵是如何培養(yǎng)一種“核心理解力”(a central intelligence),使不同學(xué)科的知識(shí)發(fā)生有意義的聯(lián)系;大學(xué)教育要培養(yǎng)“專家”,更要培養(yǎng)“有智見的人”(the educated man)。[14](PP.25,28)利維斯強(qiáng)調(diào)要在大學(xué)設(shè)立一個(gè)人文中心(a humane center),聯(lián)系不同的研究領(lǐng)域,而英文學(xué)院可擔(dān)此重任,因?yàn)槲膶W(xué)研究從文化傳統(tǒng)中汲取智慧以應(yīng)對(duì)當(dāng)下的文化危機(jī),文學(xué)研究不是純粹的學(xué)術(shù)活動(dòng),而是對(duì)“理解力和感受力(intelligence and sensibility) ”的訓(xùn)練,這些訓(xùn)練也是其他領(lǐng)域所需要的。[14](PP.34-35)因此,利維斯堅(jiān)信文學(xué)批評(píng)應(yīng)作為大學(xué)教育的核心,以培養(yǎng)具備“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心智成熟的民眾”為使命。
然而,英國戰(zhàn)后隨著技術(shù)功利主義的盛行,“科技進(jìn)步”的話語不絕于耳。隨著大眾教育的發(fā)展,英國教育撥款大規(guī)模增加,但自然科學(xué)是主要受益者。[15](P.41)不少學(xué)者和政治家聲稱:保存和發(fā)展西方文明的任務(wù)“已經(jīng)從人文學(xué)科轉(zhuǎn)到了自然科學(xué)”。[15](P.22)斯諾(C.P. Snow)1959年推出的“兩種文化”論,在貌似公允的姿態(tài)中把未來托付給“科學(xué)文化”,因?yàn)椤翱茖W(xué)是新興文化,文學(xué)文化在后退”[16](P.17),所以大學(xué)教育要回應(yīng)技術(shù)革命的需求,培養(yǎng)更多的科技人才[16](P.34)。1961年利維斯發(fā)表演講對(duì)此進(jìn)行了針鋒相對(duì)的駁斥。在利維斯眼中,斯諾代表的是庸俗文化,是“技術(shù)革命造成的文化惡果”,斯諾的演講進(jìn)入中學(xué)課堂,體現(xiàn)了英國當(dāng)下良莠不分的文化狀況[17](P.54);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是個(gè)“偽命題”,只有“一種文化”,即文化傳統(tǒng)。[17](P.101)利維斯特意對(duì)自己所推崇的“文化傳統(tǒng)”(cultural tradition)和斯諾所謂的“傳統(tǒng)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加以甄別,后者意味著沉湎于過往,“在生活和變化面前畏縮不前”,而“文化傳統(tǒng)雖源于過去,但鮮活而又富有創(chuàng)造力地幫助我們應(yīng)對(duì)當(dāng)下的變化”[17](PP.105-106);由此利維斯再次強(qiáng)調(diào):“大學(xué)不僅僅是各個(gè)專業(yè)院系的組合,它更應(yīng)該是體現(xiàn)洞察力、知識(shí)、判斷力和責(zé)任感的人類意識(shí)的中心。”[17](P.75)利維斯在該演講的美國版前言中又一次突出“心智成熟的民眾”之重要:
在真正需要知識(shí)和精神權(quán)威的領(lǐng)域,嚴(yán)肅的標(biāo)準(zhǔn)被制造名人效應(yīng)的力量所取代,這表明現(xiàn)代文明正走向一個(gè)可怕的境地。文評(píng)家要訴諸文學(xué)標(biāo)準(zhǔn),則取決于是否存在能敏銳地回應(yīng)批評(píng)并與批評(píng)家形成互動(dòng)的民眾。我相信在當(dāng)今的英國(我所言僅限于英國)存在這樣一個(gè)民眾的基礎(chǔ);這個(gè)群體由許多有教養(yǎng)、有責(zé)任感的個(gè)人組成,正在形成某種知識(shí)共同體,但力量不夠強(qiáng)大,未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共同體,技術(shù)革命的后果阻礙其形成批評(píng)家所需要的一個(gè)群體。[17](P.81-82)
利維斯在其后的著述中持續(xù)著對(duì)“心智成熟的民眾”的關(guān)注。在1969年的一次演講中,利維斯提出60年代的校園騷亂、吸毒、青少年犯罪、性解放等問題體現(xiàn)了“技術(shù)功利社會(huì)的文化斷裂和精神虛無”,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是“全社會(huì)應(yīng)持續(xù)做出一種新的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努力培育一個(gè)心智成熟、見多識(shí)廣、有責(zé)任心、有影響力的群體——一批讓政治家、管理者、編輯、報(bào)業(yè)老板尊敬、依賴而又懼怕的民眾”。[18](P.131)社會(huì)機(jī)構(gòu)中唯有大學(xué)能擔(dān)此重任:
哪怕只有一所大學(xué)能如我所愿成為創(chuàng)造性生活和人性的中心,都值得我們?yōu)榇烁冻霾恍傅呐ΑD撬髮W(xué)也會(huì)因此聲名鵲起,它會(huì)成為力量和勇氣的源泉,與其他未獲成功的大學(xué)互為鼓勵(lì);如果有一批大學(xué)如此,借助各自不斷擴(kuò)大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就會(huì)形成一大批心智成熟的民眾,他們是希望所在。[18](PP.131-132)
在兩年后的一次演講中利維斯對(duì)此進(jìn)行了更為詳盡的闡釋:大眾傳媒無助于塑造“心智成熟的民眾”,大學(xué)應(yīng)該成為文明的創(chuàng)造中心,“我們有必要擴(kuò)大真正負(fù)責(zé)的心智成熟的民眾的力量,大學(xué)的功能就是塑造這樣一個(gè)群體,保持他們的活力,培養(yǎng)他們的責(zé)任感,保持相當(dāng)?shù)挠绊懥Α薄18](P.201)利維斯把“心智成熟的民眾”與精英和寡頭政治區(qū)別開來:
心智成熟的民眾即便被稱作有教養(yǎng)的階層……也不可能被看做寡頭政治……更不應(yīng)該被稱作“精英人物”。……心智成熟的民眾或階層,由來自廣泛的不同社會(huì)地位、不同經(jīng)濟(jì)利益和政治立場的人民組成,他們的重要性正在于他們思想傾向的多元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非同一性……他們的活力不在于思想上的大一統(tǒng)而在于其創(chuàng)造性的差異,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性的差異保持了文化傳統(tǒng)的活力,而對(duì)文化傳承的堅(jiān)持構(gòu)成了他們的統(tǒng)一性。[18](P.213)
可見,利維斯心中裝的其實(shí)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少數(shù)精英的利益,他所關(guān)心的是如何使廣大民眾的心智得以成熟,或者說建設(shè)廣大而知書達(dá)理的知識(shí)共同體。
三、構(gòu)建“共同體”:“少數(shù)人”與“心智成熟的民眾”的“共同追求”
利維斯的“文化”命題一直圍繞著他對(duì)“少數(shù)人”和“心智成熟的民眾”的關(guān)注和思考,二者之間的互動(dòng)和創(chuàng)造性合作體現(xiàn)了利維斯對(duì)“共同體”的想象。
威廉斯曾指出“共同體”(Community)一詞在英語中至少有以下四個(gè)含義:(一)平民或普通民眾;(二)一個(gè)國家或有組織的社會(huì);(三)具有聚合力的性質(zhì);(四)有著共同身份和特征的意味。[19](P.75)作為“文化”內(nèi)涵的“共同體”常指后兩個(gè)定義,即一個(gè)包含共同價(jià)值觀或共同身份和特征的群體。在利維斯的“共同體”中,“少數(shù)人”與“心智成熟的民眾”的共同價(jià)值觀是對(duì)“文化傳統(tǒng)”的堅(jiān)守和傳承。利維斯不否認(rèn)科技和物質(zhì)文明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重要性,“但技術(shù)進(jìn)步、物質(zhì)水平的提高以及公平分配并非人類追求的唯一目標(biāo),人類的生存還有其他事關(guān)人性和人生意義的考量;而我們對(duì)人生意義的思考和洞察則受益于文化傳統(tǒng)”。[18](P.90)利維斯的文化傳統(tǒng)“既非烏托邦式的,也非懷舊或復(fù)古的”,而是針對(duì)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主義的。[18](P.192-193)
有學(xué)者批評(píng)利維斯夫婦總是以精英自居,“居高臨下”指導(dǎo)大眾“怎樣閱讀才符合人文傳統(tǒng)……與阿諾德的貴族意識(shí)”一脈相承。[5](P.99)其實(shí)利維斯一直把少數(shù)人與民眾的創(chuàng)造性合作(creative collaboration)和創(chuàng)造性爭吵(creative quarrelling)作為構(gòu)建共同體的途徑。根據(jù)德國學(xué)者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1855-1936)的說法,“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應(yīng)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jī)勃勃的有機(jī)體”。[20](P.19)作為“一種生機(jī)勃勃的有機(jī)體”,利維斯的“共同體”中“少數(shù)人”與“民眾”之間不是單向的“師生”或“主從”關(guān)系,而是創(chuàng)造性的合作關(guān)系。在論文集《共同的追求》(CommonPursuit)中,利維斯引用艾略特所言:“合作可能是以爭論的形式進(jìn)行的,我們應(yīng)該感謝那些我們認(rèn)為值得與之爭論的批評(píng)家”,因?yàn)榕u(píng)一向是“合作性活動(dòng)”[21](P.v)。利維斯認(rèn)為真正的文學(xué)教師不是“教授文學(xué)”,而是“與學(xué)生一道從事批評(píng)事業(yè)——究其本質(zhì),就是合作”。[18](P.109)利維斯提出一種文學(xué)研究中相互促進(jìn)的交流對(duì)話的模式:“是這樣的,對(duì)嗎?”——“說得對(duì),但是……文化傳統(tǒng)由此存于鮮活的當(dāng)下,存于個(gè)體參與對(duì)話的創(chuàng)造性反思中,這些個(gè)體合作性地更新、延續(xù)他們所參與其中的事業(yè),因而構(gòu)成一個(gè)文化共同體,具有共同的文化意識(shí)”。[15](P.75)
利維斯的“共同體”是個(gè)開放的共同體。利維斯一再聲稱自己并非“英語福音主義者”,大學(xué)是人類創(chuàng)造力的中心,各專業(yè)學(xué)科和專門知識(shí)都要發(fā)揮積極的作用。[18](P.186)利維斯推薦學(xué)生讀哲學(xué)家、科學(xué)家的著述,他認(rèn)為英文學(xué)院的理想狀態(tài)應(yīng)該有其他學(xué)科的老師。[18](P.126)利維斯主導(dǎo)創(chuàng)立的評(píng)論性刊物《細(xì)察》(Scrutiny,1932-1953)刊行20年間,其編輯團(tuán)隊(duì)來自劍橋各個(gè)學(xué)科,共發(fā)表150多位作者觀點(diǎn)各異的論述,他們的寫作主題涉及外國文學(xué)、自然科學(xué)、社會(huì)心理學(xué)、音樂等多個(gè)學(xué)科;至少有5個(gè)深受《細(xì)察》影響的英文專業(yè)的學(xué)生最后成了人類學(xué)家[22](PP.225-229),實(shí)現(xiàn)了利維斯把文學(xué)研究作為聯(lián)絡(luò)中心、把英文學(xué)院看作大學(xué)聯(lián)絡(luò)中心的想法,利維斯的“共同體”也必然從“文學(xué)內(nèi)”走向“文學(xué)外”。
利維斯一生都在為構(gòu)建“有機(jī)共同體”而奮斗。他著書立說,通過教學(xué)、演講、辯論,也利用大眾媒體對(duì)現(xiàn)代文明進(jìn)行不懈的批判,其言辭可能有偏激之處,但也是一種文化策略。常有人嘲笑利維斯是在進(jìn)行“一場無望的戰(zhàn)斗”[23](P.9),但他從來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執(zhí)著的行動(dòng)者。他與妻子和好友創(chuàng)辦《細(xì)察》,秉持客觀公正的標(biāo)準(zhǔn),不接受任何商業(yè)資助,在逆境中保持少數(shù)人與民眾的溝通,“使許多觀點(diǎn)不同的批評(píng)家得以廣泛的聯(lián)系,形成一個(gè)堅(jiān)持感受力和標(biāo)準(zhǔn)的共同體”。[22](PP.222-223)對(duì)于社會(huì)上彌漫的懷疑主義的論調(diào),利維斯認(rèn)為必須堅(jiān)定信念,希望就在于持續(xù)的努力。[18](PP.186-187)利維斯把晚期演講集題為《我的劍不會(huì)休息》(NorShallMySword),取自布萊克(William Blake)長詩《彌爾頓》(Milton:APoem)中的詩句,表達(dá)他堅(jiān)定的信念和斗志:
我將不停這心靈之戰(zhàn)
也不讓我的劍休息
直到我們把耶路撒冷
建立在英格蘭美好的綠地。[22](P.205)
結(jié)語
1962年英國《觀察家》刊登了一篇特寫,題為《利維斯主義的隱蔽網(wǎng)絡(luò)》(“The Hidden Network of Leavisites”),文章稱“利維斯的信徒已遍及世界,尤其在英國的中小學(xué)和地方大學(xué)人數(shù)眾多”。[15](P.378)二十多年后,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論及利維斯的影響:“今天英國的學(xué)生都是利維斯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否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24](P.31)
1978年利維斯辭世,英國《泰晤士報(bào)》刊登悼詞評(píng)價(jià)利維斯的身上“混雜著苦行主義和旺盛的生命力”,對(duì)許多人來說他“好像是個(gè)走了偏道的奇才”,而對(duì)另一些人來說“他幾乎是個(gè)蘇格拉底式的人物”。[25]這個(gè)“蘇格拉底式的人物”在工業(yè)文明的大潮中對(duì)“文化共同體”的想象和形塑,對(duì)今天的中國文化建設(shè)尤其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Raymond 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M].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1960.
[2]王寧.當(dāng)代英國文論與文化研究概觀[J].當(dāng)代外國文學(xué),2001,(4).
[3]周玨良.二十世紀(jì)上半的英國文學(xué)批評(píng)[J].外國文學(xué),1989,(6).
[4]鄒贊.大眾社會(huì)理論與英國文化主義的源起[J].浙江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1,(4).
[5]陸揚(yáng),王毅.文化研究導(dǎo)論[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5.
[6]F. R. Leavis.MassCivilizationandMinorityCulture[M].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7]孟祥春.利維斯的文化理想研究[J].文化理論研究,2012,(1).
[8]Matthew Arnold.CultureandAnarchy:AnEssayinPoliticalandSocialCriticism[M].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1869.
[9]殷企平.文化辯護(hù)書:19世紀(jì)英國文化批評(píng)[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3.
[10]趙勇.批判·利用·理解·欣賞——知識(shí)分子面對(duì)大眾文化的四種姿態(tài)[J].探索與爭鳴,2011,(1).
[11]F. R. Leavis.NewBearingsinEnglishPoetry:AStudyoftheContemporarySituation[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38.
[12]Q.D. Leavis.FictionandtheReadingPublic[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79.
[13]F. R. Leavis, Denys Thompson.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4.
[14]F. R. Leavis.EducationandtheUniversity:ASketchforanEnglishSchoo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5]Guy Samuel Ortolano. The “Two Cultures” Controversy: C. P. Snow, F.R. Leavis, and Cultural Polictics in Post-war Britain[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2005.
[16]C. P.斯諾.兩種文化[M].紀(jì)樹立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4.
[17]F. R. Leavis.TwoCultures?TheSignificanceofC.P.Sno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8]F. R. Leavis.NorShallMySword:DiscoursesonPluralism,CompassionandSocialHope[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72.
[19]Raymond Williams.KeyWords[M]. London: Fontana Press,1976.
[20]Ferdinand T?nnies.CommunityandCivilSociety[M]. Trans. Jose Harris and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1]F. R. Leavis.TheCommonPursuit[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64.
[22]F. R. Leavis. Scrutiny: a retrospect[M]//ValuationsinCriticismandOther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3]王佐良.英國詩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24]Terry Eagleton.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25]Leavis Society:Life and Work[EB-OL].(2015-05-06). http://www.leavissociety.com/life-and-work,access.
(責(zé)任編輯:吳芳)
From “Minority” to “the Educated Public”: Leavis’
Cultural Criticism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U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Quite a few scholars start their criticism of Leavis from hisMassCivilizationandMinorityCultureand with a simplistic and reductive understanding of his “minority culture”, attaching a label of “elitism” to Leavi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an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Leavis’ “minority culture” should be based on an in-depth comprehension of his critique of “mass civilization” and his life-long concern of “the educated public”. In fact, the “mass civilization” that Leavis decries is the cul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industrial mass production, and the “mass culture” that he castigates is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commercial mass media rather than the folk culture creat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e culture, in the minority’s keeping, cannot do without the response and support of a strong and vital educated public, without whom there is no hope for the living cultural continuity 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In the gener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educated public at the university, specialist disciplines and specialist branches of knowledge including English have their indispensable positive parts to play. The crea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minority and the educated public is Leavis’ vision of the community.
Key words:Leavis; mass culture; minority; the educated public; cultural tradition; community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12
中圖分類號(hào):I106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2338(2015)04-0098-08
作者簡介:歐榮(1971-),女,安徽五河人,杭州師范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英美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比較文學(xué)及跨藝術(shù)詩學(xué)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基金重大項(xiàng)目“文化觀念流變中的英國文學(xué)典籍研究”(12&ZD172)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5-19 2015-06-11
文學(xué)研究英國文學(xué)中的“共同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