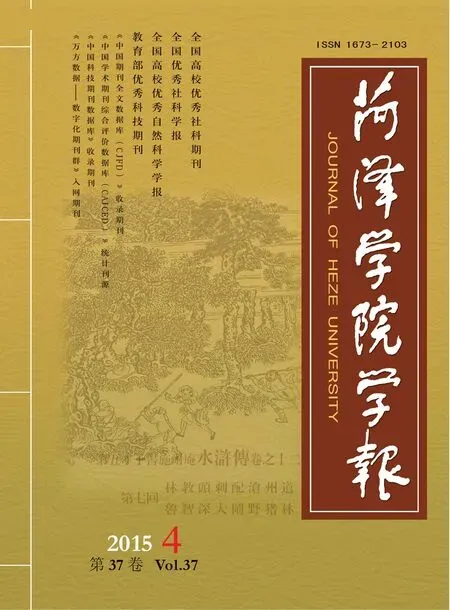試析《喜福會》的敘事藝術*
袁翔華(宜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西宜春336000)
試析《喜福會》的敘事藝術*
袁翔華
(宜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西宜春336000)
摘要:譚恩美的《喜福會》是一個人物敘述的典型文本。小說巧妙安排了兩組敘述者及敘述接受者,構造了故事的多層次性;故事中時間順序今昔交錯,地理空間轉換頻繁,建構出多重并置的文本敘事空間;小說敘述主線空間多重嵌構卻始終脈承“失去、尋求、找到”的敘述母題。
關鍵詞:《喜福會》;敘述空間;敘述母題
譚恩美(Amy Tan)的《喜福會》一出版就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九個月,獲得了多項大獎,同時也受到我國文學評論界的廣泛關注。但梳理發現,研究者的角度大多側重于對作品的跨文化思考、族裔文化身份認同以及剖析母女關系的文化內涵等,而從敘事策略角度進行研究的論文卻為數很少。[1]譚恩美也曾在報社的采訪中指出這樣一個閱讀誤區:人們往往關注她的小說所反映的美國移民史或中國傳統文化,而忽視了作為“文學本身,即故事、語言和回憶”的美學價值。①本文擬撇開文化把研究重點放在文學作品的語言符號上,用結構主義方法對作品的語言進行分解、歸類、組合。希望在結構分析中找到藝術作品形成的根源,從作品內在的語言意義入手,探討此書的語言單位如何通過作家技巧的點化,構成一個由各種敘事信息故事組成的作品整體。
一、敘述技巧:不拘一格說故事
法國結構主義敘述學家熱拉爾·熱奈特在他《辭格之三》一書中將對作品敘述法三分為:故事,敘述話語或敘事話語,敘述行為。[2]14任何敘述行為都涉及到或潛在的涉及到三個基本角色,即:敘述者、被敘述者和敘述接受者。細讀《喜福會》,16個故事,7位講述者,“敘述者通過敘述方式依據自己的目的,打破所敘述故事的自然結構次序,重新經營被虛構性所主宰的敘述話語”,小說敘述技巧不拘一格,生動印證了熱拉爾·熱奈特的敘述學原理。
譚恩美獨具匠心地安排了兩組敘述者及敘述接受者,敘述者有第一敘述者“我”——吳精美和第二敘述者——林多和薇莉、鶯鶯和麗娜、安美和羅絲三對母女;敘述接受者則有第一敘述接受者“我”和第二敘述接受者即閱讀該作品的讀者。在小說敘述中,“我”擔當了兩個角色,既是故事的第一敘述者也是第一敘事接受者;小說中的幾位母親及其女兒也身兼雙職,既是故事的第二敘述者又是第一敘述者“我”所敘述的被敘述者。
故事開始講述精美準備回中國看望母親吳素云當年在中國因病忍痛留下的雙胞胎姐姐。臨行前夜,喜福會成員相聚一堂,第一敘述者“我”精美從第一人稱視角依據故事發展,以順敘的方式展開敘述,而在敘述過程中穿插展現其他三對母女內心故事,從而揭示作品的“故事中的故事”的雙層結構,統領全篇。“故事中的故事”則是由小說當中的第二敘述者也就是其他三對母女,同樣以第一人稱,按照倒敘的敘述方式回憶她們刻骨銘心的經歷。雙重第一人稱視角,雙重第一人稱敘述,敘述者與人物合二為一,人物個性遍布全文,故事不循時序,互為補充,互為烘托,鮮明生動,真實感人,共同構造了作品的多層次性。此外,在幾位母親、女兒采用倒敘方式敘述的故事內容中,不時出現“過去”與“現在”兩種眼光對比映襯,體現出這些第一人稱敘述者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看法或對事件的不同認識程度。比如精美在聚會故事中看到鋼琴,撫摸著鋼琴,回憶起“故事中的故事”。小時候母親吳素云對精美賦予種種期望,而精美卻一直渴望自由,認為母親不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她雖然聰穎、在彈鋼琴上也有天分卻為了與母親對抗而不認真學習。在一場鋼琴演奏失敗后,終于發泄了對母親的不滿。鋼琴對于精美就是母親的霸權,是童年的痛苦,是自我的束縛。直到精美30歲生日,母親將鋼琴贈送給精美,告訴她在母親心里她一直是優秀的,只是沒有去嘗試。精美這才深切感受到母親的理解與深愛。鋼琴成了精美母親的愛、精美自我的肯定、精美母女互相理解的關鍵物。作者獨到的敘述手法使敘述客觀化,增加了讀者身臨其境之感,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聽到了不同的“我”的聲音,穿梭于敘述者的回憶和聽故事的現實之間,也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正是如此別具一格的小說敘述技巧,譚恩美得以靈活自如地調節讀者與小說的距離,形象地演繹讀者閱讀作品的全過程。
二、敘述空間:今昔交替煥奇彩
從小說的敘事空間看,《喜福會》的敘述同樣不平凡。小說以華裔美國移民的生活為背景,故事時間有跨度,地理空間轉換頻繁,表現出敘事、想象、文化多重空間結構并置與演繹的特色。
故事敘述用第一人稱敘事,但都是以母親為核心,呈現了四位母親林多、鶯鶯、安美、素云在解放前的中國及移民美國后在美國出生的女兒們薇莉、羅絲、麗娜、精美的親身經歷。林多自幼被定為童養媳,巧借迷信逃脫舊俗婚姻;鶯鶯錯嫁花心大少,不堪羞辱恍惚錯溺親生子;安美母親受辱產子被欺為四太太,以死為子女正家位;素云戰亂中身染不治忍痛棄留雙胞女嬰,傾其深愛于現有女兒。薇莉自信下棋能贏冠軍,但因不滿母親炫耀引發沖突后卻失去了自信;麗娜信奉經濟獨立與丈夫婚后開支AA制,卻發現婚姻只有金錢,沒有溫暖;羅絲因鮮明個性結緣豪門之子,婚后卻因失去自我而失去丈夫;精美渴望自由與自我,反抗母親的培養期望,鋼琴演奏失敗終于發泄不滿。故事由四位母親和四個女兒以及不同人物的上下場,展開多重的敘事空間,在敘述時刪繁就簡,只選擇幾個重要的環節加以敘寫,突出重點,構成文本敘事空間。在每個故事的敘述文本中,為了擴展敘事空間,作者有意將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故事場面的轉換和人物特寫的變換,通過同一空間、不同時間的插敘或追敘方式,建構出多重并置的文本敘事空間,構成了不同敘事空間之間的直接對話關系。
故事中,移民美國前母親們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生動直接地呈現了封建社會中國女人必須遵從“三從四德”的可悲場景,這也成為她們與美國出生的女兒們的故事之所以發生的背景,為母女的關系和矛盾發展的根源奠定了時代情境。生在封建中國的母親在中國所遭受的經歷教訓竟最終成為母親們不得不再次傳授給與自己在美國出生的女兒的忠告,幫助她們改變或擺脫自身在婚姻愛情等方面的困境或窘境。如此,中國與美國兩個地域之間進行了跨時空的交流對話,這種敘事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文本中線性呈現的敘事空間,完整構成一個相互對峙的立體敘事空間,為讀者、觀影者甚至表演者提供了一個感受迥異的審美世界。文本中封建的故土、動蕩的戰爭、自我的美國等多重敘事空間的交錯并置,母親的母親、母親、母親的女兒三個敘事焦點交替展現,描繪出一幅苦樂悲歡的文本空間圖,有效地激發了閱讀者和觀賞者的審美感受和文化思考,促使他們深入探究那些超越于故事與人物之上的時代精神和文化意義。
三、敘述母題:相隔千里脈相依
母題是“在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人類基本行為,精神現象,以及人類關于周圍世界的概念”,法國結構主義學家茨韋坦·托多羅夫的結構主義敘述理論中認為,母題系“敘述句的最小單位”,對結構主義者來講,文學成了語言的某些特性的一種擴充和運用,而“作者所做的無非是理解語言”,在他看來,“如果人們考慮到名詞和動詞在敘述中的作用,那么也就更好地理解它們了”。[3]
小說《喜福會》第一人稱的敘述主線應該說是明晰的:母親素云隱藏思念之心,傾其希望于在美國出生的女兒精美;素云的朋友們堅持偷偷地萬里尋親;精美終于理解母親,跨越空間遙隔,終圓母親夢。但其中空間多重嵌構,故事層層相連,始終脈牽“失去、尋求、找到”的敘述母題。
小說中的四位母親都出身在地位低下、沒有自我的生存空間里,母親們為了擺脫處境,找到自我,不惜背井離鄉遠渡重洋奔赴美國,他們自覺地選擇遠離故鄉而投身他鄉的生活方式,想在那兒一切重新開始,讓自己的孩子過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希望在那兒沒有人會歧視她,沒有痛苦(“over there,nobody will look down her,she will always be full to swallow any sorrow”)。擺脫男權束縛,離開家園,鮮明地彰顯了母親們追求女性自我,追求自由的愿望。然而母親們身上依然烙印著傳統的中國文化的特征,如忠孝觀念、家庭利益和臉面高于個人幸福、自我犧牲以及含蓄的表達方式等,而女兒們則是生在美國長在美國有著民主、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外露的母愛表達方式等美國觀念的新人。不同的生存背景,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價值觀念使母女兩代的沖突不斷,碰撞不斷。盡管母親們想在這個陌生的國度保持傳統的中國文化,并試圖用自己中國的傳統觀念去要求女兒,[4]女兒們卻不能參透母親們的良苦用心。奈何母女終究是血脈相連,雖然出生于迥然不同的國度,美國出生的女兒卻依然重蹈母親覆轍的婚姻,委屈于男權之下。于是母親終于打破沉寂,講述自己的故事。回憶成為找回過去重建自我的途徑。
在素云已逝,精美即將代母回國認親之時,喜福會其他母親們的思緒也回到了過去。林多感嘆素云怎能讓自己的女兒這么小就失去母愛的同時,轉而垂憐自己不到4歲便被母親決定做了童養媳,但她沒有因為怨恨而拒絕母親,母親在她心里一直很重要,她銘記母親的囑咐“要有自己的主心骨”。正因如此,她學會了永遠要知道自己是誰,從而擺脫了婚姻而獲得了自由。但林多卻一直認為自己的女兒薇莉羞為其女,在即將參加女兒新的婚禮上,通過追尋回憶和對話,讓女兒知道了她的愛,也讓自己知道了自己在女兒心中的重要——“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都影響著”女兒,母女破涕為笑,冰釋前嫌。
鶯鶯嘆素云失去雙女且不知生死之悲苦,轉而憶起自己溺死了她與中國浪蕩丈夫婚姻中唯一在乎的兒子,從此自己便失了精魂,即便后來生下了女兒麗娜也沒了她的精魂。直到她看到女兒的婚姻生活,感受到女兒的痛苦,才在找回猶如老虎般的真正自我的同時告誡女兒,“失去他并不重要,值得尊重和珍惜的是你自己”(Losing him doesn’t matter.It’s you who will be found and cherished),要知道自己從婚姻中想要的是什么。麗娜終于象母親一樣,大膽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結束了痛苦的婚姻,找到了真愛。
安美嘆素云在中國的女兒盼著見的是素云這個母親,從而想起自己年幼是如何盼望見到自己4歲時就被趕出家門的母親最后隨母住進吳府。母親為了給女兒新生活,為了讓安美獲得名分和力量,吞食鴉片而死。安美因此學會吶喊,明辨是非,學會了把握自己的價值,也贏得了尊重和正視。然而她的女兒羅絲卻由因自信獲得真愛到逐漸失去了自我,陷入了婚姻危機。安美的勸說讓女兒明白自己的價值,學會吶喊,找回自信,女兒丈夫再次看到了真正的羅絲,重回女兒身邊。
小說敘述中,不論母親還是女兒,從在男權世界沒有尊嚴、沒有地位到尋求尊重、獲得自由,再到找回自我,找到價值定位,受到正視和尊重;母女從不理解走向理解,從對抗走向和解,從分離走向繼承,而女兒也走向回歸,找到自我。他們的行為舉動都清晰地表現為“失去、尋求、找到”,這也就是小說故事的敘述母題。小說語言流淌著溫馨的血脈親情,尋根文化強有力地沖擊著閱讀者和觀賞者的心靈。《喜福會》不僅是母親們過去記憶的延伸,精神的繼續,而且還是連接母親與女兒、過去和現在、東方和西方的橋梁,也是確立自我身份的開始及其延續。
總之,《喜福會》通過獨特的敘事藝術,讓我們見證了母親們刻骨銘心的經歷和文化背景差異下母女間的沖突與和解,不僅完美地表達了深而不露的母愛、獨立自強的女性意識、尋求東西文化認同等主題深意,還展示了世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具體畫面,為構建和諧大同的世界指示了一條新路。
注釋:
①出自Curt Schleier主持的采訪《The Detroit News》,1995,轉引自施敏捷《文本風格與創作語境》,載于《社會科學》,2001.11。
參考文獻:
[1]程愛民,邵怡.女性言說——論湯亭亭、譚恩美的敘事策略[J].當代外國文學,2006(4) : 34-38.
[2]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Todorov,T.Grammaire du Decameron[M].Mouton: The Hague,1969.
[4]郭宇飛等.中西文化的二元對立與融合——《喜福會》的后殖民主義解讀[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9(6) : 25 -29.
(責任編輯:譚淑娟)
[5]Amy Tan,The Joy Luck Club.[M]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1989.
On the Narrative Art in The Joy Luck Club
YUAN Xiang-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Yichun University,Yichun Jiangxi336000,China)
Abstract:The Joy Luck Club,one of Amy Tan's stories,is a typical text of character narration.Two groups of narrators and narrative recipients are cleverly arranged to display a multilevel structure.Time exchanges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and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ransforms frequently,which construct the juxtaposition of multiple narrative space,while the multiple narrative structure keeps on representing the motif of“To lose,to seek and to find”from beginning to end.
Key words:The Joy Luck Club; narrative space; narrative motif
作者簡介:袁翔華(1978-),女,江西遂川人,宜春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
收稿日期:* 2015-05-10
文章編號:1673-2103(2015) 04-0032-03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I712.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