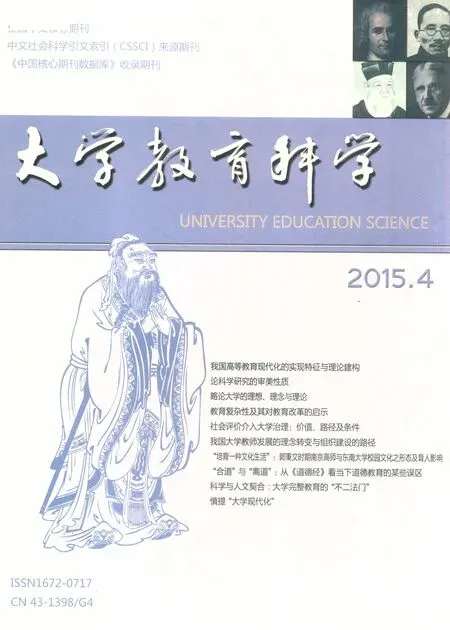哈佛大學預備教育源起——19世紀初的哈佛教育改革
□ 曹春平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學院承擔著傳授白種人的語言文學、宗教和文化等職能。隨著獨立戰爭的勝利和啟蒙思想的傳入,美國學院的另一項職能開始得到部分白人中上層階級的重視,他們期望學院教育推動美國成為一個在政治上獨立于舊世界的共和國。然而,在1820年代之前,多數美國學院招生規模小,教職員工人數稀少且財政赤字率較高[1],甚至,有的學院時常發生學生暴動事件[2],從而,學院通常只發揮了宗教文化傳承和文字讀寫教育的功能,遠遠未發揮出培育共和主義政治美德的功能。于是,在19世紀,美國精英人士邁出了學院教育改革的步伐。自1819年起,在歐洲游學的喬治·蒂克納和愛德華·埃弗里特等人陸續歸國。1821年,蒂克納率先在哈佛發起了教育改革倡議,建議將哈佛改革為一所能提供高等教育預備訓練的、以培育青年的理性心智為教育目標的高級中學。這一改革倡議得到校長、董事會和幾位教授的接納。隨后,董事會頒布了改革建議,但是,它遭到大部分教職工的反對,以失敗告終。1823年,哈佛發生大規模學生暴動事件,導致蒂克納及其支持者再度燃起教育改革熱情。7月23日,蒂克納、哈佛董事會代表、哈佛監事會代表和2位教職工共同舉辦了改革動員會議,并決定向教職工群體推行擬定的改革計劃。然而,這種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方式再次引發了教職工群體的反感,甚至引發了教職工群體的自治權訴求行動。因此,在哈佛大范圍內而言,這一次改革雖然仍舊失敗了,但是,這種建構高等教育預備教育的精神得到了后繼教育者的重視。
蒂克納發起的教育改革在美國教育史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反思中國大學預備教育也有一定啟發意義。但是,目前國內尚未出現描繪這一改革歷程的專門研究,并且,美國學者多從美國大學向德國大學轉型的角度定義這一改革事件的性質。問題是,蒂克納發起教育改革的初衷是讓哈佛成為一所現代性大學嗎?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蒂克納是通過何種路徑先后兩次發起教育改革的?經研究顯示,蒂克納等留學德國的青年學者構想的是一個由相互銜接的中等和高等專業教育構成的教育系統,并且,他們認為,在高等教育預備教育階段,應以活躍學生心智和塑造學生理性為主要目標,以自由課程為主要材料,以學生心智特征為依據進行分班和教學。蒂克納尤其指出,哈佛尚未奠定德國式大學教育的基礎,哈佛改革的首要目標不是仿照德國式大學改革,而是成為一所能夠激活學生心智和塑造學生理性的高中。從史料來看,應把蒂克納發起的改革事件解讀為一場以德國式高級中學為模板的教育改革。此外,研究還顯示出,改革之所以受到阻礙,一方面是由于哈佛教職工不理解大學預備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美國學院董事會、監事會和教職工這3個群體之間存在較大張力。后文將會呈現兩次改革的宗旨,以及參與改革過程的3個群體在教學和管理權力方面的分配以及他們在改革事件中的反應,進而解釋導致改革失敗的因素。
一、兩次教育改革規劃的宗旨以及出臺始末
在1820年代,蒂克納先后兩次發起教育改革,期望借鑒德國教育制度的優點來改造哈佛教育。這兩次教育改革歷程充滿了波折和阻力。
(一)教育改革的宗旨
蒂克納先后兩次發起教育改革,其核心宗旨在于,促進哈佛發展成為一所能夠提供高等專業教育預備訓練的教育機構,為哈佛向德國現代式大學的轉型奠定基礎。
蒂克納的第一份正式改革規劃出現于1821年7月,它是以書信形式呈現出來的。這封改革請愿信對哈佛的改革訴求是,哈佛應首先完善高等專業教育的預備教育,預備教育將包含一整套能夠規訓和塑造學生心智的教學和管理系統。蒂克納將改革宗旨定義為,將哈佛建立成為一所“規訓良好的高中(awell-disciplinedhighschool)”。并且,蒂克納也期望,若此次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則有望進一步完善哈佛的高等專業教育,將哈佛建設成為一所現代大學。因此,蒂克納提出了具體改革目標,包括三個方面:(1)將各個專業課程的基礎知識傳授給學生;(2)針對學生的未來專業,教師對學生進行心智習慣的規訓;(3)針對學生的未來專業,教師對學生進行相應道德品性的規訓[3](p97)。
蒂克納的第二份正式的改革規劃出現在1823年7月23日的改革動員大會上。他在大會上再次強調了教育改革的宗旨不是將哈佛改革為一所現代大學,而是完善高等專業教育的預備教育。他是這樣陳述這番改革宗旨的:
“如人們所見,我們并非一個大學——雖然我們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高中——我們原本應該成為這樣的教育機構…當務之急是將這所學院建成一所徹底的、規訓良好(well-disciplined)的高中……”
為了實現這一宗旨,蒂克納闡述了以下主張:(1)完全依照學生的能力與效率進行分班教學。能力是分班的唯一標準,廢除大一至大四的年級制;(2)將學院分成不同的學術系,每個系獨立考察學生的能力;(3)學生在最低必修課基礎上可以選擇某些課程,每個系控制自己系的課程選修制度;(4)變革跳級制度。以前,大二至大四的學生若想學習更高年級的內容,必須通過高年級之前的所有課程的考試,且須支付額外學費。蒂克納建議,學生只要在某一個學習科目上合格了,就可以跳級,無須修夠所有科目的課程,這個制度可以產生健康的學生競爭;(5)招收不攻讀學位的旁聽生[4]。
在1825年,蒂克納出版了《評論哈佛大學最近提出的或采取的一些變化》,以便對這一次改革宗旨進行更細致的說明。他在文中再一次強調,哈佛忽視了教育的最佳目標,即激活心智活動和創造心智習慣,具體地說,哈佛在心智的規訓方法、手段、材料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問題。蒂克納認為,在心智訓練方法上,首要問題是訓練時間不足,主要原因是,學生假期太多①哈佛假期的細節如下:畢業典禮,4周2天;寒假7周,5月份2周假期。學生畢業之前,平均有一周或5天假;每個學期開學有2天假,一個學年總共6天假;感恩節4天;齋戒日;展覽3天;考試4天;部隊選舉;7月第四周,每天有2/3的時間是沒有操練的,共6天;32周的星期六下午是休息,總共是2周2天。參見George Ticknor. Remarks on Changes Lately Proposed or Adopted in Harvard University. Cummings[M]. Boston: Hilliard &Co.. 1825.3-4.,須知,少年時期是塑造性格和塑造道德的關鍵時期。其次,在塑造心智的方法上,講座制度有待改進,課前預習、課堂筆記、師生交流方面、朗誦和背誦方法都需要改進。在心智訓練的手段方面,蒂克納認為,暫時開除制度效果欠佳,被暫時開除的學生通常被送去小鎮接受牧師教育,可是,學生所到之處缺少教學和學習資源,從而,學生沒有了學習動力,這一制度有待改革。蒂克納還提出,心智訓練需要有配套的管理制度,一方面,應有高效的財政支出效率,目前,教職員工的薪資高低與其為學生付出勞動的多寡并不相符,亟待改革。另一方面,應改變捐贈者占據董事會成員位置的傳統,應該專門從常居教授與導師隊伍中選舉董事會成員[5]。
蒂克納在改革規劃中雖然詳細陳述了他的改革宗旨和意義,但是,其倡議的改革的意義并未得到大部分教職工的理解和接納,一再引發教職工群體的反對。
(二)兩次教育改革的路徑
蒂克納發起的兩次教育改革都是沿著一條自上而下的路徑展開的。從史料來看,實際上,蒂克納在第一次正式向哈佛大學董事會發起教育改革倡議之前,曾嘗試過在小范圍內發起教學改良運動。蒂克納自1819年就職于哈佛以來,約花費一年半時間向部分教職工推薦新教學計劃,然而,幾乎無人響應這些新教學計劃。由于蒂克納的教學改良計劃未引起哈佛教職工群體的足夠注意,蒂克納開始考慮一種自上而下的教學改良路徑。在1821年春,蒂克納找到哈佛校長約翰·桑頓·柯克蘭(JohnThorntonKirkland,1770-1840)商談教學改良計劃,實則期望借助柯克蘭校長的權威引起哈佛教職工對新教學計劃的注意乃至接納。至1821年6月,蒂克納和柯克蘭校長的若干次商談并未產生實質性的結果。此外,哈佛教授安德魯斯·諾頓(AndrewsNorton,1786-1853)、弗里斯比(Frisbie)和亨利·韋爾(HenryWare,1764-1845)加入了支持蒂克納推行教育改革的陣營,在蒂克納的新教學計劃無法推行之際,三位教授一致勸說蒂克納采取自上而下的路徑在哈佛發動教育改革。其中,諾頓和弗里斯比建議蒂克納向哈佛董事會申請實施改革規劃,韋爾則提議蒂克納利用公眾輿論力量驅使哈佛教職工開展教育改革。在內外因相互交織的驅動下,蒂克納向他的一位擔任哈佛董事的友人威廉·普雷斯科特(HonWilliamPrescott)闡述了改革主張。1821年7月,威廉·普雷斯科特決定支持蒂克納的改革規劃。在普雷斯科特的要求之下,蒂克納將改革規劃寫成一封教育改革請愿信,該信長達20頁,并將該信遞交給哈佛董事會[4]。1821年7月31日,蒂克納將教育改革規劃遞交給了柯克蘭校長、賈奇·戴維斯(JudgeDavis)、洛厄爾(Lowell)等哈佛董事。至9月12日,哈佛董事會向全體教職工頒發通告,該通告反映出蒂克納指出的哈佛在教學和管理方面的問題,并附上了蒂克納的教育改革建議,要求教職工對蒂克納的改革建議予以回應[3](p99)。從而,這場自上而下推行的教育改革導致哈佛董事會和教職工展開了利益博弈。
蒂克納第二次發起教育改革的時間是在兩年之后,這場改革行進的路徑仍舊顯示出自上而下的特征。1823年,哈佛大四年級學生發生大規模暴動,這次事件刺激了蒂克納及其改革支持者再度萌發教育改革熱情。其中,蒂克納及其改革支持者諾頓和韋爾同是哈佛一位論教派俱樂部成員,他們在俱樂部沙龍中就教育改革問題進行了三次連續討論,最終決定自上而下再次發起教育改革,并期冀哈佛最高權力機構——哈佛監事會——成為發起教育改革的起點。蒂克納及其支持者發動改革的第一步是召開一個極為關鍵的改革動員大會,經過商榷,蒂克納、韋爾和諾頓決定,邀請以下人士參加改革動員大會:現任監事會委員查爾斯·洛厄爾(CharlesLowell)、賈奇·斯托雷(JudgeStory)、理查德·蘇利文(RichardSullivan)與約翰·皮克林(JohnPickering);非住校教師:詹姆斯·杰克遜(JamesJackson)、蒂克納;前教職工G.B.愛默生,J.G.帕爾弗里;前監事會成員威廉·蘇利文(WilliamSullivan)。
除了上述9位人士,校董會成員賈奇·普雷斯科特和國會議員哈里森·格雷·奧蒂斯(HarrisGrayOtis,1765-848)也收到了邀請,只不過,他們在同一天須參加哈佛董事會例會,因而缺席。7月23日,這次改革動員會議在蒂克納家中舉行,在會上,蒂克納宣讀了自己的改革規劃,并且,與會人士極為認真和細致地對蒂克納的改革規劃進行了討論。會議整整持續了一天,最終得出決議,由與會人士賈奇·斯托雷在第二日的哈佛監事會例會中提出教育改革倡議。7月24日,賈奇·斯托雷及其改革同盟在監事會例會倡議,哈佛應展開對教學和管理狀況的調查。7月25日,監事會經過投票任命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賈奇·斯托雷、查爾斯·洛厄爾、理查德·蘇利文和亨利·韋爾被選為調查委員,他們都是支持蒂克納發動教育改革的人士。此外,會議決定,由哈佛董事柯克蘭校長、普雷斯科特和奧蒂斯負責與調查委員會就改革事宜進行溝通和探討。隨后,教育改革引發了哈佛教職工、董事會和監事會三個群體之間的斗爭[3](pp110-113)。
總的來說,蒂克納先后兩次正式發動教育改革,都是沿著一條自上而下的路徑展開的。在此過程當中,既有改革使命感的驅動,也有改革環境的逼迫。這種路徑的發生背后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后文將進一步敘述和分析。
二、教職工群體的反對及改革結果
蒂克納兩次正式提出的改革規劃,經由哈佛董事會或監事會的推行,下達到教職工群體之中,繼而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教職工群體的反對。
1821年9月,哈佛董事會下發蒂克納的改革建議和改革商議通告之后,除了N.H.黑文(N.H.Haven)等幾位教授表示支持,大部分教職工反對實施“任何重要的變革”。同時,校長柯克蘭對蒂克納的“回復”頗有微詞,他指責蒂克納在新英格蘭激起了太多人對哈佛的反感態度。教職工的反對態度導致哈佛董事會決定不再推行蒂克納的改革規劃。
1823年7月,蒂克納第二次正式提出改革規劃,監事會接納意見后,任命了調查委員會就教育改革必要性進行了調查,這一舉措引起教職工的反感,從而,教職工以諾頓為核心形成了一個抵抗改革的團體。1824年春,9個住校教師與諾頓、埃弗里特向校董會遞交了一份陳情書,聲稱他們的自治權正在不斷受到“侵蝕”。1824年5月4日,監事會調查委員賈奇·斯托雷咨詢了董事會之后,起草了一個報告來推崇蒂克納的改革計劃。此外,該報告賦予哈佛校長在教育改革上的絕對個人權威。報告稱,“校長將是哈佛大學最有效的、真正的領導,…他有完全的權威巡視教授們……校長可以獨立負責或否定這所大學的所有系與其他委員會的報告與行動”[3](p110-116)。隨后,哈佛監事會將報告寄給全體教師,并通知他們于6月1日討論這個報告。結果,該報告引發教職工群體對改革路徑和改革宗旨的極力反對。德克斯特神圣文學教授安德魯斯·諾頓憤慨地寫下《對“監事會的報告”之評論》一文,一方面,他批判此次改革的路徑,尤其指出“這份改革規劃將學院教師們置于監事會、校董會、校長的權威之下……”,諾頓認為這條改革路徑是“專制主義”的。諾頓對改革宗旨也發出質疑,他質問道,“難道要將哈佛降低到高中水平?”[6]在某種程度上,諾頓的一系列反問代表了哈佛部分住校教師的疑慮。
1824年6月1日,哈佛教師們與高層管理者聚集在一起辯論賈奇·斯托雷的哈佛改革調查報告。教師們并不贊同這份報告的改革主張,認為監事會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了解哈佛的教育狀況。對此,監事會再次任命了一個新調查委員會,賦予他們權威重新調查哈佛教育狀況和撰寫新的報告。
不久,新調查委員會完成了調查工作,調查委員洛厄爾將新的調查報告呈遞給了監事會。報告顯示,哈佛大部分教職員工反對大規模變革。但是,監事會在1825年1月6日宣布接納賈奇·斯托雷的舊《報告》。隨后,以蒂克納的改革建議為主要內容的新政策出臺,哈佛教職工被推上了改革的舞臺。1826年秋,哈佛監事會的一個委員在對哈佛例行巡視時發現,除了現代語言系之外,所有系的改革舉措實施得并不成功。改革中的一個重要舉措是按照個人的效率與能力進行分組教學,眾人皆表示這個舉措難以實施,困難重重。這種情狀導致監事會對改革失去了信心,他們立刻向董事會匯報改革困境,希望董事會稍稍修改之前的新政策。1827年初,哈佛董事會出臺了新的政策。政策規定,“除了現代語言系的教職員工同意實施這條法規——按照新分班制度分成新的群體進行教學——其他系或教師在沒有得到教職員工的同意時,不得采取這種新的分班制度”。這條新政策深受教職員工的歡迎,從而,在哈佛大范圍內,教職工基本上不再執行先前頒布的教育改革規劃[4]。
1828年,柯克蘭校長辭職了,約西亞·昆西(JosiahQuincyIII,1772~1864)繼任哈佛校長,帶來了一股新的治校精神,展開了新的教育改革。蒂克納回憶之前的艱難改革,說自己曾經迫于處境做了超過本職四分之三的事情。蒂克納認為自己所實施的改革系統是成功的。
三、結論和啟示
(一)分析和結論
縱觀改革過程,蒂克納倡導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哈佛教師的大規模抵抗,其原因主要在于哈佛教育管理制度的結構特點和改革發起者的身份。
從哈佛管理體系的結構看來,哈佛教職員工處于管理體系的最底層,他們在自身群體的聘任、薪水以及學生管理政策方面幾乎沒有話語權,并且,他們幾乎無緣進入董事會與監事會體系。1821年,董事會直接在通告中公布蒂克納的教育改革意見,這種做法或許意味著挑戰教師手里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教學自治權利。因此,教師在1821年普遍反對蒂克納的改革。但是,哈佛管理體系的權力分層似乎無法解釋教師群體在1823年改革中的反對態度。1823年,哈佛監事會并沒有直接下發教育改革意見,而是選任了調查委員進駐哈佛來考察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可是,教師們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就已經集結起來撰寫教師自治權陳情書。從這點來看,教師們在1823年改革中的抵抗情緒更甚于1821年。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發起者的身份引發了教職工群體的反感情緒。
除了哈佛管理體系權力不平衡問題之外,改革者的身份是導致教職工進行反對的重要原因。1823年改革行動的主體是哈佛監事會,監事會完全由校外人士組成,包括麻省政界精英、教會精英與其他校外人士。當一群校外人士涉入哈佛校內教育事務之時,不難想象教師們可能產生的抵抗情緒。同時,喬治·蒂克納享有的特殊條件也使得1823年的改革蘊含了些許武斷的性質。在19世紀初,哈佛的教授和導師一般住在校園內,他們不僅要負責學生的教學事務,還需充當哈佛校園警察,需要在深夜巡視校園。與他們不同的是,蒂克納從歐洲歸來之時就與校長訂立了合約,根據合約,蒂克納只需要負責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并住在校外,因此,他與監事會成為了鄰居和朋友,脫離了一般的教師群體。在1823年改革中,蒂克納受到監事會的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他與監管委員們的私交關系。綜上所述,與其說蒂克納是一名“教授”,不如說他的影響力以及角色更類似于哈佛管理高層共同體的一分子。他作為1823年改革規劃的主要提出者,導致這場改革更像一場自上而下、由外向內驅使變革的運動。除此之外,1820年代是哈佛教師被排擠出董事會的時期。雖然,哈佛教師曾經擁有入選董事會的慣例,但是,在1820年代,新的慣例已經形成,董事會成員一般由非住校教師擔任。以上種種的因素推動了哈佛教師的抵抗情緒,使之在1824年達到沸騰狀態,導致1824年的哈佛教師群體自治權陳情書。
此外,不可否認的是,部分教師與蒂克納等改革倡議者在大學教育以及預備教育的內容以及意義方面存在認識差距。蒂克納推行改革,主要是基于對美國共和政體的維護之情。早在1816年留學期間,愛德華·埃弗里特與喬治·蒂克納耳濡目染了歐陸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警戒與重視之感,隨即將他們對高等教育社會功用的體會用書信告知了哈佛校長柯克蘭,并且,他們應柯克蘭校長的要求,就哈佛改革問題撰寫了《文字機構——大學——圖書館》一文,[6](p86)這篇文于1818年12月發表在當時北美最具有影響力的雜志之一《北美評論》上[7]。
喬治·蒂克納倡導的這次改革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茱麗·A·羅賓的《現代大學的形成》(1996),[8]劉保存的《大學的創新與保守——哈佛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之路》(2005)[9],劉春華的《德國大學對美國“大學化”運動影響探析》(2013)都認為這次改革在美國大學向德國式現代大學轉型中具有重要意義[10]。總的來說,雖然此次改革中的一些建議,諸如創建選修制度、將大學分成學術系等,在美國學院向現代大學變革的歷程中有標志性的意義,但是,就蒂克納發起的系列改革倡議的歷史性質來看,蒂克納發起的教育改革規劃是以德國式高級中學為參照對象的。若將此次改革置于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教育改革浪潮之中,就會發現,它在大學預備教育制度、大學與中學銜接制度方面具有源頭性質的意義。
(二)啟示
蒂克納的改革對于國內的預備教育制度的建立具有啟發意義。近些年,國內對大學預備教育構建問題的研究興趣甚濃,譬如,丁道勇的《基于教師“通曉”的高中教學改革》[11],楊明全的《大學先修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改革》[12],綦春霞與周慧的《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銜接:國際經驗與本土實踐》[13],都探討了國內的大學預備教育改革問題[14]。蒂克納改革的啟示是,在預報教育改革問題上,我們應該反思國內大學預備教育改革的路徑和原則,包括:是引入國外的大學先修課程,還是開發本土的大學預備教育課程?遵循什么樣的原則來設計這些課程?教育改革可能會遇到哪些障礙?從本文的研究來看,高等專業教育的預備教育不僅應該包括高等專業課程的思維訓練,還須包括專業道德的訓練;在預備教育改革問題上,不能停留在只研究預備教育制度的內容上,也應兼顧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建構方面;并且,外國大學預備教育制度史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它有助于探索大學預備教育制度建構的理想狀態、困境和出路。
[1] David B.Potts.Liberal education for a land of colleges,Yale Report of 1828[M].New York:Palgrave Maacmillan,2010:8-9.
[2] Steven J.Novak.The rights of the youth,American colleges and student revolt,1789-1815[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38-57.
[3] David B.Track.George Ticknor and the Boston Brahmins [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
[4] George Ticknor.To N.A.Haven [A].George S.Hillard.Life,Letter and Journal of George Ticknor Vol.1[C].London:Gilbert and Rivington.1876:354-367.
[5] George Ticknor.Remarks on Changes Lately Proposed or Adopted in Harvard University.Cummings[M].Boston:Hilliard &Co..1825.3-4.
[6] Andrews Norton.Remarks on a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Overseers of Harvard College[M].Cambridge:Hillard and Metcalf,1824.1-12.
[7] Edward Everett.Literary institution,university,library [J].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and Miscellaneous Journal.1818,2(12):191-199.
[8] Julie A.Reuben.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Morality[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24-25.
[9] 劉寶存.大學的創新與保守——哈佛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之路[J].比較教育研究,2005(1):35-42.
[10] 劉春華.德國大學對美國“大學化”運動影響探析 [J].高校教育管理,2013(3):85-95.
[11] 丁道勇.基于教師“通曉”的高中教學改革[J].教育學報,2014,10(4):34-41.
[12] 楊明全.大學先修課程與我國高中課程改革[J].教育學報,2014,10(4):49-55.
[13] 綦春霞,周慧.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的銜接:國際經驗與本土實踐[J].教育學報,2014,10(4):26-33.
[14] 張斌賢,蘭玉,殷振群.迎接工業化的挑戰:1870—1910年的美國手工訓練運動[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