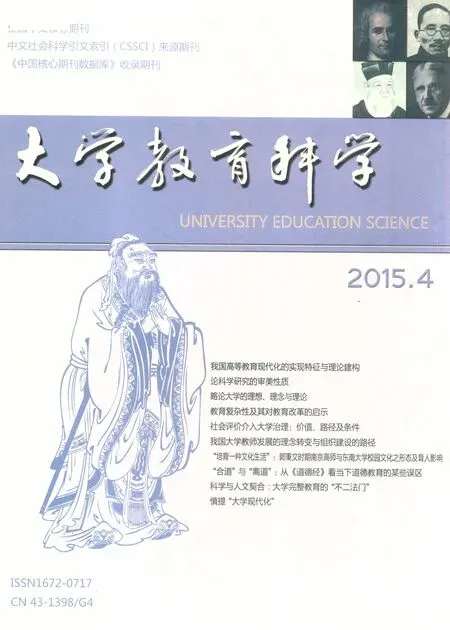慎提“大學現代化”
□ 張楚廷
一、從兩個故事說起
我們討論的是大學改革,如果我們連“大學是什么”并不十分清楚,那么,你改革什么?改到哪里去?現在的大學不就是大學嗎?誰不清楚大學是什么?如果真的很清楚了,真把大學辦得已經很像大學了,還要改革干什么?
湖南省作協主席譚談、副主席水運憲,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在長沙河西北端辦了一個以某人名字命名的文學院,還修了很漂亮的一群建筑物。想必是因為得到了財政的支持或某些領導人的特別關注,不然作協哪有這種財力?
因為跟譚談、水遠憲都比較熟,所以在聽過此事之后,我立即說:“你們能辦什么文學院?”初聽之時,他們頗為不解,卻沒有反感,直言直語,反而不會引起誤會。
我不得不進一步說,如果作家可以辦文學院,那么,商人、實業家就可以辦商學院,企業家們可以辦工學院,軍人可以辦軍事學院了。然而,這可能嗎?再說,教師一定都懂教育學嗎?工程師一定都懂拓撲學嗎?廚師都懂得營養學嗎?
我對譚談、水運憲說,你們可以辦個寫作培訓班,但你們辦不了文學院;文學院是羅成琰、譚桂林、吳龍輝、陳戌國、蔣冀騁等人才能辦起來的,是文學教授、語言學教授們辦起來的;或者說,文學院是由懂得文學理論、語言理論乃至語言哲學的人才能辦起來的。其中,有些人也許還能寫出點小說,但這只能是他們的副業,只會副業的人,怎么能辦文學院呢?
果不其然,這個“×××文學院”不久就夭折了。
還有一位楊老先生,他手上有一個叫做《詩刊》的雜志。有一次他對我說:“張校長,這份雜志就由學校來辦,好嗎?”我即刻對老先生說:“大學不辦《詩刊》,不辦《小說月報》之類的雜志。”后來,我真辦了一些雜志,除了學報增加教育科學版之外,還辦了一個文學評論雜志,是由馬積高教授等負責的;辦了一個生命科學雜志,由劉筠、梁宋平等負責學術把關。總之,大學只辦學術性雜志。
二、大學關心什么
大學是什么?幾位作家能辦屬于大學的文學院嗎?在我任職期間,湖南師大文學院成為最為強大的文學院,可以與北京師大媲美。在20余年前,我們文學院的教授20多人,具有博士學歷的教師19人。從那時起再往前推10年,我們全校的教授只有24人,而具有博士學位的,只有一位留學歸來的老教授。我們的文學院,從當代文學,到現代文學,到古典文學(又分先秦、唐宋以及元明清時代的文學);語言學從現代漢語到古代漢語,一應俱全;還有一支文學評論隊伍,即文藝學的教授們。這才是大學,這才是文學院。
沒有一流的文,就沒有一流的理;沒有一流的理,就沒有一流的工。這已經是高等教育的常識了。我作為大學校長,能不明白這種常識嗎?能不努力建設起一流的文學院嗎?當然,這也是當年我們湖南師大可以特別引以為驕傲的地方。
自博洛尼亞大學以來,就有古典四院,而文學院居于首位。文學院的地位至今沒有發生變化,它必然居于首位。而且,它更為豐富了,文史哲都在其中了。沒有強大文學院的大學,能稱為一流大學嗎?當然,強大的理學也不可少了。
我曾堅定地認為,哲學應設在文學院,且為文學院中最為重要的門類。到了柏林大學的時候,文學院就叫做哲學院了。可惜,當時迫于意識形態的原因,無奈地將其歸于了法學院,而法學院里的主流學科法律學十分薄弱。
我們學校曾經是沒有法學院的。在我要辦法學專業的時候,有一位負責人出來阻撓,說“師范大學要辦什么法學專業?”我質疑道:教育法、教師法等一系列法律師范院校不要學習和研究嗎?況且,憲法、民法、商法能不學嗎?當然,這些阻撓無濟于事的。事實上,無論什么專業,只要有條件,我想辦,就都沒有辦不成的。省府、省廳的其他領導都支持我,這些人認為:“只要張校長想辦的事,我們都支持。”
正因為這樣,后來,商學院、醫學院,工學院等眾多學院,我都一一辦起來了。只要有強大的文學院、理學院支撐,什么都可辦。我把文學院、理學院稱為大學的兩翼。只要這兩翼充分展開,大學就可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沒有理論,沒有哲學,大學怎么飛得起來?大學何以為大學?這就是一般從事工匠似工作的人所難以回答的。
實際上,作為學校深層改革的一部分,就是學科設置上的改革,學科結構上的改革。沒有一個合理的結構以及相應的高水平師資隊伍,大學怎么飛得起來?
我記得非常清楚,在我上任學校負責崗位之初,學校的專業數僅16個,在我和同事們的努力下,專業很快增至100個以上了。
我們師大所操心的,已不是學生就業問題。
有一個問題并不難回答,是學習了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還是只學了新聞專業的學生,未來的路子可以走得更寬?是學習了物理學專業的學生,還是那些只學過電工的學生在未來的道路更為寬闊?我們這樣的大學(更不必說北京大學了),學生們不是為求職和謀生來學習的。為了什么呢?
為了更多的知識,為了獲得更好的教養,為了通向更廣闊的世界……也可不可以是為了成名成家呢?為什么不可以?中國的名人太多了嗎?中國的學問家、科學家、哲學家多了嗎?
我們知道了大學該做些什么,大學能做些什么,大學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大學在社會發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知道了這么多,然而卻不一定知道大學是什么,正好比,知道了寫小說、寫詩歌之后,還不一定知道文學是什么!
三、大學究竟是什么
有點奇怪嗎?大學誕生約900年了,有多少人明白了大學是什么嗎?對于什么是大學的問題,或許多多少少能答上幾句,哈佛不就是大學嗎?清華不就是大學嗎?但你能說大學就是耶魯、哈佛嗎?大學就是北大、清華嗎?
人已誕生了380多萬年,但有幾位能說清楚“人是什么?”有位德國哲學家叫卡西爾,他寫了一本書,名為《人論》。這大概是回答“人是什么”的著作了。這是一位哲學家對人的思考,很可能,在最一般意義下思考人,就必定是科學家或哲學家了;實際上,藝術家、文學家也會思考這種最值得思考的問題。
讀過卡西爾的《人論》之后,我覺得自己也可以寫一本。也有人讀過卡西爾的這部著作,甚為贊賞,在其知道了我也要寫一本《人論》之后,說道:“你不可能寫得比卡西爾好。”熟人眼里無英雄,他很自然地這樣認為。
我寫這本書之初,想把書名確定為《論人》。跟我同事十多年的曾力平說:“就叫《人論》,不怕跟卡西爾的書同名。”這讓我下決心寫,并確定了書名也為《人論》。
我在回答認為我不可能寫得比卡西爾更好的說法時,曾表示:“我不一定寫得比卡西爾更好,但一定會寫得與卡西爾不同。”后來,在我寫作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到,我不僅寫得與卡西爾不同了,而且,我還有相當大的把握認定:我的《人論》比卡西爾寫得更好。我不但有不少的補充性闡述,而且不得不指出卡西爾著作中的許多(不是一兩處)毛病。
然而,在認定這一點的同時,我清晰地意識到,沒有卡西爾的《人論》在先,就很可能沒有我后來的《人論》;其次,后來者也應當不同于過來人,甚至還應當有所超越。這很平常,冷靜的學者不會忘乎所以的,我對我的冷靜十分信賴。
我不知道中國是否還有學者寫《人論》,關乎人的其他問題寫的人必定多,但專寫人,以哲學的視角專寫人的,有多少?中國有幾本《人論》?世界上有幾本《人論》?但我想,中國有十部《人論》,世界上有一百部《人論》可能也不算多。“人是什么”的問題比“大學是什么”的問題更難回答,或許,這個問題永遠都會有人去探索,去回答,卻永遠也不會有人能終結這一永恒的問題。“大學是什么”的問題可能也將成為永恒。
四、能提“大學現代化”嗎
現在進一步討論大學是什么的問題。
人們期待變化、變革、改革。所謂現代化,大概就是向現代的方向變化。也很可能覺得中國的大學實在是需要改革了,“大學現代化”的說法是不是就反映了這種愿望或企求呢?但是,大學的改革就是現代化嗎?大學必須現代化嗎?
古老的中國長期停滯于封建社會,好不容易迎來一個新時期,那就是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時期。然而,在這之后的20多年里,中國仍處在劇烈的動蕩之中,老百姓沒有多少喘息的機會。
其實,50年代初,曾經提出過現代化口號,叫做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簡稱為“四個現代化”。這“四個現代化”代表了當代中國人的民族復興愿望。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開始實施若干個“五年計劃”。然而,除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算是比較順利地執行了之外,其后的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直至1976年之后,才開始恢復正常,“七五”、“八五”、“九五”都一步步走過來了。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人們歡呼、歌唱,包括天才音樂家施光南在內的一些人,寫了許多歌頌現代化的歌曲。古老中國的土地上,再次吹響了現代化的進軍號角。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更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我們距離現代化還很遠;最高領導層也十分清醒,認為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真正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至少還需半個世紀,需要幾代人的努力。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搞了20多年的“假大空”,極嚴重地耽誤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
在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國防等領域提出現代化是必要的、重要的。然而,基本上是物質領域里的現代化,精神領域能這樣提嗎?附帶指出,工業化還不一定意味著現代化了;沒有工業化,就一定沒有現代化。在半個世紀之前,一般認為,當工業生產總值能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時,叫做工業化了。可是,現在還出來了一個信息經濟、知識經濟時代,工業化就與現代化相距更遠了,還需要有信息化。
這些現代化難道不需要大學也現代化與之相應嗎?為討論此問題,我們先議論:能不能提人的現代化?能不能提教育現代化?它們是否需要現代化?
當然,我們首先還要問:人的現代化指的是什么,我們不需要再茹毛飲血了吧?我們也不必再住茅草棚了吧?衣不遮體亦已過去了吧?但是,西裝革履就代表現代化嗎?高樓大廈就代表現代化嗎?飛機、汽車才是現代化象征嗎?
殊不知,我們現在還紀念孔子,連今日的西方也還說要從孔子那里去尋找智慧。殊不知,在一些大學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仍然列在必讀書目錄上,蘇格拉底、柏拉圖仍然令今人念念不忘;《離騷》、《荷馬史詩》還是香噴噴的。
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并沒有超過古人的智慧,同時,也表明我們需要守護人類的精神家園。
人要學會做人,這是古往今來未曾變更過的信條。人有人格,需要修練,需要磨礪,因而,有高尚、修養、堅毅、刻苦、情操、信念、深邃、智慧等一系列美好詞語與我們相隨,有真善美與我們相隨,還有我們對天地日月的虔誠。
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許多現代化景象,是如此的耀眼,令人目不暇接,也帶給我們無數的誘惑。在很大程度上,這意味著做人有了更大的困難。于是,我們不能忘乎所以,不能一往直前,而常常需要回望,看看我們原本是個什么樣子。
如今的黃賭毒、假丑惡以及種種功利的引誘都是可以見到的,甚至有的地方還泛濫成災,較之洪水猛獸,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都成了“現代”課題擺在人們面前,擺在社會面前;要與這些東西格斗,不正是為了保護我們人類自己嗎?不正是需要對現代化保持某種警覺嗎?
至少,近70年來,已沒有大規模戰爭了。但人類又不得不進入到另一些戰場,不僅與貧窮落后和愚昧斗爭著,還與大量可能使人變得不像人的社會頑疾斗爭著,以保護我們自己。有時,這種“戰爭”的激烈程度也相當可觀,硝煙彌漫。用人類正面臨一場“人類保衛戰”來形容,想必并不為過。
物質生活的豐富,如果伴隨著精神生活的貧乏,那的確會是災難性的。無數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一個人,一個團體,一個社會都面臨這樣嚴重的問題。
五、“教育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錯誤的口號
一個人,有自己的修養問題,這個修養幾乎是一輩子的事。有的人修練成仙,有的人黯然墮落。半輩子都走得很好,卻還有可能失足,還有可能經不起某種誘惑而發生蛻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人要始終像人,決非易事。我們的古人有訓:修身、齊家,治國,一切都從修身養性開始,再言其他。
一生都不經歷錯誤幾乎是做不到的。一輩子不做缺德的事,不做虧心事,也不容易。于是,我們還有古人之訓:吾日三省吾身。我們還需要學會懺悔。對著先祖,對著民族,對著這片土地,常捫心自問: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嗎?愧對了上天嗎?因為曲折、坎坷、犯錯難免,所以也需要有檢點與懺悔相陪伴。
宇宙歷史已有137億年,太陽歷史50多億年,地球40多億年,地球上最早的生命也有30億年以上。然而,人的出現很晚,比魚類出現還晚,比鳥的出現也晚。人的歷史不到一億年,也不到一千萬年,而只有300多萬年。有兩個相應的事實或觀點:宇宙天地(太陽、地球等)千辛萬苦才孕育出了人類;同時,宇宙也把所有的神奇、神秘安置在了人的身上。因而,人也應當有更大的責任,而首先是讓自己永遠像個人。
并且,人因神奇、神秘而神圣。人必須對自己的神秘保有足夠的尊敬和虔誠。“人的現代化”是一個不恰當的口號,也是一個有損人自己的口號。
“教育現代化”的口號是恰當的嗎?教育技術、教育手段可能體現了某種現代化,然而,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電子技術很難傳遞人的情感、意念,而且PPT仍然是人去制作的,在何種程度上納入了更大的信息,還是取決于教師的本領和理念。
教學方法的頂端是教學藝術,這種藝術是基于對教學內容的深刻理解,基于對心理特征的充分把握,對學生的熟悉和真切感情的。否則,哪來的藝術?
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對話、辯論,孔夫子的因材施教、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仍然是我們今日做教師的人,所不可不知、不可不踐行的方法。其原因就在于,這些方法里所包含的思想之深刻。唯有沿此走下去,才可能到達藝術,才是可以賞心悅目的,令學生流連忘返的。藝術是深刻思想的一件漂亮的大衣。
再說教學內容吧。如果就自然科學而言,我們只學牛頓是不夠了,還必須學愛因斯坦的學說;學歐氏幾何已經不夠了,還必須學非歐的;學剛體幾何不夠了,還必須學軟體幾何;會撥算盤遠遠不夠了,還需會電腦,一代一代更替的電腦。科學不回頭,一往直前,推陳出新,甚至是摧枯拉朽的。
但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今天的你能不學嗎?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你能不讀嗎?還有那些不朽的經典,它們一直熏陶著一代一代的后人。就拿歐氏幾何來說,大學也許不必再學了;但是,哪一位中學生能不學?它就是活的形式邏輯的經典教本;它告訴你的,不只是幾條定理,而是告訴你怎樣思維,怎樣保持思維的健康。希臘神話貢獻給了人類許多許多,那《幾何原本》亦為其一,惠及全世界。
難道在教學內容上就完全可以提現代化了嗎?不完全。前面已說過,在自然科學領域是十分需要現代化的,工程技術領域尤其要現代化。但是,在人文領域就不一樣了。在這里,有一些是具有永恒意義的,不能在現代化的名義下“化”掉了。
我曾經說過,沒有“三古”,就沒有高水平大學可言。對于中國的大學就是有中國古代史、古代文化史、古代思想史。這是我們大學最珍貴的東西。我常以自己學校有高水平的“三古”而感到欣慰,以我們有4萬多冊線裝書而自豪。
(自然)科學上是可以爆發的,但是,人文領域是靠積淀的,是要厚重的,想爆發也爆發不了。最古老的大學不一定是最高水平的大學,但最年輕的大學,除非采取特別的措施,否則,是難以有高水平的。這些特別的措施,可能包括巨額的投入,聘請大批高水平的教授,也就是把別人已有的“古老”和“積淀”搬來,再加一位杰出的校長能使這一切充分展現出來。
哈佛、耶魯是美國的常青藤大學,北大、清華是中國高水平大學的代表,都是由歷史積淀來說明的。
關于教育目的,我們尤其應當提到杜威的一系列觀點。他說:“教育的過程,在它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1](P58)杜威本人是從19世紀后半葉一直生活和活動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人物,他的身世不能代表古典,但他的教育思想,包括在教育目的上的觀點,與古典直接相連。
他對于哲學與教育的關系的論述,是極為深刻的。他認為:“哲學甚至可以解釋為教育的一般理論。”[1](P347)“哲學乃是作為審慎進行的實踐的教育理論。”[1](P349)這樣,杜威亦必想到古希臘,“歐洲哲學是在教育問題的直接壓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這一點使我們有所啟發”[1](P348-349)。
教學的、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既然學習就是即將知道,它便包含從無知到智慧的過渡,從缺乏到充足的過渡,從缺陷到完善的過渡,用希臘人的表達方法,就是從無生命到有生命的過渡”[1](P34)。
古希臘人,是把辦教育與哲學研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東方,在古中國,孔孟也是把辦教育與哲學研究聯系在一起的。杜威注意到了西方,未能注意到東方,否則,他的論說會更有力量,更令人信服。杜威本人既是哲學家又是教育家,這讓他能夠看到古希臘人之所為的精神之所在;如果他注意到了古中國,相信還會添上精彩的一筆。
為什么哲學可以解釋為“教育的一般理論”呢?為什么說“教育乃是使哲學上的分歧具體化并受到檢驗的實驗室”[1](P348)呢?在近代歐洲開始培養博士的時候,他們的博士叫做Ph.D,即哲學博士,想必歐洲人非常清楚教育與哲學的關系。
我寫過一本名為《教育基本原理》的書,在一些學者看來,這也是哲學著作,似乎教育的一般理論自然地就成了哲學,或哲學就是教育的一般理論。教育的第一問是:“教育是什么?”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會立即引出“人是什么”的問題,這就包含:人為什么能教?人為什么需要教?給人教些什么?教他如何思維?教他如何看待生活、看待人生?這不都是哲學問題嗎?
只要我們認真教書,認真培養人,所有以上這些問題都必然要深入思考,或者說,自找壓力,要求自己去思考,我們也就會在這種壓力下與哲學深深結緣。科學、哲學、藝術,這三者,在山腳下各自一家,在山上,三者一家,他們必將在頂端融為一體。
我們比較多地討論了“人的現代化”、“教育現代化”這種口號的毛病,現在可以回過來簡單地評論一下“大學現代化”說法了,這是沒有毛病的嗎?
人們不會認為大學有了先進的現代化水平的實驗設施就是現代化了吧?不會認為我們網絡化、信息化就意味著大學現代化了吧?不會在儀器先進與現代之間劃一個等號吧?更不會把古老與落后等量齊觀吧?大學不至于那樣膚淺吧?
大約16年前,我曾到過中山大學,得知他們的哲學課程達數十門,史學更多。我想,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會很多,北大可能更多。我相信,他們重視史學和哲學,與重視現代化是兩碼事,或許,對文史哲的看重正引領了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的作為。不是說有一流的文才能有一流的理嗎?
自然科學家們與哲學的關系能夠且應當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哲學是智慧之學,他們在科學領域里所需要的智慧,可以從哲學那里來;另一方面,當他們在自然科學領域里走到高端時,在那里也會與哲學行見面禮的。因而,在他們為科學的現代化而奮發工作的時候,也不會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就整個大學而言,古老的傳統和厚重的文化,正是大學之根。盡管必定有許多科學家為真理而真理、為科學而科學,然而,這正是人對真理的一種虔誠,一種無功利的境界,這正是精神境界、人文境界。當他們都是一些真人的時候,重大的科學成就在等待著他們。
因而,“人的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的不當,可以充分啟示作為教育機構的大學,作為培養人的大學,應當慎提大學現代化。
經濟及相應的體制改革,科研管理體制的改革,可能都需要追求現代化。然而,對于人、對于教育,就不宜套用了。哪里會什么都只有現代化才好的呢?
何況,今日的現代化,在100年以后叫什么?現代化含有明顯的時間性,它再長,也是短暫的,只有人及文化才是永恒的。又正是人文學者們提醒,還有一個后現代化問題。
[1] [美]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