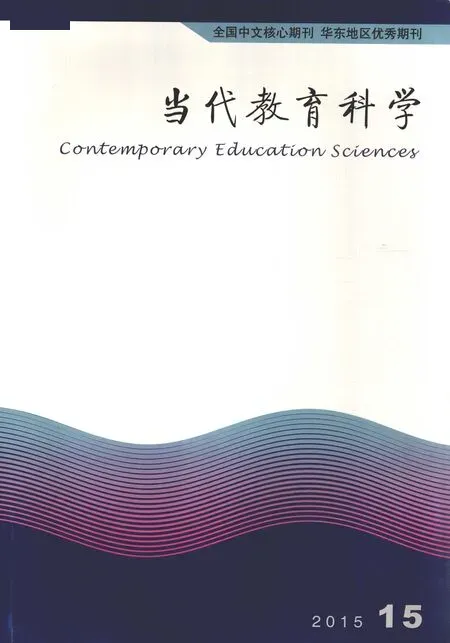農村代課人員的窘境及出路
●曹 文
農村地區中小學代課人員的待遇和出路問題,一直是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亟需解決而又長期未得到有效解決的突出問題。在許多地區這一問題已經成為制約當地師資隊伍建設的頭號難題。本文以有關部門所作的統計資料為依據,對這一問題存在的現狀、成因及其對策進行探討,以期引起社會有關方面的重視和關切。
一、農村代課人員何以存在
(一)教育剛性需求與在編教師名額差欠矛盾的催生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推進以及農村民眾教育理念的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礎教育階段學生的入學率。而農村地區和偏遠山區學生人數激增、規模擴大,要求當地教師隊伍的壯大和師資力量的增強。目前我國雖以師生比為依據確定在編教師數額,但仍存在結構性偏差。農村地區和偏遠山區經濟發展落后、條件艱苦,學生分布分散,所給予分配的教師編制數額甚少,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一師難求”的局面,僅僅依靠少數編制名額顯然無法滿足當前日益膨脹的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需求。但這些地區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的入學、求學問題卻依然客觀存在,并成為農村地區推行義務教育的頭號難題,招募代課人員不失為保障師資隊伍穩定、確保教學開展的有效途徑,緩解了教育的剛性需求與編制教師差額結構性矛盾。
(二)地方財力困難下的現實訴求
自2001年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確立了“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由此,縣級政府肩負起了保障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順利開展的重任。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地區、偏遠山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地方財政緊缺,教育經費拮據,無法支付大批足額的編制教師工資,而不得不采取控制編制教師分配額度的方法緩解財政壓力。如對河北省某省級貧困開發工作重點縣實地考察中,教育負責人提到:“如果教育的支出占到財政支出的50%,再對教育的投入就要慎重考慮,因為其他方面的支出也要保證,特別是一些應急性的支出。這種情況下的教師補充即使有了空編也難以為之。”[1]可見,教育財政不足成為催生代課人員的根源,甚至造成“缺編難補”、“有編不補”、“有編亂補”的亂象。代課人員的留存和新進成為“財政赤字”下普及義務教育的無奈和必然之舉,有著其現實合理性的需要。
(三)學校和代課人員需求的雙效作用機制
在節約開支、順利開展教學的雙贏利益驅動下,招聘代課人員成為農村地區學校生存發展的權宜之計。一方面,分配給學校的編制教師名額不足,縣、鄉、村補給的“代課人員”也滿足不了學校自身的需求,且存在編制教師因病、因事請假以及在編不在崗等狀況,致使現有的教師名額與教學任務失衡,在編人數不足、師資力量薄弱的矛盾凸顯,學校招聘代課人員成為擴充師資隊伍的快捷方式;另一方面,學校自身經費有限,在縣域分配名額不足的情況下可通過自主招聘代課人員的方式減輕校內開支,這也在客觀上為農村代課人員提供了職位供需。農村代課人員的身份構成主要為本地村民和應屆畢業生,本地村民一方面可通過自己的腦力勞動獲得部分勞動補助,另一方面也獲得了一定的職業滿足感。而對于應屆畢業生而言,選擇代課一是緩解畢業后工作難找的壓力,二是得到了鍛煉和提升教育教學能力的機會,為以后的求職擇業奠定基礎。可見,學校和代課人員自身需求為農村代課人員的留存和新進埋下了伏筆。
(四)歷史性遺留問題對清退政策的制約
代課教師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產物,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已經有了代課教師,但代課人員的大規模激增卻出現在20世紀80、90年代農村小學的學制改革時期。雖然在1997年國務院辦公廳就發布了《關于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通知》,要求“到2000年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實施‘關、轉、招、辭、退’方針”;2001年國務院在《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出“堅決辭退和逐步清退不具備教師資格的人員和代課人員”;2006年教育部明確表示“不允許使用代課教師,對尚存的44.8萬名代課教師逐漸全部清退”;2011年教育部、財政部、中央編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又出臺了《關于妥善解決中小學代課教師問題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了“擇優招聘、轉崗使用、辭退補償、納入社保、就業培訓等多種有效途徑妥善解決代課教師問題”。但就目前來看,代課教師依然留存。因其政策的執行必須以現實為依托,而短時間內“一刀切”的政策顯然不符合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現狀,雖然有部分代課人員已被清退,但在貧困的中西部地區、偏遠農村地區,代課人員依然被保留甚至仍在不斷引進,雖有違政策精神,但卻是歷史與現實“雙效管控”作用下的產物。
二、農村代課人員隊伍發展面臨的窘境
(一)隊伍建設存在結構性缺陷
1.數量龐大,流動性強
據教育部及相關調研的統計數據分析發現,農村代課人員的人數基數大,且呈流動態勢。據2015年3月中國青年報報道:“到目前為止,根據調查測算全國仍有代課教師20多萬人,主要集中在農村中小學。”[2]在農村和偏遠山區,由于生存環境艱苦、收入微薄很難吸引代課人員長期留存;加之當地人員外出務工的現狀,部分適齡子女跟隨父母進城上學或間隔性回村入學,學校對代課人員的需求也隨之浮動變化。如對甘肅某地的調查中,有代課人員坦言:“要是工資不漲,可能就不干了,生計是問題,上有老、下有小。”[3]再如宕昌縣教育局副局長說:“代課人員群體的流動性非常大,教育部門還沒有對其動態的監控。”由此可知,代課人員雖然作為龐大的社會群體存在,但實則在社會轉型時期諸多因素制約下,其高速流動態勢亦漸趨凸顯。
2.整體學歷層次不高,職業訓練不夠
農村代課人員大多未接受過正規的師范學校教育,也未經過專門教師教育培訓。以往農村代課人員的學歷主要集中在中專、高中層面,在某些偏遠山區甚至只讀過幾年小學,認識一些字的人就擔當起了教學的重任。近幾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除某些極偏遠地區,新注入的年輕農村代課人員學歷層次上均有所提高,但與其他地區相比仍處于較低水平。在中西部六省調研中,發現15.3%的代課人員第一學歷低于初中(含初中),64.7%代課人員第一學歷是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代課人員占代課教師的比例為20%。[4]2014年某市對全市的在職初中和小學教師進行本體知識的摸底測試,發現不及格的教師大都是農村小學或教學點的代課教師,還有個別教師成績在個位數。[5]可見,農村地區的師資隊伍不僅在學歷層次上相對城鎮較低,且存在教師個人專業知識不達標狀況。
3.隊伍年齡和性別結構失衡
農村代課人員在年齡結構上以中青年為主,且以當地女性居民居多。越來越多的年輕教師開始涌向農村地區,成為當地教育的新秀。華中師范大學課題組對陜西、貴州、廣西、湖北、安徽、河南6省調研表明,在3986個農村教師樣本中,代課人員的比例是5.1%;在198個農村代課人員中,教師平均年齡約32.3歲,大約82%的代課人員是中青年老師(小于40歲)。[6]西部某省對20個隨機抽取縣的72個鄉鎮的239所學校進行的調查顯示,代課人員中女性占到近60%,而公辦教師中男教師卻占到近70%。[7]再如根據調查資料,五華縣代課人員總數為1848人,其中男性代課人員205名,占11.09%,女性代課人員1643名,占88.91%。[8]年齡層次的集聚化和性別結構單一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師隊伍的整體發展,亦成為阻礙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要素。
(二)作用發揮遇到諸多掣肘因素影響
1.普遍工資待遇過低,生活條件艱苦
代課人員的工資待遇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卻又長期未得到妥善解決。2014年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最美鄉村教師”王世明時得知他每月工資僅有400元;工作了27年的代課人員朱晨霞工資從40元漲至2014年的185元,對雙胞胎兒子的大學學費只能望洋興嘆。而在甘肅省,目前和朱晨霞一樣的代課人員還有8000多人。2015年兩會期間,有委員專門就代課人員工資提出了議案,指出“在中西部農村教師中有67.34%的教師沒有屬于自己的住房,教書近30年的農村小學代課教師從每月10元報酬開始,至今才給1000元報酬”。在諸多農村地區、偏遠山區,交通不便、經濟文化落后、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代課人員工資還常常遭遇拖欠。貧寒的生活,很難讓代課人員扎根學校,捉襟見肘的生活使他們深陷窘境,苦惱不堪。
2.社會認可度低,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得不到充分發揮
對于代課人員這樣的一種稱謂,很大程度上把這些教師的角色僅僅界定為臨時代課,這其中不免夾雜著輕視與歧視之意。有學者指出,農村代課老師如同“教育民工”生活在農村的最底層,成了連維持生計都困難的弱勢群體。[9]很多當地的農村代課人員也被人戲稱為“教書的農民,種地的先生”,在某些地區甚至被視為社會的三等公民。自2005年以來,官方資料中便使用“代課人員”來代指農村代課教師這一群體,可見國家意在逐漸從政策層面將之排除在教師行列之外,再加之清退政策的全面施行,更使代課人員走向了教師的“邊緣”。社會認可度低的現狀,極易使代課人員產生消極懈怠心理,難免在教學過程中出現敷衍現象,教學積極性不高,而“腦體倒掛”的生活現實不斷沖擊和迫使他們另謀生計。
(三)職業發展受到多重制約
1.多數教師課業繁重,工作壓力大
農村代課人員大多承擔著繁重的教學重任,周課時工作量甚至超過公辦代課人員;所教科目繁多,一名代課人員通常需要擔任多門學科和不同年級的課程,因此大量的備課、上課、批改作業成了代課人員的縮影。如湖北省通山縣燕廈鄉某小學的程老師同時教語文、數學、體育、音樂四科,還擔任教導主任、班主任職務,每周課時超過26節;鳳凰縣巴幾小學一個教師代兩個年級的所有科目;在某些偏遠山區,農村教師還要擔負學生的起居生活。2012年記者采訪河南省洛陽市嵩縣艾力希望小學時,發現老師懷抱學前班孩子指導其他孩子趴在桌上午休。在某些偏遠的山區農村,一個代課人員甚至承擔著整個學校的課程。
2.培訓機會少,職業發展受限
由于代課人員的特殊身份,不被列入在編范圍的教師很難得到培訓機會。為了獲得職業發展機會,曾有代課人員曬出自己17年的工資18700元,而進修費用則高達22000元;相比之下,公辦教師卻可以免費享受國家提供的中小學骨干教師培訓計劃,在假期間可享受專門的教師理論和職業技能培訓、網絡課程培訓等。再者,從職業發展的前景來看,某些農村代課人員雖然教學成果顯著,在鄉村學校培養出了大批優秀的學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然而由于其學歷、身份的特殊性,往往無緣于先優評優和職稱晉升。
三、農村代課人員走出窘境的路徑選擇
(一)壯大鄉鎮師資力量,合理配置師資資源
鄉鎮師資力量的匱乏是催生代課人存繼的直接要素,而國家通過政策引導,擴充農村師資力量是當前減少代課人員的重要舉措。如先行試行的三年特崗教師計劃、西部志愿者計劃、免費師范生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師資建設的壓力,但由于部分鄉鎮地區條件艱苦,交通不便,使得原計劃方案的人員配置達不到教育需求。如據2015年教育部不完全統計:一年多來,各地農村中小學補充教師35.8萬人,近兩年全國招聘的13.2萬名特崗教師中,有95%到鄉鎮以下學校任教。[10]此外,可配合采用教師機動編制的做法,對在崗教師實行定期輪崗,給予經濟補償和績效考核,并納入職稱評定和業績考核,給各縣、市下達流動指標,適當安排部分優秀教師去各鄉鎮考察教學、深入調研、擴充師資。
(二)妥善調整財政支付結構,設置專項資金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以縣為主”的教育財政體系,但縣財政拮據的現狀致使教育財政投入比例較小,可分配的財政數額難以滿足增添編制人員數額的工資需求。基于此,國家可考慮執行“以省為主、中央財政補貼為輔”的農村義務教育財政體制,針對省區內的貧困農村,以設置財政專項資金的方式,定期給予財政補貼,制定具體的資金使用計劃,保證財政補貼資金的發放和使用。一方面各縣可采取自主申報,省級單位下鄉考察的方式,對符合財政補貼的鄉鎮采取財政撥付,另一方面,上級政府應當主動承擔,積極提升農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適時調整投入比重。如可參照2012年4月湖北省政府下發的 《省人民政府關于創新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機制的意見》,要求“從2012年起,全省農村義務教育學校(不含縣城)新進教師,初選全省統招統派、經費省級負擔、縣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管理、農村學校使用的新機制。”此種方式的執行,將減輕縣級政府的財政負擔,使得省內教育投資均衡化,更利于農村義務教育的全面統一發展。
(三)完善法規政策,保障原有代課人員的切身利益
“同工不同酬”是代課人員長期所面臨的困境,而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等有關規定,相對在編教師勞動強度高、薪酬低是對代課人員勞動成果的“變相剝奪”,雖然在政策制定層面上已經提出了相關的代轉公、清退補償等措施,但實則能真正轉為公辦教師的“幸運兒”微乎其微,大批代課人員面臨被清退、補償低的厄運,這部分代課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便成為矛盾的核心。在2015年的“兩會”上,也有委員提出了按任教時間給予清退的解決對策,如根據代課人員任教時間情況進行年齡、教齡劃線,進行教師分層。近兩年各省參照黨中央的指示文件,大多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如在代課人員人數不多的情況下可參照重慶市公開招考的方式,并按照教齡和工作成績給予相應招考加分,不合格教師在解聘的同時按照相關規定給予一次性足額補償。而對于代課人員人數相對較多的省份地區,可參照云南省采取不同年齡分別對待的方式,對各個年齡階段的代課人員給予相關的就業指導與安排。在某些落后農村地區,師資嚴重匱乏,則應該考慮多增加教師。在偏遠農村地區,不僅不能取消代課人員,而應該吸納代課人員,正如河南省淅川縣馬蹬鎮中心學校校長所說∶“由于待遇低,一些地方甚至請不來人當代課人員。”[11]可見,代課人員問題應該參照各村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開展,并切實保障代課人員的切身利益,包括薪金收入、勞動保險等。
(四)采用“教師雇員制度”,規范用人機制
代課人員沒有名分,很大程度上源于用人機制的欠缺。在無法解決全員編制的境況下,實施教師雇員制度是緩解農村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師資匱乏的有效舉措,是保障教師權益的可行之策,是提升師資建設的必備要素。教師雇員制度的實行要求教師專業的提升,包括對教師知識領域、教齡、任務職責、專業發展等維度的綜合評定。要綜合考慮代課人員自身專業成長發展的獨特之處,出臺代課人員職業標準認定和專業發展規劃,系統性、綜合化地做好代課人員職業發展工作。教師雇員制度通過嚴格的考核機制,篩選符合條件的教師人選(對于偏遠山區和貧困農村地區實施代課人員政策傾斜),設置統一考試,并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和代課人員個人的具體情況綜合考察,對條件合格人員簽署勞動合同,并嚴格規定合同期限、工作內容、薪酬、勞動責任等,統一進行定期培訓;對不符合條件的代課人員及時給予清退并根據其工齡、績效、成績等方面進行一次性補償,確保代課教師的基本權益。
[1][2][5]農村代課教師問題難根治:部分僅高中學歷[EB/OL].http://www.edu.cn/edu/shi_fan/shi_fan_news/201503/t20150317_1237905.shtml.
[3]劉文華.社會轉型期西部農村代課人員社會行動策略研究[J].當代教育論壇,2014,(3).
[4][6]雷萬鵬,陳貴寶.論農村代課人員的分流政策[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1).
[7]安雪慧,頡俊祥.西部農村代課人員發展現狀調查[J].教師教育研究,2008,(1).
[8]唐梓翔.代課人員現存狀況及存因剖析[J].法制與社會,2012,(8).
[9]畢延河.農村代課老師如同“教育民工”[J].觀察與思考,2006,(6).
[10]教育部:各地農村中小學補充教師35.8萬人[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5-04/02/c_1114855377.htm.
[11]秦興利,李宜鵬.代課人員,無奈的選擇[N].河南日報,2006-9-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