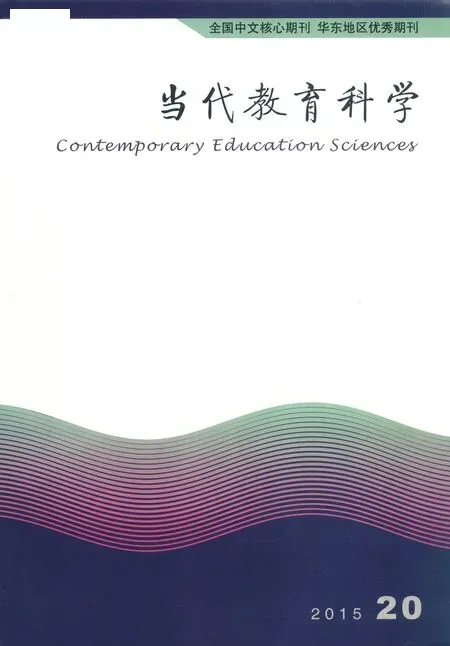論杜威教育哲學思想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張曉琴 繆虹云
論杜威教育哲學思想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張曉琴 繆虹云
經驗論構成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根基。他以經驗統攝心與物,把經驗引向本體化,導出人化的實在和生活世界。人在生活世界中就是不斷生長,因而,生長和經驗相通,生長就成為杜威教育哲學的本體。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不斷改造。它對教學改革的啟示就是要消除師生關系“中心—邊緣”的理解模式,實現“主體”關系范式到“主體間”關系范式的轉變,關注學生的生活世界的教育,與學生達成主體間性的理解與溝通。
杜威;經驗;生長;實用主義哲學
回顧20世紀,“也許惟一對20世紀教育理論和實踐具有最大影響的哲學是實用主義哲學”。[1]杜威將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理論相融合,開創的進步主義教育成為20世紀上半世紀美國教育的主流,直到20世紀60、70年代的存在主義教育哲學仍然留有進步主義教育哲學的影響。在杜威90誕辰之際,《新共和》的編輯們在其專刊上總結了他對美國的影響,聲言:“如果有任何其他人對現代智慧生活的影響可以與杜威相比的話,那么我們還不知道他是誰呢”。甚至有人提出:“沒有一個現代美國人能不受約翰·杜威的影響”。[2]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進步主義教育哲學經胡適、陶行知等人的傳播,“實用主義”成為20世紀初中國最流行的話語。杜威的思想成為20世紀初影響中國教育最深的西方思潮。眾所周知,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是其實用主義哲學在教育領域的延伸,杜威曾言:“如果一個哲學理論對教育上的努力毫無影響,這種理論必然是矯柔做作的”。[3]因此,他認為“教育乃是使哲學上的分歧具體化并受到檢驗的試驗室,哲學就是教育的最一般的理論”。[4]因而,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和進步主義教育哲學融合貫通,其關于教育本質的認識對今日的基礎教育改革和發展有著較強的現實借鑒意義。
一、經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根基
實用主義把經驗論以及來自歐陸的哲學與美國人特殊的科學和宗教相結合,在美國長盛不衰。追溯其源,內夫認為,實用主義的形成也和其他哲學流派的形成一樣,有其歷史淵源,那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河流”的思想,普羅塔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的觀點;圣經上的“你將要從它們的結果知道他們”的思想。[5]以及從洛克對先天觀念的拒絕,貝克萊對物質的排斥,休謨對實體的靈魂的反抗,到穆勒把事物解釋為感覺的恒定可能性,英國經驗主義有種總的傾向,就是努力從認識中排除一切無法為經驗證實的東西。[6]這也正是現代實用主義所擁護的。
現代實用主義哲學的興起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那就是20世紀偉大的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以及人們對所從事的活動的物質利益和實用性更感興趣。其主要推動力是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出現。人類自身是遵循自然選擇,適者生存規律緩慢進化的產物,這個事實提示著人類的精神和能力和他的身體一樣也是適應生命的實際需要緩慢進化的產物。因而,經驗和生長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進入了實用主義領域。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是對皮爾士和詹姆士實用主義哲學的繼承和發展,其最核心的概念是經驗,即把經驗看作世界及人類認識世界的基礎。杜威從存在論的視角,對自柏拉圖以降的現象與理念的二元論傳統哲學思想提出批評。因而在本體論上,杜威貶斥形而上學,實際上是:“試圖系統地超越人們從占有統治地位的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傳統中繼承下來的那些重要的二元論,例如自然和生命的二元論、心身二元論、質料和形式的二元論、感覺和理智的二元論、行動和標準的二元論。”[7]杜威的基本傾向是用“經驗”這個概念包攬一切,主體和客體、人和環境、精神和物質、知和行等統統被收入經驗的范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渾然一體,名為“經驗”。杜威指出經驗“不承認任何行動和材料、主體和客體的區別,而把雙方面都包含在一個不可分析的總體之中”。[8]人所面對的世界是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人化的實在,其本質是生活世界,它剔除了超驗性,使之與人的生存狀態、日常生活密切相連,形成并開展于主體作用之中。
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在本體論上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擯棄,從而強調經驗,只有經驗才是真正的實在。因而經驗就上升為實用主義的本體論,成為人化的實在,是具體的、一次性的、多元的生活,從而把經驗與生活相溝通。杜威在存在論上界說經驗:是人與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所發生的一種相互作用或交涉,經驗不等于知識,不全是主觀的,不只承認過去,不是個別的和孤立的,并非不包含推理,它是有機體和環境的互相作用,具有推理能力、客觀性、連續性和能動性。[9]因而,從杜威哲學本身來看,他的經驗論構成其哲學的一個根基,他的認識論、方法論、教育哲學等內容都從這兒生發出去,具有內在的融貫性。經驗包攝心與物,心物的區分只是功能上的,而不是實體上的;知與行是心物相互作用的兩種相關方式,并沒有分離,故而引出認識論上的知行合一。經驗是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如果把環境理解為社會,那么存在論上的心物膠合就導出群己之辯上的個人與社會和諧互動以及社會民主化。[10]經驗具有連續性和生長性,它與生活合拍,因而在教育哲學上引出其對教育的獨特理解。
二、生長:杜威進步主義教育本質
從經驗到人化的實在,進入生活世界。人在生活世界中與外界環境是交互作用,自然而然的引起教育的概念,即從經驗的本體化傾向通向教育的本體論。教育是什么?杜威回答說“教育即生活”。什么是生活呢?“生活就是發展;而不斷發展,不斷生長,就是生活”,[11]要保證繼續生長,就要不斷改造經驗。“教育就是經驗的改組或改造”。[12]由此可見,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改造。
(一)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
從經驗論出發,杜威認為生長是一個連續性和階段性相聯系的動態心理發展過程。在對傳統的“某物由不完全而達到完全之變遷”的生長觀的反動的基礎之上,杜威聲稱:“向著應該后來的結果,逐漸往前發展的運動就是生長的意義。”[13]并認為“全體生活皆是生長,凡是生命之所在,即有動的生長,而所謂停止生長者,并非一個人的道德的生長已經完備,簡直就是生活的停止,生命的死亡了。”[14]并且,他還指出,兒童的生長表現為兩個方面。即物質的方面和心理的方面,是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節律性的。同時,杜威指出,生長必須以兒童的本能、能力為依據。其起點是兒童的“未成熟狀態”,但是“未成熟狀態”決非是一塊空無所有、可以任人涂抹的白板,實際上它標志著一種“積極的內容”、“積極的能力”。兒童依據本身的依賴性和可塑性,在未受教育前,有一種天生的“本能、性情和沖動”。他把兒童的本能比作是“萌芽的種子,含苞待放的蓓蕾”。[15]因而,兒童的“未成熟狀態”是處于生長期,兒童主要是通過自己的主動努力的活動,通過經驗的不斷改造來改變自己,使自己達到新的發展,而不是單靠外力的作用。
杜威又從教育與社會生活關系的角度指出教育即生活。兒童的本能生長總是在生活過程中展開的。他說:“生活即是發展;發展、生長,即是生活”。[16]杜威將教育的本質也理解為就是生活。什么是生活呢?“生長”、“發展”的生活就是好生活;在生活世界中,用經驗來解釋生長。生長就是“經驗的改組或改造”。“這種改組或改造,既能增加經驗的意義,又能提高后來經驗進程的能力”[17]這是一種“善”的經驗流向取向,而這種取向的過程又必須通過經驗的連續性與經驗的交互這樣兩個途徑獲得;而這兩個行動原則的執行就涉及到兒童的經驗性活動的形式—社會性活動。這種社會性活動應該服從的準則只有一條——民主的社會活動形式。
杜威從教育即生活中引出他的教育無目的論。生活的特征是生長,教育即生活。這句話意味著教育即生長的過程。因而,教育只是一種過程,除了這一過程自身發展以外,教育是沒有別的目的。“生活就是發展;發展,生長,就是生活。如果把這個意思用教育上的話來說,就是:①教育的歷程,除了這個歷程自身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②教育的歷程,即是繼續不斷的重新組織、重新構造,重新形成的歷程”。[18]教育不是為未來的完滿生活作準備。教育就是讓兒童現時過上完滿的生活。這種生活過得是否完滿,就看它是否符合一定的標準—民主,這就是《民主主義與教育》的核心。兒童的生長不僅指智力和道德的生長。如果說教育是一個培養什么人的問題,那么在杜威所設想的教育中,兒童生長期望的目的在于良好的公民。即:不僅要成人,成就一位有道德的有品味的人,而且要成才,成為一位有技藝、有創造力的人才,從而成為“有用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造成生活的進步,推動現代生活民主化。這才是教育的真正的目的。梁漱溟對杜威的教育無目的的解釋更把握住其含義,“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個什么,是教你更會受教育,教你學習更會學習,這就是杜威的真意思,他反對達到固定的目標……他說的開展是無目標的開展,只許長,不許成”。[19]因而,杜威的教育無目的論是對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的強調。
(二)教育是經驗的繼續改造而體現生長
生長的理想歸結為這樣的觀點,即教育是經驗的繼續不斷的改組和改造。這是杜威對教育即塑造、教育即復演和追溯兩種教育哲學的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的教育哲學觀。杜威稱“教育即改造”、“經驗的繼續不斷的改組和改造”,為教育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具有的“當前的目的”。所謂經驗的改組和改造與經驗論里的經驗的“連續性”有關,表現為主體與客體、有機體與環境的一種相互作用。他將此思想稱為經驗的“交互作用原則”。在此基礎上又提出了經驗的“連續性原則”。經驗的連續性指的是:人最初的經驗來源于“先天的能力如做事、探究的本能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但在人的一生中要不斷經歷、改變各種事物,在活動中獲得新的經驗增加到原來的經驗上去以后,就會對兒童的經驗進行改組改造,使初步的原始的簡單的經驗,逐漸向充實、成熟、復雜的方向發展。他認為,兒童經驗的改組、改造有兩點意義。其一,是“增加經驗的意義”,即通過一系列教學活動,使兒童認識到過去未曾感覺到的事物的某些聯系、種種活動的相互關系。杜威認為,兒童通過活動所獲得和增加的經驗,既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社會的,依活動的性質和內容而定。杜威主張通過大量的社會活動,甚至可把學校辦成簡化、凈化的雛形社會的方式,來使兒童獲得社會經驗、社會意識,把個人經驗和社會經驗結合起來。經驗改造的第二點意義是“提高指導后來經驗進程的能力”,就是指兒童在參加某種有意義的活動時,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和“預料將會發生的結果”。這樣獲得的經驗就是“一種有意義和足以提高能力的經驗”,也具有開拓創新的意義。[20]由此可見,杜威提出的教育概念是對“傳統教育”的反動,從教育本體論角度延伸開來的教育理論,開辟了教育理論的新范式。
三、杜威教育哲學的借鑒與啟示
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哲學開拓了教育理論的新范式,其體系完整的教育思想,如同它所受到的熱烈歡迎一樣,在美國乃至世界也受到猛烈的批評。在中國,對實用主義的批判多于對其傳播,而對其批判大多數是在對其思想誤讀的情況下作出的。正如克雷明所言“在對杜威發起猛烈攻擊的人中,多半是未讀過他著作的人”。[21]因此,在借鑒杜威教育哲學思想之時,應建立在反思性批判基礎上。立足我國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實踐,杜威進步主義教育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全人教育的價值觀
杜威教育哲學是建立在對傳統哲學的批評基礎上形成的,尤其是對傳統哲學中二元論的批判,其經驗哲學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形而上學理論,而是一種立足于人,以人為本的價值理論。無論是對于自然、社會還是認識和真理,他都企圖確定它們對人的生活的意義和價值。[22]在其基礎上,杜威教育哲學根本點是以經驗統攝世界,致力知與行、經驗和理性、理論與實踐、理想與現實的整合,由此建立起教育生活的豐富性、恢復生活的連續性,這就是杜威教育哲學的價值所在,體現了一種個體與社會相互影響,注重個體發展,注重社會變化和秩序穩定的特點。由此可見,杜威在教育無目的論的口號下實際上蘊含著獨特的教育價值觀,即教育的宗旨在于受教育者的自主發展和個性發展。在當代社會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杜威的教育價值觀更是觸及教育的如此深刻和深層問題。受杜威思想的影響,人本主義教育、全腦開發教育(wholebrain education),合作學習以及建構主義教育等思潮的綜合發展,最終形成全人教育思潮,其價值目標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即個體在智力、職業、生理、心理、社會、道德、倫理、創造性、精神各方面的和諧發展,強調受教育者與他人及自然的相互關聯,尋求將個體與意義的情境相互關聯,強調多樣性的統一。[23]長期以來,我國基礎教育中關于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爭論,從表象上來看,是教育范式的轉換,從本質上來看,則是教育價值觀的根本變革。杜威教育哲學關于人的存在及其全人教育的價值取向,是要從人的視角來看待教育問題,人的發展即教育的根本目的。因此,《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把育人為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育人為本要做到立德樹人,以學生為主體,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把促進學生成長成才作為學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落實規劃綱要精神,切實推進素質教育,就應確立全人教育的價值觀,把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作為教育根本目的。
(二)生活教育的方法論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其哲學的延伸,用杜威的話來說“哲學、教育和社會理想與方法的改造是攜手并進的”。[24]作為其教育哲學的核心,經驗和生長是其教育哲學的本體論,通過對杜威教育哲學本體論的梳理和反思,可以看出,杜威以經驗來消解“二元論”,從而引起教育方法論的整體變革,杜威進步主義教育哲學深層地蘊含著教育主體視角應當向主體間視角的轉換:從師生的“主體”關系轉向師生的“主體間”關系。[25]教師和學生在教授和學習活動中無疑都具有主體地位。因而,如果將經驗和生長聯系起來考慮,在主體間范式里,師生關系是一種特殊的主體間關系,在師生互動過程中,教師和學生是平等的合作者,教和學的合作者。因而,用“中心”和“邊緣”的主體性范式去理解教育,就會把教育看作是幾個孤立的、分離的活動的湊合,這一點與杜威的哲學思想相違背,在某種意義上說,冠以杜威的教育理論以“兒童中心論”,也是對其教育哲學的一種誤讀。因此,基于生活教育的方法論,基礎教育改革要實現從“主體”關系范式到“主體間”關系范式的轉換,教育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在異鄉的科學世界中進行理性進修的同時,尋求家鄉世界精神家園的意義,[26]實現日常生活的教育與科學世界的教育兩個領域的融合,構建整體意義上統一的教育生活世界,關注學生的經驗、生長和作為人的本質存在,這是杜威教育哲學本體論對今日基礎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啟迪,也是“以學生為中心”教育價值觀的真正意蘊。
[1]杰·阿基比魯.教育哲學導論[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121.
[2]W·F·康內爾.二十世紀世界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79.
[3][4][24]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44,346-347,347.
[5]崔相錄.二十世紀西方教育哲學[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104.
[6]T·E·希爾.現代知識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366.
[7]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現代美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247.
[8][11][12][15][17]趙祥麟.杜威教育論著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272-273,15,159,84,159.
[9][10][25]顧紅亮.實用主義的誤讀[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6,22-23,292.
[13][14][16][18]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M].鄒恩潤,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49,27,58,16.
[19]梁漱溟全集(第7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690-691.
[20]楊漢麟.杜威的生長論初探[J].教育研究,1992(2):71-75.
[21]L·A·克雷明.學校的變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1.
[22]王守昌,蘇玉昆.現代美國析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85.
[23]吳立保,唐赟-周竹萍.類主體視野下立德樹人的范式轉換與路徑選擇[J].中國教育學刊,2014(11):57-61.
[24]項賢明.泛教育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258.
(責任編輯:金傳寶)
本文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江蘇省人才強省建設研究基地課題“面向江蘇戰略性新興產業人才需求培養機制研究”(課題編號:SKRC201400-3)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張曉琴/南京林業大學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副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為教育生態學 繆虹云/濟南市特殊教育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