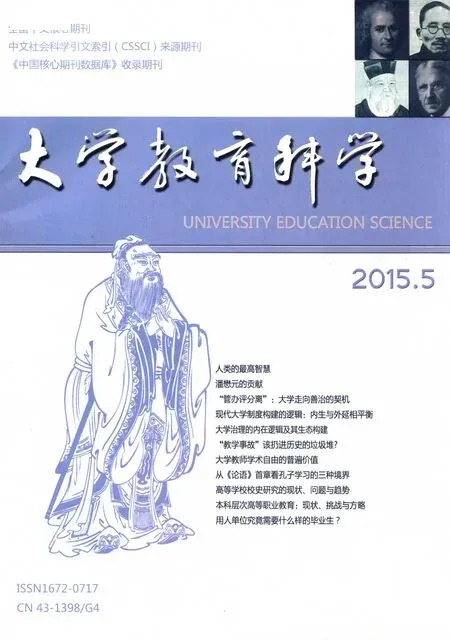大學教師精神實體的當代建構
□ 魏傳光
作者曾在《大學“立德樹人”的文化省思》一文中提出,教師文化是完成“立德樹人”目標的主體性文化載體[1]。隨著思考的深入,針對一些大學教師成為“事務主義者”、“教書匠”和“純粹職業者”的現象,越發覺得大學教師需要自我建構作為精神實體的存在,與學生精神相遇于大學校園,利用大學教師職業的空間平臺,享受對日常生活的體驗與反思、對教育的批判性與哲理性思考、對時代變革敏銳的觀察與把握等精神生活,歆享精神生命的光輝。本文以大學教師精神實體的建構為重點,續承“大學‘立德樹人’的文化省思”,求教于大方。
一、大學教師“為何”要作為精神實體存在
精神實體最早出現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中,但笛卡爾強調的是精神實體的獨立存在意義。而在此,精神實體是指大學教師經過漫長的精神教養和思想努力,擺脫單純的生物實體和知識實體狀態,以包攝生命充盈、精神充實、情感充沛、德性充達的狀態存在。或者講,大學教師作為精神實體存在,就是俄羅斯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所講的“自由、意義、創造的積極性、完整性、愛、價值”的擁有[2];海德格爾所講的“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黑格爾所講的“就人作為精神來說,他不是一個自然存在”[3];文天祥所講的“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當然,精神實體還是精神的創新、文化的傳承和“立德樹人”使命的重要承擔者。大學教師的“精神實體”建構既是基于直面問題之后的現實憂思,又是基于教育價值而澄明教師存在方式的理論思索。
(一)現實的憂思
近些年受市場體制的影響、文化觀念和多元價值的碰撞,整個社會的價值狀態和觀念形態不斷裂變,對大學教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一些大學教師只是作為物質實體單向度存在,而精神實體日益虛化,具體表現為:
1.精神虛無。在市場經濟社會中,貨幣資本是社會身份確立的“強勢資本”,教師所擁有的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屬于布迪厄所謂的“弱勢資本”,這就導致“轉型期知識分子在神圣秩序與世俗秩序、神圣價值與世俗價值之間感受到了緊張與焦慮”[4]。一些教師為了緩解這種緊張,開始用馬克思·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替代“價值理性”,用“功利主義”觀念理解生命與職業,以至于“只知有物質的我,不知有精神的我”。一些大學教師生命的價值被肉身的價值所取代,快樂、享樂、有用性成為評判標準,呈現“終極價值的貶損”與“價值信念的坍塌”。精神虛無的教師在教育中不再有希望與夢想,不對美好、高尚與丑陋、卑下進行區分,教育活動中很難容納任何形式的激情、愛欲與沖動,平庸主宰了生命的自我形塑,日常情感體驗也呈現出鈍化狀態。正如尼采所言,“失去了主要動力”的人們無所事事,而在精神上人們卻更加“疲憊”,對人們而言,“迄今為止”所有的作為“都是徒勞之舉”[5]。
2.激情缺失。教育是一項“靈魂工程”,需要教師產生“相連于靈魂自身的知覺。”這就是笛卡爾(Descartes)所講的“激情”[6]。羅素也堅信:“人類成就中最偉大的東西大部分都包含著某種沉醉的成分”[7]。但一些教師由于缺乏“激情”的精神生命,沒有動力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活動之中,更難在教育中心無旁騖,拒絕庸俗。一些教師在教育中雖然呈現出“理性”,但由于壓抑了激情,顯得生機萎頓,形如委衣,志如死灰,沉寂枯萎,抱殘守缺,隨波逐流,被動地聽從命運的安排。正如羅素所言,“許多聰明的心靈被磨鈍了鋒芒,他們敏捷的思維遭到了毀壞”[8]。
3.德性迷失。由于現代大學教育越來越突顯“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智力開發”的教育,再加上知識信息的更新、教育技術的跟進、學習方式的改變使得教師“權威”地位和“主體”形象雙重陷落,使得一些教師對師道不再敬畏,放棄了職業圣神感的意義定位和追求,甚至“敬”便成了“肆”,隨意、放任教育活動。這樣“人師”淪落為“經師”,在教育中自覺疏遠羞恥與遠離規則,教育生活中只剩下及時行樂和物質躁動,職業只剩下為生存、“稻粱謀”的意義,“出售知識”和“商品交換”成為一些教師的職業理解。這樣,教師團體只是知識實體,并復合狀、結晶化為“物質利益集團”,而本屬于精神與真理的學術研究也成為物質生產與消費體系的“共謀者”和“附屬品”。精神生命中德性的遮蔽和迷失,最終使得一些教師遠離崇高,精神貧乏,情感放逐。
(二)理論的澄明
精神是教育的基本起點和重要訴求,教育在本質上是啟迪人的精神世界、建構人的精神生活方式、實現人的精神生命價值活動的事業。教師作為精神的展示者、牧養者和引領者,本身需要首先作為精神實體存在,需要在角色發展的語脈和坐標中,敞亮和澄明教師精神實體的存在方式。
1.“立德樹人”價值目標的應有要求。
“樹人精神”和“使人文化”是大學教育的“立德樹人”的應有之意,而“樹人精神”和“使人文化”是需要教育過程中師生精神家園同構,需要教師有情有義地與受教育者一同共赴知識的海洋,同舟共濟地去探尋精神生命的發展。“教育教學活動呼喚的是教師的經驗改造與心靈豐富,顯示的是教師的文化底蘊和教育追求”[9]。因而,只有精神生命煥發的教師,才能培育精神生命旺盛的學生。大學教師需要時刻銘記自己的工作對象不是器物而是人,因而自己的職業本質是創造人的精神生命。如果對技術熟練程度的過分關注和對精神發展的漠視,就會失去了“公眾教師”和“社會思想者”的精神氣質,成為典型的“教書匠”和“學科專家”。惟有肩負創造人的精神生命的使命,摒棄技術工匠對工作對象不需情感關照的比照,教師職業的非理性本質才不會淹沒在科學主義技術論的煙飛云散中[10]。這樣,學生才能在教育中能夠感受幸福,分享智慧,充滿詩意,提升精神生命,而教師才能完成“人類價值的守護者”的精神擔當和“立德樹人”價值目標。
2.教師主體的存在根基。
“真正好的教學來自于教師的自身認同與自身完整”[11]。孔子十五歲志于學,從此學而不厭,樂而忘憂,正是由于貫穿于其中的精神成長和精神充盈讓他感受到了精神自由的樂趣。之所以在此提出教師主體的存在根基是精神實體而不是物質薪酬,根本原因在于“教師的專業成長歸根到底取決于教師自身,純粹依靠外力推動的教師專業可能會使教師在職業上獲得一定的地位,但并不必然地促使教師個體的專業成長”[12]。一些研究認為,民國前期大學教師薪酬普遍較高,因而出現燦若星辰的大師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實體[13]。誠然,“物質上不受牽制,精神上才能獨立”[14]。但事實告訴我們,物質的豐裕只是精神充實的前提,并不是必然。相反,如果教師的視線僅聚焦于薪酬本身,反而會消解教師生命的敏感與豐富,摧殘教育精神的靈氣與生動。因而,教師的幸福與快樂最終要源于精神生命的蘇醒與綻放,教師主體的存在根基只能定位于教師精神實體的完滿、充盈與健康,教師的精神底蘊和心靈契約才是教師自身蓬勃發展的重要基礎。
3.大學教師作為知識分子存在的要求。
大學教師作為掌握知識并以知識傳播為己任的群體,容易被民眾當作社會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著名思想家薩義德認為,“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15]。因而,僅僅掌握知識并不構成完整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還應該是真理與正義的化身,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大學教師作為知識分子存在,身上必須具有批判意識、公共意識、人文精神和獨立人格等特質,必須有公平、正義、民主、平等、生命等這些精神價值追求,大學教師的“學術研究”必須具有引領社會精神文化發展的價值。從這個角度看,大學教師需要具有謙謙君子的精神追求,能夠超越物質追求,保有道德激情,既要“學問凸顯”,也要“思想彰顯”,堅守“人類價值守護者”的職能和對普遍道德法則的信守,追求真、善、美的統一,作為精神實體勇于“布道”。
二、大學教師“何為”才能作為精神實體存在
大學教師精神實體的建構是一件綜合事件,涉及社會氛圍、價值導向、薪酬制度、教育機制等等,在此方面學界已經形成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本文立足于以大學教師為主體視角,探討在當前的大學教育機制和薪酬制度下,大學教師如何從體認職業的內在自由、理解職業的創造性、體驗精神生活的愉悅出發,建構自身精神實體存在。
(一)通過體認職業的內在自由以喚醒教師的精神實體自覺
約翰·穆勒在《論自由》一書里對自由和精神之間的關系做了這樣的診斷:“假使文化史對我們有一點教訓,那么,就是這樣:有一個完全可由人力獲得的精神進步與道德進步的最高條件,就是思想和言論的絕對自由[16]。由于“人是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絕對主體”[17],思想自由對于人的精神生成意義尤為重要。思想自由可以使大學教師冷靜地尋求真理和知識的自治領域,在超越功利主義的客觀立場上對社會保持清醒的洞察力和批判思維。更為重要的是,自由是教師獲得道德尊嚴、善良意志和責任意識的基本前提,在自由之中易使大學教師沉思于諸如人生意識、存在價值等終極性問題。
雖然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有其底線要求,大學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場域。但總體上而言,相對于其它職業,大學教師擁有著許多可以按照生命本性所固有的內在要求支配自身存在和發展的自由。主要體現在:(1)在學術研究中,大學教師具有從事學術活動的自由,在進行學術探討和發表學術見解方面具有較大的自由空間,教師可以在學術研究中突破原有的知識框架,突破傳統,突破權威,突破成見,而這實質上是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顯現。(2)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可以超越教材而面對生命與意義,超越預設而面對境遇與挑戰,超越灌輸而面對對話與生成,超越框定而面對自身的完善與發展[18]。(3)在日常生活中,大學教師有較大的自由時間更加真誠地、機動地安排“現實生活”,有較大的自由空間與世俗生活保持適度的“距離”,對物質化的世界進行批判,容易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經濟主義的社會環境中“自由抽身”、“潔身自好”。教師職業的內在自由彌足珍貴,很多職業根本難以企及。因而,大學教師應積極體認職業的內在自由,這有助于教師主動構合情合理的精神世界,由被動的“在場”過渡到有情感融入的、充滿激情的“入場”,從而促進教師的實踐智慧與教育素養走向嫻熟。
(二)通過理解職業創造性煥發教師精神活力
創造性活動與精神活力的正向關系已經在心理學領域得到印證,由美國學者Merten和Fischer共同進行的心理測繪表明,由演員、作家構成的高創造力組比一般人構成的控制組在“精神質”量表上得分顯著更高[19]。實際上,人作為一種能動性的主體存在,不斷通過生存實踐破除作為“存在者”的狀態而獲得存在意義感。由于創造性活動內在具備的主體性、主動性特征,容易使其演化為生命的表達、主體的呼喚、意義的闡釋、價值的建構。創造的過程也是尊重差異、張揚個性、關愛生命的過程。因而,創造性活動容易使人體驗到生命脈搏和精神成長,體驗到“我”的生存意義和自我實現,從而容易激發生命活力和豐富內心世界。另外,創造性活動能夠讓人產生“高峰體驗”,從而產生心醉神迷的精神快樂和自我實現的幸福。
大學教育就是一種“新人”的創造活動,它既需要教師的創造性,也為教師的創造性活動提供實踐平臺,并形成積極的反饋與激勵。大學教師創造性活動的實踐平臺主要體現在:(1)激發創造性的因素較多。相對于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中存在著各種復雜、非線性外在變量,存在著很多影響教師成長的潛在偶發性。這些偶發性可以有效激發教師擺脫“常人束縛”,避免重復、機械的教育活動長期存在,刺激教師對教育活動保持敏感性與批判意識,在教育生活中展現出創造權;(2)具有創造性的實踐對象,即未定型的大學生,他們具有與教師創造性互動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是教師創造性活動的合適對象;(3)可以創造性地重組和理解教材和創造性地設計彈性化教學方案。大學教學允許教師以自己的視角、深邃的眼光重新詮釋教材內容的意義,實現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換。甚至允許自己編著教材,使用自己的講義。一般來說,大學教學鼓勵教師創造性地設計出具有開放性和彈性的教學方案,為創造性的生成留下空間;(4)教學活動中充滿的活力與歡樂為教師的創造性活動提供了及時反饋。教師如果能夠體認并理解創造性的價值與意義,就容易在創造性的教育活動中印證生命的意義、獲取職業尊嚴與職業幸福,在發展學生精神力量的同時獲得職業發展的精神動力和自我的精神滿足。
(三)通過享受精神生活激發教師的精神自信
不可否認,在市場機制中,精神活動不斷從人們日常生活中心退處邊緣,“變成生活中最無關輕重的外圍裝飾品”[20],甚至在短效功利的目光中,逐漸瓦解,成為褻瀆的對象。但物質中心并沒有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相反,它還經常降低我們的生活質量。比如,友情、愛情、親情,這是構成生活質量的重要元素”[21]。其實,有一些事物是人離不開的,諸如,人是需要一個精神學意義上的想像空間,一個精神扎根的地方,一個精神的來源地[22]。“文化熱”、“國學熱”的崛起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自由、平等、尊嚴、幸福等處世道德哲學在經過物質崇拜的浪潮之后也逐漸浮現。如果大學教師在教育活動中更多地進行師生的精神交流、動態的精神建構,體驗生長的精神愉悅和發展的精神快樂,那么大學教育實際上就成了教師的精神家園。在精神家園里可以進行人生經驗的分享與表達,日常實踐的體驗與反思,心靈的敞亮與對話,形而上問題的探討與辯論,對教育的批判性與哲理性思考。大學可以給教師提供這樣一種獨特的精神享受,是很好的遏制精神斷裂、心靈荒蕪的平臺。
如果大學教師能夠享受到更多的精神生活,就容易激出精神自信,自覺抵擋物質誘惑,享受精神生活充足所帶來的“雅福”。這種精神自信就會使大學教師自覺重拾“文化人生”與“士人精神”,在日常生活層面選擇精神富足而不是物質富足來消除沮喪、疲憊、冷漠的心靈,在靈與肉價值選擇的激烈沖突中利用高尚的精神理想去超越世俗社會,超越現世的、世俗的生存目的的生存法則,選擇健康、合理、正當的倫理價值主張。
三、師生精神相遇:大學教師作為精神主體的“何在”
德國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雅斯貝爾斯指出,“大學把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按照大學的理想,彼此應該毫無限制地相互發生關系,以達到完整的統一體。不只是在科學的專業范圍內需要交往,而且從事科學研究的個人生活也需要彼此溝通。因此,在大學圈內,研究者之間、研究者與學生之間都應互相討論并發表各自不同的看法”[23]。這句話實際上指出了大學教師作為精神主體“何在”方式,那就是與學生進行精神交往,精神相遇于大學校園里。
師生的精神相遇是教師和學生基于主體間的平等地位,自由而敞亮地進行精神的理解、溝通和接納,達成富有生命的精神交流,以促進雙方的精神建構和精神超越的實現。師生的精神相遇是大學教師精神主體“何在”的核心呈現。
(一)文化分享、社會批判、意義交流、情感溝通是師生精神相遇的基本內容
首先,由于文化是人類精神的承載,是“發現和表達意義和價值的首要方式”[24]。所以,精神的相遇,是借助藝術的、宗教的、科學的、哲學的方式來表達的對優秀文化的分享。通過文化分享,實現人的自我認識和自我理解,以表現生活、改造生活和提升生活,達成師生雙方的維真、求善、尚美。其次,大學教師是文化的批判者和創造者,社會批判是大學教師作為精神實體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師生的精神相遇的基本呈現方式。師生遵循“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理念,在教育活動中“介入”社會大眾生活,通過對拜金主義、個人主義、虛無主義、消費主義等思潮的反思性批判,引導社會大眾追求正義和真知。再次,人是尋求意義的主體,人無法忍受無意義的生活。尤其當社會處于低迷、失落的危機時代,更是如此。因而,師生需要精神相遇于意義交流,通過意義探尋、意義賦予和意義創造,發現、形成、深化生活意義。尤其當師生遭遇苦惱與無奈,更要真誠地面對現實生活,思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主動而理性地追求有意義的“可能生活”。最后,教師與學生是情感共同體,需要彼此給予對方一種心靈的、情感的相遇、相知與相助。因而,精神相遇離不開情感交流。情感交流需要師生通過換位思考、有意的反思和經驗的積淀達到交流中情感的自然真實流露。當然,由于教師具有豐富的多重生活體驗,深刻的情感感知、想象能力,應在情感交流中處于分享與關懷的主導位置。
(二)“我—你”關系是師生精神相遇的基礎
師生的“精神相遇”所尋求的是師生主體間的心靈交流,所以師生的精神相遇中,教師不能以權威姿態出現,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模式應是平等的“我—你”關系。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我—你”關系是一種主體間關系,教師與學生是兩個平等交往的主體,而兩個主體只有同時處于自由平等狀態,才愿意把整個身心投入到交往中。所以,處于精神相遇中的教師不是人類靈魂的“塑造者”,而是“引發者”,既引發對方也引發自己體驗自由、民主、尊重等,并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與情感體驗。其次,是因為“我—你”關系實質是分享關系,分享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并通過分享人類文化中創造教育的意義,提升生命的價值和雙方的精神境界。最后是因為“我—你”關系是一種精神與精神的關系。“我—你”的相遇不是為了單純地增加知識,更不是功利性的物質交換,而是精神受到對話的啟迪和引導,獲得充實,趨向“超越”和“自由”。
(三)“精神商談”是師生精神相遇的基本方式
“精神商談”是指師生兩個交談主體在理想的話語環境中用熱情的、豐富的精神狀態,通過相互傾訴與傾聽進行的思想、文化和情感交流。交流對話、節目表演、實踐活動等是師生最常見“精神商談”方式。“精神商談”是師生精神相遇的基本方式,它可以讓師生之間相互參與以獲得真理、領悟生命、創生意義。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言,它是一個“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在對話中,可以發現所思之物的邏輯及存在的意義”[25]。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精神商談”所呈現的不是師生之間知識和信息的單向傳遞,而是平等地共同對世界進行探索與實踐[26],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相互的表達與傾聽,帶有明顯的交互性、動態性和體驗性,這正是精神相遇所需要的主體基礎。其次,由于“精神商談”是一種生動活潑且易于學生接納和感悟的方式,既有利于在師生的精神相遇中調動學生的精神狀態,更對精神相遇時精神沖突具有更好的調節作用,從而讓師生產生愉悅的精神體驗。最后,“精神商談”作為一種交流活動,必須借用豐富的包含感情和思想的語言,這有利于激發師生對不同精神形態的理解與認同,從而重構自身精神世界。
最后必須指出的是,大學教師作為實體精神的存在,并不是要求教師只講奉獻,不講報酬,也無意否定教師物質生存的需求以及經濟基礎對精神存在的重要支撐,更不否認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著一些制約教師精神成長的因素。但由于教育是一種基于信仰的崇高使命活動,當選擇大學教師這一職業時,每位教師都應重視自己精神成長,并在教育活動中盡量做到“以德樹人”,“以文化人”。
[1]魏傳光.大學“立德樹人”的文化省思[J].北京社會科學,2015(2):119-124.
[2][俄]尼古拉·別爾嘉耶夫.精神與實在[M].張百春,譯.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33.
[3][德]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92.
[4]陶東風.社會轉型與當代知識分子[M].上海:三聯書店,1999:148.
[5][德]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張念東,凌素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672.
[6][法]Descartes.Les passions del’ame, introdeution de Michel Meyer[M].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caise.1990:55.
[7][英]羅素.西方哲學史[M].何兆武,李約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9.
[8][英]羅素.羅素自選文集[M].戴玉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99.
[9]張華.教師自我:展現生命語境下的美麗人生[J].福建教育,2005(8):12-131.
[10]王鳳英,柳海民.走向以“情”為根基的教師專業發展[J].教師教育研究,2012(3):22-25
[11][美]帕克·帕爾默.教學勇氣—漫步教師心靈[M].吳國珍,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01.
[12]何茜,孫美花.教師專業化視野下的教師教育改革[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59-162.
[13]李海萍,上官劍.物質牽制與精神自由:民國前期大學教師薪酬研究[J].教師教育研究,2012(4):69-77.
[14]李大釗.物質和精神(1919年12月28日)[A].朱文通,等.李大釗全集(第三卷)[C].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430.
[15][巴]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M].單德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16-17.
[16][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M].宋佳煌,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7.
[17][美]邁克爾·J·桑德爾.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M].萬俊人,等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1:8 .
[18]張培.讓教師詩意地棲居于教育中[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6(7):34-38.
[19]Merten,T.&Fischer,I.Creativity,personality and word association responses:Associative behaviour in forty suppos-edly creative persons[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1999(27):933-942.
[20]余英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邊緣化[EB/OL].二十一世紀(網絡版).http://www.cuhk.edu.hk/ics/21c/2006-5-15.
[21]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M].上海:三聯書店,2006:265.
[22]于堅,謝有順.于堅謝有順對話錄[M].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18.
[23][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M].鄒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169.
[24][美]勞倫斯·E·卡洪.現代性的困境[M].王志宏,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442.
[25][日]佐藤學.學習的快樂—走向對話[M].鐘啟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2004:77.
[26]吳芳,宮寶芝.對話式教育理論與實踐——從弗萊雷到桑德爾[J].現代大學教育,2013(10):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