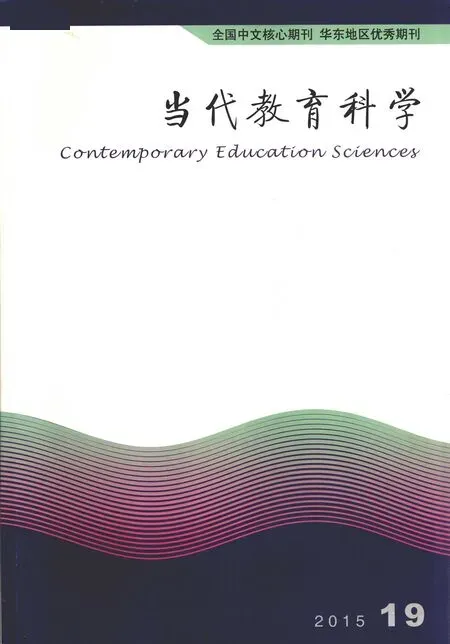教學學術研究的反思與重構**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教育學青年課題“教學學術視域下西部新建本科院校初任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研究”(課題批準號:CIA130177)的研究成果。
●黃培森 劉世民
教學學術研究的反思與重構**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教育學青年課題“教學學術視域下西部新建本科院校初任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研究”(課題批準號:CIA130177)的研究成果。
●黃培森劉世民
摘要:“教學學術”的概念是教學學術言說的邏輯起點。自“教學學術”提出以來,先后經歷了三次視域轉換:學術范式下的教學學術、教學實踐視域下的教學學術和教師專業發展視域下的教學學術。未來的“教學學術”研究,應廓清教學學術研究的邏輯前提,明確“教學學術”的價值何在,其研究的思維路徑是什么。在此基礎上,以生態思維代替非生態思維、以復雜性思維代替線性思維,從工具價值取向走向人本取向,實現“教學學術”的重構。
關鍵詞:教學學術;生態思維;人本取向
黃培森/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文理學院教育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教師教育研究
劉世民/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教師教育研究
教學與科研作為大學的基本職能,其間的矛盾歷來是大學教師工作中關注的焦點所在。“教學學術”這一概念的提出,無疑為人們探尋教學與科研之間的平衡點,提升大學辦學質量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然而,隨著學界對教學學術廣泛持久的關注和研究的不斷深化,亟需在本體論意義上對教學學術的內涵進行反思與重構,這是深化教學學術理論研究的前提,也是切實促進大學教學實踐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擬基于對教學學術這一概念的歷史譜系的梳理,嘗試反思并重構有關教學學術的理解。
一、教學學術研究的歷史譜系
自大學創立伊始,教學就是大學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重要職能。然而,將“教學學術”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明確提出,卻只是近三十年的事。究其根源,主要源自于對大學中教學與科研失衡而導致大學精神喪失的反思與批判。美國歷史學家佩琦·史密斯在《扼殺精神:美國高等教育》中所表達的觀點不無代表性:“美國高等院校已呈現出如同荒蕪沙漠般的景象,昔日的輝煌已不復存在,剩下的只是對教授職位的‘廝殺’,對本科教育的無視……這種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表明,美國高等教育的精神正在被大學教師扼殺”。[1]在某種意義上,“教學學術”這一概念的提出,不僅標志著恢復教學在大學中的地位的努力,更蘊含著重建大學精神的使命。因此,“教學學術”的概念一經提出,就多角度地獲得了其存在價值與意義的論證。
(一)學術范式下的教學學術
美國著名學者厄內斯特·博耶首次把教學的學術納入學術的范疇,將學術劃分為發現的學術、應用的學術、整合的學術和教學的學術四種,并提出了教學學術的概念。其后繼者卡內基教學促進中心現任主席李·舒爾曼將教學學術的內涵進一步深化,把“教與學的學術”視為教學學術。他認為,教學學術就是對教學實踐活動中教和學的問題進行系統的探究,其成果具有公開交流和評價并能被他人進行建構、應用和反思等鮮明的學術性特點。[2]教學學術的內涵經過不斷的發展,形成了如下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是把教學學術看作是對教與學的研究;二是把教學學術等同于優秀教學;三是把學術性教學視為教學學術。[3]這三種觀點中最接近于教學學術本意的當屬第一種觀點,把教學學術視為一種新的學術范式,認為教學學術也是一種智力活動和創造活動,體現了教學學術活動的創造性和探究性的特征。
(二)教學實踐視域下的教學學術
教學實踐視域下的教學學術內涵側重于對知識的有效傳播、教學問題的有效解決和教學質量的有效提升等方面的關注。眾多學者對此作了專門闡述。帕默認為,教學學術就是通過尋求學科與學科的知識之間的關系,促進理論與實踐的契合,實現知識的有效傳授。[4]馮軍認為,大學教學學術不是一種純粹的教育理論研究,而是大學中的教師、教學管理者、教輔人員等,通過邊研究、邊應用的方式將教學過程中的實踐經驗加以歸納總結和反復提煉,使其升華為相關理論并應用于解決教與學的實踐問題。[5]姚利民認為,大學教師的教學學術一是對所教學科專業知識和教育學科知識的全面掌握;二是對教學深入而透徹的認識。大學教學活動是繁難復雜的,也是難以駕馭的,教師要按照學術研究的范式來審視教學,依據學術規范進行教學。[6]綦姍姍認為,教學學術是一種特殊的、與教學相關的學識和知識,它源自于教學實踐并在教學實踐中展開,目的是為了教學實踐。[7]
(三)教師專業發展視域下的教學學術
大學教師必須關注自身的專業發展,教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學學術追求密切相關,教學學術是大學教師實現專業發展的重要途徑,教學學術水平則是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程度的重要體現。這是基于教師專業發展的視角對“教學學術”的解讀。這一視角側重強調在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教學學術的重要性。我國臺灣學者陳碧祥對此作過論述,認為大學教師的專業發展是大學教師通過獨立或合作、正式或非正式等方式進行教學、研究活動,促進自我反思,增進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專業知識與精神,進而促進個人的自我實現,學校學術文化的不斷提升,學校教育目標的有效達成,最終促進教育質量的整體提升。[8]大陸學者王建華對教學學術進行了詳盡闡述,認為教學學術是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維度,大學教師必須關注教學本身。“教學專業”的發展是大學教師發展的核心所在。教學專業的發展需要重構學術的內涵,樹立教學學術理念,平衡“教學學術”與“專業學術”之間的關系,強化對教學本身的學術研究。教學學術為有效化解教學與科研之間的矛盾提供了一個最佳切入點,有助于大學教師教學態度的轉變和研究視角的擴展,對實現大學教師專業發展意義重大。[9]
二、“教學學術”研究的前提追問
教學學術的提出,顯然表達了不同于大學科學研究的價值訴求。在這一意義上,“教學學術”研究的前提在于確證其獨特的價值追求。然而,已有不同視域下教學學術的探討,雖然在不同意義上確證了教學學術的存在價值,但在其前提假設上,無論是基于學術范式賦予教學學術以創造性智力活動的價值,還是立足于教學實踐改善與質量提升而展開的思考,抑或是站在教師專業發展的角度對教學學術的論證,都未能走出功利主義哲學的藩籬,遠離甚至忘卻了人的“生存”,背離了教學學術理應具有的價值訴求。
(一)“教學學術”的價值何在
誠然,“教學學術”提出的初衷是為了重振大學對于教學的關注,進而改善大學的教學,提升大學的教學質量。然而,這種將教學視為達成某種特定目標的手段的看法,無疑具有濃郁的工具理性色彩。它在懸置了教學作為生活與生命實踐特性的同時,也忘卻了教學對人的生命發展理應具有的關懷。站在實踐哲學的立場來審視“教學學術”,我們認為,教學學術這一概念的提出,不僅是重塑大學教學的地位,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是因為教學作為一種師生共同參與其中的生活方式與生命實踐,理應要在“學術”的意義上,使充盈于教學情境中的師生富有研究意識,在改進教學實踐的同時,關切師生生命意義的提升和自我實現。
以此為基點,我們不妨來對已有的“教學學術”研究略加省思。學術范式下的教學學術理解,與其說肯定了教學作為一種學術所具有的智力性與創造性,毋寧說是在傳統“學術”的參照中,使教學重新淪為“學術”的注腳,而未能彰顯教學的獨特價值;與此不同,教學實踐視域下的“教學學術”理解顯然意識到了上述不足,并將視線投向了教學本身,意圖在教學改進與教學質量提升的追求中凸顯“教學學術”的價值追求,重新確證人才培養在大學職能中的核心地位。然而,我們所要追問的是,教師以學術研究的規范看待、改進大學教學,在實現人才培養的生命實踐活動中,其自身的生命意義又被置于何處呢?第三種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待教學學術,肯定了教學學術之于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表面上來看,這一理解是基于教師自身而給出的。然而,遺憾的是,教師及其專業發展的地位并未立足于生命的高度,也未在本體的意義上予以框定,教師及其專業發展所充當的,依然只是服務于大學教學質量提升這一目標。
當然,我們無意否定大學所理應承擔的服務社會的基本職能。然而,在大學走出“象牙塔”,不斷拓展其職能領域的背景下,教學學術研究更應該回應協調處理不同價值主體期望和需求這一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教學學術”概念的提出,不應囿于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而應致力于時代背景下大學文化的重塑,使其成為一種價值選擇和整合模式的調整。不僅如此,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教學學術還應該回到生命與實踐的立場上,關切“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這不僅是教育和教學的本真意蘊,也理應成為大學對時代困境所做出的必要回應。
(二)“教學學術”研究的思維路徑審視
“教學學術”研究之所以未能脫離工具主義的藩籬,在根本上來說,是由于其思維方式上的偏狹所致,這突出地表現在對教育中個體與社會之間關系問題的思考上。
毋庸諱言,如果說大學中教學與科研的失衡是源于科學研究之于社會貢獻的顯性功能,表征著我們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割裂了社會與個體的內在聯系,并秉持社會本位的立場。那么,“教學學術”研究中所呈現的工具主義傾向,顯然正是上述思維方式延續的結果,強調的依舊是教學所具有的社會工具價值,使教師和學生的個體生命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就此,我們不妨重溫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這一問題的經典表述:“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有一種關于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的學說,但這種學說忘卻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10]在馬克思的理想中,社會變革或社會革命的終極目的在于“人的解放”。因為,社會環境是因人而生成,并依據人的意志而改變、改造的。在這一意義上,教育理應為人而生成,為人的發展而運行。即便教育指向社會,其終極目標也是通過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指向人。這種思維上的轉向,不僅是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發展的實踐所證明了的,站在教育的立場上來看,它同樣也是大學教育的本真追求。因為“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11]
三、“教學學術”研究的應然追求
對“教學學術”內涵的理解與研究,不僅關涉到“教學學術”的理論表達,也影響著人們從事大學教學的觀念與行為。在這一意義上,關于“教學學術”這一概念的理解,實質上濃縮著理論研究的方法論和觀念史發展的線索,也反映著教學實踐發展的邏輯。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我們獲得統一的關于“教學學術”的一致性理解,而在于我們以何種方式去追尋“教學學術”的本真意蘊。
(一)由非生態思維走向生態思維
“教學學術”的本真解讀就是對“教學學術”進行原生態的解讀,而不是從其存在的環境中肢解、隔離出來,從某一個角度和視域進行單一的闡釋。也許從某種角度進行深入分析能更好地揭示“教學學術”某一方面的特性,但這畢竟不是對其本來面貌的全面詮釋。因為教學學術的存在不僅僅是教學存在本身,教學學術的運行必須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教學學術在塑造著新的大學文化,喚醒人們認識的同時,也受到現實環境的約束。教學學術的存在狀態與教師的觀念、能力、學校的文化環境、制度條件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只有將“教學學術”放到其特定的學術生態環境當中進行研究,才能使研究的成果具有生命力和文化適應性,才能展現出教學學術的本真面貌。任何想把教學學術從其自在狀態中剝離出來,對其進行前提假設式研究的做法,都會使教學學術研究失去其本來的生命與活力,失去對實踐的指導意義。
(二)由線性思維走向復雜性思維
教學學術研究與專業學術研究相比更為復雜,這是因為除了教學實踐本身的復雜性之外,教學學術研究還涉及跨學科研究,因此,教學學術的研究應該擺脫線性思維方式,直視教學學術本身的復雜性,系統地揭示教學學術的本質屬性。首先,應系統全面地認識到教學學術具有教學和學術的雙重屬性。在解讀教學學術內涵過程中,應同時看到教學學術的學術性和教學的實踐性。作為一種學術活動,教學學術也包括發現、整合、應用和教學四個基本環節,[12]也要經歷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等階段;同時,教學學術也是一種為了促進教師和學生發展的教學學術活動,學術和教學相互交融。這體現為學術性教學和教學的學術兩個方面。學術性教學既是教學實踐活動,又是教學學術實踐的重要環節;教學的學術既是教學學術的核心,也要依托教學實踐才能展開。因此,不能像對待專業學術活動一樣,每一項研究都要有成果可供展示交流,而應該針對教學實踐的實際情況,把教學學術分為不同的梯度,再根據不同梯度的特點引導教師的教學研究朝著更高水平努力,這樣才能使教學學術活動具有可行性,成為每一位教師發展的機會,而不是束之高閣,成為少數教師的專利。其次,在教學學術研究過程中既要注重教學學術知識、能力等教育知識的研究,也要加強教師和學生在教學學術活動中的情感、態度等方面的研究,關注師生在教學學術過程中的生存狀態。這既是影響教學學術有效開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當下相關研究較為薄弱的方面。
(三)由工具價值取向走向人本價值取向
教學學術研究應懷著生命情懷,帶著對生命的敬畏,走出工具化、功利化取向的思維路徑,使教學學術研究成為教師和學生體驗自我、展現自我、實現自我的一種方式。“人之作為可能性存在,人的籌劃、選擇蘊含著人可以超越現有存在形態,既可以獲得其本身、成為其本真的存在,又可失去其本身、成為非本真的存在。”[13]其實現實中的人,既有本真的一面,也有非本真的一面;既有本真的時候,也有非本真的時候。而當下的部分高校教師在追逐社會潮流的過程中,物質力量侵蝕精神家園,遮蔽了生命的意義,教師不知不覺中失去了作為一名教師的本真存在,被外在的壓力所駕馭。“在非本真存在的方式下,此在與他人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與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代。”[14]這個他人不是指確定的他人,而是指“常人”,“這個常人不是任何確定的人,而是一切人——卻不是作為總和——倒都是這個常人。就是這個常人指定著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15]大學教師作為日常生活中的個體,教學學術研究過程中如果沒有對生命的關懷,沒有生命意識和反思意識,就會使自己的教學和教學研究逐漸被“常人”所平均化,從而完全失去自己的本真,失去作為一位大學教師最本真的存在意義。因此,教學學術研究應該隨時懷著生命情懷,關注教師和學生的內心世界,引導他們建構屬于自我的應有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1]施曉光.美國大學思想論綱[D].北京:北京師范大學,1998.
[2]P Hutchings,lee Shulman.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New Elaborations,New Developments[J].Change,1999,(5).
[3]Caralin Kreber,Patricia A Cranton Exploring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0,(4).
[4][南斯拉夫]德拉高爾朱布·納伊曼.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13.
[5]馮軍.論大學教學學術的培育[J].教育發展研究,2010,(7).
[6]姚利民.教學學術及其價值[J].河北科技大學(社科版),2010,(4).
[7]綦姍姍.論大學教師的教學學術[D].長沙:湖南大學,2005,12.
[8]陳碧祥.我國大學教師升等制度與教師專業成長及學校發展定位關系之探究[J].國立臺北師范學院學報,2001,(14).
[9]王建華.大學教師發展——“教學學術”的維度[J].民辦教育研究,2007,(1).
[10]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11]時偉.大學教師專業發展模式探析——基于大學教學學術性的視角[J].教育研究,2008,(07).
[12]宋燕.基于雙重身份的“教學學術”內涵解讀[J].江蘇高教,2013,(2).
[13][14][15][德]馬丁·海德格爾.陳嘉映等譯.存在與時間[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178,243,147.
(責任編輯:孫寬寧)
- 當代教育科學的其它文章
- 中美高校服務學習的比較與啟示**基金項目:山東省高等學校學生教育與管理研究項目“服務學習——高職院校學生教育管理創新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13B009)的研究成果之一。
- 我國臺灣地區海洋教育體系建設及對大陸地區的啟示**基金項目:青島市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藍色規劃背景下青島市中小學海洋教育研究”(項目編號:QDSKL1401026)的研究成果之一。
- 大學排名與高校教學地位之殤**基金項目: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研究課題“大數據時代研究生教學質量監測機制研究”(項目編號:C-2015Y0414-011)、江蘇大學第十四批大學生科研立項項目“江蘇省高校教學質量評價監控機制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 公共教育服務的供求矛盾及其調節措施**基金項目:肇慶市社科規劃“促進肇慶市公共服務產業發展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4ZC04)的研究成果之一。
-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研究
- 立足學校的課程整合研究**基金項目:山東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省級教師教育基地教師教育模式創新研究”;濱州學院重大課題“普通本科院校職前教師培養模式研究”。